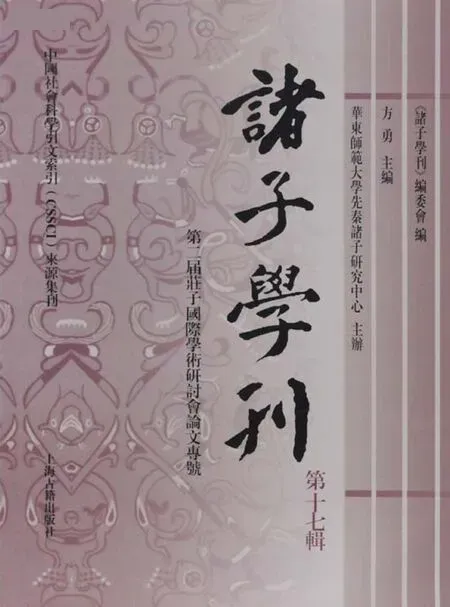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析探
(臺灣) 陳惠美
内容提要 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僅載有崔譔、向秀、司馬彪、郭象、李頤、孟氏、王叔之、李軌、徐邈等注《莊子》者,《世説新語·文學篇》所言“注《莊子》者數十家”多數在唐之前已亡佚。《經典釋文·序録》所載之注《莊子》者,除了郭象注本,其餘注本在唐宋之後也陸續散佚。有清一代輯佚風氣大開,孫馮翼、茆泮林、黄奭、王仁俊、郭慶藩等相繼投入蒐羅司馬彪《莊子》注的工作。本文以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爲考察對象,從輯佚方法的視角切入,就“佚文取材來源”、“佚文歸屬方法”、“佚文校理法則”等面向,探析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之優劣。
[關鍵詞] 茆泮林 司馬彪 《莊子注》輯本 輯佚方法
前 言
清代陳澧《東塾讀書記》説:“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蓋時有古今,猶地之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同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别國如鄉鄰,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也。訓詁之功大矣哉!”(1)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十一,(臺灣)廣文書局1970年版,第1頁。隨着時光推移,後人閲讀先秦典籍,已難究著者旨要,因此漢魏以後有許多學者投入先秦典籍的校訂與注釋。《世説新語·文學篇》:“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2)劉義慶《世説新語》卷上之下,(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3頁。由《世説新語》這段記載,可知在向秀之前注解《莊子》一書者即有好幾十家。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僅載有崔譔、向秀、司馬彪、郭象、李頤、孟氏、王叔之、李軌、徐邈等注《莊子》者(3)陸德明《經典釋文》,(臺灣)中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頁。。早期圖書,胥藉手鈔,流傳匪易;又重以水火蠹魚之害、兵戈盜劫之災,致使許多注本日漸殆亡。《世説新語·文學篇》所言“注《莊子》者數十家”多數在唐之前已亡佚。《經典釋文·序録》所載之注《莊子》者,除了郭象注本,其餘注本在唐宋之後也陸續散佚,難以一窺全貌。
明中葉以至清初,由於復古學風之影響,學者爲謀充實學術資料,並滿足其求知慾望,積極從事於漢唐久佚之古經義傳的蒐輯。清高宗詔修《四庫全書》,大規模從《永樂大典》輯存亡佚之書,學者聞其風而紛起仿效;加以前代輯佚經驗之累積、當時圖書纂輯活動之盛行、考據知識發達之助益,輯佚遂呈現前所未有之繁盛。皮錫瑞嘗云:“國朝經師有功於後學者有三事: 一曰輯佚書,一曰精校勘,一曰通小學。”(4)皮錫瑞撰、周予同點校《經學歷史》,(臺灣)藝文印書館1987年版,第363—364頁。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亦曰:“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膚蕪之作,存亡固無足輕重;名著失墜,則國民之遺産損焉。……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語留存,無不搜羅最録。其取材則唐宋間數種大類書……而諸經注疏及他書,凡可搜者無不遍。當時學者從事此業者甚多,不備舉。……遂使《漢志》諸書,《隋》《唐志》久稱已佚者,今乃累累現於吾輩之藏書目録中,雖復片麟碎羽,而受賜則既多矣。”(5)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收入朱維錚校注《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頁。在輯佚風氣大開的清代,有孫馮翼、茆泮林、黄奭、王仁俊、郭慶藩等投入蒐羅司馬彪《莊子》注(6)《晉書·司馬彪傳》有司馬彪注解《莊子》之記載:“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41頁)《隋志》載司馬彪《莊子注》十六卷,注云:“本二十一卷,今闕。”兩《唐志》並載爲二十一卷,疑承舊志所録,非佚而復出。的工作。
王叔岷《茆泮林莊子司馬彪注考逸補正》:“晉人注《莊子》,義理最佳者,當推向秀、郭象。訓詁最佳者,當推司馬彪。……孫鳳卿雖有收輯(見《問經堂叢書》),而疏略矛盾,可議者不少。茆泮林乃爲之更訂補苴,其彪注考逸(見《梅瑞軒逸書》十種),視孫書完善多矣。厥後黄奭《黄氏逸書考》中,所載《莊子》司馬彪注,蓋即全本茆書。唯未録茆氏所輯莊子逸語十五條而已(7)黄奭《逸莊子》收入《逸篇》7篇存目及“莊子逸語”15條,經比對此15條内容即王叔岷所説“唯未録茆氏所輯莊子逸語十五條而已”,詳見《黄氏逸書考》,日本中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9—2370頁。。至於郭慶藩《莊子集釋》中所舉彪注,亦幾全鈔襲茆書也。”(8)王叔岷《茆泮林莊子司馬彪注考逸補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1月,第 111頁。王叔岷先生認爲有清一代輯司馬彪《莊子注》最佳者爲茆泮林輯本,更於《茆泮林莊子司馬彪注考逸補正》一文裏比對出黄奭、郭慶藩承襲茆泮林的輯佚成果,茆泮林輯文錯誤處,黄奭、郭慶藩因襲之,如《田子方》“吾所學者,直土梗耳”條下引《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土梗,土之木梗,亦木人也;土木相偶,謂以物像人形,皆曰偶耳。”茆泮林誤卷三十三爲卷二十,黄奭、郭慶藩並本之而誤(9)王叔岷《茆泮林莊子司馬彪注考逸補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1月,第 121頁。。又如《徐無鬼》“年齒長矣”條下引《華嚴經音義》:“齒,數也。”考《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作“司馬彪注《莊子》曰:‘齒,數也。謂年壽之數也。’”茆泮林脱“謂年壽之數也”六字,黄奭、郭慶藩並本之(10)同上,第123頁。。因此王叔岷先生認爲黄奭、郭慶藩輯本,並無超越茆泮林輯本之處。王仁俊《莊子司馬注》從《原本玉篇》采録了10條司馬彪注文,爲孫馮翼、茆泮林輯本所未及,然王仁俊《莊子司馬注》輯本僅録10條注文,較似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之補遺,清人所輯司馬彪《莊子注》,以全書體例完整度視之,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確屬較佳者。至於茆泮林處理所輯録佚文之方法是否合理,本文將從“佚文取材來源”、“佚文歸屬方法”、“佚文校理法則”三個面向加以檢核。
一、 茆泮林及其著作
茆泮林,字魯山,號雩水,江蘇高郵人。道光年間諸生,生卒年未詳,《續纂揚州府志》(11)英傑修、晏端書等纂《續纂揚州府志》,(臺灣)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774頁。《再續高郵州志》(12)龔定瀛修、夏子鐊纂《再續高郵州志》,(臺灣)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455頁。《清儒學案》(13)徐世昌編,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979頁。有傳。茆泮林《梅瑞軒求是偶鈔序》《梅瑞軒蠡説漫録序》(14)序見茆泮林《梅瑞軒求是偶鈔 梅瑞軒蠡説漫録》,(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第2頁。撰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左暉春《孫莘老先生年譜序》寫於道光二十五年天中節(五月五日),序文提及:“文學茆君雩水,郵之後進也。……嘗輯《十種古逸書》,儀徵相國序而行之。曩余續修《郵志》,得君《甓社餘聞》,備采擇焉。兹編《莘老先生年譜》,旁徵博引,辨析詳明……茆君齒近七十,閉户研書,不求聞達,獨惓惓於鄉之賢人君子,其景行可知矣。”(15)左暉春《孫莘老先生年譜序》,《孫莘老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第234—236頁。由左暉春《孫莘老先生年譜序》得知道光二十五年茆泮林年近七十,尚在世(16)百度百科所著録的“茆泮林”資料,將1845年列爲茆泮林的卒年,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茆泮林”條,則著録爲“【茆泮林】(?—1845在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787條),就《梅瑞軒求是偶鈔序》《梅瑞軒蠡説漫録序》《孫莘老先生年譜序》之記載,1845年茆泮林應該還在世。,曾參與左暉春續增《高郵州志》的編纂工作。翻檢左輝春《(道光)續增高郵州志》,該志梓行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茆泮林名列分纂人員(17)左輝春《(道光)續增高郵州志》,(臺灣)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5頁。。
茆泮林篤學好古,積數十年之力,裒集編次成《十種古逸書》。又著有《孫莘老先生年譜》《甓社餘聞》《唐月令續考》《唐月令注續補遺》《吕氏春秋補校》《三禮經義附録》《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周禮注疏校勘記校字補》《宋秦少遊淮海集補遺》《宋秦少遊淮海集續補遺》。阮元對泮林《十種古逸書》一書讚譽有加,云:“壬寅歲(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莫……客有送高郵茆魯山明經所輯十種古書來覽者: 《世本》一、《楚漢春秋》二、《古孝子傳》三、《伏侯古今注》四、《淮南萬畢術》五、《計然萬物録》六、《趙岐三輔決録》七、《司馬彪莊子注》八、《晉元中記》九、《唐月令注》十。凡此十書,昔者厪散見其名於群書之中,未聞其有成書也。今老儒茆君輯散見者成卷帙,且自刻成十册,余驚喜交集,乘園林小雨之後,洗目帶眼鏡,窮一日之力讀之。老見古書,何其幸也。……今茆君積數十年之力,博覽萬卷,手寫千篇,裒集之中,加以審擇,編次之時,隨以考據,可謂既博且精,得未曾有。……此十書,拾殘成帙,實爲快事,樂爲序之。且聞茆君尚有《孫莘老年譜》諸書,亦必精善,俟再讀之爲幸。若夫老生之談,敝帚自享,老夫耄矣,安能樂之。”(18)阮元《十種古逸書序》,《十種古逸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頁。清人輯《世本》者,計有錢大昭、王謨、孫馮翼、張澍、洪飴孫、秦嘉謨、雷學淇、茆泮林、王梓材、陳其榮等十家。學者分析衆家輯本之優劣,以爲:“王、孫、陳、張、雷、茆諸家,體例基本相同,引書之謹嚴,以茆氏爲最,雷本次之。張澍本每多以意删改引文,致失原文之真;雖逐條注釋,而考訂不精,往往轉增讀者的疑惑,在各本中較爲遜色。王謨本成書最早,在清代輯本中開風氣之先,引書雖然忠實,而失之於簡。孫本成書亦早,但年代無序,去取失宜,似乎是隨筆采録,未經詳校。陳其榮於孫本之蕪雜,稍加整理,然而刊誤未盡,增補無多,本身亦有譌舛,不足以方駕茆、雷。”(19)見商務印書館編《世本八種·世本八種出版説明》,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4—5頁。與阮元之評論相比,正若合符節。
輯佚工作要做到所收資料無一掛漏,並非易事,因此茆泮林完成《司馬彪莊子注》輯本後,又繼續從事補遺的工作,後有《莊子司馬注補遺》《莊子司馬注又補遺》。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考逸自序》:“司馬彪注《莊子》見《晉書·本傳》及《隋》《唐志》。泮林幼讀《南華》郭象注本,繼復思得司馬注讀之。繙閲之餘,遇一字一句,往往見寶。輯之寖久,遂於案頭録之成帙。後見《彙刻書目》,知已爲孫君鳳卿《問經堂叢書》所載。旋於坊友購之,一年始得。及見其書,其一卷則不取《釋文》,自序則云:‘無庸爲陸氏作鈔胥,重爲編録也。唯陸氏所遺者,及他書所引與陸氏同者,將《釋文》附注,統計凡一百十四事。’其一卷則更爲考逸,專采《釋文》,既顯與序語自相矛盾,又至《天員(運)篇》‘老子’注遂詘然中止。細按之,似皆爲未完、未定之書,其中未及細審者,正復不少。……此皆孫本之疏略有可議者……孫之言殊爲附會。兹輯更增得十之二三,其略加更訂處視孫本差爲完善。”(20)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考逸自序》,《十種古逸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第477—480頁。茆泮林始自爲司馬彪《莊子注》的輯佚工作,後得知孫馮翼輯有《司馬彪莊子注》《司馬彪莊子注考逸》,旋即購之,參閲孫馮翼輯本後,發現孫本有許多未及細審、疏略、附會之處,茆泮林除了增補了司馬彪佚注的條目數,並針對孫馮翼輯本之缺失加以修訂補正。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優於孫馮翼輯本之處,詳見本文下列各節之分析。
二、 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取材來源
盧文弨《春秋内傳古注輯存序》嘗云:“蓋當古學廢墜之後,而幸有不盡澌滅者,與其過而棄之也,毋寧過而取之,以扶絶學,以廣異誼,俟後之人擇善而從,斯可也矣。何庸以一己之見,律天下後世哉?”(21)盧文弨著、王文錦點校《抱經堂文集》卷三,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9頁。又如王謨輯《經翼鈔》,云:“漢魏以來説經諸書,日就散佚以至於磨滅……況自秦火而後,去全經已遠,微言大義,究未知孰得其真……即其説之不必純且精者,亦何妨並載於册,瞭若指掌,俾讀者得以攷其純駮精粗、異同離合之致。”(22)王謨《漢魏遺書鈔經翼鈔序》,《十種古逸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又如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凡例》亦云:“文有煩簡完闕雅俗,或寫刻承訛,或唐宋以前依托,畢登無所去取。……片語單辭,未敢遺棄。”(23)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凡例》,(臺灣)世界書局1982年版,第3頁。不論是出於對古籍散亡的慨惜,或是對輯佚可資考證的認識,爲使佚文蒐輯能既全且備,清儒從事輯佚,往往片言隻字、煩簡完闕,均兼容博采。不論精粗純駁,一律廣徵博引加以采録的原則,雖然常爲後人所詬病,然而從保存文獻的角度來看,佚文之煩簡完闕雅俗,可待讀者擇善而從,但若因過度審慎,致使輯本多所闕漏,或者必須重新再輯,不免徒然耗費人力,相較之下,“與其過而棄之,毋寧過而取之”。此爲清儒務求佚文全備之苦心,雖然不盡可取,但亦不能苛責。
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從《經典釋文》采録了司馬彪《莊子注》佚文634條,從《昭明文選》李善注采得92條,於《太平御覽》抄録了23條,從《列子釋文》《史記索隱》《初學記》則各采得8條、5條、4條。采得3條資料的有《集韻》《荀子》楊倞注、《一切經音義》。采録了2條資料的有《齊民要術》《廣韻》和《華嚴經音義》。從《尚書正義》《左傳正義》《論語正義》《古今韻會舉要》《後漢書》李賢注、《戰國策》高誘注、《資治通鑒綱目》《路史》《北堂書鈔》、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廣川書跋》各采録1條。所采資料較孫馮翼廣泛,因此所輯條目數較爲豐富(24)孫馮翼分别從《昭明文選》李善注、《太平御覽》《列子釋文》《史記索隱》《初學記》輯録了81條、19條、9條、6條、3條。從《一切經音義》《廣韻》各采得2條。《左傳正義》《論語疏》《太平寰宇記》各抄録1條。。在資料的取捨上,二者態度也有所不同,如《莊子·達生》“孔子觀於吕梁”,孫馮翼采録《太平寰宇記》卷二十八《關西道》所引司馬彪注《莊子》云“吕梁即龍門也”(25)孫馮翼《司馬彪莊子注·達生》,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2頁。;茆泮林則采用《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三引《郡國志》司馬云“吕梁即龍門也”(26)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達生》,第594頁。。據《隋志》所載司馬彪《莊子注》已是殘本,宋人當未能親見該書全貌,因此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樂史所編撰之《太平寰宇記》,所載録之司馬彪《莊子注》應爲轉引之資料。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認爲:“《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盡存,大率晉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覽》,齊、梁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蹟則得之本書者也。”(27)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466頁。《隋志》及新、舊《唐志》皆載有司馬彪《續漢書》83卷,可知司馬彪《續漢書》唐代尚存,《太平御覽》所引用的資料,當較《太平寰宇記》所引的資料可信,因此茆泮林取《太平御覽》捨《太平寰宇記》是合理的。
三、 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歸屬佚文之方法
佚文歸屬之真確與否,取決於前人標示所援引古書之篇章是否明確。前人標示所援引古書篇章之方式: (一) 有書名篇名並引者,如《經典釋文·莊子音義》所引司馬彪注,均明確歸於《莊子》某篇底下。(二) 有引書名不引篇名者,如《史記·魏世家》:“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司馬貞《索隱》:“《年表》作‘義臺’,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三) 有引篇名不引書名者,如《文選》潘安仁《秋興賦》:“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李善注引:“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爲能唯變所適而何足累。優哉遊哉,聊以卒歲。’”(四) 有節引書名者,《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引《五行傳》曰:“北辰謂之曜魄。”(五) 有本文注文並引者,如《文選》鮑明遠《苦樂行》:“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李善注引《莊子》曰:“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來,若機栝之發。”(六) 有引注文不引本文者,如《左傳》僖公十五年:“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孔穎達《疏》引: 司馬彪注《莊子》云:“胥餘,箕子名。”
因古籍徵引圖書篇章之方式有詳略之不同,故清儒於判定佚文編次時乃有下列之處理方式: (一) 可考知亡書篇章情況者,依原書體例編次。(二) 未能考知亡書篇章情況者,據同類書編次。(三) 未能考知亡書篇章情況者,按佚文殘存狀況編排。(四) 未能考知亡書篇章情況者,依事件人物發生年代先後編排。(五) 未能考知亡書篇章情況者,以徵引先後爲次。(六) 古書單引佚注,可知其所釋原書之位者,據所釋原書次第排次。(七) 古書單引佚注,而所釋原書之位不明,次於所釋原書首見之字下。(八) 古書單引佚注,於所釋原書無可附麗者,統置於篇末。
《經典釋文·莊子音義》所引司馬彪注,每則注文均明確歸於《莊子》某篇某句某字底下,從《經典釋文·莊子音義》所采之司馬彪注文,僅需按原書篇章加以編次即可。
《文選》李善注所引《莊子》司馬彪注,多數爲“本文注文並引者”,如: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李善注引《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又如: 《文選》班孟堅《幽通賦》:“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李善注引《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也。’郭象爲罔兩,司馬彪爲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再如: 《文選》江文通《雜體詩》:“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李善注引《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也。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李善所引《莊子》原文,基本上都能在今本《莊子》找到,附於《莊子》原文後面的司馬彪注文,僅需編次入《莊子》原文所屬篇章即可。
雖本文注文並引,然所引本文兩出,如《文選》宣德皇后《令》:“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李善注引《莊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文選》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神功無紀,作物何稱?”李善注引《莊子》曰:“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孫馮翼《司馬彪莊子注》將“造物,謂道也”次於《應帝王》“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之下(28)孫馮翼《莊子注考逸·應帝王》,(臺灣)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471頁。。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則次於《大宗師》“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之下(29)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大宗師》,第528頁。。據注釋的原則,所注解的同義詞,僅釋義於首次出現者。茆泮林將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編次於《大宗師》“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條下,較孫馮翼輯本合理。
古人引書有引注文不引本文者,如《文選》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李善注引《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莊子·讓王》:“故曰: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莊子·漁夫》:“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均出現“緒”字,且二者的釋義應當都解爲“餘”。孫馮翼《司馬彪莊子注》將“緒,餘也”次於《莊子·漁夫》“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之下(30)孫馮翼《司馬彪莊子注·漁夫》,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7頁。。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則次於《莊子·讓王》“其緒餘以爲國家”之下(31)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讓王》,第650頁。。清儒遇到“古書單引佚注,而所釋原書之位不明”的狀況,通則爲“將該注文次於所釋原書首見之字下”。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的編次方法優於孫馮翼《司馬彪莊子注》。
四、 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校理佚文之法則
古人徵引圖書,態度有嚴謹疏略之不同,如楊慎《丹鉛雜録》,記古人引書之法曰:“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 如子産答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争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32)楊慎《丹鉛雜録》卷九“古文引用”條,(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7頁。據楊氏所考,古人引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即按原書文句忠實徵引,無所删節,不可改易。變例情況有三: 一爲省字,一爲引用書文之義而不明言出處,一爲引申書文之義而後兼引書文。
又古書經長期輾轉傳抄,文字語句也難免産生差異舛誤,劉咸炘嘗述古書前後版本歧異之狀況曰:“群書之中有逸書,存書之中有逸文,經子有逸篇,史或有録無書,人知之矣。唐人小説及六朝唐人文集,以類書校之,多有遺篇零條,在今傳本外者,此由今本原是輯成,抑或原集本有所棄也。至於版刻既盛之後,子史專行之書,宜若不當有逸矣,而書之有足本、不足本之異者,猶爲不少。蓋篇簡有完闕,版奓有先後初刻,或非定本重翻,或據殘書,必憑多本,乃克補完。又有行本皆同,而亦有逸文者,如司馬光《涑水紀聞》、蘇轍《龍川略志》,校以《八朝名臣言行録》,元本所引,多溢出今本之外,此則徒憑異本,不足爲功,更當廣采,以期完備。”(33)劉咸炘《目録學·存佚》,收入楊家駱主編《校讎學系編》,(臺灣)鼎文書局1977年版,第24頁。依劉氏之説,經子有逸篇、史籍或有録無書,均爲世人所熟知;至於唐人小説及六朝唐人文集,其書或爲後人纂輯而成,但成書之初,采集已有未遍,即使出於作者自訂,尚有部分篇章爲作者所棄,因此以類書校之,多有遺篇零條溢出今世傳本之外者。凡此爲群書纂輯成書時固有之現象。然而版刻盛行之後,又因刻書者所據有足本、不足本之差異,以此輾轉傳抄,於是篇卷之完闕、文字語句之異同,將更爲歧出。
因古人引書時有疏略、古書傳抄難免舛誤,清代從事輯佚之學者,爲求資料真確無誤,並且兼顧全書體例,避免雜亂繁蕪,因此對於佚文之甄録去取,以及佚文之校勘疏理,都有着嚴密的標準。如嚴蔚輯《春秋内傳古注輯存凡例》曰:“諸書所引漢注,即於注下注明書名,庶便檢核。或有一注而數見者,其文句之間,有多有少,蔚未敢定彼從此,祇就最詳者著録之而已,餘止載書目。”(34)嚴蔚《春秋内傳古注輯存例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凡例》曰:“各篇之末,皆注明見某書某卷,或再見數十見,亦備細注明,以待覆檢。”(35)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凡例》,(臺灣)世界書局影印1961年版,第3頁。又曰:“宋、齊、梁、陳、隋文多完篇,東漢、三國、晉文散見群書者,各自删節,往往有文同此篇,從數處采獲,合而訂之,可成完篇。”(36)同上,第5頁。任大椿輯吕忱《字林凡例》曰:“每條字句,或諸書徵引全同,悉列諸書名目於其下,用表符契之合;或字句小異,必兩存之,各標所出,以備參定。”(37)任大椿《字林考逸凡例》,《字林考逸》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上述三家,乃自言在輯書過程中,處理佚文方式,歸納之有“祇就最詳者著録之而已”、“從數處采獲,合而訂之,可成完篇”、“或字句小異,必兩存之,各標所出,以備參定”三種方法。其餘輯佚學者雖未明確標舉,但大體上不脱上述三種方法。
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所采用的方法如下: 《逍遥遊》“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條下,録有:“摶飛而上也,上行風謂之扶摇。(《釋文》)摶,圜也。扶摇,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行者若扶摇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摶,圜也。圜飛而上若扶摇也。(《文選·范彦龍古意贈王中書詩注》)扶摇,上行風也。(《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御覽》九;《初學記》一及《御覽》九百二十七引並無也字)”(38)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逍遥遊》,第482頁。《大宗師》“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條下,録有:“造物者爲道。(《文選·顔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造物,謂道也。(《文選·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注》《文選·宣德皇后令注》《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注》《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39)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大宗師》,第528頁。《在宥》“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條下,録有:“椄槢,械楔。(《釋文》)槢,械楔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40)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在宥》,第548頁。《天運》“細要者化”條下,録有:“取桑蟲祝使似己也。(《釋文》)稚蜂細要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之子也。(《列子釋文》卷上)”(41)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天運》,第567—568頁。《秋水》“吾跳梁乎井幹之上”條下,録有:“井幹,井欄也。(《釋文》《史記·孝武紀》索隱)井榦,井欄也,積木有若欄也。(《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文選·謝元暉同謝諮議銅雀臺詩注》)”(42)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秋水》,第578頁。《至樂》“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條下,録有:“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不云魯侯也。於廟,飲之於廟中也。(《釋文》)海鳥,爰居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海鳥即鶢鶋也。(《御覽》九百二十五)”(43)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至樂》,第582頁。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所采用的方法爲“或字句小異,必兩存之,各標所出,以備參定。”因每條注文並不會太長,因此不需要如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一般,將所采集佚文綴合爲可讀的篇章。
孫馮翼輯本所采用的方法爲,《逍遥遊》“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條下,録有:“摶,圜也。扶摇,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行者若扶摇也。(《文選·范彦龍贈王中書詩注》《江文通雜體詩注》,又《初學記》卷一天部、《太平御覽》卷九天部,並引“扶摇,上行風也”一句,陸氏《釋文》云:“摶飛而上也,一音博,上行風謂之扶摇。”)”(44)孫馮翼《司馬彪莊子注·逍遥遊》,第1頁。《應帝王》“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條下,録有:“造物,謂道也。(《文選·宣德皇后令注》《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注》《顔延年曲水詩序注》《陸佐公石闕銘注》《沈休文安陸王碑注》)”(45)孫馮翼《司馬彪莊子注·逍遥遊》,第7頁。《逍遥遊》“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條僅録最詳盡的注文“摶,圜也。扶摇,上行風也,圜飛而上行者若扶摇也”,而《文選·范彦龍古意贈王中書》所引的注文爲“摶,圜也。圜飛而上若扶摇也”,較爲簡短,則爲捨棄不録。《應帝王》“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條則采録引用較多的注文,《文選·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注》《文選·宣德皇后令注》《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注》《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均引作“造物,謂道也”,僅《顔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作“造物者爲道”,因此“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條下僅采用“造物,謂道也”,未將“造物者爲道”録出。
由楊慎《丹鉛雜録》所記古人引書狀況可知,不同書籍的引文差異頗大,僅就最詳者録之,很可能所録者並非原文,因此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輯本采異同並存的方法,以備參定,較爲合理客觀。
結 語
孫馮翼雖是首位有系統輯録司馬彪《莊子注》佚文者,然《司馬彪莊子注》未采録《經典釋文》裏的司馬彪注,《司馬彪莊子注考逸》雖采有《經典釋文》裏的司馬彪注,但全書僅止於《莊子·天運》。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可説是第一部完整彙集司馬彪《莊子注》佚文的輯本,並將輯録的佚注合理地編次於各篇,茆泮林《司馬彪莊子注》較孫馮翼輯本更加接近司馬彪《莊子注》原貌。民國後馬叙倫、劉文典、王叔岷於茆泮林的基礎上,繼續輯補,使得散佚於各典籍中的司馬彪《莊子注》佚文得以彙聚爲一編,頗便後人從更多元的角度研究《莊子》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