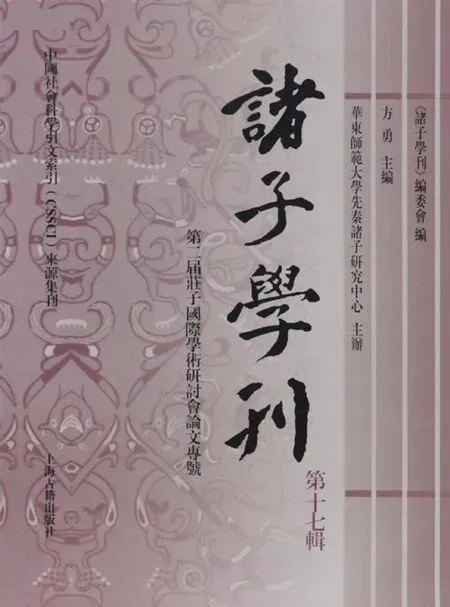莊子逍遥齊物的無用之用
(臺灣) 孔令宜
内容提要 《莊子》一書豁顯主體生命的逍遥自在,此義揭櫫於《逍遥遊》一篇,而此篇以“無用之用”之道説爲終止。本文對莊子的“無用之用”進行新詮釋。《齊物論》中“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的“無用之用”之新詮釋: 以“不用寓庸”爲“無用之用”的第三個層次,也就是經歷《齊物論》中相反相成辯證詭辭的現象界的“用”,到達“無言”的“無用”,乃是《齊物論》的得無之環中,而“照之以天”,可以“以應無窮”,因此最後可以超脱體性,而到達“不用寓庸”的“無用之用”。
[關鍵詞] 莊子 逍遥 齊物 無用之用 辯證的詭辭
前 言
《莊子》一書豁顯主體生命的逍遥自在,此義揭櫫於《逍遥遊》一篇,而此篇以“無用之用”之道説爲終止。由此可見“無用之用”在莊子哲學中的重要性。《齊物論》一篇更旨在對人間的是非、善惡、美醜等價值判斷,指點出一條解消之道,此一解消之道歷經三個層次的“以明”,最後乃是對於《逍遥遊》所説的“無用之用”之新詮釋,《齊物論》以“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加以發揮。
既然《齊物論》在化解對概念系統的執著,那麽首先莊子面對的問題是,應采取何種語言形式加以論述,以避免也落於言詮之中。故莊子使用的是一種辯證的語言,以衝破對語言正、反二分法的執著,謂之“道家式的辯證詭辭”。其次,這種詭譎的言辭,對於正、反兩造,既否定正面的論述亦否定反面的論述,看似自我矛盾,然而需進一步提出疑問的是,此種自我矛盾,斯爲表面的矛盾?抑是實質的矛盾?原來莊子以“先分解再取消分解”的方式,用超越的“道”來解消對表相的執著,遂以“道”的層次觀之,看似詭譎之言,實非詭譎之言,於現象界之外,指出形上界的終極依歸。再者,由於終極之道的逐漸逼顯,看似詭譎之相,實不顯詭譎之相,然而道與言之間,亦即形上界與現象界是否陷於二分的相對立?莊子認爲道寓諸於庸常之中,由生活世界的修養工夫中開顯出終極境界。“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本文之提出,試圖對《齊物論》道與言的層層關係加以釐析。
本文在第二節(即下之標題一,以下類推——編者注)探討莊子《齊物論》辯證詭辭的語言形式。第三節闡明莊子如何以超越的“道”解消表相的執著,運用“辯證的詭辭”以通達逍遥齊物的境界。第四節探討逍遥齊物的無用之用,《逍遥遊》提出“無用之用”,並不是要人自甘於小,而是要在大小之中都能安身立命,最後透過《齊物論》到達“無言”的“無用”,完成至人、神人、聖人的精神修養,而可以體會“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的生命境界。第五節探討《齊物論》“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的“無用之用”之新詮釋: 以“不用寓庸”爲“無用之用”的第三個層次,也就是經歷《齊物論》中相反相成辯證詭辭的現象界的“用”,到達“無言”的“無用”,乃是《齊物論》的得無之環中,而“照之以天”,可以“以應無窮”,因此最後可以超脱體性,而到達“不用寓庸”的“無用之用”。
一、 辯證詭辭的語言形式
《莊子》首篇《逍遥遊》言及自我生命的提升飛越,次篇《齊物論》續言物我之間的齊一生命,人人之所以能逍遥自得,必須建立在物我平等的價值觀照下。於是“齊物論”的提出,乃是對於人間的是非、善惡、美醜等價值判斷,尋求一可齊之道,以化解對相對概念系統的執著。然而《齊物論》本身也是論述,莊子勢必采取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避免自己本身也陷入詮説之中,以逼顯出天籟的境界,於是莊子使用的是一種詭辭——辯證的詭辭(1)牟宗三先生以爲:“無”是一個虚静而有無限妙用的心境,無限妙用於“有”處見,無有合一就是《老子》首章“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的“玄”;道的雙重性“無”、“有”於作用層上顯,道創生天地萬物。然而不同於西方以實有形態爲認知對象的認識論、知識論,西方人所謂的詭辭、弔詭(paradox),是屬於邏輯的詭辭(logical paradox);道家“正言若反”的思想是作用層上的話,不是屬於邏輯上的詭辭,而是屬於辯證的詭辭(dialectical paradox)。綜而言之,西方哲學近似“直線演繹”,A就是A(同一律),A不是-A(不矛盾律),A與-A也不能混淆(排中律);而東方哲學則近似“曲線辯證”。見氏著《中國哲學十九講》,(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版,第87—156頁。。然而此種辯證的詭辭,與一般邏輯的詭辭,究竟有何不同之處?兹舉“以明”爲例,如下: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説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我們平常説彼此、是非,這是一組相對的辭語。“物無非彼,物無非是。”在一般的情況下,物如果不是彼,那便一定是此;反之,物如果不是此,那便一定是彼。同樣的道理,物如果不是是,那便一定是非;反之,物如果不是非,那便一定是是。這是個很簡單的概念。“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因”是順着的意思,彼與此、是與非都是相因而生,没有彼就没有此;反之,没有此就没有彼。同樣的道理,没有是就没有非;反之,没有非就没有是。平常所説的生死、可不可,也是一組相對的辭語。“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是相對兩造,同時並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可”是認可,有肯定的意思;“不可”是不認可,有否定的意思。如果認可了,那一定就不會是不認可;反之,如果不認可了,那一定就不會是認可。
無論彼此、是非、生死、可不可等,均爲兩兩相對的概念,上段皆可視爲正常概念下的論述,不涉及到詭辭。然而,莊子明言“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分明是種詭辭。所謂詭辭(paradox),詭譎的言辭,就是種不合乎常理的話,莊子自己名爲“弔詭”(2)《莊子·齊物論》曰:“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詭辭可分爲兩種: 一種是邏輯上的詭辭,另一種爲辯證上的詭辭,而莊子使用的是何種詭辭?上述彼此、是非、生死、可不可等,是兩兩相對的辭語,也是吾人一般概念世界所使用的名言,在這種二元對立的關係中,彼此依待對方而成立,自己單獨便不能成立,兩者之中一定要有一個選取抉擇,非彼即此,非此即彼,若以數學形式表達,A代表正,-A代表反,雖A依待-A,-A依待A,正不是反,反不是正,A就是A,非A即-A,-A就是-A,非-A即A,這就是邏輯學、數學中的二分法,以及邏輯思想必須遵循的排中律,但是這裏不遵守邏輯上的排中律,所以稱之爲一種邏輯的詭辭(logical paradox)。
莊子的論述,跳脱二分的對立關係,爲一種辯證的詭辭(dialectical paradox)。牟先生認爲,《道德經》所説的“正言若反”,此乃作用層上的話,“正言若反”所講的就是詭辭,就是《莊子》所説的弔詭(《齊物論》)(3)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140頁。。牟先生説“正言若反”乃作用層上的話,所以也是涉及到“無用之用”的討論。
我們再來重新審視此段文本:“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無非彼”可再加上“物無非此”句,意思是: 物無非都是那個,物無非都是這個;“物無非是”可再加上“物無非非”句,意思是: 物無非都是對的,物無非都是錯的。顯然這不是彼與此、是與非的二選一,正確地解釋爲: 要説是,通通是;要説非,通通非。這是一個原則性的主張(4)牟宗三先生説:“要説對,通通都對;要説不對,通通都不對。我歷來采取這種講法,這就是莊子的原則性主張。我讀莊子的文章,反覆諷誦,最重要是語脈,上下文的係絡。”見氏著《莊子〈齊物論〉演講録(四)》,《鵝湖月刊》第27卷第10期總號第322期,2002年4月,第2頁。1987年2月至4月,牟宗三先生講授《莊子·齊物論》於香港新亞研究所。。“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彼”就是對方,當然各人從彼此相對的立場來看對方,就會有所局限,彼方有彼方的觀點,此方有此方的觀點,所以要破除二元對立的思維,自歸自己的本身就可以知道。“故曰: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因爲彼與此、是與非相對而立,相因而成,互相以對方爲原因而成立,本身都無法各自獨自成立,所以莊子要取消二分法,另取一途: 要説對,通通對;要説不對,通通不對。結果是也不是是,非也不是非,而無是無非,自然就破解了邏輯上的二分,這種違反思想律的詭辭,乃爲辯證的詭辭。
接着又説:“彼是方生之説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世間哪有剛剛生就是剛剛死,或者剛剛死就是剛剛生的説法?這當然是種詭辭。因爲死生相因,要説生,通通生;要説死,通通死,結果無生無死(5)在《莊子·大宗師》中,曾兩次言及“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人的形體變化必然會有生→老→死,但是人除了血氣形軀之外,還有心靈精神,莊子以爲,卓於父的天,真於君的君,超越在生死之上的即爲“真君”,必須通過生命修養來體現真君,有真君作主宰的人方爲“真人”,能够盡人生所應盡的,善吾死也就在善吾生。《大宗師》中又接着云:“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心裏没有生,就没有死亡的恐懼,解消對生的執著,才没有死的壓迫,殺生可以不死,生生可以不生,故道家的不死之道在不生,相對兩造,同時並生,破除對死生二分的執著、分别,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如果肯定了,那一定不會是否定;如果否定了,一定不會是肯定,但是有可才有不可,有不可才有可,互相依待而成,所以要説可,通通可;要説不可,通通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世人通常不是順着這個是走,就是順着那個非走,陷入二元迷思之中。“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所以至人不順着是非相對的路而行,而是跳出這個框架之外,像天普照大地般,用超越的立場來觀照人間的是是非非,則無是無非。莊子接着又説: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這一段是接續上段而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是也就是彼,彼也就是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中有是有非,非中有是有非。是本來就是是,但卻涵有非;非本來就是非,但卻涵有是。莊子接着用兩個疑問句來説:“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究竟有彼是呢,還是没有彼是呢?在二分法下是有彼與此之分的。但“彼是莫得其偶”,“偶”是對偶、相對的意思,如果取消彼與此的對偶性,讓生命從彼端或此端的相對中超拔出來,要是對,通通對;要是不對,通通不對,結果就無是無非,回到什麽境地呢?“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樞”就是樞紐的意思,一個圓環的中心點,回歸“道”的本身,則人間紛擾的是非,亦歸於無有,即本體即工夫,恢復生命的無限性與自由性,而不再受彼端或此端的困限,得到靈明的智慧,所以説:“故曰莫若以明。”莊子在《齊物論》中,爲避免本身論述也落於言語知解的片面性,以破除人間是非等的價值對立,遂使用一種特殊的語言形式,以辯證的詭辭的“旋説旋掃”方式,來衝破二元對立的思維,結果無是無非,道通於一,萬事萬物各自效力,到達“無用之用”自由平等的人間新境界。底下就此再加以闡明。
二、 以超越的“道”解消表相的執著: 運用“辯證的詭辭”以通達逍遥齊物境界
所謂“辯證的詭辭”,當然也是一種詭辭,既名之爲詭譎的言辭,便有其自我矛盾之處,然而我們需進一步探究的是,在《齊物論》中,此種辯證的詭辭,爲表面的自我矛盾?抑爲實質的自我矛盾?首要之務,當在區分現象界與形上界,再運用辯證語言“先分解再取消分解”的性格,來釐清哪一句語相爲指點現象界,哪一句語相爲指點形上界。兹舉例如下: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悦。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這是則很著名的莊子寓言故事——朝三暮四。“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勞煩神明想得到這個“一”,而不是由“道”,不知道本來就是一,這就叫做朝三暮四。“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詭辯學派例如惠施等人運用邏輯的詭辭,以及儒墨兩家各執著於一端之言,而没有“無言”、“無用”的修道境界,真實的道是不能够道通爲一的。他們玩弄邏輯的詭辭,以及各執於一端之見,其實只是像猴子的朝三暮四而已。養猴之人無論早上發三粒橡實、晚上發四粒,或是早上發四粒橡實、晚上發三粒,一共都是一天七粒。“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名實並没有增加也没有減少,卻有喜怒之别,“因是”就是因順,因其所是而是。“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有是才有非,有非才有是,是非彼此相因而生,是非自己立不住,所以莊子要超越是非相對的争執,要説是,通通是;要説非,通通非,如此便没有是非相對的争執,結果才可以無是無非,到達何種境地呢?停止於“天鈞”的地方,這也就是上文所説“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的“道樞”。接着“是之謂兩行”,到了天然鈞平的地方,是非才可以“兩行”,都可以行,没有争執。其實老、莊道家乃爲回應時代的問題,斯時儒家與墨家並世爲顯學(6)請參閲王邦雄先生《老莊道家論齊物兩行之道》,《中國哲學論集》,(臺灣)學生書局2004年版,第393—417頁。,有儒家種種的是,方有墨家種種的非儒,反之亦然,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肯定自己,否定對方,是非永遠争論無休,所以道家才要是非休止於天鈞這個地方,也就是回歸“道”的本身,平齊種種是是非非的物論。
從“用”上來看,世間萬物、人間各種學説都有其各自所對應的“用”,這是從現象界的“用”上來看。其實,物各有其用,論各有其是,乃是齊平的。此如《逍遥遊》所説,“堯讓天下於許由”,而許由加以拒絶説:“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三、 逍遥齊物的無用之用
名言是一種概念系統,所謂概念就有其一定的範圍、界限(limit),而人間的是非、善惡、美醜等價值標準,亦是種概念系統,彼此相對應而生,没有絶對性。如果以“是”用“正”來代替,把“非”用“反”來代替,“和”是種消融。莊子所謂“正言若反”的語言形式,當然是一種詭辭。莊子破除是非相對,先行分解,結果臻入無是無非的絶對之境;先行分解再取消分解,越過正、反,而達到合的境地,所以説“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莊子這種“辯證的詭辭”,看似矛盾,實不矛盾,破解現象界的相對,而回歸形上界的絶對。《齊物論》再舉例如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這段探討宇宙根源的問題。“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現在有如此的言説,不知跟上一段所説的“是”是同還是不同?不管同還是不同,處境等同,要找到終極之道爲何。以下所要説的,跟上一段也没有分别了。“雖然,請嘗言之。”雖然如此,請嘗試讓我説説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這是一個方式,有人説宇宙從“有”開始,那麽“有”又是從哪裏來的?於是就有“未始有始”的二次方、三次方出現,無窮後退,所以“有”不是最後的根源。“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這是另一個方式,有人説宇宙從“無”開始,那麽“無”又是從哪裏來的?於是就有“未始有無”的二次方、三次方出現,無窮後退,所以“無”也不是最後的根源。從這兩個方式觀之,莊子認爲“有”、“無”都不可作爲宇宙萬物存有的根源(7)《道德經》首章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依老子之意,“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存有的根源爲“無”。莊子則更進一步,以“無”否定“有”,又再否定“有”、“無”,認爲“有”、“無”都不是宇宙萬有的根源,是種“否定之否定”。。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俄而”是剛才,“果”是究竟,剛剛“有”、“無”同時出現,但是卻不能知道所説的“有”、“無”,究竟哪是“有”呢?究竟哪是“無”呢?現在已經有所説了,但是不知道這所説的,究竟是有説呢,還是無説呢?其實“有”、“無”的概念均可無限後退,宇宙的根源不在“有”、“無”之際,那麽宇宙的根源在哪裏呢?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這裏,一再看到《齊物論》使用一種特殊的設問方式(8)關於《齊物論》中的弔詭句式,曾昭旭先生嘗撰文辯證,何以莊子要進行如此高度敏鋭的解消動作,並舉下列八句加以析論: (1)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2) 亦有辯乎?其無辯乎?(3)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4)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5)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果孰有孰無也。(6) 今我則既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7)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8) 庸距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距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請參閲氏著《論語言與生命的詭譎辯證》,《鵝湖月刊》第28卷第5期總號第329期,2002年11月,第11—16頁。,就是提出一個疑問句,正面問一句,反面又問一句,但卻不提供一個正抑是反的答案,試問: 不給出一個明確的解答,而是用兩造疑問的方式表達,莊子的這種表達方式究竟要暗示什麽?顯然的,莊子的答案根本就不在彼端(有)與此端(無)之中,質疑由語言分解而來的相對兩端,取消對語言的執著,乃因真正的“道”(存有的根源)並不在言詮之中。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秋天的毫毛最大,太山爲小,簡直自我矛盾;同樣,小孩死亡爲長壽,活到八百歲的彭祖算是夭折,根本違反常理。但是大小、長短壽夭究竟有没有一定呢?大小、長短在經驗現象中都有一定的標準,莊子跳脱出人間的框架標準,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所以接着説:“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這兩句話是莊子非常重要的思想(9)《莊子·養生主》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莊子反省人生的困苦有二: 一在“吾生也有涯”的天生命限,二在“而知也無涯”的人爲桎梏。解消之道,前者在逍遥無待之遊,後者在天籟齊物之論。,一爲時間性的局限,一爲空間性的囿限,天地萬物與我並生、爲一的境界,是一個什麽樣的境界呢?
先看:“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然已經成爲一了,那還會有話説嗎?指向無言之意,因爲能指(主詞)與所指(受詞)已爲一,主(subject)客(object)合一,没有分别相,所以説無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既然已經説它是一了,那還會没有話説嗎?指向有言之意,因爲能指(主詞)與所指(受詞)已謂之一,主(subject)客(object)分立,有分别相,所以就有言。“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一與言爲二”就順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這句話而來;“二與一爲三”就順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這句話而來。“一與言爲二”中的“一”,因爲没有“一”與“言”的相對,落在“無”的層次上;但“一與言爲二”中的“二”,因爲有“一”與“言”的相對,故爲二,落在“有”的層次上。牟宗三先生以爲,“一與言爲二”中的“一”顯示出“無”來,“二與一爲三”的“二”顯示出“有”來,至於“二與一爲三”的“三”爲“一”與“二”的綜合,代表“有”、“無”通而爲一,“三”是兩層的綜合(10)見氏著《莊子〈齊物論〉演講録(八)》,《鵝湖月刊》第28卷第1期總號第325期,2002年7月,第2頁。,這也就是《道德經》中所表現的“道生之,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玄”理(11)牟先生以“有”、“無”爲“三”來解釋此中的一二三,一爲有,二爲無,有了之後還要以無來做作用的保存,此爲無,合有與無則爲玄。《道德經》首章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合“有”、“無”爲“三”,謂之爲“玄”。。牟先生以“有”、“無”爲“玄”來解釋此中的一、二、三,認爲莊子此中所説就是對於老子此文的詮釋。一爲有,二爲無,有了之後還要以無來做作用的保存,此爲無;合有與無則爲玄,此爲三。因此,牟先生强調老子的“無”是一種作用的保存,讓開一步,任其自在,如此所開顯的是境界形上學,是一種消極型態的主觀境界的形上學。這一種境界形上學,在“用”方面的反思,最後所達到的就是“逍遥齊物的無用之用”的生命境界。
“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這是屬於兩個層次的問題,“自無適有”,依上述所言,“三”代表“有”、“無”的融合,已爲玄之又玄的妙道,一直説道“三”就要停止了,這是屬於超越層的問題;“自有適有”,從一、二、三以降,無窮無盡,即使連最高明的曆算家也算不出來,更何況是一般人呢?這是屬於現象層的問題。“無適焉,因是已。”“適”就是往,“因”就是順,一來一往,有往就有止,所以要無適焉,通通都放下,就没有適止了;順着“自有適有”不好,連順着“自無適有”也不好,化掉“有”、“無”相對的概念,才是真正存有的根源。
莊子在《齊物論》中使用一種特别的疑問句式,分别提出對兩端疑問的語句,不給出明確的答案,欲指點出什麽?原來答案根本不在語言分解的兩端,取消分解,解消一切對概念系統的執著,而逼顯出一個終極的根源,所以説“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二與一爲三”。莊子這種“辯證的詭辭”,看似矛盾,實不矛盾,化掉現象兩兩對立的矛盾,以否定之否定,豁顯出真如的形上之道,通達逍遥齊物“無用之用”的生命境界。莊子明説“無用之用”有下列文本:
《莊子·逍遥遊》: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不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岡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人間世》:“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莊子·山木》: 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莊子以寓言故事來詮釋無用之用的道理者爲數甚多,而落在不同的層次。以《逍遥遊》爲例,“杯水”、“蜩與學鳩”、“楚南冥靈”、“宋榮子舉世譽之而不加勸”、“列子御風而行”,講的是小大之辯,而物各有其用,體會到小大之辯而物各有其用,是要能够在相對的用之中來安身立命,適性自在。然而不能僅只於此,進而還要透過無、無己的自我超越,來向上超越。在虚無中涵養精神,培養自己的深邃悠遠的精神境界,如此乃能到達無窮無待的絶對自由。這就是“堯讓天下於許由而許由不受”,講的是隱士許由的“無用”超脱了一切人間的用,乃至於超脱了堯統治天下的用,這樣的精神境界才能够不斷地從事精神創造,而又不爲物累。
誠如賴賢宗所言,莊子對於“無用之用”的詮釋道説經歷了三個面向,首先是經歷了現象論上的“用”,其次是“無用”,最後還要到達體性上的玄觀大道的“無用之用”(12)賴賢宗《莊子與海德格爾: 無用之用、以明、物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第二届莊子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年4月,第184—201頁。。《逍遥遊》最後的寓言“吾有大樹,人謂之樗”的故事,“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野之”,所説的就是這個最後的玄觀大道的“無用之用”。在《齊物論》中,表達爲“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的“不用之庸”,在庸言庸行的常道之中,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妙用無境。
人間之所以不得逍遥,失去適性通達的自由,乃在於被物論之不齊所局限,未能領略《齊物論》之奥旨;乃在於被一隅之用所局限,未能通達“無用之用”的自然天真。
四、 “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的“無用之用”之新詮釋:即道即言的齊一生命
莊子這種辯證的詭辭,旨在化解兩兩對立的表相執著,通過先分解再取消分解的辯證語言性格,以超越的“道”來解消兩端的矛盾,所以既已釐清何句爲指點形而下的物,何句爲指點形而上的道,所謂詭譎的言辭,表相看似矛盾,實已消融於一個非矛盾的終極根源。但是我們必須再追問的是,當莊子以形上之道解消表相兩端執著的同時,其本身是否也落於形上界/道與現象界/言的二元對立中?《齊物論》舉例闡明此義,最後到達“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的“不用之庸”,對於《逍遥遊》的“無用之用”的人格境界,通過辯證的詭辭,體會無言、無爲的超越,將“無用之用”予以道家知識論上的證成。其説如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公孫龍著有《指物論》:“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又有《白馬論》:“白馬非馬。”既然已經説它是“指”了,卻又説指不是指,簡直自相矛盾;既然已經説它是馬了,卻又説馬不是馬,也是自相矛盾。所以莊子認爲以指來説,不如以非指來説;以馬來説,不如以非馬來説。如此一來,根本無所謂指,根本無所謂馬。當無分别心時,天地就是一指,萬物就是一馬,故曰:“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13)牟先生在説明“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時,舉熊十力先生大海水與小海漚的例子作比喻。海漚就是小波浪,風吹起來才有小波浪,風停止了也就没有小波浪,小波浪不能獨自存在,法無自性,萬物就像小波浪一樣,没有獨立性,形形色色的萬物就像小波浪一樣,最後都歸到大海裏面,形形色色的表相最後要回歸真實的道,如此而言“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見氏著《莊子〈齊物論〉演講録(五)》,《鵝湖月刊》第27卷第11期總號第323期,2002年5月,第4—8頁。“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客觀的東西可以是什麽,不可以是什麽,都是由我們去肯定它或否定它;一個東西是什麽,不是什麽,都是由我們去稱謂它而致。“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然”是如此,“不然”是不如此。爲什麽會如此呢?因爲是由我們這樣説它才如此的;爲什麽不會如此呢?因爲是由我們這樣説它才不如此的。“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物好像有客觀的“然”,物好像有客觀的“可”。但其實“物固有所然”是從“無物不然”而來的;“物固有所可”是從“無物不可”而來的。因爲就我們所認知的概念世界,無論名言、是非、善惡、美醜等都會有一個固定的標準,但這些都只是知識論上的相對,只有打破認知世界的執著,才能進入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的非認知層次,自然體會到“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的境界。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莛”是小竹竿,“楹”是大柱子,本有小大之分;厲是癩痢頭,西施是美女,本有美醜之别。“恑”就是詭,“憰”就是譎,“恢恑憰怪”就是大大的詭譎怪異,明明這些都是最極端、最怪異的現象,但在道的世界裏,一體平舖,將執著、分别消融於無有,同於大通,所以才説“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凡物的存在,有成就有毁,解消心知的執著,回到“道心”,無成亦無毁。“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只有明白的人才知道通而爲一,“爲是”是爲此的意思,“庸”是常的意思,爲此不要把生命寓寄在“用”之中,而要把生命寄托於庸常之中。“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人間街頭的用只是小用,回歸生命本身的用方爲大用,所以無用之用是爲大用(14)《莊子·人間世》曰:“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在“用”的層次,人我之間會有小用、大用的差别,也就有有用、無用的價值判斷;但在“庸”的層次,人我之間不會有小用、大用的差别,遂没有有用、無用的價值判斷。,道通爲一,萬物自在自得。“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順任人人之所然而然,已然如此而又不知何以如此,無心自然能見道。
所謂“道通爲一”、“復通爲一”,王邦雄先生認爲“道通爲一”是同於大通,爲存有論的合一;“復通爲一”是智慧的合一,爲工夫論的合一。人間的價值判斷都是從分别心而來的,是一種心知的作用。解消心知的執著,回歸無執著、無分别的自然常道,道通爲一,此“一”已不是邏輯上A+(-A)=1的“一”;只有達者才能知通爲一,而此“知”不是一般的認知之知,“知”是覺知的意思,必須將生命寄托於庸言庸行之常的生活中,通過智慧的體悟,方能體道,復通爲一。莊子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齊物論》)聖人知道有可説的地方,也有不可説的地方,所以“聖人懷之”。而這不可説之境,言語道斷,心行路絶,將自己的生命寓寄於庸常之中,唯有通過修養工夫方能證道,寓體於用,從用見體,故東方哲學爲體道哲學,見淺言淺,見深言深。莊子之善用辯證的詭辭,乃深覺此道,所以“終身言,未嘗言”(《齊物論》)。旋即言説又再次旋即化掉言説,形上界與現象界復通爲一。
“終身言,未嘗言。”旋説旋化,隨説隨掃,最後是要通達逍遥齊物的生命境界。通過“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的“無用之用”之新詮釋,吾人開顯的乃是“即道即言的齊一生命境界”,此一生命境界呈現爲《逍遥論》所説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誠如賴賢宗所言,經歷“用”、“無用”,最後還要到達體性上的玄觀大道的“無用之用”。牟先生説道家形上學是消極型態的境界形上學(15)牟宗三先生《四因説演講録》,第六講“道家: 消極形態的動力因”,第七講“境界形態的形上學”。鵝湖出版社1997年版。。此一境界形上學還有其精神上的積極内涵,也就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不斷創造,在“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的“無用之用”之中,不斷地從事價值創造。
結 論
《逍遥遊》《齊物論》的主旨是要豁顯主體生命心靈的逍遥自在,此義揭櫫於首篇《逍遥遊》以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的精神人格,作爲逍遥境界之心靈内涵;繼而在《齊物論》中通過知識批判與點化,而達到莊周夢蝶的化境,至人、神人、聖人就是胡蝶一夢之物化。《逍遥遊》以“無用之用”之道説爲終止,而《齊物論》闡明“以明”的三層義,最後到達“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的“不用之庸”,對於《逍遥遊》的“無用之用”的人格境界,通過辯證的詭辭,體會無言、無爲的點化與超越,將“無用之用”予以道家知識論上的證成。
莊子之《齊物論》,欲在不可齊之中,尋求可齊之道,然而物論既不能取消,又不能統一,唯有超越一途。無論人間的是非、善惡、美醜等價值判斷,甚至是名言,都是概念系統,屬於認識論的層次。莊子在《齊物論》使用一種“旋説旋掃”的特殊語言形式,非邏輯上的詭辭,以破解對兩兩相對概念的執著,這種逆反式的辯證詭辭,謂之“道家式的辯證詭辭”。莊子以疑問句式,指點出不可言説之境,取消語言使用時必然出現的兩端對偶性,能指/能知與所指/所知合一,“先分解再取消分解”,呈顯出一種表相矛盾而實不矛盾的無限妙用,“有”、“無”同謂之“玄”,生命遂由現象界的彼端或此端困限中超拔出來,回歸終極之道,那個不可言喻的天籟之境,主體生命恢復其無限性而逍遥自得。然而真正的形上界不在現象界之中,也不在現象界之外,而是即現象界即形上界爲一,道寓寄於物之中又不著於物,全體大用之道方爲主體生命修養的一心朗現,此乃“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的“不用之庸”,即工夫即本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