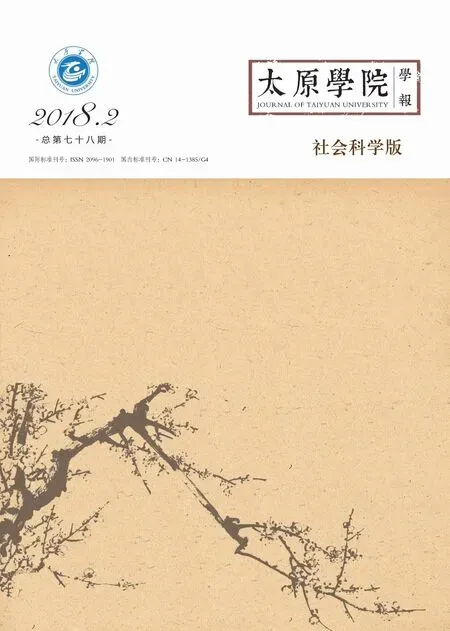石黑一雄《浮世画家》中的日本价值观探究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石黑一雄作为英国作家,其日裔背景格外引人注目。尽管他向以“国际化作家”自称,而否认他的日本化创作,正如他在谈论自己的双重文化背景时所讲:“我没有明确的角色,没有要代表的社会或国家。其他人的历史似乎都与我无关。而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不得不试着以一种国际化的方式写作”[1]21。然而他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品《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无论是在创作背景、作品内容还是封面插图上都处处尽显日本特征。
虽自幼随父举家迁往英国,接受的是正统的英国教育,连创作语言也无一例外用的是英文,但石黑一雄在家中从未间断地接受日本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他的父母随时准备着返回日本,他的祖父每个月都会给他寄送含有日本漫画和各种在日本受欢迎的礼物的包裹,在他心中,一直念想着祖父家的武士剑和家族旗帜。他的内心一直都有对日本故土的文化之根的追寻。虽然,在英日的双重文化背景裹挟之下,他不得不以“无根”来认定自我身份,但作为“流亡国外的日本人”[1]71,作家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遭受战败和原子弹之灾的故乡长崎的赤子关怀。
石黑一雄的《浮世画家》可以说是“从细节入手,反映日本人适应战败现实的一部小说”[2]105。作品以日记体的形式,时时穿插“怀旧”的主题,抽丝剥茧地将军国主义画家小野增二的早期思想和现世经历一一呈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野的思想成长历程可谓是日本人基本价值观发展转变的缩影。石黑一雄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了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异乎寻常的敏感,其细致入微处尽然展现了日本性抒写。本文便是立足于这一角度,去探讨文本所呈现的日本价值观。
一、义理观的坚持与背离
日本人的义理观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熏陶影响下发展而成的日本的特有文化,“其内容维系着日本社会中存在的浓密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3]104。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也谈到:“义理是日本独有的范畴,不了解它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4]122。
日本教育家新渡户稻造将义理解释为“一种社会舆论期待去履行的含混的义务感”[5]24。而本尼迪克特站在当今西方人的立场,将义理解读为“正道”,并将其划分为 “名誉的义理”和“社会的义理”。
名誉的义理的内容包括“遵守‘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各种繁琐礼仪的要求”[4]132。 这在日本社会生活中表现为,对社会各类人等的衣物、财产等进行的明确划分与规定。而“按照各自身份而生活,就意味着接受这种规定,并将其视之为自尊的组成部分”[4]135。
《浮世画家》以描写主人公小野增二的豪宅开篇,“在山上占据着显眼的位置,在周围的房屋间显得鹤立鸡群……精美的雪松大门,围墙里大片的庭园,琉璃瓦的屋顶”[6]1-2。居住在这样的豪宅之中,并不是因为小野增二拥有万贯家财,只是因为这是他凭借自己的品行和成就通过“信誉拍卖”赢得的。而居住在与自己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房屋,这在日本人看来是一种基于名分的义理。
保护自己的名誉免受玷污是名誉的义理的本质要求。日本是一个讲究“耻感文化”的国度,日本国民极其重视社会对自己的行动的评价。若名誉被玷污,他们便会想尽一切办法洗刷污名,甚至自杀。
在《浮世画家》中,小野凭二战时的军国主义画作达到了人生的辉煌的顶峰。然而,日本战败后,他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家里,他不再是说一不二的暴君,开始处处受到子女们的质疑和反抗;在社会上,他再也享受不到昔日的歌功颂德,开始承受人们的不屑与斥责。他甚至要去登门造访恳求老友为其讲好话,为的是扭转自己战后的名誉,为小女儿的出嫁营造良好的社会关系。他甚至在与佐藤一家的相亲会面时,为了抗议佐藤的小儿子光男的不屑与嘲讽的眼神,毫不讳言自己在战争中所犯的错误,违背了他毕生所坚持的军国主义信念,只为捍卫他那一时的自尊。然而,同样是面对战争前后的身份落差以及因战争所导致的一片狼藉的名声,三宅所在公司的总裁和在战时以创作战歌鼓舞日本青年大踏步迈向扩张之路的野口由纪夫,都以自杀谢罪。这种自杀谢罪的行为得到了青年一代的赞赏与支持,并使他们因此感到了压力,对未来充满信心。而对于那些不能以自杀谢罪的战争罪犯,他们满腔怨愤地斥责为是最怯懦的人。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讲到的:“按照他们的信条,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日本人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在一定场合,从对‘名分’的义理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方法”[4]150。
社会的义理实质上是一种报恩的义理,日本人对“恩”有独特的理解,本尼迪克特认为在英语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词。“在所有的用法中,‘恩’是一种承载,一种债务,一种负担。‘恩’是一种必须偿还的债务”[2]105。“日本人对老师、主人负有特殊之恩”[4]94。在石黑一雄所创作的《浮世画家》中,所呈现的不是对“恩”的社会义理的遵从,而是对“恩”的背叛。最典型的人物是小野增二的学生绅太郎。在小野名声大振的时候,他对小野百般恭维,表现出无比的虔敬与真诚,以至于当小野的学生黑田认为其能力根本不足以划入小野的优等学生之列时,小野却因他的“虔诚”在心中将他默认为优等生。绅太郎利用小野当时的社会地位,为他弟弟谋得了一份好工作,并带弟弟到小野家中千恩万谢,极尽表现心中的“难以报恩于万一”[4]94。可是到了战后,他出于私利,背弃老师的恩义,一改往日对小野的拥护和服从,甚至提出冒犯老师的恳求——让小野写信证明自己曾与其进行过军国主义思想的抗争,以便谋得美国人统属下的工作。如此荒唐可笑之举对小野无疑是一种讽刺,同时也投射出在战败的氛围中,崇奉以美国为指导的国家商业化运作的环境下,日本国民对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的背弃。
二、伦理观的坚守与冲突
所谓伦理价值观,指的是一系列的行为道德观念及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它主要包括家庭和社会关照下的伦理价值观。石黑一雄秉承了日本作家精致而婉转的写作特征,通过在《浮世画家》中所展现的单个日本家庭,便使读者窥见了传统影响下的日本家庭中的伦理价值观。
家庭中的伦理价值观主要表现在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和人际关系处理上。在回忆与现实穿插不断的小说叙述中,围绕着现实展开的第一个情节是节子带着儿子一郎回家探访父亲小野和妹妹仙子。在这一部分的描写中,作者对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情尤为关注。一郎在阳台上肆无忌惮地奔跑,“他放弃了正襟危坐,仰面滚在地上,开始把双脚悬在半空踢蹬”[6]11。“一郎又躺倒在地,悬空踢蹬双脚”[6]13。一郎的这些行为举止很明显与我们传统认知中日本人在礼仪上的拘谨相违背。然而,面对儿子一系列的不合礼仪的行为举止,作为一郎母亲的节子并没有对其斥责和暴怒,她只是“焦急地压低声音喊道”[6]11。而小野这一曾经的家庭暴君也并未对一郎的调皮捣蛋有任何不悦的反应。谈及此,我们很容易将其片面地解读为一郎的粗鲁行为是受美国价值观的文化侵袭的影响,尤其是作者在文本中多次特意强调节子在礼仪上的庄重严谨,这似乎在假意迷惑读者,在两者的鲜明对比之下,节子与一郎这两代在不同社会价值观影响下长大的人,在礼仪行为上呈现出巨大差异。
依据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的调查研究,“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4]230。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此时的一郎的年龄是八岁,根据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生曲线的描述,男孩六七岁以后应该学会“知耻”和“谨言慎行”,文中小野也讲到“一郎一点也不像他这个年龄的许多孩子那样腼腆”[6]39。因此,此时本该学会自我节制的他,却依然如此活泼任性。这时候,我们就不由想到一郎有一位极力推崇美国自由和民主,反抗日本传统的父亲池田。很明显,美国的价值观已渗透到日本的家庭教育之中。
相较于一郎,小野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极为严格规整。在他所展开的对父母亲的回忆中,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家庭中十分明确的等级制。毋庸置疑,父亲是家庭等级制中最高层次的代表,他的威严不仅表现在孩子面前,也表现在妻子面前。在小野的回忆中,因父亲将客厅规定为不能被日常琐事玷污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家庭中心,所以,未经父亲允许,小野和母亲都不得擅自进入客厅,小野十二岁以前对客厅的认知也仅仅是偶尔匆匆瞥过一两眼。十二岁以后,他之所以能进入客厅,是因为此时的他到了从父亲那里学习接管家族生意的年龄,所以父亲有必要在“客厅”这一庄严神圣的地方与其召开“商务会”。按照日本人的传统观念,“在若干年内,父亲仍然管理‘家务’,以后再由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能把家务让给儿子,那他自己那种角色就没有意义”[4]232。作品中,小野的父亲认为他“作为将来的一家之主,应该参与所有的决策”[6]49,正是反映了此等家庭伦理观。在与父亲的“商务会谈”中,小野总是表现得“终日惶惶不安”[6]49。当父亲要求把所有画作带到客厅之时,小野纵使心中不情愿,依然毫无条件地服从了。当小野得知自己的画作被父亲悉数烧毁,自己的雄心抱负被父亲悉尽点燃,也并未对父亲表现出任何敌意与反抗。这便是“父亲”这一最高权威在日本家庭中的体现。
谈及日本的社会伦理,离不开对“忠”的阐释。“忠”在日本道德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被誉为“武士道之魂”。小泉八云曾写道,日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其忠的非同一般的形式更加令人印象深刻”[2]106。《浮世画家》中通过一系列对“忠”的背叛的事件的讲述,反面阐释了日本的“忠”。
武士道作为日本的精神国粹,是日本国民共同的道德认知。作品中最典型的“忠”的背叛便是小野对武士道的背叛。按照武士道的精神要求,小野作为战争前夕和战争中的军国主义分子,面对国家战败和敌国的占领,必须采取复仇或自杀的行动。他刚开始对军国主义行径的拒不认错符合了对信念的基本坚守,但是当仙子之前的男朋友三宅谈到所在公司的总裁因国家战败而自杀谢罪时,他却提出质疑:“如果你的国家卷入战争,你只能尽你的力量去支持,这是无可厚非的,有什么必要以死谢罪呢”[6]67?颇为滑稽的是,为了挽救小女儿的婚事,他又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承认我做的许多事情对我们的民族极其有害,我承认在那种最后给我们人民带来数不清的痛苦的影响当中,也有我的一份”[6]156。如此言论,明显是对武士道精神的背离。
其次是对老师的背叛。日本是一个极其尊师重教的国家,教师的权威不容侵犯,这可以在作品中得到证实。曾经被毛利君视为尖子生的佐佐木,因与老师产生了分歧思想而被斥为叛徒,离开的时候就连他最好的朋友都不愿对他说一句安慰的话,而毛利君别墅里的学生们,尽管常常肆意取笑对骂,但从未出现僵硬局面,然而一旦在对骂中提及佐佐木,这个“叛徒”的代名词,局面就会立即失控,令同事们大打出手。小野也曾在心中为佐佐木辩解,他认为“正是尖子生最有可能考虑到老师作品中的缺憾,或形成跟老师观点有分歧的思想,从理论上说,一位好老师应该接受这种倾向,然而,实际上其中牵扯的情绪非常复杂”[6]175。而这种复杂的情绪,便是日本传统的尊师重教思想和教师对自己权威名分的过分防御。
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小野身上,小野的作品因为出现了“对毛利君风格的明目张胆忽视,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努力去捕捉娱乐世界里转瞬即逝的灯光,而是用大胆的书法来强调视觉冲击,使用毛利君教学所反对的硬笔轮廓的画法”[6]218。仅鉴于此,便令他的同事好友乌龟大惊失色,更令他的其他同事们都对他惧而远之,更惹得毛利君将画作付之一炬,将其赶出别墅。从这一层面上讲,小野无疑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对于“忠”的叛变者。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他先后两次背叛师门,第一次自我美化为“不屑于艺术对商业价值的追求,要为艺术而艺术”[6]218,第二次又以追求作品的实用主义之导向而再次背叛师门。他还以其自我标榜的“优胜劣汰”的价值理论鼓励学生不要随波逐流,勇于挑战权威。且不论这一主张放于任何国家制度之下的合理性,但仅仅从日本千年传承的“忠义”文化而言,小野的行为实乃不忠不义之举。
三、历史观的变通与妥协
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广岛和长崎被美国投放的原子弹夷为平地,本土被美军占领。美国人曾在太平洋战役中见证过日军的嗜血好斗和誓死抵抗,本以为对日本的占领和统治将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令其惊讶的是,日本人却以与战场上截然不同的转变来友好地对待昔日的敌国。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描述过这样的情形:“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身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前往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为安全担心,并且受到曾经是国家主义者官员的有礼貌的接待,未发生过一次报复行为。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站立道旁高喊‘你好’‘再见’,婴儿自己不会招手,母亲就把着他的小手向美国兵挥动”[4]155。
日本人的这种“善变”,在美国人看来简直是不真实的,这与他们民族长期接受训练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机理是相关的。日本人把“名誉”看作毕生追求的目标,因为“名誉”是使他们获得他人尊敬的必要条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的道德标准随时可以视情况而改变。即使二战中他们在投降书上签字,但他们也从未承认自己是民族的失败,而只是他们用军国主义的武力手段向全世界猎取崇拜这一方针的失败。既然武力强国的道路行不通了,那他们就理所应当地把它视为错误的方针而予以抛弃,寻求新的和平处世之道。这正如日本人常说的:“咬自己肚脐也没用”[4]276。因此,日本投降后,在美军尚未登陆的情况下,东京的《朝日新闻》就公开发声:“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4]275。另一家东京大报《每日新闻》也是发出了同样的社论:“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4]275。这种价值观不仅表现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而是从东京街头到僻远寒村,整个日本都保持着同样的转变。这正如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的较为中肯的评价:“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4]2。
《浮世画家》的取材地是长崎,故事论述时间是1948年10月到1950年6月,刚好是日本结束战争和遭受原子弹之灾后的三到五年间。作者在文中对战后满目疮痍的描写,尤其与昔日的繁华热闹相较更显凄凉,但却从未出现人们对导致荒凉的祸首——投放原子弹的美国的任何敌意与谴责。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挑起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这与战争前夕和战争中为日本侵略扩张而摇旗呐喊的态度大相径庭。不仅如此,日本的年轻一代在战争的乌云还未退却的短短几年间,就似乎全然接受了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价值观。
小野惊诧“战争前两年跟节子结婚的那个谦逊的、彬彬有礼的青年,如今已经判若两人”[6]70,困惑于为何女婿池田会对长辈怀有此等怨恨,他甚至用“刻薄”“恶毒”来形容池田的观点。而池田的这种改变并非个例,这已然成为了战后青年的共性。他们大力谴责战争罪犯应自杀谢罪,鼓吹美国的民主、自由,并积极畅想日本的民主蓝图。这种颠覆性的转变还体现在对一郎这一新生代的教育上。节子说:“池田认为,一郎与其崇拜宫本武藏那样的人,还不如喜欢牛仔呢。池田认为,现在对孩子们来说,美国英雄是更好的榜样”[6]40。
小说的结尾,仙子的婚事顺利解决,小野的两个女婿所供职的日本电气和KNC公司也得以迅猛发展,日本国民在美国的民主革命领导下极为乐观地评价道:“我们日本在理解民主和个人权益等问题上已经前进了一大步”[6]233。当小野站在犹疑桥上抚今追昔,对抑郁的过往尽显释然。过去的荒凉废墟已经重建,一座座现代化的办公大楼簇然新起,人们过往的消沉已然退却,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和昂扬向上。小野“坐在长凳上注视着这些年轻的职员,兀自微笑……看来,我们国家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误,现在又有机会重振旗鼓了。我只能深深地祝福这些年轻人”[6]258。
回溯小野的一生,实则代表了整个日本战争前后的精神缩影,其乐观圆满的结尾,不仅吻合了石黑一雄创作的救赎色彩,更是体现了石黑一雄对日本所展现的民族情怀。正如他在访谈录中所谈到的:“人生短暂,若一步走错则可能全盘皆输:这一认识是令人辛酸的。然而,那些犯下的错误可以让后代有所收获,这一点至少能让人从中感到安慰。这是那样一种辛酸,那样一种情感,受挫却依然寻找理由让自己感受某种乐观因素”[7]137。
参考文献:
[1]梅丽.危机时代的创伤叙事:石黑一雄的作品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2]李霄垅.石黑一雄小说《浮世画家》中的背叛[J].外语研究, 2008(5):104-107.
[3]黄宝珍.日本人的义理观解读[J].贵州大学学报,2009(6):103-106.
[4]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5]新渡户稻造.武士道[M].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6]石黑一雄.浮世画家[M].马爱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李春.石黑一雄访谈录[J].当代外国文学,2005(4):134-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