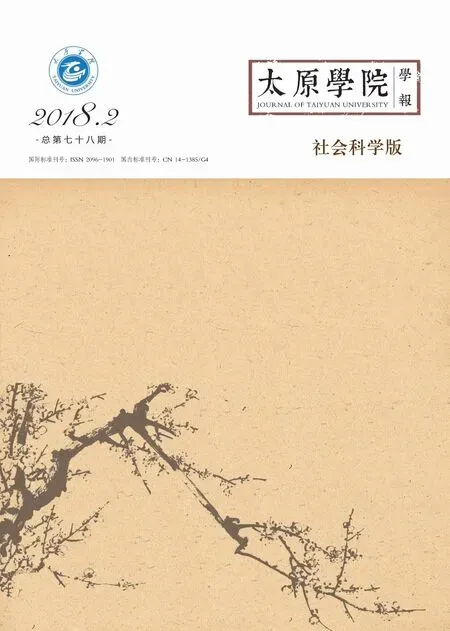《锦衣》:传统技法与民间视角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作为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莫言除了小说创作之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剧本创作的野心。无论是由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本《红高粱》《幸福时光》《暖》,还是话剧剧本《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无不显示了莫言的剧本创作才华。近期在《人民文学》第9期发表的戏曲剧本《锦衣》,是莫言剧本创作的又一尝试。
《锦衣》是一部借鉴山东戏曲茂腔的戏曲文学剧本,既有着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又有民间特色。莫言曾多次提到家乡的茂腔给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这个小戏唱腔悲凉,尤其是旦角的唱腔,简直就是受压迫妇女的泣血哭诉。高密东北乡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哼唱茂腔,那婉转凄切的旋律,几乎可以说是通过遗传而不是通过学习让一辈辈的高密东北乡人掌握的。”[1]422-423莫言小的时候经常跟随着村里的孩子去邻村听戏,自己也曾在村子里的业余剧团跑龙套,扮演一些小角色,还和一个会拉琴会唱戏的邻居叔叔编写了九场大戏《檀香刑》。后来的小说《檀香刑》就直接引用了茂腔剧本的大量唱词,并且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等方面大量借鉴茂腔的戏曲文学技巧,使茂腔获得文学界的关注。
《锦衣》正是在莫言创造积累的基础上,延续了他一贯以来的民间立场,将茂腔直接搬到当代文学的大舞台,实现对民间文艺的传承。作为一部戏曲文学,《锦衣》在人物塑造、情节模式、语言艺术、主题内蕴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色。
一、人物的脸谱化
与小说塑造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不同,中国戏曲自有一套人物塑造的规范,即人物的脸谱化。受民间艺术“别善恶、分美丑、寓褒贬”的美学原则的影响,传统戏曲多使用脸谱将人物按照不同的性格、身份进行分类,观众通过脸谱就能识别人物的忠奸善恶。剧作家与观众对剧中人物形成一种默契,将剧中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类,人物的丰富性主要体现于人物在性格的支配下作出的种种行动。
茂腔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地方小戏,简约质朴,内容多是反映男女爱情和家庭伦理,人物的选择上也多是一些取材于民间的小人物。“剧中的人物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多为‘高密东北乡’的老面孔,但是这次莫言没有给他们充分展示人性的机会,而是进行了合乎戏曲规律的‘脸谱化’设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行当,赋予不同的表情、动作、语言”[2]2,“多情善感”而又“敢作敢当”的春莲、“坑蒙拐骗”的王婆、“见利忘义、见风使舵”的王豹、“昏庸贪官”庄有理、“纨绔子弟”庄雄才等,在未出场时就有了各人鲜明的标签。正是这些类型分明的人物,显示了民间世界的丰富与多彩。
剧中人物性格的展开主要是由人物对话和唱词体现出来的种种戏剧冲突实现的。“戏剧冲突是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斗争在戏剧舞台上的反映,亦即经过剧作家精心艺术处理的、典型化的社会生活矛盾在戏剧作品中的体现。它既是结构戏剧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基础,又是戏剧赖以表现社会生活的特殊手段。”[3]56人物性格的不同引起种种戏剧冲突,而尖锐的戏剧冲突又能反映出人物性格。按照冲突实质的不同,《锦衣》中的主要戏剧冲突有利益冲突、情感冲突、阶级冲突三类。
利益冲突。清朝末年,内忧外患,清政府的软弱腐败、列强的欺压蹂躏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故事最先展开的场景是通往县城的石桥边一个小型集市上,这里混杂着小贩们热情的喊叫声,与热火朝天的氛围不相适应的,是宋老三用绳子拴着女儿春莲的登场。宋老三是个大烟鬼,将万贯家产挥霍完,气死自己的老婆之后,又想卖掉自己的女儿获利。以宋老三卖女的戏剧冲突来塑造宋老三嗜烟如命、麻木不仁的形象,并在一出场就渲染了春莲的苦命、悲情色彩。同样是利益的趋动,姑侄俩王婆、王豹将贪婪之手伸向了顺发盐铺寡居的季王氏。王婆本也是大户人家之女,家境殷实,却因媒婆李大嘴的欺骗嫁给了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婚姻不幸,反抗无果后只得认命,从此将挣钱作为人生的主要目的。眼看着顺发盐铺老掌柜刚去世,季星官又远在东洋留学,便寻思着给老太太娶个儿媳妇回来作伴。劝诱无果后,王豹又用奉命抓捕季星官威胁,迫使季王氏答应了姑侄俩娶儿媳妇的要求。宋老三、季王氏、王婆、王豹等人,本都属于社会的底层,却因利益纠葛,呈现出不同的人性。宋老三的堕落、春莲的身不由己、季王氏的软弱无依、王婆王豹的狡诈贪婪表现得淋漓尽致。
情感冲突。春莲嫁到顺发盐铺之后,首先面对的是与婆婆季王氏的冲突。季王氏是旧时代标准的婆婆样板,“多年的大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4]22,当年新婚三日就被婆婆逼着去挑盐的经历,转化为教训儿媳的资本,逼迫春莲从事挑盐的体力劳动,以使她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季王氏一心盼着儿子回来继承家业,误以为儿子去世之后,就把守护好家族的产业作为主要追求,一味要求媳妇干活。但偶尔流露出来的对媳妇的心疼和维护,又使季王氏身上流露出人性的光彩。而作为作者叙述主线的春莲的爱情,比较具有传奇色彩。季星官先是在桥头对春莲一见钟情,后扮演公鸡幻化之人与春莲情投意合、两情缱绻。在面对纨绔子弟庄雄才的调戏时,春莲不惜撞墙反抗,正是她对爱情的坚贞,才守护住了她与季星官的爱情。传统戏曲在塑造爱情故事时也多如此,剧中的女主人公更多地承载了作者对爱情的美好期望,《西厢记》中勇敢追求爱情的崔莺莺、《牡丹亭》中为爱而死又为爱而生的杜丽娘等人身上,都有春莲的影子。庄雄才的登场构成了爱情的阻碍,以此突出春莲对爱情的坚贞。
阶级冲突。剧本中体现出的阶级冲突,主要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知县、庄雄才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庄雄才仗着自己知县公子的身份,抢取百姓钱财、调戏良家妇女,并在父亲的帮助下,窃取县盐业局局长、洋枪队队长之职。庄雄才贪图春莲的美貌,借着自己盐务局长的身份,对季王氏百般刁难。季王氏无力反抗,想要讨回公道,也被庄雄才与县太爷、太守、巡抚的种种关系压制。官官相护,压制得人民走投无路。春莲不得已,只能撞墙自尽。以季星官、秦兴邦为首的革命党人,正是认清了清朝腐败落后的现状,深知人民的水深火热,组织了革命以救亡图存。而清政府对此严厉打压,知县更是想借抓捕革命党立功。季星官等人最后的暴动算是成功了,但极具讽刺的是,剧中坑蒙拐骗的小人物王豹,在看到革命形势之后,也翻身革命,想到新政府里混个小官做。革命的命运不言而喻。
与传统戏曲类似,剧中的好人往往处于社会中的弱势,因个人意志受到压制而处于被动地位。“人类意志的争斗,自然是因人类生活状态的不一致而起的,而其表现则每每是伦理道德的观念之冲突与矛盾;反映到戏曲上,则成为剧中人个性的互相搏战。甲要奴隶工人,乙要改良工人生活,丙要扶起工人来做统治者,自然甲乙丙各有其生活上的立场,而个人的主张则体现出伦理道德观念的争执;戏曲虽不是执行伦理道德的裁判的权力者,但它应当决定甲乙丙的谁是谁非,而予观众以有力的暗示,这才是戏曲站在了社会的前面,这才能生出戏曲推动社会的功绩。”[5]22王婆王豹的贪图小利,自然有对秦兴邦的敲诈;庄雄才欺压百姓,自然有季星官等人要革命反抗。不同的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的道德水准,在作者和观众心中都有一定的标准,而各人在不同的标签下表现出来的种种行动,会对人的心灵有不同的冲击。
二、情节的模式化
《锦衣》主要的叙述线索有两条,一条是以季星官为首的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历史叙事,一条是以春莲的命运发展及公鸡变人的鬼怪传奇。显然,依托着民间文化滋养的第二条线索是作者叙述的主线。莫言曾坦言,“饥饿和孤独是我的小说中两个被反复表现的主题,也是我的两笔财富。其实我还有一笔更为宝贵的财富,这就是我在漫长的农村生活中常听到的故事和传说。”[6]123儿时从家中长辈处听来的“公鸡变人”的故事,给莫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在2000年莫言在澳大利亚演讲的时候就使用过“锦衣”这个题材,2014年创作了《锦衣》剧本,后来经过不断尝试、修改,最终完成了《锦衣》的创作。
《锦衣》除了前面的序幕和最后的尾声,共有十四场,如此多的篇幅在情节设置上比较严格地遵循了戏曲文体的特色。关于戏剧的结构,郁达夫提出“序说、纠葛、危机、释明、结尾”五部,刘守鹤将其概括为“起兴、极峰、结局”三部:“序说就是起头,结末就是结局,危机就是形成剧情结构中心的极峰,纠葛是从起头到极峰之路,释明是从极峰向结局之路。”[5]21此种结构是中国戏曲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做出的一致的选择,焦菊隐在中国剧协举办的第一期话剧作者学习创作研究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概括为“豹头、熊腰、凤尾”,更能够说明戏曲结构的特征。
豹头。写戏,开头要像豹头,即“提出的问题和事件,总是很单一、很醒目,或者很惊人的,使观众一下子就能懂得。但是,以后的发展,却要变幻莫测,既有这样变化的可能,也有那样变化的可能,向观众提出悬念,使他们一下子就被抓住。从一开头就要随时设下伏笔,才能叫单一的问题,贯串到底。”[5]119《锦衣》的开头部分,着重描绘了春莲被父亲贱卖的情形,以此作为全剧发展的开头,之后的剧情就围绕着春莲的命运展开。为了使这一问题单一、醒目,作者并未安排较多的人物登场,麻木潦倒的宋老三、虚情假意的小商贩,勾画出世道险恶、人心不古,春莲之后的命运可见一般。
豹头除了要单一、醒目之外,还要尽量设置悬念,吸引观众的兴趣。作者并不把故事中蕴含的鲜明态度直接表现出来,“而让生动的故事去吸引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加强作者与观众之间的交流,使观众在故事中、或者在人物的行为中产生悬念。悬念越多,观众对于舞台上的生活和人物的命运便越关心,对于事件的每一过程便越提起精神来观察、思考、分析、判断,对于戏剧便越感兴趣。”[5]125《锦衣》在第一折有限的篇幅中,设置了一些悬念:春莲被卖给了谁,之后的命运怎样,季星官和春莲还会不会有交集,秦兴邦和季星官的革命能否成功……以此来调动观众对剧情的关注。
熊腰。剧情发展到中部,情节开始错综复杂起来,“这时,需要集中笔力塑造人物性格,需要细致地编织情节和线索,也需要妥当地陪衬旁枝细节,使剧本变得充实饱满,粗壮有力,有如熊腰。”[5]119剧本的中间部分,是整个戏曲的主体,人物命运的走向在此尽情展现。随着剧中人物的一一登场,以春莲的命运发展与清政府抓捕革命党的两条线索,相互交织,构成严密的情节网络。一边是季王氏在王婆王豹的威逼利诱下接受了儿媳,春莲被设计抱着公鸡加入季家,从被婆婆压迫、被庄雄才调戏的悲情,到与季星官幽会、情投意合,以春莲命运和公鸡变人的传奇故事结合的主线层层发展。另一边,季星官巧设谋略,借家中暗道制作炸药,秘密策划暴动。剧情紧凑,张弛有度,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叙述技巧。
随着两条线索的发展,剧中的人物一一登场。其中,矛盾冲突的正方始终是春莲,而随着反方的频转,人物矛盾层层激化,以此展现了广阔的人物画卷。如果说在开头部分,作者还有所保留,那么在熊腰部分,作者除了编织故事情节,最主要的就是塑造人物。人物的性格是故事情节有力的推动力量,使剧情合理有序地向前发展。
凤尾。“全剧由单一线索发展到错综复杂的主干之后,到了结束的时候,又需要回到条理清楚、问题单一的路子上来,有如凤尾用少数修长而有力的漂亮羽毛,把周身的斑彩衬托得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5]119-120剧本最后的“聚歼群丑”,既为“公鸡化人”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也用出人意料的手法,点出了季星官巧施谋略,披一件彩光闪烁的锦衣亮相,借公鸡的形象,完成了革命党身份的掩护,完成了革命的任务。文章讲究前后呼应,戏曲也是一样,剧本开头介绍的两条线索,在结尾部分,都有了很好的结局。而结尾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在于豹头与熊腰是否充实,有无安排合理的戏剧冲突和耐人寻味的伏笔。当众人都在关注公鸡变人的传奇故事时,革命党攻入了县城,作者借王豹之口点出了季星官的计谋:“老爷,您还没看明白啊?他们演了一场公鸡变人的苦情戏,吸引了您和少爷的洋枪队,然后,县城里的革命党便乘虚攻进了县衙。”[4]38至此,观众才恍然大悟,季星官借家中暗道的隐藏也有了很好的交代。
《锦衣》在情节结构上,严格按照传统戏曲“豹头、熊腰、凤尾”的要求,各部分功能突出,而又配合紧密,显示了莫言对传统戏曲结构模式化的借鉴吸收,同时加入的公鸡变人的传奇故事也使剧本更具民间魅力。
三、语言的抒情性
与西方戏剧重叙事不同,中国戏剧的本质特征在于抒情性,抒情性是中国戏曲的固有传统和规律,“先秦时期提出的物感说和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说,是戏曲和戏曲文学具有抒情性的根本原因。这种对我国文学艺术起着巨大影响的传统美学思想,使得我国的戏剧样式沿着以诗歌、音乐、舞蹈为主的综合形式发展,最后在宋、金、元时期形成熔唱、念、做、打于一炉的独特戏曲形式,并在艺术表现上显示出重情感感受和重情感抒发的特点。”[5]170“唱”即歌唱,“念”指念白,“做”是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为武术和翻跌的技艺。其中,供以歌唱的唱词,承载了戏曲更多的抒情性功能。
不同于话剧中用人物念白构成的对话来展现故事情节,戏曲中人物表情达意的方式有念白和唱词,富有音乐性的唱词建立在中国传统诗词的基础上,在句式、平仄、押韵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茂腔的唱词比较灵活,有规则的七字句、十字句,为了表情达意的需要,还会临时变换为六字句、八字句等,形成混合句。如:
我与神鸡成婚配,(七字句)
方圆百里人皆知。(七字句)
神鸡即是我的夫,(七字句)
季公子就是那神鸡。(八字句)
我与公子同床睡,(七字句)
合人性,顺天理。(六字句)
谁要你们管闲事。[4]38(七字句)
既从整体上遵循了七字句的格式,又能根据情境灵活调整,更好地表达人物情感。作为戏曲文体的一次尝试,《锦衣》并未完全遵守茂腔唱词的要求,而是比较自由,以使人物更好地表达情感。
从抒情的方式来看,有直接抒情、间接抒情,间接抒情即借景抒情,叙事抒情。一些评论者将戏曲称作“剧诗”,即主要从戏曲能够使用不同的抒情方式表情达意来说的。
直接抒情多是剧中人在对话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如第一场“桥头卖莲”的情节,宋老三与春莲的对话不仅介绍了人物的身份来历,也通过直接对话表达了春莲对父亲的失望和宋老三的自私麻木。第十二场“两情缱绻”中,春莲与季星官互诉衷情,唱词使两个人的情感抒发达到了制高点。第十三场中,面对知县无理的判决要求,季星官和春莲更是表达了对彼此的忠贞与坚定:
季星官 既然知县做判词,我即刻变化赴火死。鞭打我妻无公理,可怜她弱女子屡被人欺。娘子啊,我死后你要多保重,不要垂泪犯相思。等待金凤传捷报,城头变换汉字旗。我会夜夜来入你的梦,再续鸳盟赴佳期。
春莲 郎君啊!我不想苟且偷生让你变异类,你且莫将锦衣身上披。你是堂堂正正奇男子,我与你心相印,情相依。相爱相知,一夜良辰,早胜人间千百日。[4] 38
季星官为保护春莲,宁愿自己投火赴死,春莲为捍卫两人的爱情,夺过锦衣投入火中。两人的情感真挚感人,令人动容。
间接抒情即借景抒情、借事抒情。“借景抒情的手法运用于戏曲文学,经过戏剧化,演变为戏剧诗人运用诗的语言,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描写剧中人对周围景物的感受,以抒发剧中人的思想感情。”[5]171《牡丹亭》中杜丽娘游园之后留下了千古绝唱。《锦衣》第五场春莲与公鸡拜堂后,独坐洞房,三更鼓响,春莲仍未入睡,面对凄清寂寞的寒夜,春莲不仅感慨:“人声静更鼓响夜已过半,洞房中清冷冷脚生寒、自古道红颜多薄命,普天下薄命人数我春莲。自揭开盖头布定睛细看,不由我鼻发酸泪如涌泉。只有这笼中鸡与我为伴,洞房中无人气我形只影单。”[4]20也是身处荒凉之夜的春莲由环境生发的对自己命运的感慨。“借事抒情的手法运用于戏曲文学,经过戏剧化,演变为戏剧诗人运用诗的语言,通过描写剧中人在特定戏剧情境中对特定事件的反应,抒发了剧中人的思想感情。”[5]172《锦衣》主要运用的就是借事抒情。面对刘四无赖的欺压,季王氏新寡后对丈夫的埋怨、对儿子的期盼,春莲挑盐时得到挑担夫妇的帮助后,对夫妻生活的羡慕、对自身孤独的感慨,都属此类。
唱词是戏曲语言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人物对话或内心独白来表达人物心声,并用歌唱的方式抒发人物的情感,由此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具有悠久的抒情传统。抒情性也是中国戏曲永保魅力,不能被西方话剧取代的重要因素。
四、主题的寓言性
寓言性是中国戏剧特有的传统。刘汉光从戏剧的起源出发,认为中国戏剧发端于上古巫术宗教祭祀中的乐、乐舞,两者都采用了问答体的体式。在巫史文化的兴替中,寓言的形象层面,即寓言的寓体,更多地借鉴了巫官文化的内容,多为谬悠之说,后逐步扩大到现实题材。寓言的意味层面,即寓言的寓意,建立在形象层面的基础上,寓言荒谬幻想的形象特征,体现着现实的象征性、批判性。戏剧的寓言性也就意味着,作者对来源于生活的题材进行虚构、改造,从而传达出主体的主观态度。中国戏曲所演的大多是已成之事,由此,寄寓于情节中的人生观念、思想哲理才是剧本的关键。
《锦衣》取材于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历史传奇和公鸡变人的鬼怪故事,带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色彩。莫言称其为“亦真亦幻之警世文本”,其寓言性在于用取材于民间的故事,反映民众的生活和心理,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乱世丑态的揭露。《锦衣》发生在清朝末年,但作者并没有着力关注国家伦理与民族矛盾的激烈碰撞,而是将舞台放置在高密东北乡小县城的一隅,借普通百姓的生活展示广阔的社会面貌。季星官等人策划暴动一直作为故事的暗线,并未被莫言倾注较多笔墨,而县城的大众生活才是作者描绘的重点。以庄有理、庄雄才为首的统治者卖官鬻爵、横行乡里,衙役为虎作伥,百姓卖女求财,社会的混乱不堪可见一般。莫言尤擅细节描写,王婆撞破春莲和季星官的约会后,明知是件缺德事,还要跑去报信:“我干吗自己拷问自己?这世上比我坏的人多了去啦,大家不都假模假样有滋有味地活着吗?”[4]35面对这个虚情假意的世界,革命本是唯一的希望,但王豹等人转投革命又用寥寥几笔消解了革命的意义和希望。
对人间真情的赞美。“公鸡有情变成人,人若无情变公鸡”[4]39,在“有情”的统领下,全剧弥漫着对人间真情的赞美。莫言用戏剧手法,塑造了一个“一朵芙蓉头上戴,锦衣不用剪刀裁。果然是个英雄汉,一唱千门万户开”[4]6的锦衣形象。公鸡外形潇洒,勤勉务实,在农村的劳动活动中,更具备着晨起报时的功能。在民间故事中,人们多对公鸡持赞扬、喜爱的态度。莫言有意将剧中的公鸡塑造成“神鸡”,它是顺发盐铺的守护神,在男性角色缺失的情况下,是寡居的季王氏和春莲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它又是春莲拜堂成亲的对象,是春莲丈夫般的存在。在春莲受到伤害时,总是英勇抵挡。反观剧中出现的另外两种动物鹰和狗,作为庄雄才跟班的登场,却是作者否定的对象。王婆用“鹰眼狗鼻子”点出了衙役们的“职业素养”,但由庄雄才、衙役、鹰、狗一行组成的队列,浩浩荡荡,却是用鹰和犬对付春莲这个弱女子。而无论是本能翱翔千里的鹰,还是身形比鸡大很多的狗,在公鸡面前都败下阵来。公鸡的朝夕陪伴感动了春莲,因此春莲爱上了公鸡幻化的季京,而拒绝与自己毫无交集的季星官:“我是鸡精的娘子……你是革命党的首领”[4]39。脱去锦衣的季星官并未获得春莲的认同,自此,有情与无情的界限如此分明。
对光明美好的向往。无论是锦衣“一唱千门万户开”的寓意,还是季星官、秦兴邦想要推翻清朝统治,“一把火来照亮前程”的豪气,都寄予了民间百姓渴望光明美好的愿望。故事中的清朝末年的高密东北乡不过是一个虚拟的时空,而普通百姓的生活却具有普遍意义。无论是何时代、何种地方,深沉的压迫必定会激起人们的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作者在剧本的最后,起义军攻进县城时,又加入了王豹等人投机混入革命党的闹剧,但革命党为了人民的美好未来而奋斗的贡献却是不容抹去的。春莲、季星官身上勤劳善良、敢作敢为的优秀品质,正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努力奋斗中凝聚的精神内力,这种力量不会消失,人民向往的光明美好也终将实现。
民间文化一直是作家创作的重要源泉,但真正做到深入借鉴民间艺术形式的作品却是少之又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言的《锦衣》对山东茂腔的借鉴尝试无疑是珍贵的。莫言以其创作实践践行了他“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宣言,在这里,现实与童话、真实与虚假、梦幻与现实轮番上演,显示着民间世界的丰盈与复杂。戏曲创作是莫言的首次尝试,传统与民间的融合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多种可能的莫言。
参考文献:
[1]莫言.檀香刑[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徐健.莫言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剧作家的“野心”与“匠心”[N].文艺报,2017-9-11(3).
[3]赵红梅,李焕顺.论戏剧冲突[J].职大学报,2005(1):56-58.
[4]莫言.锦衣[J].人民文学,2017(9):4-39.
[5]李小菊.戏曲文学研究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
[6]莫言.莫言演讲新篇[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