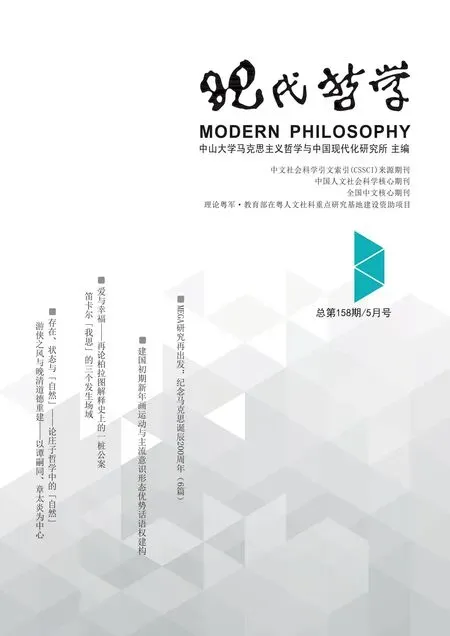游侠之风与晚清道德重建
——以谭嗣同、章太炎为中心
吕存凯
根据相关研究,侠兴起于封建制度逐渐瓦解的春秋战国,盛行于两汉。这段历史时期的侠依赖于地域、乡党、宾客等社会基础,多为集团活动的任侠、豪侠,拥有很强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唐宋以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侠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大多变成一种以个人活动为主的“游侠”。这成为后世所理解的侠的基本形象*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20—371页。。
尽管侠在上述两个发展阶段有诸多不同,但都被目之为侠。这是因为他们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恪守其独有的道德意识,如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81页。;二是游离于政治统治之外,与政治权威处于对抗地位,如韩非所批评的“侠以武犯禁”*[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五蠹篇》,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49页。、班固所说的“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汉]班固:《汉书·游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99页。。由于第二点,游侠始终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厉打击和压制,难以进入主流话语体系,这也是汉代以后的正史中不见“游侠传”的原因。而由于第一点,游侠多以传奇形象在世俗文化中广为流传,在民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侠”自东汉起就开始突破武的领域,抽象化为一种超越精神,并首先进入儒生文士的道德意识之中*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前揭书,第379页。。因此,游侠作为一种象征性意象,在历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中绵延不绝。
对于晚清士人而言,他们所处的无疑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在提出政治革新要求的同时,也担负着道德重建的任务。在这种时代主题之下,传统的任侠/游侠*关于“任侠”与“游侠”的区别,前人多有讨论,如方以智、钱穆、余英时等都认为任侠为养士结客、为人所依附者,具有明显的社会集团性质;游侠则指单人或少数的侠客、剑客。以上诸位先生从历史考证的角度分析两者的区别,当属可信。不过,自唐宋以后,“侠”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主要成为一种个人行动,“任侠”与“游侠”不再有明显区分,因而“任”常被解释为“保任”、“放任”之意。晚清士人多用“游侠”,但谭嗣同、梁启超等也间或使用“任侠”。在晚清的语境中,将两者作同义理解应该没有问题。因此,本文主要使用“游侠”一词,但在具体行文中则随论述对象而有所变化。(参见余英时:《侠与中国文化》,前揭书,第325—327页;汪涌豪:《中国游侠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1页。)精神被重新发现并加以弘扬。晚清士人不仅著文褒奖,而且身体力行,形成一股强烈的游侠之风,对晚清的革命进程和社会道德产生极大影响。在这一风潮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谭嗣同和章太炎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学界目前对晚清游侠风潮的研究并不多见,而且尚未对谭、章二人在其中的作用予以专门关注。因此,本文将以两人的相关论述为主要考察对象,尝试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风潮进行探究。
此外,在以往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中,谭嗣同与章太炎一般被认为分属改良派和革命派,或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因而显示出较大的差别;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两人在行为和思想上的相似之处。就笔者所见,仅有张灏先生曾关注谭、章思想的相似性*张灏先生指出,谭嗣同与章太炎的世界观同样具有“无我同一”的精神性主题。参见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8—262页。。然而,谭、章二人的相近不仅体现在思想方面,而且体现在对于晚清士风的表率和引领方面。因此,本文效颦汪荣祖先生的“康章合论”,进行“谭章合论”的初步尝试。
一、学术与政治:游侠形象的重塑
游侠虽然多以急公好义、锄强扶弱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印象中,但也有“以躯借交报仇”的一面。换言之,他们虽然有其固持的道德标准,但多是与个人恩怨相关的私德,未必与晚清的时代主题自觉相符。另一方面,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对立面。这种对抗性格当然与晚清激进人士的目标有一致之处,但如何规范其狂放不羁的性格、将其引导到政治变革的轨道上,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游侠尽管在民间影响广泛,但并非一个有着明确界定的政治或学术派别,因而始终被摒除在传统学术主流之外。如何改变其在学术史上少人问津的边缘地位,重新引起士人的关注,也需要有所发明。
在晚清思想史上,谭嗣同并非最早表彰游侠的思想家*郑观应是较早表彰任侠精神的思想家。他曾仿前人《剑侠传》而辑录《续剑侠传》一书,与原书合刊于世。其序言曰:“余悯世宙之迍邅,慕仙人之神妙,而剑侠一流于今为宜于用为切。苟有其人,何患乎异端,何虑乎强敌!”提倡以剑侠用世。参见汪涌豪:《中国游侠史》,前揭书,第152页。,但或许是影响最大的一位。在其著作《仁学》的“自叙”中,他明确提到游侠,认为其源出于墨家之一派:“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谭嗣同:《仁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9页。以任侠出于墨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墨家“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担当意识和“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无畏精神,与任侠颇为相像。这让谭嗣同倾心不已,并以墨子“摩顶放踵之志”自任。
任侠的精神,被谭嗣同概括为“仁”。表面上看,他所提倡的任侠之风的根本精神与传统任侠相同,即仁(义)。不过,他对“仁”的内涵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在谭嗣同这里,“仁”的价值追求背后是他的“以太-仁-通”的宇宙论,“仁”是宇宙根本精神的体现。具体到伦理原则方面,“仁”并非传统儒家的主流观点强调的“爱有差等”,而是以墨家“兼爱”以及理学中“万物一体”思想为内涵的无差别的普遍之爱。以这种无差等之爱为前提标准,尊卑等级分明的“三纲五伦”遭到严厉批判,取而代之的是以“朋友”原则为核心的、以自由平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伦理规范。
在传统的“三纲五伦”中,君臣关系是最不平等的一种。在谭嗣同看来,“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337页。。因此,他寻求一种激烈的政治变革方式来改变君主专制的局面,而以“仁”为己任的游侠无疑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西汉之“内和外威”与日本之变法自强,都与游侠风俗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中国当时所处的乱世中,也应该提倡游侠,从而提振民气,倡导和培养一种勇敢无畏的社会道德,进而“鼓更化之机”,为反抗君权、伸张民权准备社会基础。
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西汉民情易上达而守令莫敢肆,匈奴数犯边而终驱之于漠北,内和外威,号称一治。彼吏士之顾忌者谁欤?未必非游侠之力也。与中国至近而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其变法自强之效,亦由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之气概,出而鼓更化之机也。儒者轻诋游侠,比之匪人,乌知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言治者不可不察也。*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334页。
可见,谭嗣同所提倡的任侠,与传统游侠形象相比有很大转变。游侠所从事的不再是局限于私德私恩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改变世风士气甚至世运国运密切相关的公共行为。将狂放不羁的游侠作为“拨乱之具”,实际上是将私德“收编”进公德之中。古代游侠的道德水准和政治主张不一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谭嗣同所提倡的游侠精神与反对君权、伸张民权的政治理念直接相关联,与近代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根本趋势相符合,其行为就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因而,游侠成为挽救衰世、革新政治的重要手段。
谭嗣同对游侠形象的重塑,在章太炎的《儒侠》一文*《儒侠》主要有三个版本,分别收于《訄书》的初刻本、重订本以及《检论》,均收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三个版本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没有大的改变。本文以《訄书》重订本的《儒侠》为主要文本。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呼应*《儒侠》最早发表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实学报》第四册,之前尚有《后圣》《儒道》《儒兵》《儒法》《儒墨》诸篇,共同构成章太炎对先秦学术史的梳理。值得留意的是,章氏1897年任职《强学报》时,曾因宋恕得见谭嗣同《仁学》手稿,但认为其“怪其杂糅,不甚许也”。章氏早期文章颇有回应谭嗣同之意,最明显者为发表于1899年的《儒术真论》及《视天说》《菌说》等。其作《儒侠》,或许也有回应谭嗣同《仁学》之意。(参见《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光绪二十三年”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页。)。与《仁学》认为游侠出于墨家不同,《儒侠》开篇便明确指出游侠出于儒家:“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根据《韩非子·显学》的记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一派为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显学》,前揭书,第458页。章氏《儒侠》也引用该文作为论据。其坚忍仗义与游侠颇为契合。章太炎提出“侠出于儒”之说,将游侠与儒家联系起来,其目的一方面是要以游侠的尚武精神弥补儒家重文轻武的不足,改变儒家的柔弱形象;另一方面是要以儒家扶危拯溺、心系天下的忧患意识引导和规范游侠放纵不羁的性格,将其纳入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中*如他说:“然则任侠岂异于儒哉!独其睚眥报仇为非,以儒兼侠,自无逾轨之事矣。”(章太炎:《菿汉三言·菿汉昌言》,上海:上海书店,2011年,第102页。)。因此,他指出游侠立身行事的原则与儒者“杀身成仁”、“除国之大害,捍国之大患”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那些为国奔走、乃至舍生取义的大侠往往也是大儒。
从学术史看,“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摈之”*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儒侠》,《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始终被排除在传统的学术派别之外。在现实中,游侠则发挥着重要作用:“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同上,第140页。章太炎将游侠分为两大类:一是所谓“大侠”,如侯生、北郭子以及平原君、信陵君等人,他们利及朝野,为国之辅弼,是当之无愧的“侠士”;二是“击刺之萌”,即聂政、荆轲等刺客之流,章太炎高度评价“击刺者,当乱世之时,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同上,第141页。。当乱世可以击杀暴虐百姓的统治者,以灭除天下之弊,“为国民发愤”;当治世之时,若法律无法对奸邪之徒施行应有的惩罚,则需要侠客采取行动,维护社会正义。尽管《儒侠》是一篇学术史论文,但显然是借此呼唤一种“以儒兼侠”的儒侠人格的出现。
为提倡“儒侠”,章太炎特别表彰《礼记·儒行》篇,认为该篇所载十五儒“皆刚毅特立者”。直到晚年,他仍不遗余力加以提倡,指出其中“大氐坚苦卓绝、奋厉慷慨之士”*章太炎:《〈儒行〉大意》,原载《国学商兑》1933年第1卷第1期;参见章太炎讲演,诸祖耿、王謇、王乘六等记录:《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页。“皆以气节为尚”*章太炎:《国学之统宗》,原载《制言》月刊第54期,前揭书,第1页。,甚至提出将其作为“新四书”之一以教人。这不仅有改变“侠者无书,不得附九流”的边缘地位之意,更重要的是在近代危局中,以之作为儒侠人格的典范,对治当时道德堕废、民气不振的现实局面。故而,他明确表示“救弊之道,必以儒侠相附”*章太炎:《菿汉三言·菿汉昌言》,前揭书,第103页。“今日宜格外阐扬者,曰以儒兼侠。故鄙人近日独提倡《儒行》一篇”*章太炎:《与张季鸾》,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58页。。
当然,就实际历史情况而言,无论认为游侠起源于墨家还是儒家,都是不够准确的。根据现有研究,游侠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游侠的精神与儒家、墨家乃至道家都有相通之处,但并不能由此得出游侠起源于某个学派的结论。*参见彭卫:《游侠与汉代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页。不过,谭嗣同、章太炎立论的主要目的,不是从学术角度探讨游侠的学派归属,而是以学术史为方法,将数千年来为正史和各学派摈弃不载的游侠重新纳入主流视野之内,通过阐发和提倡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以此作为重建道德、革新政治的重要手段。在这一重新阐发中,狂放不羁、纵情任性的游侠被吸纳和整合到救治国家、人民这一整体目标之中,与政治和社会变革建立起明确关联,借助其仗剑行侠的破坏作用,为推翻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建设一种新的制度准备必要条件。
二、作为刺客的游侠:晚清的暗杀风潮
在人类历史上,暗杀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长期存在。大致而言,刺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刺客为职业者,或是权贵政客所豢养之死士,或是为金钱利禄而奔走之杀手,其行事完全依照主人或雇主之要求,并不区分善恶对错,没有独立的道德操守和主体意识;另一类则如《史记·刺客列传》所载诸人,往往特立独行,无所倚傍,有其所坚持的道德准则,或为国事,或报恩仇,无论其行为本身如何,皆有合于道德者。这两类刺客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往往判若云泥。因此,就实而言,游侠与刺客不能等同视之。司马迁在《史记》中虽然对二者均有所褒奖,但分立两传,正是由于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从道德角度来看,游侠与上述第二类刺客又有不少相似之处。实际上,游侠为抵抗强权,往往会击杀政治人物,以振奋人心、救国救民,此时游侠就同时具有刺客的身份。章太炎在《儒侠》中所举的聂政、荆轲等“击刺之萌”,就是典型的作为刺客的游侠。
在晚清的政治变局中,有一股强劲的暗杀风潮,在很大程度上与游侠精神相关联。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在所引《仁学》段落的“任侠”二字之后自注曰“暗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页。。这一细节透露出刺客与游侠的结合在晚清社会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晚清的暗杀事件,相当一部分为革命派人士所为。据学者统计,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和暗杀预谋不下五十余起*参见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78页。。一般认为,晚清革命派的暗杀风潮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为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活动,二为中国传统的游侠刺客刺杀统治者的行为*参见戴学稷:《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暗杀活动》,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选(1949-1979)》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518页。。就第二点而言,当时的革命派曾公开呼唤“游侠魂”,并宣言“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壮游:《国民新灵魂》,原载《江苏》第五期,1903年8月;参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574页。,明确将暗杀与游侠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派的暗杀活动与谭嗣同、章太炎等人对游侠精神的褒奖实有相互呼应之效果,从而共同推动了这一激进风潮。
以晚清两起著名的革命派暗杀事件为例。1905年9月,吴樾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谋炸准备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事败而死。1907年4月,《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刊载其遗书。在其遗书《暗杀时代》的“暗杀主义”一节中,吴樾开篇就直接引用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倡游侠的文字,为其所提倡的暗杀主义张目:
谭嗣同有言曰:“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又曰:“困于君权之世,非此益无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败。”至哉言乎!可谓明于时事者矣。*吴樾:《吴樾遗书·暗杀主义》,《民报》临时增刊《天讨》,1907年4月25日,《吴樾遗书》第8页。
谭嗣同虽然并未明确提到刺客或暗杀,但他所提倡的任侠精神实已暗含此意。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戊戌政变时拒绝出走,甘愿以死明志,并倡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546页。可以说,谭嗣同的主动就义对于当时的士人产生了笼罩性的道德感召力,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为其理想信念而献身*谭嗣同的就义不仅深深震撼了康、梁、唐(才常)等人,而且对革命青年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邹容曾题谭嗣同遗像曰:“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也称赞谭嗣同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他的影响超越了后来形成的保皇派与革命派的对立,成为不同政治派别人士共同推崇的志士。1903年《苏报》案之后,邹容、章太炎成为革命派志士的新代表,此后更是接连涌现出各种烈士人物,但谭嗣同的影响并未因此衰退。1910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章谭合钞》,辑录章太炎和谭嗣同两人的部分著作,合为一集,体现出时人对谭的评价。谭嗣同之死所造成的影响,参见李喜所:《谭嗣同评传》第8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82—296页。。正如梁启超所说,他是“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梁启超:《仁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372页。。吴樾引用其文字作为暗杀主义的证明,并非无由。
此外,吴樾给素昧平生、当时正因《苏报》案而身陷囹圄的章太炎写信,表达仰慕之情,申言自己愿“死此不自由”以为诀别*吴樾:《吴樾遗书·与章太炎书》,《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吴樾遗书》第28—30页。。我们不能确定吴樾是否读过《儒侠》一文,但章太炎、邹容在《苏报》案时主动投狱、欲以死鼓动革命之“尚侠轻生”的无畏精神,无疑激励了包括吴樾在内的诸多青年,二人的道德高度一时无两,不逊于戊戌殉难的谭嗣同,成为革命青年新的道德楷模。这从章太炎出狱东渡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的盛况可见一斑*《民报》第六号刊载民意《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记载了当时的盛况:“章枚叔先生于六月二十九日出狱,即夜偕本报社特派员二人东渡。留学生闻之,乃于七月十五日,为会于神田锦町锦辉馆,以欢迎之。是日至者二千人。时方雨,款门者众,不得遽入,咸植立雨中,无惰容。迨九时许,先生至,人人致其诚款。先生居狱中三年矣,社会情状,无足慰者。与先生同入狱者,有邹君容,今恫不可复见,惟能致爱于先生。且吾人托足异国,始得为会于此,若在内地,将并此不能。此情尤足念也。”(参见《民报》第六号,1906年7月25日,第119页。)。
又如,1907年7月,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并发动起义,旋即失败被杀。章太炎在同年10月所作《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中将他们比作古代击杀人主的刺客:
专诸、聂政,死二千年。刺客之《传》,郁堙弗宣。泰山有士,曰张文祥。睚眦报仇,新贻是创。期死虽勇,未登明堂……韩良狙击,乃中副车。豫让漆身,杇刀割虚。渐离矐目,庆卿断股。剑术粗确,卒何云补?未若君曹,风行霆举。铅丸部发,踣僵胡虏。二十一代,勇夫消沮。剥床斯复,今乎反古。浙虽海滨,实兴项楚。其亡其亡,系于三户。谁云黄鹄,谶书无语?呜呼,哀哉!尚飨。*章太炎:《祭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文》,《民报》第十七号,1907年10月25日,第117—118页。
章太炎以豪健之笔,高度赞扬了四人的行为。他不仅称赞徐锡麟等人暗杀成功,较之历史上大多数刺客为善,而且将他们视为湮灭二千余年的刺客精神的复兴。祭文结尾更提到秦末项氏一族起兵反秦的历史事件,将他们的暗杀行为与排满兴汉的民族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其足以作为满清覆亡的先声与标志。以章太炎的文笔所具有的感染力与影响力,他对徐锡麟等人的颂扬无疑会进一步激励知识青年投入到革命与暗杀的事业之中。
之所以晚清的革命者以暗杀相号召能群起响应,蔚然成为一股特异之风潮,原因在于他们将暗杀作为革命的一种手段。如当时蔡元培、宋教仁等著文宣称,革命之道有二:一为暗杀,一为暴动*参见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前揭书,第768页。。由于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异族政府,拯救国家民族,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暗杀作为“革命之道”自然成为一种道德的行为。这与经过谭嗣同、章太炎阐发的游侠精神,无论在为国为民的道德方面,还是在激烈破坏的行为方面,都是相一致的。
需注意的是,从事暗杀活动的革命者大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而非专业刺客。上文提到的吴樾、徐锡麟都是当时积极办学、办报的新型知识分子,具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思想主张,与蔡元培、陈独秀、刘师培等都是当时“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成员。这些人的暗杀知识往往只是通过非专业的训练获得,因此行动多以失败告终。但这不仅没有吓退后来者,反而感召了更多志士前赴后继地投入暗杀和革命中,形成一种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的循环。在晚清的时代语境下,作为刺客的游侠被赋予强烈的道德性,造成了这一轰轰烈烈的时代风潮,不仅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且成就了个人精神的光辉。由本节的分析可见,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谭嗣同和章太炎实际上早已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对当时的士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开启并推进了这一潮流。
三、生死与道德:生死观的重建
有学者指出,在对游侠的诸多赞美中,“最令晚清志士倾心的,其实是其‘尚侠轻生’(译成儒家语言是‘杀身成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的确,崇拜流血、渴望牺牲,这种烈士诉求在晚清志士中是普遍存在的心态。怀生畏死本是人之常情,晚清志士却纷纷视死如归。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不仅是“舍生取义”的传统信念在晚清时代的彰显;在谭、章等人那里,还指向了一种新的生死观。
谭嗣同的英勇就义成为他短暂一生中最为光辉的时刻,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烈士传统。对他而言,主动就义行为的背后有一种并不复杂但很明确的生死观作为理论依据。在《仁学》所阐发的世界观中,以太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其本身是不生不灭的。谭嗣同将张载、王夫之的“气一元论”嫁接到近代自然科学的物质学说,指出物质界的一切生灭现都只是以太之聚散,并非真正的生灭。同理,生死现象也是如此。他将个体生命分为体魄和灵魂两部分,并指出:
匪直其精灵然也,即体魄之至粗,为筋骨血肉之属……皆用天地固有之质点粘合而成人。及其既敝而散,仍各还其质点之故,复他有所粘合而成新人新物。生固非生,灭亦非灭。又况体魄中之精灵,固无从睹其生灭者乎。*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308页。
谭嗣同虽然兼论体魄与灵魂,但其重点显然是后者。他指出灵魂“自无始来,死生流转,曾无休息”*同上,第312页。,乃是不生不灭的。他还从孔、佛、耶各家学说中寻找证据,如耶教之“灵魂”、“永生”,佛教之“轮回”,孔教之“原始反终”、“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等。在他看来,灵魂而非体魄才是生命的本质。于是,克服死亡恐惧的方式获得新的哲学论证:死亡之所以不再可怕,不仅由于名节比生命更有价值,可以通过名垂青史的方式实现不朽;更重要的是,肉体虽灭,灵魂却不会消亡,死亡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对灵魂的强调,一方面是为了破除世人好生恶死的瞢惑之见:既然灵魂不死,仍有来世,则既可以促使人们心生敬畏、改过迁善,又可以克服畏死心理,激励人们成仁取义:
今使灵魂之说明,虽至誾者犹知死后有莫大之事,及无穷之苦乐,必不于生前之暂苦暂乐而生贪着、厌离之想。知天堂地狱,森列于心目,必不敢欺饰放纵,将日迁善以自兢惕。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亹亹。*同上,第309页。
另一方面,灵魂可以超越时空与个体生命的限制,实现普遍的感通,这是以太“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体现。因此,谭嗣同极为推崇墨家之兼爱,认为“惟兼爱一语为能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墨学中之最合以太者也”*同上,第312页。。由此推论,个体并非局限于体魄躯壳中的“小我”,在“万物一体”的普遍感通中,无一物非我。于是,不以“我之一身”为可私可爱,有我之见得以破除,从而能够“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以行吾心之所安”*梁启超:《仁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373页。。正如他自述其志曰:“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谭嗣同:《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290页。梁启超阐扬其亡友之精神曰“大仁之极,而大勇生焉”*梁启超:《仁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前揭书,第373页。,可谓最为精准凝练的写照。谭嗣同对生死的理解,实际上可以引申出克服小我之私、成就大我之公的含义。此后,梁启超按照这一理路更为明确地阐发出“无我以建立群体”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苏报》案中,章太炎坐以待捕,其本意是要主动流血牺牲、为革命造势。他自陈道:“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4页。另据记载,章太炎当时还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0页。章氏的引颈待戮与谭嗣同的主动就义形成时代呼应。不过,他当时或许仅是激于“致命遂志”之心,对生死问题未必有深入思考。而经过狱中研读佛典的思想转变期,章氏试图诉诸佛教学说解决生死问题与道德问题。
章太炎在出狱东渡后,提倡一种革命道德。所谓革命道德,“不必甚深言之”,就是“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章太炎:《革命道德说》,《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7页。,是“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四)》,前揭书,第375页。。这正是他所提倡的儒侠精神。这种革命道德的培养,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宗教的力量。他所采用的宗教,是在华严、法相二宗的基础上改造过的佛教:“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前揭书,第274页。华严宗的宗教实践,可以让人们树立普度众生的理想信念;而法相宗的“万法唯心”之说,可以让人们破除对一切外在之物的执着,树立无所依傍、自尊无畏的精神。这种“依自不依他”与“普度众生”的宗教精神,与革命事业的需要正相符合。
法相之理与华严之行的结合,是章太炎东渡之初为革命道德寻找到的宗教和哲学依据。此后,他进一步以唯识学贯通这两个方面,具有更强的理论色彩。他指出,真正的“自我”,就是唯识学所讲的阿赖耶识,“我为幻有,而阿赖耶识为真”*章太炎:《人无我论》,《章太炎全集(四)》,前揭书,第427页。。常人所执之我,是末那识执持阿赖耶识而生起之“幻有”,并非真实之我。从根本上讲,“无我”(无生)才是真相,好生恶死之心是对幻我的虚妄执着。章太炎的目的很明确:“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四)》,前揭书,第418页。即要以唯识宗教破除人们的畏死之心,提振社会道德特别是革命者的无畏精神。
另一方面,章太炎所确立的自我并非一己之小我,而是真正之大我。按照他的理解,阿赖耶识并非局限于个体,而是“普遍众生,惟一不二”*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四)》,前揭书,第415页。的。这与“灵魂”有根本不同:“阿赖耶识为情界、器界之本,非局限于一人,后由末那执着,乃成我相。而灵魂乃个人所独有,此其分齐绝殊,不得无辨。”*章太炎:《人无我论》,《章太炎全集(四)》,前揭书,第427页。由于阿赖耶识的普遍性,自我与他者之间得以建立本质的关联,“不以一己为我,而以众生为我”;因此,“以众生同此阿赖耶识,故立大誓愿,尽欲度脱等众生界,不限劫数,尽于未来”。章太炎将度脱众生的行为划分为不同层次,最高者是“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其教以证得涅槃为的”,其次是“财施无畏施等,亦与任侠、宋、墨所为不异,乃有自舍头目脑髓以供众啖者”*章太炎:《建立宗教论》,《章太炎全集(四)》,前揭书,第415—416页。。这种利他的宗教精神落实在世俗生活中,就是他大力提倡的革命道德。
从谭、章二人所阐发的生死观来看,近代以来对生死问题的探讨与社会道德的重建直接相关。尽管他们的言说方式和理论指向有很大不同*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章太炎以唯识学建立的“革命道德”并不能等同于谭嗣同、梁启超等所阐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章太炎所确立的“自识”之个体就是价值本身,因此他强烈反对“以社会抑制个人”的“公理”。关于梁启超和章太炎生死观的区别,参见张志强:《生死·道德·革命——晚清“志士”理想中的个体、社会与道德》,《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18—27页。,但其核心关切是根本一致的:一方面,破除人们对生死的执着,培养勇猛无畏的敢死精神;另一方面,将个体与他者建立起本质关联,使个体生命的意义与民族、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近代烈士精神的道德内涵,而传统的游侠精神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获得新的政治和道德生命力。
四、余论:治乱之间的游侠
本文以谭嗣同和章太炎的相关论述为主,讨论了晚清的游侠之风与道德重建的关系。游侠作为一种长期处于正史之外、为主流学术所排斥的社会和精神现象,在晚清这一剧烈变动的时代被重新发掘出来,成为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手段,为晚清志士所提倡和践行。因此,游侠特立独行、尚义轻生的人格形象成为中国近代烈士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直接指向一种新的生死观和道德观。谭嗣同将游侠视为君权黑暗时代的“拨乱之具”,把游侠的破坏作用收束于挽救国家、民族的政治图景之中。章太炎同样将游侠作为“天下有亟事”之时变革社会的重要选择。这是晚清志士的普遍认同,但却未必完全符合游侠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状态。纵观历史,游侠大多活跃于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之际,在政治与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的时代则沉寂无闻。某些游侠或许会被统治者收编,但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其本质正是作为政治权威对立面的社会存在。因此,历代统治者在开创之际多会借助游侠之力,但在夺取政权、建立统治之后总会采取各种措施对他们进行打击。
在认识到这种历史规律的前提下,章太炎在褒奖游侠“当乱世则辅民”的同时又提出其“当治世则辅法”的作用,就是需要我们有所关注的。如他所言,在政治清明时代,刑罚往往偏轻,这很容易使某些奸狡之徒逃脱法律的制裁;此时,以游侠对其施行惩罚,能补充法律的不足,使正义得到伸张。章太炎显然希望为游侠在“治世”的存在寻找正当性,但难免有些一厢情愿。法律作为国家实行统治的暴力工具,是一种绝对的、排他性的权力;而游侠往往按照其所秉持的最直接明了的正义观念而行动。无论游侠的行为是否真的符合正义,其“冒法抵禁”的行为都在事实上侵犯了国家权力的排他性,这是任何政治统治都无法容忍的。从国家的立场看,如果任由人们按照自己的正义观念各行其是,政治和社会秩序必然会陷入严重混乱;因此,游侠的行为并非“辅法”,而是“乱法”,是必须进行严厉打击的。章太炎特意提出这点,表明他所秉持的是一种最为直接的正义观,一如他在《复仇是非论》中所说的“洁白”的伦理*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四)》,前揭书,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