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幸福
——再论柏拉图解释史上的一桩公案
樊 黎
一、一篇论文的两个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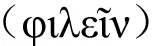
当然不会,他说。*本文使用伯奈特(J. Burnet)校勘的柏拉图文本(Platonis Opera, 5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9-1907)。译文由笔者自希腊文译成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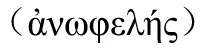
应该指出,弗拉斯托认为这一命题反映了柏拉图学说的对话依旧成立,例如他在其后考察的《理想国》和《会饮》。然而,p1并没有说明X带来的善是带给谁的善。按照弗拉斯托的论述,《吕西斯》在下文中表明(213e ff.),为人所爱的东西会把善带给爱者,正如一位医生会把病人自身的健康带给病人:“A爱B,因为B给A带来善。”(p2)如果我爱一个东西,是因为那个东西对我自己有好处。弗拉斯托由此断言,《吕西斯》对爱的论述是以自我为中心的(egoistic)。*Vlastos, “The Individual as Object of Love in Plato”, in Platonic Studies, Princeton, 1973, p.10.需要注意的是,egoism可能但并不一定导致一般意义上“自私”的行为。这里,egoism的意涵仅仅是指,行为的最终动机一定是“促进我的善”,但并不排除直接的动机是促进他人(例如朋友)的善。


与此同时,弗拉斯托还试图运用《会饮》和《斐德若》来证明他的论点。他援引《会饮》中最著名的段落:爱的阶梯(scalaamoris)。当爱者沿着爱的阶梯到达顶点时,他将看到美本身,或美的理念。“我们之前的一切辛劳都是为了这个”(210e5-6),弗拉斯托引述第俄提玛(Diotima)的说法,借以说明理念是最高的目的,或“友爱的第一对象”。
然而,之前的一切辛劳为的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因为“这个”即理念或对理念的观瞻有可能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实际上,正是在《会饮》中,最高的目的被明确地等同于幸福(204e1-205a4):
那么,她说,要是有人把问题变了一下,用“善”替换了“美”,问道:说说看,苏格拉底,欲求善的东西的人有所欲求;他欲求的是什么?
欲求[善]成为自己的,我说。
善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之后他将会拥有什么呢?
这问题倒容易回答,我说,他会幸福。
照这么看,她说,因为有了善的东西,幸福的人就是幸福的,所以,也就不需要进一步问,想要幸福的人究竟为了什么而想要幸福?问题似乎到此为止了。
的确如此,我说。
令人困惑的是,弗拉斯托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段,但仍然将理念当作爱的最高对象。无论如何,弗拉斯托通过这样一个成问题的观点,得到了他的结论:柏拉图自己关于爱的学说是以理念为中心的(ideocentric):“我们爱的是那个人身上的理念的‘影像’。我们爱一个人,当且仅当他是善的或美的……如果我们所爱的仅仅是他的德性或美,那么作为一个个体,他(她)独特和完整的个性将不会成为爱的对象。”他认定,“柏拉图理论的首要缺陷”是“它并没有提供对整个人的爱,而是对这个人身上最好的品质拼凑成的抽象形象的爱”。*Vlastos, “The Individual as Object of Love in Plato”, in Platonic Studies, Princeton, 1973, pp.30-31.
正如考斯曼(L. A. Kosman)指出的,弗拉斯托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两个不同的批评*L. A. Kosman, “Platonic Love”, in Werkmeister (ed.), Facets of Plato’s Philosophy, Van Gorcum, 1976,pp.54-55.,因为“为某人/某物自身而爱他/它”有两种含义*F. C. White, “Lo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Plato’s Phaedrus”, in Classical Quarterly 40.2, 1990, pp.398-399.。首先,为其自身之故而爱某人/某物的意思可以是,不为了某个更高的目的而爱他/它。在另一个意义上,为其自身之故而爱某人/某物的意思是,爱者关注的是被爱者的善,而非爱者自己的善。按照弗拉斯托的分析,柏拉图对话中,爱在上述两种意义上都不是为了被爱者自身而爱。这两个批评恰好对应于“为其自身之故”的两种含义:弗拉斯托一方面批评《吕西斯》中的苏格拉底从未关注将被爱者自身的幸福,即这种爱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他批评《理想国》《会饮》《斐德若》中的苏格拉底总是关注体现在被爱者身上的善或美,而非这个人本身,即这种爱以理念为中心。下面将从“理念中心论”出发,检讨弗拉斯托的两重批评。
二、理念与个体
按照弗拉斯托的解读,柏拉图的爱是对理念的爱,他的苏格拉底并不爱某个人,除非这个人体现了美或善的理念。因而弗拉斯托指责柏拉图的爱缺乏个体性。
诸多研究者曾试图为柏拉图辩护。*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L. A. Kosman, “Platonic Love”, in Werkmeister (ed.), Facets of Plato’s Philosophy, Van Gorcum; A. W. Price, “Loving Persons Platonically”, in Phronesis 26.1, 1981, pp.25-34; M. C. Nussbaum, “The Speech of Alcibiades: A Reading of the Symposium”, in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Cambridge, 1986, pp.165-199;F. C. White, “Love and the Individual in Plato’s Phaedrus”, in Classical Quarterly 40.2, 1990, pp. 396-406.一种辩护思路以普莱斯(A. W. Price)为代表,试图表明个体同理念一样是柏拉图的爱的对象。普莱斯认为,柏拉图的爱的确是以理念为中心的,但被爱者在其中并不仅仅扮演工具性的角色。对个人的爱没有“升华”为对理念的爱,也没有被后者所“扬弃”,而是与后者相容,甚至对理念的爱在某种意义上需要对个人的爱,因为“[在爱的阶梯中]上升的一个关键在于,爱者并不满足于他自己同美本身的接触(212a2),而是将他与美本身的后代生育在被爱者身上(参《斐德若》253a:‘他将这些都归功于被爱者’)。通过正确的爱恋,哲人(即爱智者)得以接近他所追寻的智慧(211b);他与被爱者分享他获得的智慧。[柏拉图]从而赞美了对个人的爱,而不是[用对理念的爱]把它取代了”。*A. W. Price, “Loving Persons Platonically”, in Phronesis 26.1, 1981, p.30.简言之,爱的阶梯的顶点包含了对个人的爱。
但这种解读是成问题的。即便我们允许不同文本间的互证,普莱斯引用的《斐德若》文本也不一定支持他的观点,而恰恰可能证明了相反的观点,即被爱者的价值仅仅在于他引发了爱者对天上的美和诸神的回忆。另一方面,按照《会饮》中的说法,观瞻美本身让爱者生育真实的德性。其中并没有提到被爱者或任何个人(211d8-212a5):
想想看,她说,要是一个人瞥见了美本身的样子,纯粹的,洁净的,不羼杂的美,不是沾染了人类的血肉、色泽和其他什么会死的傻玩意的美,而是那神圣的纯然清一的美,这人会怎样?你觉得对一个人来说,朝那边看,借助必须的手段,观瞻美本身,与它在一起,这种生活还可怜吗?难道你不觉得,只有这样,以美本身能够被观看的方式去观看它,一个人才会触及到真实而非它的影像,从而生育真实的美德而非美德的影像。
这段文本清楚地表明,最高意义上的爱人观瞻美本身,也只观瞻美本身。他不通过任何人来观瞻美,也不需要任何人在场。这样生育出来的真实的德性,显然只属于窥见了真理的人,即最高意义上的爱者自己。爱的阶梯的顶端完全没有被爱者个人的位置。

考斯曼的方案非常巧妙地把“善”或“美”同被述说之物的存在本性联系起来,其背后是古代哲学的自然目的论传统。但就这一提议的最初目标而言,它对弗拉斯托的回应并不算成功。他试图回应的批评在于柏拉图的爱并不关涉个人,而是关涉个人所体现的善或美的抽象理念。虽然他通过自然目的论把某物的美善同它的本性,或“最真实的自我”相联系,但他所谓的“最真实的自我”其实是一个种类的概念。在他的解释中,被爱者“最真实的自我”不是弗拉斯托想要的个体性,而恰恰是被爱者作为“人”这个类的抽象本质。考斯曼的回应在某种意义上反倒支持了弗拉斯托的论点:在柏拉图那里,爱的对象不是个体。
让我们稍稍调整一下思路。如纳斯鲍姆(M. C. Nussbaum)所言,弗拉斯托希望爱所具有的那种个体性或个人性,反映在《会饮》阿里斯托芬的发言中。*M. C. Nussbaum, “The Speech of Alcibiades: A Reading of the Symposium”, in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Cambridge, 1986, p.173.阿尔喀比亚德的演说也反映了这一特征。他强调苏格拉底是独一无二的,与任何人都不类似。按照纳斯鲍姆的解读,阿尔喀比亚德的演说词补充了第俄提玛的教诲(p.197)。这位喜剧诗人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们先前曾是圆球人,后来因为对神不敬,遭到惩罚,被劈为两半。所谓的爱就是我们在世间找寻自己另一半的冲动(189c-193d)。因此,我们所爱的都是独特的、无可取代的个体。相对地,假如像苏格拉底说的那样,我们爱的是被爱着身上体现出来的美或善的品质,那么原则上被爱者就可以被同样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所替代。阿里斯托芬的观点不仅是与苏格拉底-第俄提玛不同的,而且是绝不能相容的。因为任何理性论说都必须使用抽象范畴或类。*按照《斐德若》中的说法,人类必须有能力回忆起理念,“一个人必须按照种类(kat’ eidos)理解被说出的东西,通过理性把感官的杂多收集起来成为一”(249b6-c1)。如果爱者所爱的是被爱者身上的独特的个性,那么爱就不能被任何理性论说所解释,只能像阿里斯托芬的故事那样,归结为神秘的前定命运:我和他曾经是同一个。这种爱是无法用道理解释的,因此阿里斯托芬故事中的爱人们说不清自己的欲望(192c1-d2)。反之,如果爱像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爱这种感情中总是存在着认知性的因素,一个人的可爱之处总是在于某些可解释的特征,那么对一个爱者来说,可能的被爱者就必定是一类而不是唯一的一个。绝对的个体性与理性是不相容的。
弗拉斯托如果看到这点,就应进一步辨析他的论点,放弃追求独特的个体性,承认被爱者是可替代的,承认在爱中吸引我们的总是被爱者身上的一系列特征,而这些特征总是将我们引向被爱者个体之外的某种普遍之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被爱者对爱者而言只是一种中介性,甚至工具性的手段?无论如何,在柏拉图哲学中,那种普遍之物——理念——似乎比个体具有更高的价值。就此而言,弗拉斯托没有看错。
三、理念与幸福
弗拉斯托将苏格拉底在《吕西斯》中对友爱的分析称作“精神化的自我中心论”他同时也认为,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柏拉图自己,即《理想国》《会饮》《斐德若》中的学说。然而,他在分析“爱的阶梯”时,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关于自我中心论的论述。爱者从低处向上攀登,直到达到理念。在这一叙述中,对个人的爱不过是其中较低的阶段。如前所述,弗拉斯托将这一特征称为“理念中心论”。他认为,这意味着被爱者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是为了理念的缘故而为人所爱的。他进而将理念等同于《吕西斯》中提到的“友爱的第一对象”,因为据第俄提玛说,“我们之前的一切辛劳都是为了这个”(《会饮》210e5-6)。那么,这句话是否想弗拉斯托设想的那样,意味着我们爱其他东西,都是为了理念的缘故?
事实上,这并不是第俄提玛的意思。第俄提玛实际是这么说的(210e2-6):
显然,“爱的阶梯”上“各种各样美的事物”首先都是被观看的对象。这段旅程的终点则是观看美本身,或美的理念。几行之后,第俄提玛总结了整个过程(211b7-d1):

“为了美本身”即“为了观看美本身”,之前的一切辛劳是为了在这一阶段能够观看美的理念,认识美之所是。那为什么这种观瞻被当做最高的目的?第俄提玛接着说(212a2-7):

第俄提玛意图呈现的是观瞻理念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在她的教导中改变立场。她曾明确地把幸福当作最高的目的,或者按照《吕西斯》的说法,“友爱的第一对象”。所有欲求的对象,最终都是因为幸福的缘故而被欲求的(204d1-205a4)。“之前一切辛劳”之所以都是为了观瞻理念,是因为对理念的观瞻构成了人类生活中的最高幸福。我们并非为了理念的缘故而爱他人,而是因为幸福的缘故而观看理念;而为了观看理念,我们必须经历攀登“爱的阶梯”的一系列辛劳。谢菲尔德(F. C. C. Sheffield)敏锐地指出,第俄提玛的中心论点在于“(a)只有获得某种智慧才能够满足对幸福的欲求;(b)就获得智慧而言,美好的身体与灵魂,作为理解的对象,具有某种手段性的价值”*F. C. C. Sheffield, “The Symposium and Platonic Ethics: Plato, Vlastos, and a Misguided Debate”, in Phronesis 57.2, 2012, p.112.,理念仅仅在认知的意义上具有某种目的性的价值;幸福则是伦理生活的最高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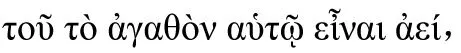
将幸福看作伦理生活的最高目的,是希腊伦理学的典型形态。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斯多亚学派,幸福都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完善。而德性,这一希腊伦理学的核心关切,最终着眼于一种以自我完善为目的的伦理生活。因此,在西方伦理思想内部的古今之争当中——争执的双方分别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德性伦理学、以康德为代表的法则伦理学——德性伦理学总是被自我中心论所困扰。有意思的是,即使是为德性伦理学申辩的现代学者,其理由也无外乎是:如果幸福的生活意味着公正、勇敢、慷慨的生活,那么为自身的幸福而生活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J. Annas, “Virtue Ethics and the Charge of Egoism”, in P. Bloomfield (ed.), Morality and Self-Interest, Oxford, 2008, p.209.也就是说,支持德性伦理学的一方,仍然同它的批评者共享着同样的道德意识:道德绝不是出于对自身之善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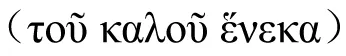
四、结 语
在柏拉图式的爱里面,令弗拉斯托不满意的究竟是什么?尽管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学说被弗拉斯托认为具备柏拉图学说中缺乏的东西,即为被爱者自身之故的爱,但显然处在幸福论伦理学传统中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同样深刻地分享着对自身之善的关注。同时,即使是为朋友自身之故的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仅仅存在于拥有自足的德性的个体之间;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弗拉斯托对柏拉图理念中心论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学说。*弗拉斯托明确地对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精英倾向感到失望。参见Vlastos, “The Individual as Object of Love in Plato”, in Platonic Studies, Princeton, 1973, p. 11.那么,弗拉斯托究竟想要在一种关于的爱的学说中找到什么?让我们回到他指出柏拉图学说的“首要缺陷”的时刻:
由于优秀杰出的人实在太少,而我们可能爱上的人当中最优秀者,也不能免于丑陋、低贱、平庸、可笑的特征,如果我们的爱只是由于他们的德性和美好,那么个体的独特而完整的个性,将不会成为我们爱的对象。*Vlastos, “The Individual as Object of Love in Plato”, in Platonic Studies,Princeton, 1973,p.31.
如果“个体的独特而完整的个性”要成为爱的对象,就必须能够在德性和美好之外,同样地去爱个体身上的“丑陋、低贱、平庸、可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爱人只能爱德性,却没有能力爱这些缺陷。这样一种对卑下微贱者的爱不为希腊思想所知,却是基督教思想中的独特命题:“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约翰一书4:10)
这是在上者对在下者的爱,不产生于任何缺乏和欲望的爱。弗拉斯托心目中最高的爱,正是这一精神的后裔。希腊人无法理解,如果被爱者不值得被爱,为什么爱者仍然去爱。在此我们无法展开思想史的讨论,只能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别,不能简单归结为希腊思想家对某些人类感情缺乏体认,而需要追溯到希腊人和基督教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对于希腊人来说,没有缺陷便不会有需要,没有需要便没有爱;因而爱是人作为一种有缺陷的存在者的标志。但对于基督教思想,爱恰恰是完美的存在者之完美的标志,它不是人性中向上的动力,反而证明了人身上具有完美的存在者某种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