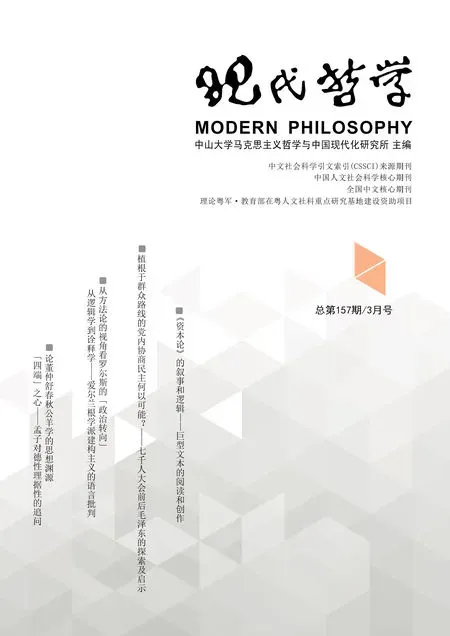“四端”之心
——孟子对德性理据性的追问
匡 钊
从批评“仁内义外”的论点开始,到提出著名的“四端”之心,孟子这些思考的真正诉求,或是为德性的成就寻求一个最终的理据性支持。此种诉求实际上分解为两个相互密切关联的问题。一是为优良人性寻求一个最终的论证根据。对于德性何以成立或者说某些人性品质何以被认定为优秀,以往儒家似视其为不言而喻,这或与儒家将此向度的思考追溯至不容置疑的三代传统有关。到了孟子的时代,随着三代传统不断崩塌,被儒家视为善的那些人性品质、那些自春秋以来便被称道的德性,何以具有此种地位,成为一个潜在的、需要被澄清的问题。二是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我们作为人能够获得此种优良品质。在实践层面,自孔子始,儒家早已形成一套独有的“为己之学”或者说塑造理想人格的方式*参见匡钊:《孔子对儒家“为己之学”的奠基》,《深圳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但对于相关方式为什么可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尚缺乏明确的反思性说明。在战国论辩的语境中,儒家的上述不足成为批评者诟病的对象。典型如老子,不但怀疑儒家所继承自三代的“德”不足为法,更以为礼乐设施亦不能挽回世道人心之颓局。以拒杨墨为己任的孟子,面对此天下滔滔,自然需要给予儒家所谓德性及其成就以更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树立其之所以成立的必然理由。孟子不断转向人的内心,进一步发扬孔孟之间儒者已经初现端倪的“即心言性”之理路,其未曾明言的问题意识出发点,或即在于上述方面。孟子明确从心灵出发来看待成就人性、获取德性、塑造理想人格品质,也就是使人成为其所应是的成人之道,即“先立乎其大者”: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得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在对公都子的回答中,所涉及到的关于人心的许多见解,比如“大小体”、“心之官则思”等内容,都是对已知的之前儒者和更早传统的继承,近从《五行》,远从《诗》《书》的文本中都能找到语义上的线索。研究聚焦于人心带来的负面的后果,便是在历史上长期将儒家的思想形象局限于心性之学的小格局。如果暂时跳脱出此理论格局,对孟子在早期儒家“为己之学”之全局中地位的把握,应首先从他对于德性理据性的追问与对“四端”之心的规定开始:“孟子欲肯定价值意识为自觉心所本有,只能就本质历程讲。此所以孟子就四端而言性。”*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一、有性不可谓命
德性的理据性问题在孟子这里与人性之善恶纠结在一起,而后者也是他与告子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孟子言性最大发明在于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努力,将原本表与生俱来之禀赋的“性”,转化为抽象的对于人之应是的回答。此回答呈现在一个动态成长的过程中而不表现为某种预先确定的“本质”:“在社会体制的‘后面’或者历史‘之前’不存在任何使我们成为人或将我们定义为人的东西。尤其特别的是,不存在那种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真实所是或怎样才是最好的生活的所谓的‘人性’。”*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转引自Aaron Stalnaker: Overcoming Our Evil: human nature and spiritual exercises in Xunzi and Augustine,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6,p.36.
相形之下,告子言性,如《孟子·告子上》中记录的其各种主要论点所示,还停留在与生俱来之生命禀赋的意思上:“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在告子看来,这样的人性既无法改变也无需改变:“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这种意义上的“性”不外就是孔子所讲的“命”:“天命、人性二观念,在其演进之初,本属同一范域。”*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141页。对于命或天命的基本地位,从孔子早已奠定的天人有分的角度看,本属于“不可求”者*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1卷,前揭书,第102—105页;匡钊:《〈论语〉中所见孔子的天人观》,《孔庙国子监论丛》,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第259—273页。。但孟子在对告子的驳斥中所要强调的是,人性的观念早已由“不可求”者彻底转化为“可求”者了。后一种意义上的“性”,也就是孟子所谓的“求在我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上》)此“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相对:“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所谓“求在外者”就是孔子早先所谓“不可求”者。在传统解释中,典型如朱熹对此“求在我者”的理解包含着一个问题:“在我者,谓仁义礼智,凡性之所有者。”这个论点或来自孟子本人将恻隐羞恶等四心直接表述为仁义礼智的某些说法,其最大缺陷在于混淆了心性之间的差异,即在一定程度上将人性养成或者德性获得的问题(心的问题),与所欲养成或获得的对象混为一谈(性的问题),或者说将德性的潜能与实现混为一谈。这种混淆带来两个理论问题:一是难以说明人性中恶劣部分的存在,中国传统中相对缺乏对恶的正面讨论和充分警觉,或拜此所赐;二是模糊了“求”“舍”之间在实践层面的巨大张力,这使儒家的学问在汉代流于形式,而对工夫的自觉需待宋人重新努力。在人心的天然能力或禀赋中,可能存在德性与人性被目为善的根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因此便无条件拥有某些先天的、非获得性的品质,否则儒家的全部修身工夫,或者福柯所谓“自身技术”便无从挂搭。在严格意义上,心与性是两回事,人心只是人性之成就的不可或缺的起点,却并不反映后者的完满状态。
孟子所谓“求在我者”的人性,乃是“人之异于禽兽者”。对此,有论者参照孟、告论辩中所举出“白”之类的例子认为:“按照孟子的看法,谈到‘白’这一概念,我们所关注的是对象的抽象共同性……但是,‘性’这一概念所表示的,却不是像‘白’一类概念那样的抽象共同性或抽象属性。当我们说‘性’的时候,我们意谓的是一类物在其整体存在上所显现出来的根本的特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李景林:《教养的本原——哲学突破期的儒家心性论》,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此亦如张岱年先生所言:“孟子所谓性者,实有其特殊意谓。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徵。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但在何种意义上将“抽象共同性”或“抽象属性”与“根本特性”、“特殊性徵”或“人之所以为人者”加以区分,却不是非常清楚、显而易见的。较为明显的是,孟子在自己的论辩中,实际上使用了偷换概念之类的手法:告子对于“性”的一般理解,是将其作为事物的某种天然具备的规定性,仍然是有效的;而孟子所关注和谈论的人性,已经超出了此范围,并非如告子所理解的属于人的某种天然禀赋,而是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暂不考虑其论辩的形式上的有效性,孟子正确地揭示出人性和白之类的观念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那么,白作为一种“抽象属性”和与之不同的性作为一种的“根本特性”或“特殊性徵”所指分别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应该如何将两者加以区分,并进一步将后者与人联系起来?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或者可以设想,告子所谓白是指事物或某一客观对象的抽象的“属性”(Attribute)。这样的属性,如某物之为白,可以是偶然的,即“偶性”(accident)。虽然告子与孟子均未言及这层意思,但告子的错误显然在于将此种偶然属性,视为与“性”这个概念无异。这种理解在较早的时候或许并不算错,但随着“性”被独立出来、在一系列特殊的用法中被用来指谓人或物的某种特性,理解上的鸿沟就产生了。虽然就目前而言,性这个术语如何具有我们这里所指出的这种特殊用法的观念史细节仍然有待研究,但结合孔子后学与孟子的言论,尤其是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可较为清楚地看出,孟子对此术语与以往告子所谓白之类的属性或偶性,即白羽、白雪之白之间的差异,所见则更为深刻精细。孟子有意识地指出,“性”所指称的内容是特性,与白之类属性并无交集,其内涵远非后者所能覆盖。孟子在自己的论辩中,赋予“性”这个术语全新的积极用法,这种用法的来路,或许与之前儒者的努力密不可分。但以完全自觉的意识,强调性之为特性,则应是孟子重大的理论发明和哲学推进。如是,更向前推进一步,孟子所完成的最后努力,便是将人性明确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或者说,他将人的特性进而表达为人的“本质”(essence),即本质意义上的人性,可以为德性所充实,并在这种意义上是“善”的,而这划定了人之不同于禽兽之类的根本所在。当然,如果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孟子的思考在这里仿佛出现一个无法容忍的理论跳跃,即将特性直接与本质等同起来,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对此,笔者的理解是:其一,孟子在利用人性来规定人的本质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人与物相比,近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种属之间的差异,他的判断完全是针对人这一专门的物种而言;其二,孟子在这里遵循了某种目前尚未得到正面研究的、不同于古希腊式的思维程序,这种程序从西方哲学的角度看,便是孟子并没有如亚里士多德那样,从种属关系和定义的角度,清晰揭示上述问题的理论构造。可以肯定的是,相对于告子而言,孟子在谈论人性时,所希望谈论的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而绝非人的某种一般属性,此正如《孟子·尽心下》之“口之于味”章所言“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尤为重要的是,上述这种本质并非是被预先决定的,人性并非某种完成时的本质主义概念,而是一个低语义内容的、形式化的概念,有待于从实质上加以充实之后,即通过德性的获得或者向善的努力,方能充分显示出其内容。于是动态地看,人性便是一个变化、成长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孟子这里,人性指的是一个人通过某些内心原则所支配的实践活动来使自己区别于一切非人者的提升、改变自己的过程:“在孟子那里,把一个人从人类兽性中区别出来的东西不是某种不受侵犯的自然赐予,而是一种暂时的和永远特殊的文化上的细致提升。”*[美]安乐哲:《孟子的人性概念:它意味着人的本性吗?》,[美]江文思、安乐哲编,梁溪译:《孟子心性之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6页。类似的观点,即认为孟子言人性并非重在说明其是被“给定的”(given),而更在于强调其作为某种人文意义上的成长与创造,早为张岱年、徐复观、葛瑞汉、安乐哲等诸多学者所主张(参见[美]安乐哲:《孟子的人性概念:它意味着人的本性吗?》,前揭书,第86-97页。对此,王夫之曾有相当正确的看法。冯友兰曾引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言,说“他提出了关于性命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命日受则性日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而“性日生”正是对人性的过程性的强调。最终,可以说孟子所言性就人而言,恰恰表述的是一种完全与告子的意见相对的“不自然”的、培养塑造人格品质的过程;而作为其最终成果的人性,则是某种为人所独具、“异于禽兽”的特殊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性或人的本质。进一步,在接续孔子后学思考方向不断强调内心作用的孟子看来,此过程最终应当本人心来加以呈现和解决:“‘性’只是孟子为了建立人类的复杂形象时所需要的词汇表上的一个术语。事实上,‘心’是使得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那部分本性的终极‘处所’(locus)。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性’只是人心(heart)朝向充分实现其道德能力的天赋趋向。的确,孟子在处理人的问题时,其问题意识(problematique)的中心实际上并不是本性(性)而是人心/心灵(心)。”*[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
在以上的理论空间中,孟子的思考在德性理据性寻求的过程中,最终在实践层面和德性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上均向心灵收束:其一,在工夫论之所以可能的意义上,基于某些心灵能力的精神修炼,为人性的塑造提供了先天的动力与途径;其二,被以往儒家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德性何以成立、其必然的来源如何的问题,在孟子看来也须从人心中寻找其根据。抛开具体的精神修炼细节*有关孟子精神修炼细节的讨论,参见匡钊:《论孟子的精神修炼》,《深圳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以上第一方面问题以往学者已多有体察,如牟宗三曾参照康德的观点加以说明:“‘纯粹理性如何其自身就能是实践的’……这问题底最后关键,是在‘心’字,即康德所谓‘道德感’、‘道德情感’……最终是指这‘心’字说,所以最后是‘心’底问题。”*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这个问题包含两个层次:人心在精神性的意义上,是人性内容的实现场所;修身工夫的精神性维度或者说精神修炼,在孔孟之间儒者便已经开始成为重要的、甚至主导性的力量,如《性自命出》所谓“心术为主”*参见匡钊:《简书〈性自命出〉中“道四术”探析》,《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至于以上第二方面问题,与形式化的、动态的、成长性的人性为什么是值得追求的最终依据何在有关。在孟子看来,这正在于人心所本来具有的成就德性的自觉能力。如此,人性、人心与德性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人在其中通过各种工夫追求善的理想人格的努力,完全成为不依赖任何外在力量的“求在我者”。如徐复观便曾从类似角度评价孟子言心的贡献:“在孟子以前所说的心,都指的是感情、认识、意欲的心,亦即是所谓‘情识’之心……在自己心的活动中找道德的根据,恐怕到了孟子才明白有此自觉。”*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以上问题,最终在孟子对“四端”之心的论述中交织在一起。
二、四心只是善端
反观孟子与告子的全部争论,孟子相对告子那种较为传统和“自然的”人性论,所强调的不外是人性所具有的两个特征:其一,人性的成就是修身努力的结果;其二,此种努力具有确定的必然方向,即以成就被称为德性的那些优良品质为目标。前者上文已论及,而后者一方面与孟子对人性最终能达到某种“善”的判断有关,另一方面直指德性的理据性何在的问题。关于孟子言“善”,如胡宏《胡子知言·疑义》所称“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也,不与恶对。’”,乃是称许人性的赞叹之辞。对此,或如葛瑞汉所言:“完善孟子人的本性理论的是去掉人的本性是善的主张。”*[英]葛瑞汉:《孟子人性理论的背景》,[美]江文思、安乐哲编,梁溪译:《孟子心性之学》,前揭书,第76页。实际上,孟子对人性的称许仍然出现在驳斥告子的语境中: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在驳斥对手时,颇为“好辩”的孟子有时大概难免因逞口舌之利而有损于思想上的精确与清晰。对人性的观念而言,善的评价本应出现在这个过程的终点,但在孟子的话语中,很容易让听者以为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善的;同时,这里将四心直接等同于仁义礼智的表述,也是引发后世争议的源头。*对于孟子言“性善”只是从“善端”和潜能的意义上讲,即性“向善”,除前揭张岱年、葛瑞汉等观点外,亦可参见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46页。孟子对“善”这个字的使用,是将其作为对某种一般意义上好的、值得赞扬的行为、言词、人物或事件的评价和修饰。但是,善作为一个正面的评价,其根源不能出于某种公共的约定性或公认。如果把问题还原到这个层面,那么我们基本无法摆脱庄子所设想的那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陷于相对主义泥淖的公共评价混乱。在孟子看来,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评价,理由在于对人心中本来具有的成就德性的倾向的认定。从逻辑上讲,人性的全部过程当然既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不善的。那么,为什么人性在孟子这里最终会得到善的评价呢?这是因为人性的成就,取决于德性的获取。具备德性的人,所呈现之人格面貌便可谓善。孟子的思路,或的确可与康德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对照:“善和恶的概念必定不是先于道德法则(从表面上看来,前者甚至似乎必定构成后者的基础)被决定的,而只是(一如这里所发生的那样)后于道德法则并且通过道德法则被决定的。”*[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8页。他们的区别在于,孟子在对人性之善加以认定时,所诉诸的根据并非康德所设想的那种“道德法则”,而是将其基于德性潜能之实现的必然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董仲舒论人性之时反而把握到了孟子的核心意思:“善如米,性如禾,而禾未可谓之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之善也。”(《春秋繁露·实性》)这里的“性”字如置换为“心”字,大概更符合孟子的原意,“心未可谓之善”即心是无善恶的,但这并不妨碍基于此取得的人性成果是善的。这个由无善恶的心得出善的人性的过程,后儒中大约王阳明领悟得最为明确。人心与人的养成的过程,从评价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先行于善的;而之所以最终能给予这个过程善的评价,则是由于这个过程最终呈现出的,乃是被认定为优良的德性品质。追问至此,德性何以可能必然实现,或者说人心何以一定具有成就德性的内在倾向,便是一个不得不加以正视的问题。孟子这里给出的答案,便在于人心所先天具有的“四心”。
在谈论此“四心”之前,孟子还提及两个可能会产生误解的观念“情”与“才”。就孟子所言的“情”,朱熹《集注》似乎是从情感之义来看待,并据此做出自己的推论:“情者,性之动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性之本善可知矣。”*[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8页。无论此“情”所指为何,朱熹将其与“性之本善”联系起来。对此,笔者难以苟同。孟子此处所言的“情”,首先应是取“情伪”之义,其次才有可能涉于情感,应是指人心“实有”向善的先天潜能或倾向(“才”),就人性之实际结果而言,它当然是善的。只是孟子没有立即追加说明,此人性的实际结果并非现成之物,而是修身成德的后果。“才”是对人心具有实现理想人格之潜能的第一个表述,或是为后面引出“四心”做铺垫。善作为对人性之应然的评价,其在现实中的面貌如欲实然如此,则从逻辑上讲,必须获得“求则得之”的“求在我者”之德性,而人之所以能够获取德性的第一个保障,便在于人心之才。但是,人心具有此等改变自己的潜能,却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在现实生命中达成理想人格。这种潜能需要经历实际的修养过程方能成为现实,而上述潜能在现实中完全可能因为种种阻碍而无法正常发挥,致使我们对于德性的追求受到阻碍,并导致现象界总有不善或者说恶的东西存在。孟子的“牛山之木”比喻,便是要说明这层意思。同时,孟子虽然在原则上同意“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但他似乎没有认真考虑过人心所具有的成就德性的潜能,或者说“才”是否必定具有实践上的强制性。原本应向善之人不能为善,大约不外是因为无知、主观故意或者意志软弱这三方面的理由。孟子虽然意识到人心中追求德性的潜能可能会受到阻碍,但并未清晰区分上述各种情况。实际上,孟子可能是把上述前两个人无法为善的理由混淆在一起。他斥杨、墨之徒为“禽兽”,显然是认为这些人之所以未能最终展示出人性的优美,是因为认识上的错误,否则他“好辩”就显得毫无意义;比较麻烦的是关于纣之类的反面典型,孟子并未明示这种“残贼之人”作恶的理由何在,即他们是出于对人之应是的价值的无知,还是在了解这些价值真相的情况下故意作恶。不能为善的第三个理由,孟子曾先后从两个角度加以考虑:一是曾以“挟太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做比喻,主张导致意志软弱的消极影响完全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立场而加以克服;二是曾将其与人们因“好货”“好色”之类的私欲遮蔽联系起来,为了克服这些阻碍自身心灵内潜能发展的私欲,孟子简单地提供了“寡欲”的方案。虽然在人性向善的过程中存在上述各种不和谐的状况,但仍不足以否定人心有可能开展出的正面德性与价值,这便是孟子所谓“非才之罪”的意思所在。
回到孟子提出“四心”的基本立场,除了上文引《告子上》中容易发生误会的内容,孟子还在《公孙丑上》中明确将恻隐羞恶等“四心”称为“四端”,以更确切的方式提出“四端”之心的著名论断:“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个表述彻底摆脱了将德性与人性视为心中现成之物所可能带来的理论后果,也与孟子其他论述形成更为融贯的整体,充分显示出从人心之“端芽”到人性之成就间的距离。从后果角度可被评价为善的心之端,只是德性养成的潜能或“才”。如果希望真正实现有德性的人格,还需要“扩而充之”的修养工夫:“凡有四端于我者,皆知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孙丑上》)
将孟子前后言及的“四心”视为“端”,比直接指其为某种德性本身更为可取且贴合孟子本意。孟子从来没有主张人性无须任何努力、当下即是善的,否则他与各种修身工夫有关的思考就毫无意义。但从他与告子论辩的语境看,孟子在不精确的意义上,完全可以从人心可能获得德性的意义上,称道人心具有德性,也就是从“仁之端”最终可以为“仁”的角度说“仁之端”就是“仁”,或者从无善恶的心可以为善的意义上说心是善的。抛开这种论辩的立场,结合前面已有的对于孟子与早期儒家人性论的讨论,笔者认为孟子的实际观点,乃在于将心之“四端”作为引导人达成理想人格和德性价值的潜能,这种“才”通过适当的修养,一定能够得到必然实现,但却需要大量的努力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孟子继续主张“四端”之心不但是“实有”的,即“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也是与生俱来的,如同人天生具有“四体”,这就意味着德性养成的潜在苗头“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样的“四端”之心,任何人普遍具有,用孟子的话说就是“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如果我们能够主动并恰当地培养这种人心之“端”,便都可能达到理想人格境界:“孟子思想中的’心’具有普遍必然性,又有自主性。这两个特质都表现在孟子的’心’之作为价值意识的创造者这一点之上。”*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6页。现实中之所以有人因丧失自觉的价值意识而失去这种人的身份并堕落到禽兽的地步,仍然是因为未能妥当对待、滋养心之“四端”。如上文所言,从逻辑上讲一定可以向“善”的心灵之潜能之所以不能发育成熟,不外是因为故意、无知或无能。从《孟子》全书多处对“求则得之”的强调看,孟子最为重视的是第三种情况,也就是如何通过适当的修身工夫克服意志的软弱。这正落入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范围之内。
上述讨论意味着,孟子将“四端”之心视为德性的理据性所在,而这点具有前所未有的理论意义。在先秦时代,对类似的根源性观念的探寻,已经在道家谱系内有所突破。老子所谓的“道”是一个外在的超越性权威,但此权威对人而言,却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后者对价值的“自由”获得,即人的价值来自以“无为”或“自然”的方式得道或顺应道。这种思路无异于将人置于一个更高的客观权威之下,而这对于坚持天人有分立场,并认为各种价值目标均应是完全取决于人自身的“求则得之”的“可求”者的儒家而言,应当说不是令人满意的答案。孟子将此德性的根据追溯到人心,便避免了上述困难,既坚持了儒家天人有分的基本立场,也突破了以往儒家谱系内部对于根源性观念的探索无所贡献的局面。但孟子的思路也并非完全没有疑问,至少在荀子眼中,这个直指人心的答案,由于在最初的辨识上与人的一般生理或生命禀赋层面的情感活动有关,如孟子“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所体现出的那样,或许在可说明性方面显得不那么清晰。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荀子在自己对类似内容的探究中,放弃了孟子已经建立的思路,转而从“圣人”那里寻找德性的根源,如《荀子·性恶》所谓“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这种说法的理论后果,实际上仍然倒向了不“自由”的“他律道德”。如果更进一步对圣人如何知礼义之源加以追问,则恐怕荀子也无法提供合理的答案。对完全贯彻并充分理解早期儒家天人有分的思想传统的荀子而言,他的上述观点不能不说是其思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荀子似乎没有真正了解从孔子到孟子所强调的“可求”或者“求在我者”的那些仅仅并完全取决于人自身的价值目标的全部意义,即德性的价值在于其获得是“自由”的,人成为自己之应是可以并且能够对于自身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应无所依傍。
实际上,孟子所谈论的作为德性根据的心之“四端”,既不是一个生理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如果心的问题最终被归于前一方面,那么哲学活动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人之所以为人,恰恰不是因为这个物种有生命,而是因为这个物种有“异于禽兽”的意义。同时,对于这些意义的发掘,也并未仅仅停留在理智思辨的层面上,而主要是贯彻在生存(existence)之中的实践问题,或者说“为己之学”问题域中出现的问题,即人的全部意义均来源于他们改变自己、成就德性、塑造理想人格品质的实践活动。探索这个孟子在理论上的真正发明,在于如何理解从“四端”之心开始,德性由某种潜在而得到全幅实现的过程。
孔子早已认为德性作为构成人格品质的要素乃是“内在的”,但他并未明示追寻这些德性的内向转向是对一种现成之物的发现,还是根据某些外在的规范对人自身人格的重建,或者是对原有的某些苗头或者倾向的精心培养与发展。从人如何成就德性的修身过程看,“宽泛地讲,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伦理修养的过程:发现、重建和发展”*Bryan W. Van Norden, 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3.。上述三种不同的修养模式为不同的中外哲人所主张,从孟子指出仁、义、礼、智这些品质起始于某种具有特定倾向之“端”来看,他所设定的人获得伦理德性的过程是发展和发现式的*Cf. ibid., p. 46.。持论者可能出于对孟子言“性善”之传统理论未加分辨的认可,而认为他对伦理生活的考虑同时具有发展和发现两种理论趣味,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孟子的观点仅同意发展类型的伦理生活,这与典型的柏拉图式的通过回忆来发现人本来完整具备的某些素质根本不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荀子对伦理生活的了解属于重建式,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模式同时也含有发展式的因素。*Cf. ibid., pp. 50-51.从涉及德性养成过程的角度看,发展和重建式的伦理生活有共同之处,只是它们的起点完全不一样,前者起源于人内在具备的倾向或者潜能,而后者诉诸于外在的法则。从这个角度看,荀子的伦理学属于典型的重建类型,认为人在开始其伦理修养时并不具备任何与德性有关的素质。那么,孟子所据以发展出德性的特定倾向性或者“端”,与什么样的精神性内容有关呢?从“情”即是人天生即能表现出的“情感”的拓展意义看,“四端”之心可被视为与人心特定的情感状态有关。这种情感状态先于思虑,但需要在思虑中才能得到反省性的揭示。这个观点来自对较早儒者观点的继承,上述意义的人之情早已被以郭店简书为代表的儒者认为是人性成长的真正起点。举孟子自己最常用的例子“恻隐之心”而言,上述这种情绪又被孟子称为“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这样的心情被冯友兰与作为人之根本规定性的“仁”联系起来:“他(孟子)认为‘仁’的重要内容是‘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看见别人痛苦的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前揭书,第75页。至于“不忍看见别人痛苦”可被视为人在情感或情绪方面的诸如“同情-移情”这样的通感:“孟子单挑出同情-移情(‘不忍人之心’)来作为我们人性的独特的和规定性的特征。”*[美]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段德智译、林同奇校,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类似这种“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也可从情绪或者感觉的角度加以理解:“伦理上的羞耻……乃是当我们认为自己(或那些我们与之相认同的人)具有重大品格缺陷时所具有的一种不愉快的感觉。”*Bryan W. Van Norden, 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p. 260.“恭敬之心”作为某种对心情的表述,无疑与以上两种心态类似,而“是非之心”也仍然是对人情感上好恶的表达,包含了基于这个好恶的价值判断而非单纯的真假判断。孟子思考“四端”之心的根本思路,是对作为人格构成之品质的德性加以进一步的追问,通过将其潜能充分情感或情绪化而使之成为对于人之应是的根本规定。孟子通过“四端”表达情绪是德性和人性成长的真正起点,这些内容在孟子看来“可以为善”。
三、作为非规范性依据的四端
德性之成立,取决于人心本有的“四端”之“情”,这就是孟子即心言性的理路。据此加以推论,或可以认为人性和德性之成立的理据性,即“四端之心”,占据某种本体论地位。在此意义上,谈论一种儒家的“形而上学”当然是可能的,但这种形而上学未必具有牟宗三等揭示的面貌。关于四心的本体论地位,需要阐明的是:其一,并非如康德所主张的那种普遍有效的、理性的、绝对的规范或法则;其二,只是修身问题或者说儒家所关怀的“为己之学”的一个子问题域。上述第一方面对于理解孟子的思想更为关键。
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相反,孟子所谓“四端”之心是德性的非规范性依据,如前文所述,其构造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的传统。“四端”的存在,不是作为某种人心中的先验理性法则或绝对命令,对于后者的起源我们无法追问;而是作为人心的先天成就德性的倾向,可能是社会-生物演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其起作用的方式也并非通过对特定规则的简单遵循与演绎,而需要大量的实践训练、检验以及经验积累。现代认知科学与哲学自然主义的发展,更鼓励我们从孟子、亚里士多德和休谟的角度去看待人的道德活动,而无需额外为其增加一个康德式的论证*关于康德伦理学的现代批评以及当代哲学自然主义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的兼容性,参见徐英瑾:《儒家政治理想之新唯物主义重估》,《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3期;徐英瑾、刘晓力:《认知科学视域中的康德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在更大的社会历史维度上,德性的发展模式与人类的整体演化密切相关;成就德性的理据性,对个体而言是先天的,但对大时间尺度中的人类而言则是经验性的。
孟子的追问抵达“四心”之后,还引出良知良能的问题,孟子由此对德性发展的起点再三做出说明。用孟子自己的话讲,良知是“不虑而知者”,良能是“不学而能者”(《孟子·尽心上》)。站在我们的立场,可以认为“孩提之童”能如此,是社会-生物演化的结果,但孟子本人并未对其加以追问或推测。孟子将“四端”与“良知”、“良能”均托付于个体的先天性,这在解释上为康德式逻辑的渗透留下了空间。如果一定对其进一步追问,则来自现代认知科学和自然主义的回答似乎更为可取。不过,笔者此处并非意在从上述现代哲学发展的角度对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合理性加以备述,只是想据此说明孟子乃至早期儒家的整体学术形象与康德式的形而上学想象之间的差距。实际上,笔者认为利用某些现代哲学工具追问上述孟子思想中观念的遥远起源没有哲学史意义,这个问题不属于孟子而仅仅属于某些具有特定倾向的现代学者,而有关结论恐怕也不会产生针对孟子思想内部构造的新知识,更何况对现有的知识体的融贯的解释,可以无需诉诸于起源的神话。
那么,“四端”之心的本体论地位应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如将上述问题还原到学术史现实,可以清楚看到,其发生是儒家“为己之学”不断发展“倒逼”出的结果。孔子所关心的成德之教,经由其后学和孟子不断向心的问题收缩,最终在孟子这里出现了对德性之理据性的追问与回答;而他提供的答案,只是为了表明,为什么现实实践中某些德性是成立的,且其对于成就理想人格是有效的。而在我们的解释中,似乎也没有必要颠倒这一思想序列,假设孟子预设了某种肇始于特定起点的理论体系,并由此推衍出其实践上的后果,即将某种本体论问题置于对德性养成工夫的考虑之前。经由孟子的努力,围绕心所可能建立起来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实际上出现在更为广阔的儒家“为己之学”问题域内部。孟子对“四端”的思考,作为上述问题域的一个支点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但我们必须避免以其覆盖该问题域之全局。
——论阳明学派对告子思想的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