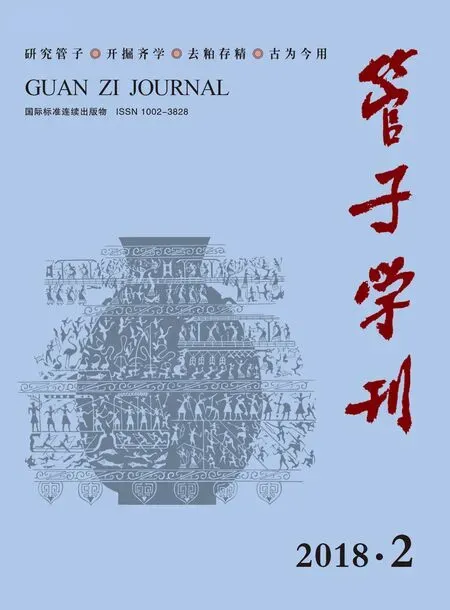《管子》之学与秦汉制度及后世借鉴
刘 敏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管子》①本文所引《管子》均依据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一书内容恢宏而驳杂,价值极高。关于该书的作者、学派、成书年代,尽管在学术界存在严重分歧,但丝毫不损该书在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地位,不损其对后世历史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仅就《管子》的学派归属问题,《管子》可以独立成学的问题,《管子》中某些篇章内容与秦汉制度的关联问题,以及《管子》的后世鉴戒问题略作讨论,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曾经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使之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主,但人们较少纠缠管仲到底是哪一家哪一派,与此不同的是,因管仲其人而命名的《管子》应该归属于哪一派哪一家,却是学术界久辩不衰的论题,何以会如此?笔者以为是时代不同的原因,管仲生活的时代是春秋前期,而《管子》最终的成书年代无论如何不会早于战国时期,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虽然接踵相连,确有颇大的差异。清人顾炎武对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的差异曾有过精彩的归纳,即《日知录·周末风俗》中那段经典之论。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1]749-750。
顾炎武这里主要是从风俗的差异来揭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的差异,当然这两个时代的差异绝不仅仅限于风俗,它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就本文所关注的思想学术而言,同样是有明显的裂变和差异的,即春秋以前思想学术混然一统,是无家派之分的,而分诸子以为百家实乃战国以降之事,《汉书·艺文志》就指明了这种差异发生的情况: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弛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2]1746。
班固这里指出所谓的诸子百家是在天子式微、诸侯称王、好恶殊方的社会变革背景下产生的。
管仲之人和《管子》一书或生活和或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前者在学术分裂之前,后者在学术裂变之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管子》一书与管仲之人无关呢?回答是否定的。认为《管子》一书与管仲之人无关和认为《管子》一书是管仲所著,同样是不可取的,《管子》一书应该是包括管仲及其后学在内的管子学派长期积累的思想和著述成果。
《汉书·艺文志》把诸子百家划分为十大家、一百八十九(其实认真算应该是一百九十)小家,毕竟战国去春秋较近,故很多思想家的思想主张都带有春秋以前混然一统的特色,不是醇一的,会有兼包并蓄的特点。而《管子》这种混然兼包的特点更是突出,尤其值得注意。虽说《汉书·艺文志》将《管子》作为一小家编录在道家者流之中,但在其之前的刘歆编撰《七略》时却是把《管子》列于法家之中,后来的《隋书·经籍志》以降的目录学著作都把其归入法家者流,这当然也有他们的道理,仅就其所含的篇目来看,并非全然都具有道家思想的特色,而是明显的归属于不同的学派,不仅包括法家,还有儒家、阴阳家、兵家等。
“道”是道家学派的宗旨所在,其在《管子》中也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有众多处论说“道”“天道”“天之道”及其重要性。如:“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3]234;“为而无害,成而不议,得而莫之能争,天道之所期也”[3]80;“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3]42。此外,又有多处论及“道”与“德”、“天道”与“人道”之关系等,这也是《汉书·艺文志》将之归入道家的缘由所在。
制度与法令是法家思想的精髓,其在《管子》中也非常突出,其把“法”作为管理国家的根本。如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3]1008;“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3]1181;“法者,民之父母也”[3]298,“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著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3]301。
“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最突出的内涵,同样也构成《管子》思想的重要原则。如:其《戒》篇中说:“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以德予人者,谓之仁”。其中包括了德、信、孝、悌、忠、恕等最具儒家特色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恕”的解释,管子与孔子之言简直就是如出一辙:“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139而《管子》亦曰:“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3]959于此可见,《管子》的儒家思想特色也是颇为浓重的。
阴阳学派在战国时期实现了与五行思想的融合,形成了阴阳五行学派。阴阳五行思想对当时多种思想流派均有影响,管子学派也不例外。《管子》中对“阴阳”及其重要性多有论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3]85“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3]838“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而发出节……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忧哀、静正严顺,居不敢淫佚……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其事号令,修禁,徙民令静止。”[3]842-855《管子》认为阴阳、四时、五行均是密切相连的,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是一个有序运转的统一体。《管子》的阴阳五行思想对邹衍直至董仲舒等一大批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先秦齐地是兵家思想最为活跃和发达的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兵家著作皆产于此,根植于齐地的管子学派及《管子》与兵家的关系也颇为密切,如《管子》篇目中专有《兵法》篇,其与兵家之关系自不待言,此外,《地图》《制分》《九变》《参患》《幼官》《七法》等篇目之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兵学内容。《管子》不但重视战争的作用和影响,而且特别强调“夫兵事者,危物也”[3]494,“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3]535,即主张用兵必须慎重。
《管子》一书,内容恢宏而驳杂,气象万千。不仅有政治,也有思想;不仅有制度,也有习俗;不仅有经济,也有军事;不仅有道、法,也有儒、墨、阴阳;不仅有历史学,也有心理学和医学;不仅有民生,也有自然环境;不仅有文学,也有艺术……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就其思想道术而言,几乎囊括了战国诸子各家特色的思想内容,如果一定要确定其学派归属的话,笔者以为只能将之归于杂家,但同时也认为《管子》更应该作为一门独立学问来研究,可以称之为“管子学”。
二
《全汉文》辑录的刘向《管子书录》曰:“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5]381《汉书·艺文志》也说“《筦子》八十六篇”,今天我们所见《管子》一书即是刘向删除定著的八十六篇,其中十篇有目无书。检考这七十六篇,其中大量和主流的似乎更应该属于法家学派,重君权、重法治、重制度、重农耕、重富国强兵等,特别是其中的《任法》《法禁》《重令》《七法》《法法》《明法解》等篇,更是探讨《管子》法家思想的重要篇目。
《管子》中的法律思想有两个特点尤其令笔者重视。一个是对法令的极端重视,赋予法令极高的地位,特别是体现在君主与法令二者的关系上。如《任法》篇说:“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重令》篇说:“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法法》篇说:“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即认为法是国之重器,是君尊国安之所在,法令虽然是出自君主,但一经制定,包括君主在内,都要受其约束。再一个特点是重视法令的同时也重视道德,强调法令与道德的辩证关系。如《权修》篇中说:“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把道德教化放在先于法令的重要地位。
历史上法家学派的最重要特点就是重法治,但处于先秦诸侯分立、文化多元的状况下,各地区由于历史与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别所致,不同地区的法家也存在差异,战国时期东方的法家和西方的法家就存在差异,呈现不同的特色。如果说《商君书》和《韩非子》是西方法家的代表作的话,那《管子》恰恰代表了东方法家的特色思想。笔者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说《管子》之东方法家思想和西方法家思想的差异。
一是对法令与礼义道德的关系认识不同。与上文所说《管子》之学在重视法令的同时也重视道德,把道德教化放在先于法令的重要地位不同。《商君书》和《韩非子》是完全否定礼义道德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一味地主张重法。如《商君书·说民》曰:“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举,奸之鼠也”[6]35,主张“任其力,不任其德”;《韩非子·内储说上》亦曰“成欢以太仁弱齐国,卜皮以慈惠亡魏王”[7]213,主张“不务德而务法”。
二是执法的严酷程度不同。众所周知,商君之法以严酷著称,法治体现为严刑峻法,甚至俱五刑,甚至逮三族,甚至什伍连坐,简单粗暴,极端而不顾及情理。管子之法则不同,执法讲究尺度,考虑情理,在重法的同时非常强调礼义廉耻,将之提高到与法同等重要的地位。《汉书·贾谊传》载:“《筦子》(师古曰:‘筦,与管同。’)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2]2246-2247这是贾谊对《管子》重礼思想的概括,与《管子》原文不同。《管子·牧民》篇原文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袛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袛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又:“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可见,《管子》的法治不是简单粗暴的,而是与“四维”,即礼、义、廉、耻相结合的。管子之法明显高于商君之法,这应该是根基于齐地社会和文化较秦地进步的反映和表现。
三是重视农耕的目的不同。战国时期的法家都具有重视农耕,重视发展农业经济的特点,但其目的性也存在差异。商鞅重耕的目的主要是强兵兼并,故在《商君书》以及之后的《韩非子》中常见“耕战”“耕战之士”的记载。如《商君书·慎法》曰:“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于此二者力本……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而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韩非子·亡徵》亦曰:“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韩非子·和氏》曰:“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而《管子》则与《商君书》《韩非子》不同,其重视农耕的目的主要在于富国安民,《管子》中有很多与之相关的精彩说法。如《牧民》篇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山权数》篇云:“谷者,民之司命也。”《八观》篇云:“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治国》篇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欧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五辅》篇曰:“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谄谀,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是以一战而正诸侯。”
《管子》重视安民、重视民生、重视谷物,将此看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也是国家富强的目的,具有民本主义倾向。故《全汉文》辑录的刘向《管子书录》点睛道:“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5]382
三
《管子》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内容,其中既有宏观的理论阐释,也有具体的制度建构,这些内容对于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汉的政治变革,对于从贵族封建制到君主集权制的社会演进链条般的作用和影响。而且,《管子》书中的一些篇目,有关国家体制及具体行政制度的思想和设计对秦汉时期的行政制度有直接影响。
首先,看一下有关“皇帝”的问题。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要建立一个不同以往的国家,故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既有开天辟地的创新,也有对原有制度的发展完善。所为第一件大事,就是“议帝号”。在初并天下的二十六年,秦王嬴政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8]303-304结果把上古人世间最尊贵的称号“泰皇”去掉“泰”字,再加上古代“帝”位号,合称为“皇帝”。司马迁对于“皇帝”称号产生的具体细节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看到在《管子》一书中有关于“皇”和“帝”的阐释,《兵法》篇开篇即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这构成了皇帝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链条。
皇帝制度是高度专制集权的君主制度,皇帝是上天之子,是独一无二的,这在《管子》书中说得异常明确,其《霸言》篇曰:“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理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理也。”家、国、天下,均是同样的原则和道理。《管子》中不但论说了天子的独专性,也同样阐明了君主的主要责任,那就是审势用人。其《立政》篇曰:
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便辟无威于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众。
主张“德”与“位”、“功”与“禄”、“能”与“官”要相符,否则就会“良臣不进”“劳臣不劝”“材臣不用”,就是君主的失职,此点具有普遍意义。
其次,再看中央官僚机构的设置和职权问题。春秋以前的三代基本实行的是贵族世袭官吏制,战国时期,与君主专制相伴随,非世袭的官僚制逐渐取代原来的贵族官吏制,秦朝建立后最终完成了这个转变。这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革,对此《管子》的态度是积极鲜明的。如其《立政》篇曰:
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死罪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庙,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者,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曰侈专制,不足曰
亏令,罪死不赦。首宪既布,然后可以布宪。而在全国的官吏中,《管子》又特别重视君主身边之官吏,其称之为“中央之人”,如《君臣下》篇曰:
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贤不肖,而可威党于下。有能以民之财力,上陷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下。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实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
君主用好了中央之人,他们就是股肱重臣、左膀右臂,否则他们就是障碍和祸乱,故《管子》强调君驭臣有术,严防臣子作乱。
再次,关于郡县制的问题。郡县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其成熟完善并推广至全国,则是秦始皇的功劳,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变迁,它使古代王朝最终摆脱了血缘族群的束缚,而成为地缘性国家,或者更准确说,把故有的血缘族群纳入到地缘性国家机制中,对此变革,《管子》的态度也是积极促进的,虽然书中“郡县”二字出现得并不多,但其为郡县制的国家蓝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设计,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乘马》篇和《立政》篇。如《立政》篇曰:“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乘马》篇曰:“五家而伍,十家而连,五连而暴,五暴而长。命之曰某乡,四乡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国语》转述曰:“管子于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9]224另外在《管子》一书的《九变》《小匡》《问》中也都有过于国家地方行政制度的设计描述,相互之间存在差异,且与齐国的地方行政制度的细节也并不吻合。这反映两个问题,一是《管子》各篇确非出于同一人之手,二是《管子》的行政设计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但其非血缘的郡县性质是肯定的,而“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在西方的秦国及后来的秦朝、汉朝均已变成了实践层面的现实制度。
四
管子学派及《管子》一书不仅在政治和行政方面对秦汉制度存在链条般的作用影响,而且作为先秦重要的思想流派,对汉代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更为突出,尤其是在以商鞅、韩非等西方法家极端专制主义为思想指导的大秦皇朝速亡后,汉初的思想界对吸纳了道家、儒家、阴阳五行家、兵家等多学派思想精华的东方法家,或者说是杂家学派代表的《管子》尤为重视。顾名思义,杂家本来就具有兼包并蓄的特色,在行政上大一统的国家建立后,在思想方面照说应该对诸家思想取其精华,整合包容,吕不韦在秦统一的前夜,曾经网罗各家各派的思想家,编撰了《吕氏春秋》一书,遗憾的是秦始皇过早结束了吕不韦的政治生命,《吕氏春秋》也没能发挥其本来可以发挥的历史作用。汉初吸取秦朝速亡教训,在思想上以黄老之学说为主导,政治上实行无为政治。学术界基本认为,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形成于齐地的稷下学宫,而《管子》之学的发展形成也与稷下学宫密切相关,其所包含的道家思想也是以黄老道家为特色,其中特别是《管子》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等篇目,被看作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对汉初思想界影响颇大,特别是对《淮南子》的影响更为突出。
《淮南子》诞生在西汉前期,在黄老之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将其与《管子》相对比,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思想影响和学术承继关系,略举几条以证之。
如《管子》曰“无为者帝”[3]84;而《淮南子》书中则曰“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10]269,两书均主张君主要清净无为而治。
如《管子》曰:“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3]1379;“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 ”[3]728。而《淮南子》则曰:“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 ”[10]314;“食者,民之本也”[10]308,两书均表现出对粮食、对农业生产、对民生的高度重视。
如《管子》曰:“明君不为亲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亲;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3]316,而《淮南子》则曰:“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仪也,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10]295两书均主张君主也要遵守法令,主张以法令来制约君权。
如《管子》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3]13;“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3]188。而《淮南子》则曰:“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10]467;“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苟利于民,不必法古”[10]426-427。两书具有一脉相承的民本思想。
《管子》数十篇,十数万字,其中最最普通,而又让笔者倍感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3]2,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无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特别是对汉代思想家的影响颇深,从《史记》到《汉书》,再到《后汉书》,从《新书》到《淮南子》,再到《盐铁论》,从《论衡》到《潜夫论》,再到《风俗通义》,《管子》这句话每每被引述,并由此而作进一步论述发挥。如《新书·无蓄》载:“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11]163《淮南子·主术训》云:“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史记·货殖列传》曰:“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盐铁论·授时》载贤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饶乐,国无穷人,非代之耕织也。易其田畴,薄其税敛,则民富矣。上以奉君亲,下无饥寒之忧,则教可成也。语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徙义而从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百姓足而知荣辱。’故富民易与适礼。”[12]192《说苑·建本》篇载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即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13]7《3汉书·食货志》云:“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论衡·问孔》篇载:“问[曰]: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14]422-423《汉官仪》载:“张敞、萧望之言曰:‘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其势不能。请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15]156
《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给汉代思想家、政论家们极大的影响,进而也影响了两汉政治与社会民生。这一认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即使在当代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的这一思想既是简单明了的,又是唯物深刻的,遗憾的是千百年来,太多的统治者、领导者对此缺乏认知,没有把安民作为国家强盛之根本。
参考文献:
[1]日知录集释(中册)[M].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论语注疏[M].何晏等注,邢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严可均.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9]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0]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3]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孙星衍,等.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