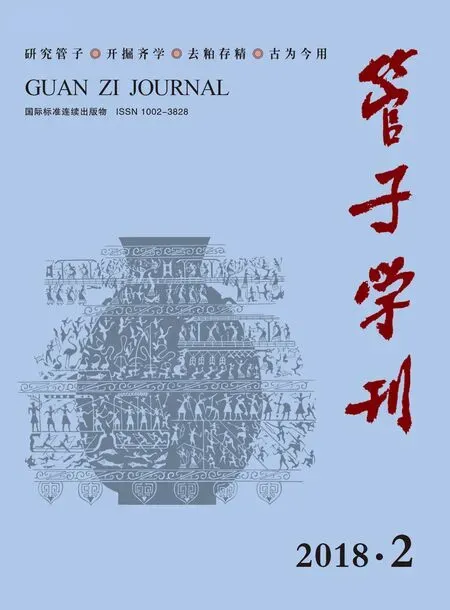论福泽谕吉儒学与西学的视域
史少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福泽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出生于1834年(天保五年),卒于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被誉为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日本当今流行的纸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福泽谕吉的名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他是日本资本主义文化的先驱者,日本学者对福泽谕吉的思想体系,亦有不同评价。例如丸山真男认为福泽谕吉是典型的市民自由主义者;嘉治隆一认为福泽谕吉的思想是纯粹英美之流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远山茂树、服部之总俩人都认为福泽谕吉的思想是专制主义;还有学者认为福泽谕吉的思想中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是一位日本近代的军国主义理论家。此人一生著述颇多,著名的有《唐人往来》《劝学篇》《西洋事情》《文明论概论》《通俗国权论》《通俗民权论》《丁丑公论》《民情一新》《福翁白话》《时事小言》《脱亚论》《帝室论》等,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福泽谕吉对“儒学”思想的排斥以及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汲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军国主义思想,具体分析如下:
一、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排斥
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于1942年出版了《福泽谕吉的儒教批判》(日本即:《福沢諭吉の儒教批判》),丸山真男在其著作中以1882年前后为界,将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分为两个时期,认为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是全方位的激烈批判,大体用了三种批判儒学方法:其一,用社会关系的偶然性或者变动性,批判儒学中认为绝对的或者固定的模式。例如福泽谕吉对儒学中君臣关系的批判;其二,福泽谕吉指出了儒学中特定观念的本来意图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差距,从而对此进行讽刺批判。例如福泽谕吉对各种伪君子的讽刺,从而引发对儒学批判;其三,福泽谕吉对儒学思想功能方面的批判。例如福泽谕吉指出儒学的遗毒造成专制,影响社会发展,造成社会停滞不前等。丸山真男在其著作中认为,福泽谕吉后期对儒学的批判,较之前期对儒学的批判,从批判方式上从激烈的批判转向了稳重、和缓的批判,也从前期对儒学全方位的批判,转向了后期对儒学有限定的批判,例如福泽谕吉后期肯定了儒学的历史作用。但是从总体来看,福泽谕吉对儒学还是排斥的,我下面做具体分析。
福泽谕吉排斥“儒学”中某些对“孝”的阐述。福泽谕吉指出:“从古以来,在中国和日本,劝人行孝的故事很多,以‘二十四孝’为最著名,这类书籍,不胜枚举。但其中十之八九,是劝人做世间难以做到的事情,或者叙述的愚昧可笑。……孟子不是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我的回答是:对于提倡违反天理,倒行逆施的人,即使孔子孟子,也不必有所顾虑,仍当视为罪人。娶妻而不生子,怎么认为是大不孝呢?这真是故甚其词,只要稍具备人心,又岂能相信孟子的妄言?”[1]40-41福泽谕吉不是反对人们对长辈的“孝”,而是他认为“儒学”中的某些对“孝”的阐释是不近人情的,是封建家长式的,是错误的,故而进行了排斥甚至讽刺、批判。
福泽谕吉排斥“儒学”中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反对封建的三从四德思想。他指出:“须知生存于人世间的,男的也是人,女的也是人;更就世间所不可缺少的作用来说,天下既不可一日无男,也不可一日无女,其功用确实相同。……对妇女的要求则极其苛刻。……有些人极力维持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倡导虚名,以实施专制,毒害所及,遂成为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犯了这种毛病的人就叫做伪君子。……所以我再三地说社会上最不可靠的是名分,流毒最大的是专制压迫。”[1]40-54福泽谕吉不仅在他的著作《劝学篇》中阐释了他反对男女不平等的观点,而且在他的著作《福翁白话》中也多次阐释反对男尊女卑的观点。
福泽谕吉对“儒学”中的上下贵贱的名分极其排斥,反对封建式的旧道德,提倡推翻封建时代家族制度的名分观念,建立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新道德。他批判儒学的君臣关系时说:“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2]36又进一步指出:“所以后世学孔子的人,也不可不考虑时代这一要素而确定取舍。要是有人想把两千多年前的教条原封不动地搬到文明时代来施行,那就是不识时务了。”[1]63福泽谕吉认为孔子用抽象的道德之说用来教化天下是行不通的,用来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是起作用的。福泽谕吉还反对“儒学”中的“天意”“天命”等思想。他说:“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2]18又指出:“说君主是受命于天,或者说其祖先曾登灵山会见天神,或说梦兆或说神托,如此荒唐而恬然不以为怪。”[2]26福泽谕吉还反对“儒学”的“仁政”及“仁爱”思想,他认为孔孟之道可以称为伦理学,是讨论抽象伦理道德的。并指出:“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2]53还认为不能用孔孟之道的“仁政”治国。正如福泽谕吉指出:“所谓仁政,如果不在野蛮不开化的时代,是不会起作用的;所谓仁君,若不面对着野蛮不开化的人民,是不能显其尊贵的。”[2]111在我们看来,其观点非常偏激。
福泽谕吉反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指出:“贫富强弱并非天定,而决于人的努力与否。今天的愚人可以在明天变为智者。”[1]11他认为人的一切善行都来源于智慧,一切恶行都来源于无知。并且指出:“道德只是个人行为,其功能涉及的范围是狭窄的,而智慧则传播迅速,涉及的范围广泛。道德范围一开始,就已经固定下来,不能再有进步,但智慧的作用,确实日益进步永无止境的。……道德又突然的变化,智慧则一经掌握就不会消失。……如果以道德为幌子,企图笼络天下人心,甚至在道德之中别立门户。……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自由,把人们置于无为无知的境地,而扼杀真正的文明,这是我最反对的。”[2]101-102其实其并不是反对道德的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意思不是说私德无用而把它摈弃,而是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2]77
福泽谕吉认为“儒学”的思想助长专制而加以排斥。且指出:“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尊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的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2]147可见,他认为儒学的思想助长了专制,认为日本要学习西洋,打破封建的禁锢。
日本学者指出:“福泽向本居宣长排斥‘汉意’那样,企图一扫‘儒魂’,而作‘国学’,教‘史学’即英学,犹如忠实《古事记》那样,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方面也罢,在殖民帝国主义也罢,看起来似乎忠实地以西方中资产阶级社会为楷模的。”[3]254福泽谕吉对“儒学”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排斥“儒学”思想,但是不否认日本历史上“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他说:“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2]145可见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排斥,也是在肯定了儒学历史功绩上的排斥。但就日本近代发展视野分析,福泽谕吉主张“脱亚论”,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脱亚”,实际上就是“脱儒”。日本哲学家丸山真男被日本学家称为“福泽研究大家”,在《丸山真男集》中搜集的关于研究福泽谕吉的论文就有18篇,丸山真男认为“脱亚入欧”一词不是福泽谕吉创造的,并且指出福泽谕吉在明治18年3月16日的《时事新报》上,阐明了“脱亚”论的观点,丸山真男指出福泽谕吉所说的“脱亚”,实际上是指“脱清政府”与“脱儒教主义。”
二、福泽谕吉对西方近代思想的汲取
日本从幕府时期开始,就热衷于引进西洋文化,向西方大量地派遣留学生。到明治维新以后,正式引进西方文化,进入了所谓文明开化时期。1859年(安正六年),福泽谕吉初次访美,对美国的风俗感到惊奇,无论是美国的文化,还是美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给他以强烈的刺激,回国时买了一本《韦伯斯特大辞典》带回。1862年(文久二年)他作为日本幕府的遣欧使节的随员,访问了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而后又多次访美,买了各门类的很多书籍带回日本。他在自传中回忆到:“回来后,在翻译和著书方面,虽比以往更忙,但为全体社会而打破门阀制度的信念却更加强烈,此事在师友的谈笑间被当成极热门话题。”[4]150福泽谕吉为欧洲的平等观念所感动,大为欣赏欧美的文明开化,于是他总结了几次访问西方国家的感受,于1866年(庆应二年)写作了《西洋事情》,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外交原则、社会设施等,详细地叙述了西方国家的税法、国债、纸币、外交、兵制、文学、技术、学校、报纸、医院等。福泽谕吉认为日本的近代“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所以他主张汲取西方近代的民权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意识;宣扬西洋文明,并且认为如果让西方近代文明在日本扎根,首先要说服日本国内以儒教为代表的所谓东洋文明的代表们,不要以西洋文明为敌。“在福泽谕吉看来,虽然儒教文明与西洋文明性质不同,两者也有可以融通的方面,甚至也可以使儒教故老利用和支持西洋文明。”[5]246福泽谕吉倡导文明开化的风气,推动了日本所谓文明开化的进程。正如在其自传中说:“希望不管怎样要把日本闭关自守的局面打开,并把日本导向西方那样的文明界,使日本能富国强兵,在世界上不致落后。”[4]156
福泽谕吉多次参观访问西方国家,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抨击当时日本的封建统治,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成立了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启蒙思想组织“明六社”,翻译西方的书籍,以西方思想家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为中介,传播西方近代思想,通过汲取西方近代文化而促进日本的文明开化,倡导汲取西方思想中的“自由”“独立”思想。他认为西方近代文明体现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人类活动的领域分化、精神多样化后能够产生自由,而人的自由精神的彰显,才能建立人类社会的文明。“‘一身独立,一国独立’这句福泽谕吉的话与明治初年的畅销书之一《西洋立国篇》(明治四年刊)有共通之处。那是由中村敬宇(正直,1832—1891年)所翻译的英国的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年)撰写的《自主论》,该书汇集了西洋的有志气、克服了重重困难的人物的传记故事。……福泽谕吉、中村敬宇都主张自立的精神对日本国家的独立、发展有益。可以说,在明治初年肩负日本未来的那些人的观点在上述著作中很好地体现出来了。”[6]120福泽谕吉在汲取西方之文明思想过程中,把文明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近代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是独立精神。上述这两个方面,在他看来正是西方近代文明之底蕴与精髓,认为日本必须要汲取并且要学习。
福泽谕吉汲取西方的平等思想,对日本的等级观念深恶痛绝。他说:“生在小士族家庭里的人,自然就经常受到上等士族的蔑视。人们当中尽管有智愚之别与不肖之异,但上士蔑视下士的风气却在横行,我从少年时期就对这种风气感到极端不平。”[4]150其实,他的思想是复杂的,因为他一方面想引进西方平等观念,反对封建统治的顽疾;另一方面又想汲取西方的思想,维护日本万世一系的“国体”。正如他提出:“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这又何必踌躇呢?应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2]24可见,他汲取西方近代思想的目的,就是想尽快使日本独立、富强。
福泽谕吉在主张汲取西方文明的同时,更主张抵御中国的文化,特别是排斥中国的“儒学”。其认为社会的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类智慧的进步,故而民族的智慧是日本文明开化的时代主题,进而提倡“实学”,排斥“虚学”,并且号召日本人民积极学习“实学”,兴办实业,学习西方发展日本的资本主义。并指出:“对各项科学都实事求是,就每一事物深切追求真理,以满足当前的需要。……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1]2实际福泽谕吉认为“儒学”是虚学,故而对“儒学”进行了排斥。且指出:“我们多年提倡的乃文明之实学,非支那之虚文空论。……即吾辈修西洋文明之学问,非折中、附会汉学,要从根本上颠覆古来之学说,以开文明学之门。”[7]261可见,他在极力地汲取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在极力地排斥中国的文化。其文明论的实质,就是想汲取西方近代文明之精华,谋求日本之独立,发展日本之文明,使日本尽快强大。
三、福泽谕吉的影响
(一)福泽谕吉推动了日本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
一定意义上,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运动的缔造者。他在日本的明治前后有很大的影响,被日本誉为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是明治维新以后教育发展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也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有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之美称。福泽谕吉说:“按我的主见来说,首先我讨厌锁国,更讨厌那守旧的门阀制度的无礼压制。”[4]142可见,其主张对外交流,反对闭关锁国的陈旧观念,提倡开国,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福泽谕吉以启蒙思想组织“明六社”创办的刊物《明六社杂志》为阵地,介绍西方文明,猛烈抨击封建制度与封建意识形态,大力宣传启蒙思想。在其著作《劝学篇》《文明论概论》《丁丑公论》《时事小言》《民情一新》都有阐述启蒙思想与文明理论。日本学者尾藤正英说:“只凭借传统观念还不能引进西洋文明,因此传入了新的近代观念。被称为明治初期启蒙思想的便是那种观念,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以及《劝学篇》等便是那种思想的代表。”[6]119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中详细地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状态及信念,介绍了西方的风俗人情,分别介绍了美国、荷兰、英国、俄国、法国的历史与现状。《劝学篇》在当时的日本发行量超过了70多万册,在当时的日本是极大的发行量,被誉为“明治圣书”。《劝学篇》中集中体现了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其目的是让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文明开化之门。福泽谕吉劝学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人人平等、国家平等,坚持民族独立,建立富强的国家。他把个人独立作为社会的基础,从而阐释了其民全论。并认为“文明”是人类智慧之进步。他说:“如果不能使人身心各安其所,则不能谓之文明,而且‘人之安乐不应有限,人心之品味也不应有极’。所谓安乐,所谓高尚,是指‘正在发展与进步之时’而言,所以‘文明应谓人之安乐与精神之进步。’而且,‘人之安乐与精神之进步乃是依靠人之智慧而来’。因此,归根结底,文明应谓人类智慧之进步。”[2]183并且福泽谕吉把“文明”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在的“文明”,也就是物质文明;一种是内在的“文明”,也就是精神文明。认为人类智慧的发展,是随着人类文化和社会的进化而进步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从野蛮到文明不断发展的历史。“西方文明”标志着历史的进步,具有普遍的意义。日本在当时的任务,认为就是以西方近代的文明为目标,日本要赶超西方近代文明。
日本启蒙思想者们认为日本的旧弊是人民愚昧无知,缺乏独立、自由的民主精神,并且认识到自由、独立的国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日本国民都具有这种气质。于是启蒙者们把启迪民众的愚昧当作任务,以培养民众的自由、独立的精神。福泽谕吉说:“如果把东洋的儒教主义与西洋的文明主义加以比较,可知东洋所缺乏的是有形方面的数理学和无形方面的独立心这两点。”[8]206丸山真男也分析:“他把独立自由的精神与数学物理学的形成作为欧洲文明的核心,这一点生动地说明了他对近代精神的结构具有渗透的洞察力。”[9]34福泽谕吉并且认为在培养民族的独立意识方面,知识分子要起重要的作用。福泽谕吉试图让日本汲取西方近代文明,加速日本的独立发展,建设富强的现代性国家。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私立大学的创始人,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力培养人才。关于如何提高日本民众的自由、独立气质,福泽谕吉认为主要是通过教育。
日本近代的启蒙运动,提倡以欧美为目标改造日本社会;排斥“儒学”,提倡学习科学技术;提倡自由平等,推进日本政治改革,开启民智;引进西方哲学思想,批判封建社会的旧道德。福泽谕吉摄取了西方的“自由”观念为日本启蒙运动的源泉,反对日本封建制,反对日本封建制度的身份制。他指出:“在旧幕府时代,武士和平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武士们作威作福,对待农民商人就像现在对待犯人一样。”[1]8为此,其对封建制度深恶痛绝。从福泽谕吉的“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的观点,体现了“福泽既不是单纯个人主义者,也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者……应该说,他正因为是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才是国家主义者,福泽谕吉作为一个个人在日本思想史上出现,其意义正在于他把国家与个人的内在自由嫁接起来。”[10]81也就是说不要把福泽谕吉的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思想割裂分析,因为其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福泽谕吉论自由、民主的启蒙思想也推动了日本学界的论争。例如日本学者加藤弘之认为福泽谕吉的某些思想是“自由主义”,加藤弘之认为如果过度地扩张民权、减弱国权,就会使国权衰弱,反而危机国家的独立;还有日本森有礼也对福泽谕吉的观点进行了质疑,“福泽认为,不能仅仅靠政府的力量推进文明。森反驳道,‘近世之文明者,难为政府之本务’,应该完成这项任务的,是‘知此而主张之人’,‘务民之义,近世之公利’,而作为官吏行动的‘独立’行动都可以。当然,结果也否定了‘偏袒独立’(《劝学篇》)的福泽的看法。”[11]229但无论如何,福泽谕吉对日本启蒙运动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也是日本人公认的。
(二)福泽谕吉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国学者的影响
近代国学家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多次去日本,福泽谕吉的思想给予了他们很大影响。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人在日本时,通过日本人翻译的大量西方书籍,进一步了解了西方近代思想。康有为在构想中国社会改革时,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思想,并且提出兴商业来救国。
“梁启超到日本之后,读福泽谕吉之书,深受影响。他著《自由书》,大倡‘独立自尊’之旨,认为福泽谕吉之所以提出‘独立自尊’,是由于福泽谕吉尊重人道与国民。在他看来,中国人正是由于缺乏自尊之品格,才使国家糜烂至此,而自尊之品格是国家独立强盛的必要条件。”[12]78梁启超受福泽谕吉的“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的影响极大,故而也强调了自尊品格是国家独立强盛的条件。梁启超指出:“为国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资格,则断未有能自尊其一国之资格焉者也,一国不自尊,而国未有能立焉者也。……吾闻日本人自尊之言曰:日本者,东方之英国也。万世一系,天下无双也。”[13]58福泽谕吉重视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对梁启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福泽谕吉为了抵抗西洋列强的侵略,主张摄取西洋文明之精神,他认为要做到这点,必须自上而下地开展启蒙工作,即先使‘文明之气风充满全国’,使国民各自均能‘独立自尊’,然后在‘一身独立’的情况下实现‘一国独立’。梁启超到日本后,深受福泽谕吉的影响,也把自己的着眼点放到了人民的启蒙教育上。他非常重视福泽谕吉所说的‘独立自尊’,把它当成国家强盛之原动力。”[12]80梁启超还受福泽谕吉的野蛮──半开化──文明三段论影响,用“春秋三世”来解释福泽谕吉的的三段论,并且希望自己的祖国也尽快进入文明阶段。“梁启超到日本后,通过读日本之书,‘思想为之一变’。他认识到,若要使国家跨入文明阶段,首先要使民众具备文明之精神,在社会上要造成一种文明之‘气风’。”[12]82“梁启超所谓的使国与民之所以立的‘元气’,即福泽谕吉所说的‘一国人民之气风’,即所谓的‘文明之精神’,只是梁启超将福泽谕吉的‘气风’更加发挥,将其称之为‘精神之精神’而已,此外,在‘文明之形质’上,梁启超的观点与福泽谕吉毫无二致。”[12]71梁启超也模仿福泽谕吉把“文明”分为两个层面,提出“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14]1梁启超在《论自尊》一文中,推崇福泽谕吉的独立思想。《清议报》《新民丛报》上还曾经翻译刊登了福泽谕吉的《男女交际论》和《福泽谕吉语录》,可见,福泽谕吉对梁启超的重大影响。
福泽谕吉不仅对我国近代国学家梁启超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近代国学家康有为、章炳麟、王国维、黄侃、刘师培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激发了中国近代国学家的爱国之心,促进了中国近代国学家挖掘中国传统的精髓、整理国故;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国学家试图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改革封建主义旧弊端的思想发展。
(三)福泽谕吉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历史罪人
福泽谕吉在1882年发表《帝室论》,1885年又倡导“脱亚论”鼓动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扩张,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有很大关系,从而推动了天皇绝对政权的确立与军国主义的形成。在1875年福泽谕吉发表的《文明论概略》中,系统地阐述他的“国体”观,提出日本人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自己的“国体”。指出:“凡力图伸张本国的权利,使国富民强,提高本国人的智慧和发扬本国荣誉的人,称为爱国的人民。”[2]1751889年日本天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福泽谕吉于是把启蒙运动和民权运动所宣扬的民权思想,转化到了尊皇、崇皇的“国体”意识中了。福泽谕吉启蒙运动所主张的人权是有限制,这个限制即“皇权”。1871年(明治四年)明治政府就基本奠定了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基础,之后逐渐完备了“天皇”绝对统治的机构。1875年11月启蒙组织“明六社”解散。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人当时的任务就是保卫国体,维护日本的政权和独立。
福泽谕吉尽忠报国的尊皇思想不断地进展,以至于发展到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美国学者迈克莱恩分析:“教育家和报刊撰稿人福泽谕吉也为亚洲的形势感到苦闷。19世纪六七十年代,福泽谕吉鼓励全盘引进西方观念和制度。……然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当他为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而焦灼,转而思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诲时,福泽谕吉变得愤世嫉俗了。福泽谕吉坦白地说,以前他认为仁善公正的国际法主宰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现在他认识到,实际上世界根据丛林法则运行的,所有的国家都为了实力和财富而奋斗,强的吞噬弱的。他警告道,美国和欧洲的先进国家比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强大得多,西方的入侵会使亚洲遭受和非洲及中东一样的屈辱与毁灭。福泽谕吉警告,这个进程会直接危及日本。……福泽谕吉否认日本与中国、朝鲜一样,但是,日本怎样才能避免被西方的可怕力量碾碎呢?福泽谕吉为他自己的问题提出了两个答案。首先,他宣布,日本必须建立军事实力,必须随时准备动武。他写道:‘别人使用暴力时,我们必须以暴治暴。’其次,他主张日本必须鼓励亚洲邻国进行改革,以便经受住西方的冲击;如果他们拒绝,他认为日本应该强迫他们这样做。他向日本同胞说起这样一个寓言:居住在石屋里的人应该尽量劝说其邻居改建房子,但是假如‘危机在即,断然侵入邻居的地方是正当的,不是因为他觊觎邻居的房子或者憎恨邻居,他不过是想保护自己的房子免遭火灾。’1885年3月,在一篇发表于他自己的报纸《时事新报》上有影响的文章中,福泽谕吉重申了他的主张。……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其他有影响的作家更加公开地鼓吹帝国主义的益处。”[15]277-288福泽谕吉为了“不为别人的刀下俎,先为他人座上客”的思想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思想,可以说福泽谕吉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福泽谕吉站在了“国权主义”立场上,拥护“天皇制度”,倡导尽忠报国的道德教育,主张对朝鲜和中国进行扩张。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之时,其积极地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大造舆论,极力倡导“脱亚入欧”论。1885年他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脱亚论”,明确指出:“我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之东,但其国民之精神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引进了西洋之文明。然不幸的是邻国……今日之谋,我国已不可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共同兴亚矣。莫若脱其伍而与西洋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办法,不必因其为邻居而稍有顾虑,只可随西洋人对其办法对待之。”[16]313他的“脱亚论”,也给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人很大影响,推动了军国主义的发展。福泽谕吉还把中日甲午战争称为“文明和野蛮的战争”,并且为帝国主义战争的胜利欢呼雀跃,都显示了其军国主义倾向。可以说福泽谕吉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这一方面看,他成为了历史的罪人。
参考文献:
[1]福泽谕吉.劝学篇[M].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2]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M].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下][M].唐月梅,叶渭渠译.北京:开明出版社,1995.
[4]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M].杨永良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
[5]刘岳兵.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三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6]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历史[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福澤諭吉.半心半意ば不可なり[M].東京:岩波書店,1960.
[8]富田正文校訂.新訂 富翁自傳[M].東京:岩波書店,1991.
[9]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近代现代化[M].区建英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10]丸山真男.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M].区建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1]今井淳,小泽富夫.日本思想论争史[M].王新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2]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13]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4]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J].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议报).
[15]詹姆斯·L.麦克莱恩.日本史[M].王翔,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
[16]芝原拓自,等.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 12卷)[M].東京:岩波書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