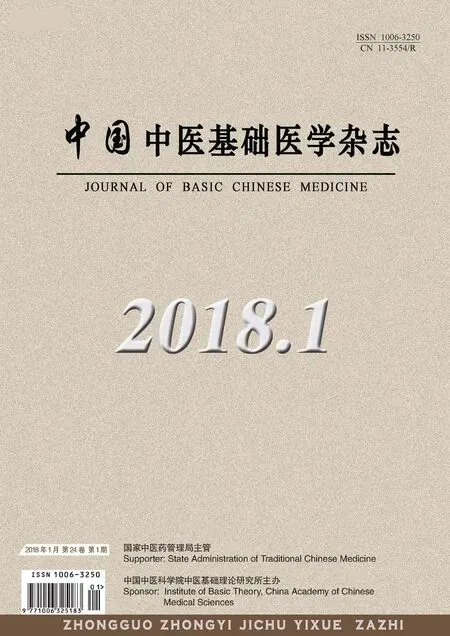五运六气疫病预测思路与方法探讨❋
杨 威,王国为,冯茗渲,杜 松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中医将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特点的疾病归之于疫病、疫疠、时行病、瘟疫等范畴,对疫病的预测原理与方法自成体系,百家争鸣,各具特色,其中五运六气相关的疫病预测方法颇具代表性。中医疫病预测的具体推演方法与预测结果见仁见智,尚需进一步探讨。本文仅探讨五运六气相关疫病的预测思路。
1 疫病预测以预知病机规律、确立辨治思路为原则
现代传染病学对传染病流行趋势的判断,较为依赖哨点疫情及病源报告(小样本抽样)、实报疫情汇总(大范围监测统计)的趋势分析、有效防控措施的实施进展(干预效率)、具体病源的传播流行认识等,倾向于监测型预测,以截断传播、降低发病为目标,强调病源、传染途径、易感人群三要素。
中医早已具备疫病传染性、流行性、易感性等基本认识,疫病的中医病名界定与疾病分类却一直存在学术分歧,却更重视对病机规律的认知和辨证防治原则的确立。中医疫病认识根植于天人相应的生命观、疾病观,强调人与天地之气相参,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化变,又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可“顺天察运,因变以求气”,可见中医对疫病的发生条件与发病流行规律的认识自成体系。
自然环境的非时之气乖戾或应时之气暴烈是疫病发生的重要外因。如《诸病源候论》[1]称:“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冰寒,为四时正气之序,民无疫疠之患。若冬时严寒,为应时之气暴烈,触冒而即病者为伤寒,寒毒藏于肌骨中不即病,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若春时应暖而反寒,夏时应热而反冷,秋时应凉而反热,冬时应寒而反温,为非时的时行之气,导致时行疫病。春分后至秋分前,天有暴寒而病为时行伤寒,又称时行寒疫;若冬有非节之暖为冬温之毒。
人体内在脏腑之气的不充沛、不均衡是疫病发生的关键内因。民国时期疫病专著《时疫温病气运徵验论》[2]认为,“按《内经》所论,瘟疫出于有时,人所共见,过时则无。温病乃个人之疾,所感者风寒暑湿燥火,乃天地六淫之常气。”疫疠与温病均属邪火致病,“盖瘟疫,天火也,由天之五运六气而生,谓之标病,出现有时,过期若失,由外而至,又谓之客病也……夫温病者,人火也,由人之五脏六腑而生,为本病,积于平日,由内而生,即主病也。”若精亏无水以济火,一遇岁气天火流行,外则疫焰熏蒸,内则温病乘机而发,内外之火会合,难逃疫疠之殃;若脏腑平和,虽外有疫焰之威,身无内匪,难惹外盗之侵;若五内有蕴热在先,偶值岁气融和,外无助火之薪,亦无妨害。因此岁气流火外因虽难避免,内因“人积温病深浅”却可自控,于未病之前避温病、节饮食、慎风寒,“即偶沾疫疠,可无性命之忧”,故“守身在我,何患于六气耶”!
社会环境的不稳定(如战乱、水旱虫灾、饥荒等)是疫病发生的诱发因素。清代温病大家吴瑭在《温病条辨》[3]原病篇叙气运以原温病之始,称“每岁之温,有早暮微盛不等,司天在泉,主气客气,相加临而然也。细考《素问》注自知”。“盖时和岁稔,天气以宁,民气以和,虽当盛之岁亦微。至于凶荒兵火之后,虽应微之岁亦盛。理数自然之道,无足怪者。”凶荒、兵火等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劣会严重影响人体脏腑之气,当脏腑之气因故虚衰与天地之气的偏盛偏衰达到特定利害关系之时,就易爆发瘟疫。
五运六气理论是以阴阳、五行、六气、干支等为纲目,将古代天文历法、气象物候、藏象病候等知识有机融合,以阐述自然、生命、疾病规律的中医经典理论,用以揭示天地阴阳之理、四时之气变化以及一岁阴阳客主等[4],因而具备推演四时气候变化“常”与“变”的功能,又可推演与天地变化相对应的人体脏腑之气变化。《宋太医局诸科程文格》[5]称:圣人“虑庶民为众邪之所害,乃随上下客主之加临,预立寒热温凉以为治,使疾疢不作,灾害不生,同跻于仁寿之域矣。”形气相感,损益以彰,上下相召,盛衰以著,故医者依五运六气“察其所在而施于药物”“审当其所宜,而施于方治,和其运而调其化,折其郁而资其源”,高者抑之以不致太盛,下者举之以不致太衰,上下无相夺,气运得于平治,百姓远离疫病危害。
通过五运主岁之太过不及、六气司天在泉及主客之气变迁、运气加临以及胜复、郁发等格局推演,结合气候、物候、藏象、病候的特征描述,得出自然应时之气、非时之气盛衰及其对人体脏腑之气影响的相应推断,形成有关疫病流行趋势、证候特点、防治原则的推论,进而求证于实际气候、物候、脉象、症状表现及辨证论治的符合情况以修正完善,采取生活调适、药物调理等措施趋利避害,以顺应天地之气之常、规避其变,纠脏腑之气之偏、补其不足,从而降低疫病发生与流行[4]。因此,基于五运六气的中医疫病预测分析,倾向于推演型预测,以预知病原病机规律确立辨治思路,从而降低病邪损害、以提高防治措施针对性为目标。
2 基于五运六气的中医疫病预测方法
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6]阑入的运气七篇大论基本奠定了中医五运六气推演格局,《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及历代医家阐发使疫病的五运六气格局推演得以不断完善,并在疫病防治医疗实践中发挥其应有作用。如宋代政和七年(1117)起,宋徽宗“公布次年运历,示民预防疾病”,并推行天运政治,逐月颁布“月令”以教导民众;宋代《圣济总录》、明代《普济方》等详列六十年运气变化图文,以知常达变。在历代疫病诊治著作中,也有获益于五运六气格局推演的疫病防治验案,还有以五运六气格局推演为纲目的疫病防治方剂配伍与用药大法[7-8]。
五运六气理论首先以纪年干支确定岁运的太过不及、六气的司天在泉,各年对应的气候、病候详载于《素问》。五运六气为天地阴阳之理,先立其年以明其气。《宋太医局诸科程文格》解释:“运则有五,随其化而统于年;气则有六,因其岁而纪其步,分司天、在泉之殊,别左右间气之异”,平和则物阜民康,乖异则物衰民病。如庚寅(2010)年,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耳无所闻。纪曰坚成,其化成,其气削,其政肃,其令锐切,其动暴折疡疰,其德雾露萧瑟,其变肃杀雕零,其病喘喝胸凭仰息。少阳相火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咳嚏、鼽衄、鼻窒、疡、寒热、胕肿;厥阴风木在泉,风行于地,尘沙飞扬,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
五运六气理论再以六气的主气、客气分别阐述自然的正常变化与异常变化。主气为常,客气为变,次依客主之气立六气治法。以“正月朔日”为初之气,依次六气轮替。“天气运动而不息则为之客,地气应静而守位故为之主”。主气为常,静而守位,应节候分布,依次为木、君火、相火、土、金、水位。客气随司天而递迁,且司天应于三之气动而不息,依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之序递迁。气候异常(非时之气)与民病流行随客气而变化,治六气之药各依客气立法。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庚寅“初之气,地气迁,风胜乃摇,寒乃去,候乃大温,草木早荣,寒来不杀,温病乃起,其病气怫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等。
细考《素问》,瘟疫好发之时的客气为少阴、少阳。《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记载:辰戌之岁,初之气,民厉温病。卯酉之岁,二之气,厉大至,民善暴死;终之气,其病温。寅申之岁,初之气,温病乃起。丑未之岁,二之气,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子午之岁五之气,其病温。己亥之岁,终之气,其病温厉。各岁瘟疫好发之时的客气为少阴、少阳,用药主张咸补、甘泻,咸软、酸收,以免大剂苦寒药冰覆闭邪之虞。据《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9]初步统计,汉建武元年(25年)至清宣宗道光五年(1825年)之间明确标注疫情月份或季节的瘟疫资料,《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论诸岁诸气的瘟疫发生率略高于每岁六气平均发生水平,其中丑未岁二之气(30.2%)最高,寅申岁初之气(25.9%)次之[10]。
基于五运六气格局的疫病预测推演方法,还需参考客主加临、胜复郁发、升降迁复、三年变疠化疫等相关内容,其核心为自然天地之气的自我平衡修复,先胜必复,郁极乃发。如《黄帝内经素问遗篇》所述三年变疠化疫,提示刚柔失守、迁正失序所致疫病发生规律,亦属于自然环境非时之气致疫的具体预测推演方法,是对五运六气基本格局的一种补充。在五运六气格局基础上,结合已知的气候、物候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与适当修订,可提高疫病预测推演的准确性和针对性。
五运六气格局在提示自然环境非时乖戾之气、应时暴烈之气变化规律的同时,还反映出受自然天地之气影响的人体脏腑之气的变化规律,如四时之气对藏象的影响、胎运禀赋对体质的影响等,从而使疫病发生、流行的理论推导更为精细复杂[4]。“气运虽有定数,犹有变焉”。在运用五运六气格局推演疫病流行趋势时还需知常达变,结合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因人辨证制宜,若因循于单一的分析模式或偏颇的理论解读,偏偏难免预测偏差。
3 戊戌(2018年)五运六气预测举隅
依照五运六气基本格局推演方法,综合考虑戊戌年岁运、司天在泉之气、主客气等五运六气基本格局特点,兼顾四时初、盛、末变化及节候特征,兹述戊戌年时气规律如下。
3.1 天地之气变化规律
火运太过的赫曦之纪,气化运行先天,当为蕃茂火盛之象,阴气内化,阳气外荣,炎暑施化,物昌政动,炎灼妄扰,暄暑郁蒸,甚则炎烈沸腾,雨暴而雹。若太阳寒水司天客气过旺则抑制运火,天政气肃,阳令徐行,泽无阳焰,火郁于内,易于少阳相火主气之时发之,火动雨散,泽流湿化。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岁半之前,太阳寒水天气主之。若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若运火炎烈,雨暴而雹。岁半之后,若湿淫于内,埃昏岩谷,易见阴郁,黄反见黑。
初之气,主气少角厥阴风木,客气少阳相火,初春升温较快,春风早拂,草木早荣。二之气,主气太徵少阴君火,客气阳明燥金,燥热相遇,大凉反至,寒潮反复,时暖时凉。三之气,主气太徵少阳相火,客气太阳寒水,天政布,寒气行,冷热交争,凉雨阵作。四之气,主气少宫太阴湿土,客气厥阴风木,土木相刑,风湿交争,易风雨交织。五之气,主气太商阳明燥金,客气少阴君火,阳复化,凉爽怡人,草木茂盛。终之气,主气少羽太阳寒水,客气太阴湿土,阴凝太虚,埃昏郊野,寒湿重浊,雪雾较多。
3.2 藏府证候特点
一是岁运之化,火气流行,心气旺盛。若火炎于内,易耗劫津精;若火为寒水客气所制,易外寒内火,郁极乃发;二是岁运所主,易从火热而化;上半年司天所主,易从寒化,或寒热交织;下半年在泉所主,易从湿化。
3.3 疾病、疫病特点
火运之岁,病本于心,易见笑、狂妄、疟、疮疡、血流、目赤等邪伤害神明、血脉之症。若运火炎烈,易见胸腹满、手热胕挛腋肿、心澹澹大动、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嗌干,甚则色炲明艳、渴而欲饮等火热之象。
上半年若司天寒淫,易见痈疡、厥心痛、呕血血泄、鼽衄、善悲、眩仆等外寒内热之症。下半年若在泉湿淫,易见饮积、心痛耳聋、浑浑焞焞、少腹痛肿、腰腿拘滞等湿困脾土、下肢之症。
2~3月升发较盛,内热易扰,易见温厉、温病、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等,发热温病高发。4~5月寒热反复,火气遂抑,易见气郁、中满、中寒等风寒感冒高发。6~7月时有外寒内热,易见寒反热中、痈疽注下、心热瞀闷等急症危殆。8~9月风湿交织,易见大热少气、肌肉足痿、注下赤白等,夏季感冒、心腹病、脊骨病好发。10~11月燥湿相兼,秋燥不甚,凉爽舒适。12~1月寒湿较重,体感凄惨易见受寒感冒夹湿。
3.4 辨治调养要点
地气胜天气,天气虚调治宜先资化源以助水化,抑其运气扶其不胜,无使暴过而生疾,食玄黅之谷以全其真,避虚邪之气以安其正,药食宜苦以燥之温之,适气同异多和制之。岁运与司天客气相异,调治宜以燥湿化,药食宜上苦温、中甘和、下甘温。
上半年宜辛平,佐甘苦、咸泻、和其寒热。下半年宜苦热,佐酸淡、苦燥、淡渗,化其湿浊。
六气各随客气为治,初之气宜咸补、甘泻、咸软,岁谷宜玄,二之气宜酸补、辛泻、苦泄,三之气宜苦补、咸泻、苦坚、辛润,四之气宜辛补、酸泻、甘缓,五之气宜咸补、甘泻、酸收,终之气宜甘补、苦泻、甘缓,无犯司气之邪。
基于五运六气的疫病预测,以预知病原病机规律,确立辨治思路为原则,对天地之气、藏府证候变化规律的预判,有助于提升中医疫病防治能力。同时,疫病预测的复杂性、干扰因素的多变性均影响理论预测结论的精准程度,仍需立足于继承、发展,古为今用,不断创新,才能使中医疫病预测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健康期待。
[1]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39-60.
[2] 李天池. 时疫温病气运徵验论[M]. 广州:维新印务局,1919:12-13.
[3] 吴瑭.温病条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2.
[4] 杨威,白卫国.五运六气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
[5] 宋太医局诸科程文格注释[M].李顺保,校注.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6] 王冰注,宋·林亿补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7] 杨威,刘寨华,杜松.五运六气经典集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
[8] 杨威,于峥,鲍继洪.五运六气珍本集成[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
[9] 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6-105.
[10] 杨威,于峥.温疫与六气之少阴、少阳的探讨[J]. 北京中医药杂志,2009,28(10):778-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