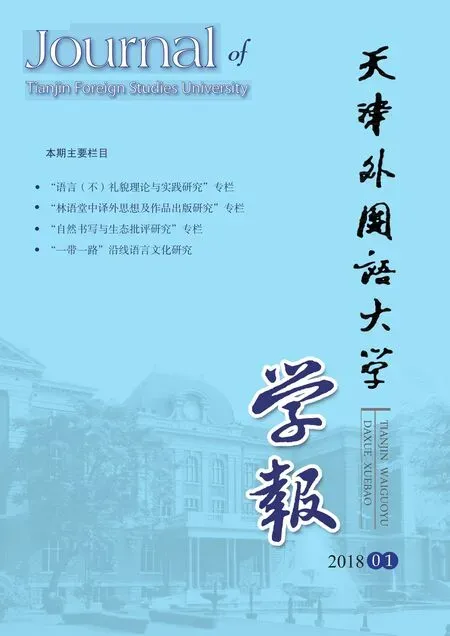《话语、政治与女性全球领袖》评介
李 珺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J. Wilson & D. Boxer. 2015.Discourse, Politics, and Women as Global Leader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60.
一、引言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乏女性领导者的身影,她们和男性领导者一样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过(或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话语、政治及女性全球领袖》这本书中提及的女性政治家就包括英国的萨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智利的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丹麦的赫勒·托宁-施密特(Helle Thorning-Schmidt)、澳大利亚的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中国香港的林郑月娥(Carrie Lam)、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等。这些作为领袖的女性如何通过将合作式话语转换为强势语言成功保持了她们作为专业人士的地位是该书两位主编想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收入该书的13篇论文分四个部分,分别从“领导者的话语特征”(第一部分)、“话语、媒体与权力”(第二部分)、“领导权、身份与公众”(第三部分)、和“领导风格塑造”(第四部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下面先介绍各章的基本内容,之后对该书在女性话语研究方面的贡献作一简单评论。
二、内容简介
第一部分“领导者的话语特征”由三章组成。第一章讨论了英国前首相萨切尔夫人的话语。撒切尔在演讲中通常选择较低的音调,以使她的声音更深沉,同时采用被认为具有进攻性和斗争性的讲话风格。这些话语特征一般都是男性政治家的话语特征。但是这一章的研究表明音调低沉可以被公众信任,而进攻性强的讲话风格则是英国众议院的特征,并非男女有别。本章得出的结论是撒切尔夫人的话语特征并不说明她是一个女性,而是说明她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第二章“打破玻璃,留住屋顶——拉丁美洲女总统的话语实践”分析的语料来自两位拉丁美洲女性领导人:智利女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与阿根廷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是一名单身母亲,她当选后强调消除社会阶层之间的区别。阿根廷女总统的当选被看成是丈夫权力的延续。这一章对这两位拉丁美洲女性领袖的话语风格进行分析,探索她们走向总统职位的话语实践。
第三章分析了丹麦女首相在代词使用上的特征。这一章的语料来自两家电台:一个是丹麦本国的丹麦语访谈,一个是BBC HARDtalk节目的访谈。本章认为,女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在使用代词方面虽然没有受她女性身份的影响,但也是她构建自己身份的一系列因素之一。
第二部分“话语、媒体与权力”由第四至七章组成。第四章“作为政治话语的推特——以萨拉·佩林为例”分析的语料是萨拉·佩林(Sarah Palin)的1 000条推特的推文。推文展现了她传统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保持着过往选美冠军的身材,同时采用了蓝领男性的话语特点。她将工薪阶级男性的演讲风格直接用书面方式展现出来,近乎于一种视觉化的方言。她只使用闪笑(wink smiley)这个表情符号,使其在不断传播和使用过程中逐渐失去原本的意义,变为一种复杂的、微妙的感情意味。使用表情符号的人意在使用它的言外之意,同时也向使用者提供了一种矢口否认的机会,让传播的内容意义在观众中自我发酵。佩林在推文中大量使用缩写,以此为自己创造非正式的发声方式,从而躲过了严肃的负面抨击。她还技巧性地采用了视觉方言和半禁忌词汇。佩林从2008年起开始使用推特,并以此在公开政治环境中争取到一席之地。她通过推特表达自己的观点,支持其他竞选人,并获得了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的机会。尽管佩林并非实力候选人,但她在推特上的粉丝数量跟希拉里·克林顿几乎一样(超过一百万),成为一部分政治势力的公众代言人。
第五章“性别与突尼斯的政治话语”以范戴克(van Dijk)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如话语如何产生霸权成为利益集团行使权力的工具,以及语言如何被用来挑战权力和改变权力的分配等。在突尼斯,女性话语作为男性话语的另一面被置于从属的地位,女性领导人的出现另很多人感到震惊。在女性成为真正的政治参与者之后,男性开始要求女性回归家庭,承担生育角色。在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声音被认为是一种性唤醒,许多不同主题的电视辩论最后都演变为关于女性身体、面纱、全脸面纱、一夫多妻制、离婚、堕胎以及女性运动为主题的谈话。突尼斯国内本身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成为研究女性话语的土壤。这一章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提出五个问题:(1)在电视辩论或政治环境中,是否认为女性感染力较小并更容易被说服?(2)更信任男性政治家还是女性政治家?(3)女性政治家所采取的政治话语与男性政治家的是否相同?(4)女性政治话语风格是否存在?(5)左派、自由派、伊斯兰派和共产党派的女性政治家在话语、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别?问卷语言为法语,通过邮件和人工方式发送给突尼斯一所大学中不同系部的老师和学生,其中教师100名(男女老师人数各半)和学生100名(男女学生人数各半)。只有50人传回了问卷(28名女性,22名男性),女性调查者的答案通常包含一定长度的细节,男性受访者的回答通常较为简短,有时答案只有是或否。而20到30岁的伊斯兰教学生受访者中的大部分都给出了带有性别偏见的回答。这一章的研究表明突尼斯女性在政治领域是无声的,这种无声是很明显的。
第六章“朱莉娅·吉拉德的愤怒”选取了六家澳大利亚主流报纸的报道作为语料,从福柯关于实践系统地构成演说的客体这一论题出发,围绕双重束缚(double bind)、非智人(an unintelligible being)及实践性别(doing gender)展开分析。朱莉娅·吉拉德面对双重束缚(double bind)的挑战,女性领导人被群众赋予厚望,希望她们能展现典型的男性特质,同时保持女性化特点。吉拉德曾被性别歧视者在媒体中冠上“非智人”的称号,她谴责自己所遭遇的女性厌恶经历,重新将自己定位为连接性的政治权力。在澳洲主流媒体对吉拉德的报道中,她的当权过程被描绘为一种无情的个人野心行为,媒体希望吉拉德能展现更符合其性别特征的行为。不断有人质疑吉拉德是否拥有领导者的强悍能力,她未婚无子的状态也引来了不少批评。吉拉德最终打破沉默,回应了性别歧视问题,她关于女性厌恶的演讲(The Misogyny Speech)更是引起了媒体的分裂和讨论。保守派的媒体认为,她借势女性话题,玩弄政治手腕。但吉拉德关于女性问题的回应也为遭受性别歧视的女性政治家提供了支持,让女性政治家在澳大利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里得以重新出现。
第七章“政治及媒体中的女性——喀麦隆女性领袖合作的话语构建”选取的语料集中于2012年上半年,分别是两篇媒体评论,原始语料为法语。从女性新闻记者与女性政治领导人的关系入手,一方面分析女性记者影响自己的新闻同事,另一方面分析女性记者通过媒体话语来创作一个对女性参政更宽容的环境。在非洲媒体中,女性记者日渐活跃,与女性政治家互动合作,普遍相信女性政治家能实现更多的性别改变。
第三部分“领导权、身份与公众”由第八至十章构成。第八章讨论分析了希拉里·克林顿在2008年总统竞选过程中应对突发事件的话语策略,语料来自YouTube上关于此次事件的四个记录性质的视频。或许是因为厌女症在政治环境中被正常化,希拉里在市政厅的演讲不断被打断,起哄者甚至高喊“给我熨衬衫!(Iron my shirt.)”希拉里采取的策略是避免与闹事者有眼神接触,走离闹事者所在区域,并试图用更高的声音压过闹事者的声音。她拒绝了与闹事者发生对话的可能性,避免与闹事者进行正面冲突,侧面提醒工作人员对闹事者进行管制,直到闹事者的牌子被收走,让她重新获得了全场观众的注意力。
第九章“美国州长辩论——场景的、话语的、可转变的身份之作用”对来自10个州的女性州长在电视辩论中的话语进行分析。她们在这些辩论中试着向大众展现一个可信的、知识渊博的官方形象,在提问环节中她们维护自己的身份,并通过不同的语言策略来创建自己未来的领导人形象。
第十章“后殖民时代香港的女性领导人话语”讨论了林郑月娥和刘慧卿这两位妇女参政者的话语实践。林郑月娥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现任行政长官,在被任命为总秘书之前曾为香港政府工作了30年,可以说除了特区首长外,她是香港最有权力的女性。刘慧卿曾任记者,1991年成为首位当选的女性立法会议员、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及前线政党前召集人,1989-1991年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这一章的语料来源于2010-2013年间她们在立法委员会发表的公开演讲,一共有三份语料,两份语料是刘慧卿的议会演讲,一份是林郑月娥的新闻发布会。文章所选用的分析框架来源于斯科隆(Scollon)和弗劳尔迪(Flowerdew)的有用话语(utilirarian,西方话语)和无用话语(孔子话语,东方话语)。斯科隆对东西方话语体系作了详尽的解释,认为西方话语体系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崇尚理性和自由;东方话语体系来自孔子的思想体系,看重权威、和谐和社会秩序。西方的话语多包含平等权利,演讲中会出现冲突;东方的话语通常包含阶级观念,在表达上更为间接。刘慧卿的话语多选用“我们”而不是“我”,并多次出现感叹词,试图唤起听者的参与度与情感。林郑月娥的话语选择更为官方,语气正式,打磨圆滑,在她的语言中没有任何关于女性特质的记号存在。与刘慧卿相比,她的话语无性别,并带有真诚和官方特质。两位女性领导人都成长于同样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但两人的话语策略却大不相同。
第四部分“领导者话语风格的塑造”是该书的最后三章。第十一章讨论了默克尔及其权力驱动领导风格的媒体话语。这一章关心的问题不是默克尔在媒体中如何代表女性,而是新闻话语如何操纵性别这一概念,具体关注媒体报道中对默克尔的称呼、媒体报道中对默克尔衣着和行为的描述及政治决策的制定。在媒体报道中,默克尔经常被称为总理,媒体也经常在强调她的理性时提到她科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身份,谈到政治风格时她被称为改革总理及经济总理。默克尔也经常被标记为女性,如第一位女性总理、默克尔女士、有远见和勇气的女性、德国的母亲。在现有的词汇中对女性政治领导人的描写词汇相当有限,经常被局限在关于家庭生活的想像之中,导致媒体报道用母性的、养育型的词汇去形容默克尔在政治方面的功绩。在政治领域默克尔通常被看作是有权力的女性,但即使是带着这样的身份,默克尔仍然体现出女性是男性的附属支持者。在对衣着和外形的报道上,2008年4月12日在奥斯陆举办的国家剧院开幕式上默克尔穿着一件低胸礼服,在媒体中引起轩然大波,可见权力与女性特质的并存状态并不是被广泛接受的,而是极易在媒体话语中引起反感和讨论的。传统权力经常在报道中与男性特质联系起来,当媒体把默克尔描述成权力政客时经常用与男性相关的词汇。该项研究表明女性领袖是可以得到认可的,但获取认可的可能性存在于一个性别化的系统中,强调了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成功。
第十二章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通过讨论芬兰报纸对芬兰女性领导人的报道揭示女性领袖在芬兰媒体中的形象以及媒体对芬兰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刻画。定量研究的语料来源于2008年芬兰发行量最大的四家报纸,共计11654篇文章。定性研究的语料来源与定量研究相同,从中选取了对两名芬兰女性政治家的报道,时间跨度为2008年一至六月。定量研究发现即使除去关于首相的报道,剩下的关于男性议员的报道仍是女性议员的一倍之多。同年男性议员的图片在报纸上有3337张,女性议员的图片仅有1014张。媒体并非性别中立机构,尽管芬兰女性比其他国家女性更早获得了选举权,女性参政的时间也因早于其他国家而使得芬兰被看作是模范国家,但是对于性别的理解媒体的再生产还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十三章探讨了媒体对利比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的形象建构。约翰逊-瑟利夫2006年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位由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女总统,之后在2011年11月成功连任。2011年10月7日,她与活动家莱伊曼·古博薇(Leymah Gbowee)及也门活动家塔瓦库尔·卡曼(Tawakkul Karman)因维护妇女权益共同获得201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一章的分析语料是2005年和2011年两次总统竞选期间的各150篇报道,分别出自非洲、北美、欧洲、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媒体。在非洲的媒体报道中,约翰逊-瑟利夫的身份多是联盟党的领袖,一个没有性别的角色。美国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重新当选总统后的机遇和挑战。有20%的媒体将约翰逊-瑟利夫称为祖母。在英国媒体的报道中,她最常被提起的身份是一位66岁的哈佛毕业、前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官员。在意大利媒体报道中,她被描述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铁娘子、四个孩子的母亲、六个孩子的祖母。这一章的分析或许说明当越来越多的男性不再需要专业背景知识就可以进入政治领域,女性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却在经历着严苛的审核。
除了这13章内容之外,本书的两位主编还共同撰写了引言和结论。在引言部分,威尔森和鲍克瑟以英国议会为例讨论了女性在西方政坛从政的现状,指出从 1918年起英国女性就已经获得了以候选人身份参选下院议员的权利。但是近一百年过去了,一共只有253个女性有幸进入西敏寺成为议员。现在虽然在总体数目上已经实现了增长(尽管仍是限制性的增长),英国上下议院中女性占 22% 的比例表明女性参政人数在总体比例上仍远远低于男性。原因在于女性所拥有的品质则往往是软弱、合作和善良,而这与政治似乎格格不入。这种二元对立的看法一旦被人们接受,就会渗透到投票习惯中,影响女性所能涉足的政治工作。在话语方面,男性和女性的话语风格不同,男性语言常常与地位、权力联系起来,女性语言常被与迟疑和退缩联系起来。究竟是女性天生的语言特性导致她们在政治地位中的弱势,还是所处的弱势政治地位导致女性选择了相对不确定的语言?采取合作话语的女性政治领导者在公共生活中所刻画出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在政治领域里女性参与者采用了男性特有的话语特征,还是推广女性话语,或者说对话语风格的选取态度远远比简单的男性、女性话语风格更为复杂多样?如果民众接受两种风格,是否说明政治话语并不局限于青睐任何一种性别?所有这些问题为本书的内容作了实质性的铺垫。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两位主编对引言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总结,指出随着女性领导人走进政治参选,民众对参选者的外貌、声音和行为的解读发生了变化。话语在女性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当她们试图适应由男性话语主导的政治环境时,她们的话语方式和话语策略对她们形象的建构以及成功从政都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然而,威尔森和鲍克瑟也指出,书中的各项研究结果并没有表明女性政治家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媒体在报道女性政治领导人时也没有摆脱对性别的固定化概念,而是将传统男女概念应用到对她们的行为和外表的解读上面。这种现象在吉拉德和默克尔的例子中都有体现。在面对传统性别概念的审视时,女性政治家有选择作出回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撒切尔选择了隐去她的女性角色,将自己的政治家身份放在首位,从而成功在男性政治环境中得到了支持。而当吉拉德希望被作为政治家看待时,她的性别却被标记并被作为攻击她的武器。
三、简评
阅读全书深切地感受到两位主编对女性领袖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在全书的结尾他们为女性参与政治提出两点建议:(1)提出更多的女性议题,这样可以寻求代表妇女和解放妇女的权力;(2)提出平等这样的一般性政治议题,这样女性政治家与其他政治家一样宣称代表全体民众。这样的人文关怀,或者说是社会关切,实际上也是这本书被收入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的话语研究》系列丛书的一个原因。这个系列丛书强调(批评)话语研究的理念和原则,如坚持基于语言学分析的跨学科研究,推崇从社会问题而非语言现象出发进行研究的传统,提倡话语研究促进社会变革的社会关切(田海龙,2016)。《话语、政治及女性全球领袖》成为这个从书出版的专著或主题文集的第63本,充分体现了话语研究的这些理念和原则。
《话语、政治及女性全球领袖》这本书另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同样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看,是它关注话语、政治和全球领袖性别问题的独特视角。诚然,语言与性别是一个广泛的研究课题,如拉考夫(Lakoff,1975)关于男女性别语言特点的研究、奥巴与阿特金斯(O’Barr & Atkins,1980)关于性别语言特征与权力地位的关系研究、沃达克(Wodak,1997)关于女性语言与女性身份话语建构的研究以及蔻慈与卡梅荣(Coates & Cameron,1989)根据言语社区理论对女性语言的研究。但是,本书将女性语言聚焦在全球领袖这样一群有权威的女性身上,讨论她们的语言与女性政治家身份的关系,进而分析她们的从政风格,考察女性话语风格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领域中如何通过语言合作来实现政治抱负,在语言与性别研究方面仍然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因此,本书不仅对话语研究和女性身份研究是一个贡献,在全球化以及更多的女性参与政治的背景下对政治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致谢:作者感谢导师田海龙教授。他为研究开设的“话语研究导论”及“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与流派”两门课程激发了我阅读该书的兴趣。感谢导师对此书评初稿的修改和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和指导。
[1]Coates, J. & D. Cameron. 1989.Women in Their Speech Community[C]. London: Longman.
[2]Lakoff, R. 1975.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M].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3]O’Barr, W. & B. Atkins. 1980. “Women’s Language” or “Powerless Language”? [A]. In S. Ginet, R.Borker & N. Furman (eds.)Women and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d Society[C]. New York: Praeger.
[4]Wodak, R. 1997.Gender and Discourse[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5]田海龙. 2016.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J]. 外语与外语教学, (6): 1-9.
——以“把”字句的句法语义标注及应用研究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