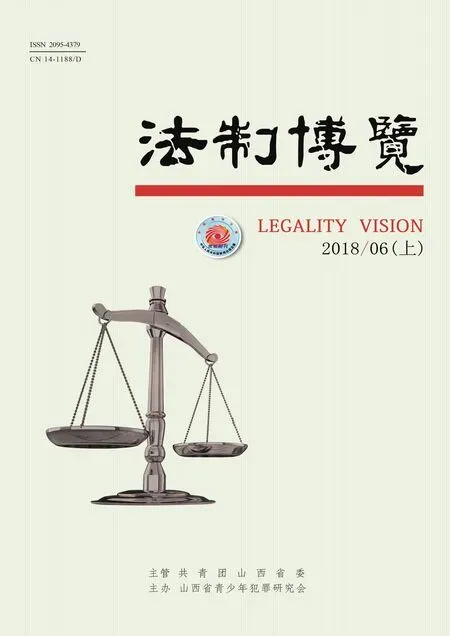网络直播平台与政府协同治理模式构建论
周雯露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000
2016年被称为“网络直播元年”,网络平台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尔后2017年监管政策的急速收紧迫使直播行业逐渐回归理性;而2018年开年来直播答题又一风口的出现再次凸显了直播行业“野蛮生长”的特点。直播内容低俗、存在法律风险等顽瘴痼疾仍存,直播行业的现状迫使我们重新反思该领域治理模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在行政法领域,政府、平台和行为主体之间会产生三种法律关系,其中政府和平台间的关系最为瞩目,政府要求平台承担一定的监管义务,这种类似于“行政授权”的行为一直饱受争议,学界试图用“民营化”、“公私合作”等概念定义该行为。[1]平台以私人主体身份执行公共任务,在此特殊情形下该如何厘清政府与平台间的责任边界,是二者协同治理模式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本文着眼于直播平台与政府协作治理模式,在行政法领域审视公私合作在我国本土化的问题,明晰政府和私人主体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责权利,分析行政法边界拓展带来的艰巨任务。
一、治理责任的重构及实践困境
(一)现行法中的政府及平台的治理责任
截至2018年3月,已出台的与网络直播相关的法律法规近十部。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先行,法律如《网络安全法》几经修改,最后得以施行。由于网络市场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法治进程,立法显得十分被动。
笔者进行归纳后,总结出了现行法中政府和平台各自承担的主要治理责任。政府责任主要集中于通过行政许可限制市场准入、通过“双随机一公开”进行定期抽查、以行政处罚等手段进行事后惩治等方面,而平台承担更为具体的责任,包括管理用户和内容发布者、监控直播内容、配合政府执法、提供违法信息并备案、健全用户举报投诉渠道等。
(二)直播平台的行政法责任——借助“第三方义务”等理论分析
1.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及动因
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公共管理运动使得公私合作渗透至秩序行政领域中,私人主体会基于政府的要求或者自我规制行业发展的需要逐渐融入以政府为主导的规制框架中。[2]
“第三方义务”[3]即是指具有中立性的私人主体强制要求执行监管任务以协助政府进行治理。该种义务具有强制性、惩罚性以及公益性的特征。我国政府规定的各直播平台应当履行的行政义务与“第三方义务”基本相符。此外,还有被学界频繁提及的“民营化”、“公私合作”等概念也是直播平台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的理论基础。“民营化”可以分为功能民营化、程序民营化等,将私人主体定位为配合者或者辅助者。而公私合作则是强调政府与私人主体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实现公共利益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政府相关部门强化平台责任的动因是借平台优势减轻执法压力,可从实用主义和规范两种角度予以解释。[4]实用主义角度结合“守门员理论”分析,网络平台在治理过程中属于成本较低的违法行为的控制者。规范角度则是指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平台从行为主体的违法行为中获益,同时作为信息框架的提供者客观上为违法者提供了便利,所以应当承担一定的义务。
2.实践困境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这种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首先,直播平台的不中立性。根据笔者对直播平台盈利模式的考察,流量变现是直播平台盈利的主要途径。理论界对平台的定位从“单纯通道”到“内容框架提供者”,再到“公共承运人”以及“守门人”的转变,[5]侧面印证了网络平台不中立性的现实。平台的不中立性的核心通常体现在干预流量方面,阻碍其恪守监管义务。
其次,直播平台对公众私人权利的侵害。平台在执行公共任务时势必会减损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掌握的所谓“私权力”[6]性质不明,没有完善的救济措置与之对应。在行政诉讼法尚未涵盖该种特殊“行政主体”时,平台用户只能基于其与平台所签订的民事合同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且由于无法苛责私人主体肩负与政府部门同等的行政责任,严格遵循正当程序,有效监督平台的问题也应当成为重要议题。
(三)政府的保障责任
1.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基于过往社会治理的经验,在整体制度设计中,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和责任类型不会影响国家保障者的角色。[7]互联网领域的“去中心化”式的治理模式并非要求政府将自身边缘化,反之,治理模式的转型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秦伟教授引入了“保障国家”、“后设规制”等概念阐述国家在将治理机制扩展至私人主体时应当承担的保障责任。[8]繁重的社会规制任务要求政府采取弹性化、间接化的规制,在尊重自由经济市场的自我规制的同时予以积极的引导和调和。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当掌控程序正当性,保障私人主体的营业自由也保障平台用户的基本权利,且尽可能减小私人主体对治理过程造成的损害。为保持新兴产业的活力,政府应当保有谦抑的治理态度,但不可僭越的基本行政法原则则要求政府守住底线,在复杂的治理过程中找准位置,以灵活手段及时调整治理方向。
2.实践困境
首先,治理手段单一、僵化。政府部门的治理手段仍然较为单一,对直播平台及具体的违法者的规制手段限于事先审批,事中运动式抽查以及事后运用公权力惩治等刚性手段,不擅长使用柔性规制手段,如激励性规制和非正式责任机制等。不注重公私主体间的互动,仍表现出政府向私人主体的单向“合作”方式。
其次,对平台的定位出现偏差,明确引导阙如。政府未能对平台的能力进行准确的定位,造成一系列负面后果。首先,政府所设立的审核标准十分模糊,“九不准”标准沿用至今且并未精细化,可量化标准较少。而具体审核中违法事实十分复杂,标准的具体适用需要专业解释和具体分析,这已超出了一般平台的审查能力。平台将承担不合比例的注意义务,此时若强行审查,将会导致大量错判结果,遑论将违法行为削株掘根。其次,根据《侵权责任法》,平台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观要件是“明知或应知”,实践中平台常被推定为“明知或应知”违法的直播内容。面对庞杂的直播内容,平台信息处理技术并不具绝对优势,难以做到实时监管。
再次,与行政法治之间的差距。我国政府热衷于“运动式治理”的定期抽查模式,使得执法过程缺乏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在正当程序方面,政府部门未在此领域建立有效的公共参与或者专家咨询的渠道,过程性控制不足。
二、治理方向
(一)明确义务,明晰责任
由于直播平台需要承担大量的主动监控义务,为确保实效性,政府部门应当参照平台的技术能力明确违法信息的判断标准,提供明确的负面清单。同时为保障相关用户的知情权,应将此类清单公示。而面对需要具体分析的违法事实,则应当采取现行法中的“通知—删除”模式,由平台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保障相关用户的正当权利。
(二)建立平台激励机制
政府部门应当促进私人主体在执行公共任务的同时将日常市场行为与公共目标更好地融合。被我国长期忽略的非正式责任机制,即日常奖惩机制,也应当更多地运用到治理过程中,以回应平台作为市场主体的合理诉求。当前政府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形式对平台进行抽查,其实是变相地设定直播行业的黑名单系统。而除了负面的威慑性措施外,政府也应从正面有效激励守法企业,如公开正面典范的名单,并适当赋予市场机会和财政奖励。
(三)引入多方治理主体
为防止直播平台滥用权力,在治理过程中寻租,在传统的政府规制之外,可引入第三方主体对平台进行监督,提高规制的全面性,形成相互制衡的稳定状态。
私行政法主张将执行公共任务的私人主体纳入到行政主体的范畴。私人主体也应受行政权限的限制,受平等原则、比例原则等一般原则的约束,受公民基本权利的约束。政府应当为私人主体设置明确的程序要求,将监管义务具体化,防止公法价值的实现因私人主体的特殊身份受到阻却。同时也应当建立完备的用户救济体系,防止基本权利受损者求告无门。
引入第三方主体监督实则也是引导社会自我规制的重要步骤,除建立完善的用户举报奖励机制之外,还应充分提高行业组织和行业协会的自律性,鼓励行业协会通过自律公约进行自我约束。将“软法”[9]与“硬法”相结合,完备治理手段。
三、结语
社会规制手段随经济市场的发展而流变,而治理问题的庞杂迫使与此密切相关的行政法重新审视公与私、政府规制与社会自我规制之间的关系。将社会力量纳入公共治理的末梢,国家面临的新行政任务不容轻视。公共治理为我们展现的图景十分美好,公私角色间的壁垒被打破,传统规制者的规制手段显得更为灵活。[10]但将其融入中国实践,道阻且长。无论如何,合作治理的模式势不可挡,应当充分发挥私人主体灵活、迅速回应行业动态的特点,夯实公权力机构保障功能的落实。由国家政府平衡公益与私益,保障私人主体和其他相关主体的正当权利,引导各方主体共同实现公益目标,实现行政法治的理想。
“野蛮生长”的直播平台和政府间的协作治理可谓是互联网领域合作治理的典型,前者为后者带来接连不断的规制挑战。结合直播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其正朝向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相信只要不断完善治理模式,该行业会呈现更为良好的发展态势。
[1]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J].中国法学,2015,5:73-98.解志勇.互联网治理领域中的平台责任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5:102-106.胡敏洁.合作行政与现代行政法发展的新方向——读《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J].行政法学研究,2012,2:134-135.
[2][德]贡塔·托依布纳.反思性的法——比较视角中法律的发展模式[A].[德]贡塔·托依布纳.魔阵·剥削·异化——托依布纳法律社会学文集[C].泮伟江,高鸿钧,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66-267.
[3]高秦伟.论行政法上的第三方义务[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1:46-56.
[4]赵鹏.私人审查的界限——论网络交易平台对用于内容的行政责任[J].清华法学,2016,6:122-124.
[5]解志勇,修青华.互联网治理领域中的平台责任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5:103;高薇.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承运人规制[J].政法论坛,2016,34:84.
[6]周辉.平台责任与私权力[J].电子知识产权,2015,6:37-43.
[7]王瑞雪.论行政法上的治理责任[J].现代法学,2017,39:35.
[8]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J].中国法学,2015,5:87-91.
[9]秦前红.网络公共空间治理的法治原理[J].现代法学,2014,36:15-26.
[10][美]朱迪·费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M].毕洪海,陈标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