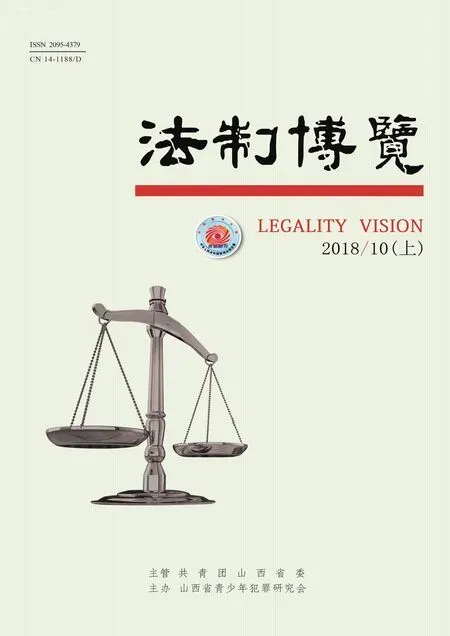论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
王旻昊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由此可见其将侵权行为视为债的发生依据之一,但一百二十条又规定“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从这一规定看,民法总则似乎又认为侵权人因其侵权行为所承担的应是相应的责任而非侵权之债。
一、责任的含义
自从亚里士多德将被当时司法认可的行为规范系统化并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加以论述后,责任便成为了哲学、神学的主要论题之一。其所称的“责任”在本质上是顾后的。但事实上还存在着前瞻性的责任,即人们有一种为他人的目的或一件事情而采取行动的义务。此两种责任都有“应当负责”的含义,但事前责任还具有一种内在的促使和禁止某一事件产生的目的。
二、伦理学上和法学上的事后责任的差异
法律上的事后责任要求行为人必须解释和证明其过去的行为符合现有社会规则——这种社会规则是存在于行为人主观之外的。而伦理学视角的事后责任则要求行为者要解释和证明他相对于自身所承认的或者自身所认识到的道德准则,并且其行为能够符合这种规则的要求。换言之,法律责任是社会强加的;而道德责任则表现为行为人自律的结果。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区别出行为人对于道德责任的承担与法律责任承担其心理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对于道德责任,是在于行为人明确的感觉到其过去的行为根本有违其自身所信仰的传统、价值观或权威,该行为与其内心确信的矛盾在其内心产生了某种不适,这种不适使得行为人主动承担道德责任以图修补或恢复其行为带来的后果——不限于造成的损害。当其恰当地承担道德责任之后,他会在内心得到满足和不适感的消除,这反映出行为人的自律与自觉。而法律责任则并非如此,一方面,行为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下并不一定同样需要承担道德责任。这是因为,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权威存在于行为人之外,而评判其是否需要承担道德责任的权威实属行为人内心确信,行为人的一定行为很可能并不有违行为人内心信仰的传统、价值观、权威,却被外部权威评价为不合理或不适当。另一方面,行为人承担法律责任的动机与道德责任相比实在有很大不同。我们上文说到行为人在承担道德责任的目的在于实现内心的完满和消除不适,而相对于法律责任则更多的体现在对于法律的消极评价与法律上的不利后果的不安上,行为人在为一定被法律认为是不合理或不适当之行为后,可能并不会给行为人本身带来道德上的矛盾和不适,但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依然主动承担法律责任是依据行为人自律这一理由所无法解释的,这也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个体,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人,他首先要关注的是个人的利益,并且这对他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对于其他人的利益只会给予有限的关心。因此,其不可能主动损害自己的利益以求得他人利益的完满。行为人之所以会主动承担法律责任——这在很多时候都表现为对自己利益的损害以补偿他人受到损害的权益——是因为行为人知道针对其行为法律会对其课以相类似或更为严重的惩罚,并且当行为人意识到法律责任中所包含的特殊强制力使其无法逃避这种责任的承担时,其才会考虑主动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行为人在主动承担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方面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也就应当能够清楚的认识到一些学者所言的“法律责任并不具有强制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三、观察我国的责任理论体系
我国学界将权利、义务、责任作为基础概念构建我国民法学理论体系。但笔者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明显对于权利、义务和责任之间逻辑关系的错误。其没有考虑到责任的产生要后于义务,义务仅仅是作为责任产生的一个要件,义务的违反才可能产生责任。反映在侵权法中,那么就应该说只有在侵权人对其因侵权行为所应负担的对受损害着的债务的给付义务不履行时,方得追究其债务不履行之责任。
另一方面,我国民法依“不法行为”侵害的对象划分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责任一语的适用。并且我国采用“侵权责任法”这一表述也体现了责任的适用,因为在此种情形下,对某种权利的侵害直接导致了责任的产生,即行为人对他人绝对权的侵害会直接导致其承担责任,而不是在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产生为一定给付行为之债,在此债得不到履行的情况下才追究侵权人的责任。
——以《民法典》第1182条前半段规定为分析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