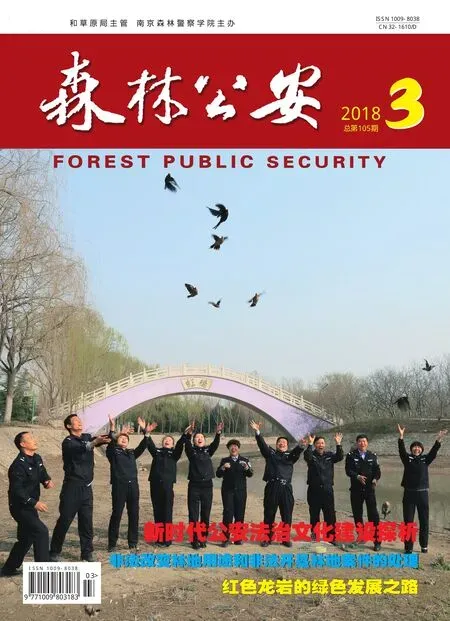对于“一地两证”引发的毁林行为之定性分析
——从物权法视角看犯罪对象的属性对刑事立案的影响
陈 玲
随着林权改革的深度推进,司法实践中民事主体可以通过受让、承包、租赁、互换、入股等诸多方式取得林权。一般情况下,林权个体都会通过林权登记机构办理林权证以确保自己的林权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但由于权利个体法律意识差异或者登记机构变化调整、工作疏忽等原因,导致流转的林权因未经登记无法受到物权保护或者重复登记带来保护冲突的情形时有出现。本文就后一种情况结合真实案例进行探讨,以期增强林权证的权威性、提高林权改革质量、保障林权改革顺利进行。
一、案情介绍:
2001年,某市开发区某村村民陈某通过林改承包经营该村的集体荒山52亩并办理了林权证,经营期限30年。2011年,该市××公司通过林地流转方式租赁了该村750亩林地种植油茶,于2012年办理了林权证。由于相关部门在办理林地流转过程中存在一定瑕疵,导致××公司林权证确定的林地范围包括了陈某承包经营的山场范围。2012年,××公司开始在林地上种植油茶,陈某见状提出异议,但××公司未予理会。2015年,陈某在自己承包林地范围内××公司种植的油茶林中种植白茶。2018年3月,陈某将××公司种植在争议林地范围内的1260株油茶砍掉,价值约42万元。
面对该案中价值42万元的油茶被砍伐的法律后果,对陈某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在实践部门产生了许多不同观点:有的认为应当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有的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还有的认为陈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当作为民事纠纷处理……具体到本案的细节,破坏生产经营罪所强调的“由于泄愤报复或其他个人目的”主观要件在陈某身上的体现不够明确。陈某砍伐生长中的油茶虽看似破坏生产经营,但由于其只是将自己林地范围内被××公司栽种的有争议的油茶砍伐,并未破坏××公司所属无争议林地范围内的油茶生产经营活动,客观上争议林地范围内的白茶生产经营活动反而更有保障,所以认定破坏生产经营罪有失偏颇。争议较大的还是故意毁坏财物罪和民事纠纷之说。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公司在陈某林权证拥有的52亩林地使用权范围内栽种1260棵油茶的行为合法性及油茶的权利归属问题。如果××公司依据后取得的林权证也能合法享有案涉争议林地的使用权,那么其在自己享有使用权的林地范围内栽种油茶自然取得油茶及其收益的所有权,进而对陈某为了自己经济利益而砍伐毁坏油茶的行为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则顺理成章;相反,如果××公司对案涉争议区域不具有合法的林地使用权、油茶又归陈某所有,那么首先陈某客观上并未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其次陈某的主观方面也欠缺“毁坏”的故意,其动机更准确地说是出于对于自己合法利益的保护,则对陈某的行为就不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性。
二、在争议林地上栽种油茶的行为合法性分析
关于××公司在争议林地上栽种油茶行为的合法性,由于该公司所取得的林权证颁发于2012年,其林地使用权范围包含了陈某2001年取得的林权证中的林地面积,对于这重叠区域的林地使用权问题,无论是陈某基于承包取得的林地使用权,还是××公司基于租赁取得的林地使用权,性质上都属于我国《物权法》中规定的用益物权。所谓用益物权就是通过对他人的物进行占有、使用以取得收益的排他性权利,其权利的享有和行使必须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前提。虽然都是他物权,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有所不同。我国担保法理论相对完善也是建立在物的担保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加之物的价值大小、担保方式的不同以及是否对物直接占有的差异成就了一物可以设定多种担保的情形,为解决一物之上各种担保权利的实现顺序之矛盾,《担保法》及司法解释专门做了具体规定。但用益物权以直接占有标的物为常态,和担保物权相比较,用益物权具有更强的排他效力,除个别情况下基于权利行使方式不同出现同性质的用益物权之间并不排斥的情形外,在同一个物上无法并存两个以直接占有为内容的用益物权。
在本案中,很显然陈某对林地的使用权和××公司对重叠区域林地的使用权完全属于内容性质相同的直接占有、使用权利,这就决定了重叠区域的林地上只有一个使用权是合法的。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也强调“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依据不动产物权登记公示原则,陈某2001年办理的林权证标志着其对争议林地的用益物权发生了可以对抗任何第三人的效力,也就是说陈某的林地使用权2001年已经基于承包经营合同而设立,假如其未曾申请办理林权登记而面临××公司2012年取得林权证的情况,则该区域的林地使用权由××公司享有,陈某只能依据承包合同行使债权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正是陈某办理的林权登记产生了对抗××公司的效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司对争议林地不能依据错误的登记行为产生合法的用益物权。××公司在陈某向其提出异议后并未向登记部门提出异议登记、变更登记请求或者向司法机关提起行政诉讼,而是直接在争议林地上栽种了油茶,其无视争议栽种油茶的行为实质上也忽略了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应该对损失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从行为本身来看,由于陈某和××公司均基于对公示的林权登记行为之信赖行使用益物权,不能断定行为实施当时哪一方主观上存在过错,因而笔者认为认定哪一方的行为构成侵权都不准确。但是基于物权公示之对抗效力,可以排除××公司对争议区域林地的使用权,进而其在不享有使用权的林地上栽种油茶行为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三、在他人林地上所栽种油茶的权利归属
对于××公司在陈某所享有使用权的林地上栽种的1260棵油茶的权利归属问题,笔者认为,××公司在争议林地上栽种油茶苗目的是获得油茶收益,如果其对争议林地享有用益物权则取得收益理所应当,基于前面的分析由于××公司不具备合法的用益物权则收益也无从谈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国物权法理论中,所有权的取得无论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都不认可这种方式,因此××公司虽然对当初购买的油茶苗拥有所有权,但对生长在他人林地上产生一定收益的油茶并没有必然取得所有权的合法依据。相反,当××公司将油茶苗栽种在陈某享有合法使用权的林地上,随着油茶在生长过程中产生更多的财产价值及生态价值时,油茶与土地已经形成了添附,而作为动产的油茶苗与土地不动产形成添附之附合后,应当由油茶所附着之土地使用权人即不动产物权权利人取得油茶的所有权。我国《担保法》第九十二条明确将林木列为不动产,也是因为树苗生长后产生了财产和生态复合价值继而与土地不宜分离的原因。虽然《物权法》及其司法解释对非使用权人在他人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土地上栽种的林木及农作物作为附着物归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所有并无更详细的规定,但从所有权原始取得之添附的规定可以合理解释案涉1260棵油茶收益权的归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司法实践也只有如此处理才能避免鼓励在他人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上种植林木并得以请求土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购买所种植林木的情形发生。
分析以上争议焦点可知,笔者其实是认同陈某砍伐油茶的行为应当作为民事纠纷处理的观点,由于其作为不动产用益物权人依据添附而取得油茶所有权,所以也应当依添附理论同时给予××公司适当的合理补偿。
还有观点认为即使是可以由陈某最终享有所有权的油茶,在砍伐时也可能会受到采伐许可的限制。由于有些省的林木采伐限额管理办法将油茶这种小乔木也纳入森林资源采伐限额管理,需要办理采伐许可证才能采伐,所以陈某的行为就有滥伐林木之嫌。笔者认为,陈某2015年就在自己享有使用权的林地上种植了白茶,2018年才对油茶进行砍伐,其主观上明显是将油茶视作影响白茶生长收益的杂枝野草等有害作物一般予以清除,客观上也并未直接造成国家森林资源法益被侵害的后果,因此也不宜认定为滥伐林木行为。诚然,如果探讨双方矛盾之合法有效的解决路径,笔者认为无论是陈某还是××公司都应该依据《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选择公力救济途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虽然我国的法律体系也还允许适当的合法私力救济存在,但也仅限于适用条件严苛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必要的自助行为。文明社会的立法宗旨还是引导权利主体尽可能的采取公力救济来维护自己合法利益。
四、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的立案困惑及相关建议
对于这样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作为林业案件的执法机关,确实应该在客观合理分析行为的属性,有时甚至包括行为对象的基本属性之后再做出相应决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面临的困惑在于,类似于本案情形的双方权利外观都合法,而自己又不是具有最终确认权的主体,在界定不清时又直接影响案件性质导致立案困难。面对一宗地两本林权证的情形,公安机关自然会感到棘手。本文旨在论述对陈某行为的定性分析,更多的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加以思考。实践中依据基本的法律规则和相关证据,对于可以明确的案件事实,公安机关应该做出常规的判断,比如本案中对争议区域林地的使用权;如果是现有证据不足以明确,依据基本法律规则也不能做出常规判断的情形,公安机关面临受害人报案一方面需要做出相应处理,而另一方面案涉犯罪对象的基本属性只能取决于司法机关的认定时,比如本案涉及的油茶权利归属问题,公安机关不可能等到当事人先就案涉犯罪对象的归属有了生效的司法判决再确定是否予以立案,况且财产归属作为民事主体的基本财产权利,是否先以诉讼的方式主张确权取决于民事主体个人。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又不允许案件受理部门以类似事由予以推托,否则也可能会导致行政不作为的后果。对此,笔者认为还需要考虑公安机关的职责所在,毕竟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公安机关承担的是对涉嫌犯罪立案侦查的职责,确定构成犯罪与否是人民法院的职责。至于在无法明确陈某所砍伐油茶归属于陈某所有的前提下予以立案,审判过程中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对争议焦点做出准确判断之后,再进一步做出有罪判决或是无罪判决则取决于司法机关对法律依据的准确适用。换句话说,笔者在探讨本案油茶的权利归属问题时纯粹是以物权视角适用相应的法律依据及法律原则做出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