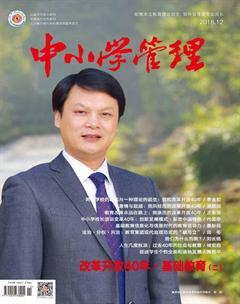走向内涵更加丰富的选择性:中国高考改革40年的主线①
摘要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考改革的历程,选择性理念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2014年启动的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再一次把选择性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导向,从考试科目、考试次数、志愿填报方式等多个方面来推动。应对选择性导向面临的严峻挑战,高考改革需要重视增加教育资源的投入,加强学生、高中和高校的能力建设,解决选考科目的可比性等考试本身的技术问题。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周年;高考改革;选择性;“新高考”;走班教学;等级分制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18)12-0036-03
自1977年国家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以来,围绕考试内容与形式、科目设置、考试技术、录取方式等方面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各个时期的各种条件下,这些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在维护社会公平、选拔人才、引导高中教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近年来,社会上对高考改革的一些举措提出批评,认为是“翻烙饼”“新瓶装旧酒”,但如果据此认为高考改革就是瞎折腾,则显然是欠妥的。理性看待高考改革走过的历程,需要对改革系列举措的内在联系有清晰的认识,需要对形式变化中的内在线索有深刻的把握。其中,选择性无疑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一、丰富高考选择性的探索历程:科目设置的调整与变化
其一,“文六理七”模式的形成。选择性集中体现在高考的科目设置上。1977年教育部发文规定,高考分文、理两大类,共同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3门,文科加试史地(史地合为1科),理科加试理化(理化合为1科)。1978年,高考文理科共同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外语4门,外语成绩不计入总分(报考外语专业除外),理工类加试物理、化学,文史类加试历史、地理。1981年,理工类考生要求加试生物。[1]至此高考在科目设置上形成了“文六理七”模式。短短几年之中,高考科目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数量的增加有利于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但实际上学生只有文理两个选择。由于高考的高利害性和对教学强有力的导向性,这种科目组合模式给高中教学和学生知识结构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极端的片面追求升学率行为和偏科现象。如何在保证选择性的基础上避免偏科,成为教育界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
其二,增加科目设置类别及选择性的思路渐成共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场全国范围的高考改革大讨论开展起来。其中关于高考科目设置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意见主张分七八类或十四、五类,每类考不同科目;一种意见主张根据各科类学校、系、专业的不同要求,设20~30个考试科目,即使同一学科也可以有不同类型的试卷。例如:根据中文、新闻等系的特点设“语文1”,根据法律、财经等系的特点设“语文2”,根据理、工、农、医等系的特点设“语文3”,根据中医对古汉语的要求设“语文4”等;各高等学校的系、专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选定若干个考试科目。[2]这些意见和建议既注重学生的选择性,也注意到了高校招生在科目上的选择性,体现了双向选择的内涵,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非常有远见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很有借鉴意义。
随后,国家教委委托若干省和高校分别开展了大量研究,形成了高考改革的系列报告,对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举措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各种报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所差异,但这一次高考科目改革大讨论的价值在于使得“增加科目设置类别及选择性的改革思路成为一种普遍共识”。[3]1989 年,国家教委在《关于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及录取新生办法的意见》中又提出:考试科目分为必考和选考,其中必考科目为语文、数学,选考科目包括政治、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各高等学校根据其专业特点,提出1~2 门选考科目建议。国家教委在综合各校建议的基础上,将高考科目编排为若干组,供高等学校及专业招收新生考试时使用。这一意见是对前期探索的一个重要总结,更是强调了选择性在考试招生制度中的重要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围绕选择性的有关改革举措继续出台,一些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试点。1990年10月18日,国家教委公布了《关于改革高考科目设置及录取新生办法的意见(试行)》,提出高考科目分为四个类别,即第一组:政治、语文、历史、外语;第二组:数学、语文、物理、外语;第三组:数学、化学、生物、外语;第四组:数学、语文、地理、外语。可见,原来文理分开的做法开始被打破,这是在推进选择性上的一个标志性举措。1991年,湖南、云南和海南开始试点,这一改革方案也被简称为“三南方案”。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方案并没得到推广,三个省的探索也很快被叫停。
其三,“3+X”再次把选择性推向高潮。1999年,《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明确提出在科目设置上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推行“3+X”科目设置方案。“3”是指每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都必须考语文、数学、外语3科,“X”指的是每一位考生必须从政治、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6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确定1科或幾科,这些选考科目由高校根据办学层次等要求来指定。其中,综合科目是指建立在中学文化科目基础上的综合能力测试。这一举措“使学生和高校具有较大的选择权,也兼顾了统一性和选择性”,[4]受到普遍欢迎,很快得以在全国范围推广。
需要指出的是,在推进“3+X”改革过程中,各省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变式,如上海的“3+1+X”,但仍旧体现了选择性的基本导向。然而,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双刃剑,“3+X”的科目设置造成了高中教学组织困难、选科文科化倾向、科目之间难以比较等现实困难,加上新课程改革提出的一些新要求,最后促使不少省份开始逐步回归“大文大理”的模式。
二、“新高考”改革赋予选择性新内涵:重塑高中教育生态
高考改革在追求选择性的道路上可谓充满艰辛。尽管在科目设置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也在短期内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其原因极其复杂,有政策层面的,也有技术层面的,更有社会认知层面的,根本上还与高考的高利害性有关。改革中的很多利弊难以回避也难以取舍,但是增加选择性作为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始终没有被放弃。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正式启动。从具体的改革内容上看,选择性教育理念渗透其中,浙沪两个试点地区在多方面的举措体现了这一基本的价值导向。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考试科目改革,也就是目前形成的“3+3”高考模式,即语文、数学和英语为必考科目,在选考科目上,浙江实行“7选3”,上海实行“6选3”,学生可以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技术(仅浙江省有)中任选3科,其成绩与必考科目加总得到高考总分。“6选3”有20种组合,“7选3”有35种组合,这与传统的“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模式有着天壤之别。同时,高校在招生时对有关专业提出选考科目的要求,作为学生决定选考科目的一个依据。这一制度设计扩大了学生对科目的选择权和高校对学生的选择权,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个性,也有利于高校专业性人才的培养。[5]
另一个充分体现选择性的改革举措是志愿填报。在目前广泛实施的平行志愿录取模式上,浙江和上海均采取了平行到专业的做法,从数量上来看,在本科批次上考生可以填报的志愿大幅增加,浙江考生最多可以填报80个志愿。可以说,这一改革举措对选择性的弘扬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我国高考改革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更加关键的是,与传统的平行志愿相比,它把考生的选择权下沉到了具体专业上,考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实现了考生专业性向与专业学习之间的无缝对接。
2014年启动的这一轮高考改革,是对本世纪初高考改革所倡导的选择性理念的一次升华,而且是在深刻理解选择性内涵基础上作出的理性决策。在多个场合,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来自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提及本轮高考改革时基本上都认为这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6]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选择性所带来的。与已往的改革举措相比,本轮高考改革选择性的内涵更加丰富,体现选择性的举措涉及考试科目、考试次数、志愿填报等多个方面,选择的主体涵盖了学生、高中和高校。选择性带来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教育阶段或某一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整个高中教育生态的一次重塑,也系统推进了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工作。
三、坚守高考改革选择性导向面临的挑战:保障经费、完善管理、提升能力
从理论上讲,选择性的教育理念早已有之,经过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相关理论更加成熟,实践也更为丰富,目前已成为当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从这一点来看,本轮高考改革所坚持的基本方向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走向选择性的过程却非常艰难,在已往推出的改革中有一些举措实施不到两年就停止了。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本轮高考改革从多个方面来倡导选择性,尽管力度空前,但挑战仍旧严峻。
首先是教育投入的保障。众所周知,高考科目改革后,由于学生科目选择的多样性,走班将成为高中普遍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这对学校的教室数量、师资提出了更高要求。据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的统计,2017年普通高中平均班额为52人,全国普通高中专任教师177.4万人,生师比13.4∶1。在一些中西部省份,甚至一些相对发达地区的县级高中,大班额的情况更严重。即使在不实施走班教学的前提下,这一问题已经非常突出。校舍的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来解决,而师资的增加还受制于人事、编制、社保、职称等一系列因素,仅仅依靠教育部门很难解决。2018年下半年,一些原计划进入新高考改革的省份纷纷推迟,现有办学条件不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次是相关主体的能力建设。这主要包括学生、高中和高校三个主体。对学生而言,如何进行科目选择已经成为一个高利害性的难题。这方面的选择既要考虑现有的学业成就、兴趣爱好、特长等,还需要了解高校在人才选拔方面的要求、各专业的就业和发展前景等。而且,这些问题需要学生一进入高中就认真考虑,因为这会影响到个人学习资源的分配。对此,尽管不少高中开展了生涯教育,但成效并不显著。学生的选择能力依旧面临很大挑战。对高中而言,由于走班教学的实施,学校教学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班级的学情异常复杂。这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持续的专业发展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极大地增加了学校管理的难度,如教学质量如何把握,教师绩效如何评价,教研活动如何组织,等等。这些指向的都是高中教育领域的深层次问题,目前大部分还处于探索之中。对高校而言,改革后面临的一个现状是考生知识结构的差异化。高校针对不同专业提出的选考科目要求仅仅针对少数专业,大部分专业没有严格限制。因此,同一个专业的学生,其选考科目也会有较大差异。高校的教学工作、人才培养方案有着较大的改进空间。
最后是解决选考科目的可比性。科目选考是保障选择性的根本措施,但各科目成绩之间的比较也随之成为一个难题。为了保证科目成绩之间的可加、可比,一种全新的计分方式—等级分制度被采用。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可比性,也减轻了分分计较的压力,但也带来了不好的导向。在等级分的计分方法中,不同等级考生的人数按预先设定的比例来确定。这使得选考科目的成绩不仅取决于原始的卷面成绩,还取决于同时参加考试的学生数量。由于各选考科目的课程内容、试卷难度、学时等方面的天然差异,等级分制度给予考生和高中在选科上一定的博弈空间,一些本身比较难的科目,如物理的弃选现象严重,而其他一些科目选考的人数大幅增加。这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有关试点地区也出台了一些补救措施,但仍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1] 羅立祝.高考科目设置改革对高中教育的影响[J].中国考试,2015,(9).
[2] 教育部学生管理司,本刊编辑部.《改革高考分类、科目设置与计分比例讨论》结束语[J].人民教育,1984,(7).
[3] 刘希伟.高考科目改革的轨迹与反思:基于选择性的视角[J].全球教育展望,2018,(4).
[4] 章建石.关于选考科目等级赋分的改进:历史经验、现实限制与可能方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
[5] 苏红.对浙沪高考改革试点后中学“选课走班”的调查与思考[J].教育测量与评价,2018,(5).
[6] 辛闻.教育部:招考制度改革着力解决违规招生等现象[EB/OL].(2014-09-04)[2018-11-14]. http://news.china.com.cn/2014-09/04/content_33427847.htm.
注释:
①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院级青年专项课题“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对学校管理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课题编号:GYD2016013)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