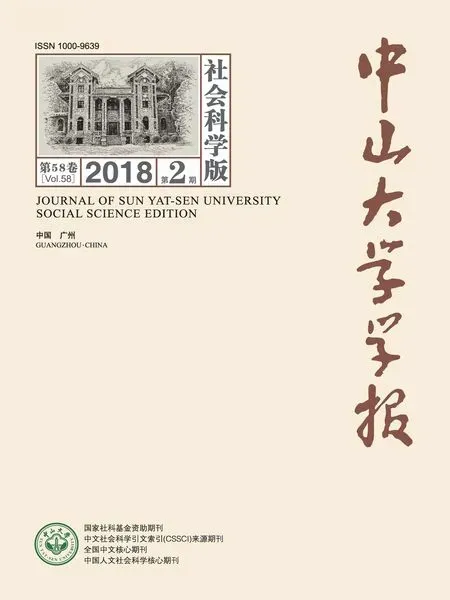晋武帝时期的政治生态与皇室赋诗活动
来森华
西晋皇室成员大多短于文才,“既未曾作出任何理论性的提倡或引导,亦无可能在文学创作上率先垂范”①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56—257页。,但是喜好利用其尊位积极组织赋诗活动。西晋皇室赋诗活动频繁举行,究其原因,除大量的文士聚拢在各级皇室成员身边可为其提供智力支撑外,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也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此类赋诗活动多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并且随着当时政治生态的变化,其动机或主题又呈现出诸多差异。从史籍记载与现存应制诗两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武帝、惠帝、怀帝、愍怀太子以及成都王司马颖等人都曾组织过赋诗活动。其中由于武帝在位时间(265—290)相对较长且当时政权内部相对稳定,这一时期皇室赋诗活动更为频繁,不同阶段、不同场域、不同皇室成员均有赋诗活动,可作为分析当时政治生态与赋诗活动关系的典型。
一、武帝初治与泰始四年华林园赋诗
经过两代三祖的不懈经营,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司马氏集团到了司马炎手里即迅速地复制了当初曹魏代汉的方式改朝称帝,改元泰始。泰始四年(268),晋武帝在华林园宴请王公大臣时进行了第一次赋诗活动。《文选》“公燕诗”类选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一首,李善注引《洛阳图经》曰:“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园,齐王芳改为华林。”又引干宝《晋纪》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园,与群臣宴,赋诗观志。”又引孙盛《晋阳秋》曰:“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86页。《晋书·文苑列传》亦云:“帝于华林园宴射,贞赋诗最美。”③④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92,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0,2406页。至于应贞诗为何最美,唐修《晋书》中的“史臣”如是评价道:“至于应贞宴射之文,极形言之美,华林群藻罕或畴之。”④很显然,他们认为应贞诗胜于形式。不可否认,出身于文学世家的应贞在此诗中呈现出的宏大结构、华丽辞藻、典雅风格等确实有可称道之处,但是仅从这一个方面去体认就难免失于偏颇,更何况应贞诗作为现场应制之作在形式上也并非没有瑕疵,如其诗在结构上各章并不完全工整。笔者认为,此诗之所以能够夺魁,不但“形美”,最主要的还是“志美”,即诗中所言之“志”高度契合了武帝欲观之志。“赋诗观志”源于春秋时期,是中国诗学的重要传统。在华林园集会中,当政治领袖并不是同时以文学领袖的身份出现并能够率先垂范进行创作时,所观之志自然就偏重于对赋诗者政治态度与立场的考察,反言之,赋诗者所言之志亦是对尊者政治意图的领悟。
四言颂体赋成的应贞诗中所言之志,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前三章称颂晋室继皇统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此属尊帝位;中间三章赞扬武帝具有帝王之相,并在即位后树德建功,此属彰帝功;其三,赞美文武大臣之前各司其职,又训诫诸位以后不要懈怠,此属显帝威。那么,以上之志又何以赢得满座喝彩、拔得头筹呢?或许结合武帝即位诏书就会其意自明。制于泰始元年(265)十二月的《即位改元大赦诏》有云:
制诏御史中丞等:昔朕皇祖宣王,圣哲钦明,诞应期运,熙帝之载,肇启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缉熙诸夏。至于皇考文王,浚哲光远,允协灵祗,应天顺人,受兹明命,仁济于宇宙,功格于天地。肆魏氏弘鉴于古训,仪刑于唐虞,畴咨群后,爰辑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弗敢违,遂登坛于南郊,受终于文祖,燔柴班瑞,告类上帝。惟朕寡德,负荷洪烈,允执其中,托于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惟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心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以弼宁帝室,光隆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案,误作“体”,据《晋书》改)祚。其大赦天下云云。①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2,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474页上。
上引诏书依次表达了三层大意:首先通过颂美三祖功德而强调晋室继承大统系“应天顺人”、遵循上古之制;其次武帝谦称自己寡德少功,虽登皇位但惴惴不安、没有底气;最后希望王公大臣像辅佐先王那样弼宁皇室、成就帝业。不难看出,应诗与此诏在主题架构上颇为相似,只不过应诗在更进一步强调晋室享祚的合理性的同时,自谦的寡德少功变成了颂美的仁德丰功,对待臣下的语气亦由期许变成了训诫。个中缘由,与受禅三年以来的政局变化息息相关。武帝受禅虽有守成之嫌,但登基后能够励精图治,主要表现为存仁恕之心、弘俭约之风、举贤良方正、纳直言之士、勤务农功、勉励学者、恪守礼数、制定律令等。到了泰始四年,武帝治世有了初步成效,皇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时需要一个媒介对此予以充分表达。作为君臣宴会之作,站在皇家与尊者的立场,应诗顺应了歌功颂德的需求,帝位得以牢固,帝功得以彰显,帝威得以强化,故能称美于时。
从当时的诗歌评比环节看,此次宴会所赋之诗断然不止应诗一首,惜今存者不多而无法窥其全貌。然根据诗歌内容可以断定荀勖《从武帝华林园宴诗》亦为同时之作,一则诗中有“天施地生,以应仲春”两句,时间上吻合;二则诗中所呈现的内容与应诗有高度相似之处,尤其诗中“其庆惟何?锡以帝祉”两句是对前面所论述的尊帝位、授帝德、显帝功、扬帝威之赋诗动机的有效印证②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2页。按,荀勖又有《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五言一首,“逯案”有云:“此与上篇为同时之作,盖一用四言,一用五言也。”笔者认为逯氏案语误,因为四言中有“天施地生,以应仲春”两句,而五言中却言“清节中季春,姑洗通滞塞”,依“仲春”“季春”之别可以明显看出非同时之作。。另外,王济《从事华林诗》今存“郁郁华林,奕奕疏圃。燕彼群后,郁郁有序”四句③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2,第597页。,亦很有可能为此次宴会所作。
关于此次华林园赋诗的评价,梁代萧纲曾云:“晋集华林,同文轨而高宴。”④萧纲:《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序》,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21,第1929页。时修亦言:“到泰始四年,可以说到了整肃诗赋的时候,应贞诗正好顺应了晋武帝的这一要求,武帝以此诗为众诗中之最美者,实际上树立了朝廷、公府等重大场合诗歌的四言形式、颂赞、训诫基调和典雅风格。之后西晋的侍宴诗,不论是侍愍怀太子,还是侍成都王宴诗,大致都沿此套路而下。”⑤俞士玲:《西晋文学考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就价值或影响而言,以上评价没有问题,但是也应充分认识到,从根本上讲,武帝并不是为了整肃诗赋而举行这场赋诗活动,“赋诗观志”中包含着明显的政治动机,尽管客观上这场活动确实起到了整肃诗赋的作用。简言之,泰始四年武帝华林园赋诗非为同文轨而文轨同。另外,前贤时修没有注意到的是,此次赋诗活动实开赞颂武帝之先河,除去后期的赋诗活动进一步光大之外,还可根据当时制作礼乐歌诗的情况予以印证。据《晋书》记载,晋初食举所用歌诗依旧沿袭魏时所用之《鹿鸣》,荀勖等认为其“未知所应”,故到了泰始五年(269),也就是应贞去世的当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①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2,第3册,第685页。,而后成公绥亦应诏创作。这些礼乐歌诗从文辞层面观之,极尽颂赞武帝之能事,“圣皇”“圣帝”“我皇”“天子”等尊称莫不加于武帝之身。而从创作时间看,较之泰始四年的华林园赋诗活动晚了至少一年。
综上而言,此次赋诗活动顺应武帝登基后励精图治的政治背景,在巩固帝王威严的同时拉开了颂赞武帝的序幕。
二、平吴庆典与太康二年华林园赋诗
今存武帝时期应诏诗又有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程咸《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诗》两首,根据诗题看创作背景甚是清楚,即作于平吴后在华林园举行的庆典之上。但是,学者普遍将此次赋诗活动的时间系于吴亡当年,即太康元年(280)②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93页;陈文新总主编,汪春泓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两晋南北朝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时修立论者更是不出此误区,笔者之前疏于考证从而导致行文时亦随陈说,认为此次赋诗活动于平吴当年举行。,笔者认为不妥。关于吴国灭亡的确切月份,史书记载不一,有三月壬寅(十五日)说,有四月说,前人对此例举甚详③详参陈力:《西晋灭吴时日考异并中华版〈晋书〉校勘体例商兑》,《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9期。。姑且不去深究二说何种确切,因为结合诗题“平吴后三月三日”之说,均可证明太康元年三月三日庆典赋诗在时间逻辑上说不通。另外,吴未平而举行庆典更不符合武帝的行事风格,《资治通鉴·晋纪三》载:“朝廷闻吴已平,群臣皆贺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④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81,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567页。又《晋书》载太康元年事云:“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帝谦让弗许。”⑤⑥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3,第1册,第72,73页。从武帝慎重、谦让地对待平吴之功这一点观之,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提前举行庆典赋诗就更加不可能。那么,此次庆典赋诗活动更有可能在次年即太康二年(281)三月三日举行。关于此年此月之事,《晋书》载曰:“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诏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⑥可见次年三月依旧在处理平吴后续之事。作为旁证,太康二年三月三日处理史载之事之际举行庆典赋诗,不但时间逻辑上说得过去,也更加符合当时的政治生态。
确定了此次赋诗活动的背景与时间,再通过文本对读,可考定闾丘冲《三月三日应诏诗》亦为此次宴会赋诗所作⑦此诗的文本形态,《艺文类聚》等典籍中“连而不分”,逯钦立辑录时却题曰《三月三日应诏诗二首》,但是又加案语云“似是一首”,故不从“二首”之说而题曰《三月三日应诏诗》。,其内容较之程、王二诗更为丰富,也更能彰显此次华林园赋诗之盛貌及帝王之丰功伟业,堪称此次华林园赋诗“最美”。其诗有云:
暮春之月,春服既成。阳升土润,冰涣川盈。馀萌达壤,嘉木敷荣。后皇宣游,既宴且宁。光光华辇,诜诜从臣。微风扇秽,朝露翳尘。上荫丹幄,下藉文茵。临川挹盥,濯故洁新。俯镜清流,仰睇天津。蔼蔼华林,岩岩景阳。业业峻宇,奕奕飞梁。垂荫倒景,若沈若翔。
浩浩白水,泛泛龙舟。皇在灵沼,百辟同游。击棹清歌,鼓枻行酬。闻乐咸和,具醉斯柔。在昔帝虞,德被遐荒。干戚在庭,苗民来王。今我哲后,古圣齐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乐酒今日,君子惟康。⑧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8,第749—750页。
诗中第一段铺叙华林园盛景,同时又通过“后皇宣游,既宴且宁”一句道明此次活动的主题。第二段开头“浩浩白水,泛泛龙舟。皇在灵沼,百辟同游”数句,程咸诗作“皇帝升龙舟,待(侍,逯本注)幄十二人”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1,第552页。,王济诗言“我皇神武,泛舟万里。迅雷电迈,弗及掩耳”②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2,第597页。,三人所描写的武帝泛舟情景极为相似;加之对音乐和美酒的描写,更是将一统后的和睦气氛烘托到顶峰。接着“在昔帝虞,德被遐荒。干戚在庭,苗民来王。今我哲后,古圣齐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八句将武帝平吴功业与帝舜伐三苗之功等视,此为当时文士所共识,如张载《平吴颂·序》即言:“闻之前志,尧有丹水之阵,舜有三苗之诛,此圣帝明王,平暴静乱,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大上成功,非颂不显;情动于中,非言不彰。猃狁既攘,《出车》以兴;淮夷既平,《江汉》用作。斯故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乌可阙欤?”颂文又云:“帝道焕于唐尧,义声邈乎虞舜。”③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85,第3册,第1950页下。以武帝媲美尧舜古帝,自晋以来可谓渊源有自。最早是为了美化受禅之行为,如前引《即位改元大赦诏》有“肆魏氏弘鉴于古训,仪刑于唐虞”之说,应贞诗亦有“陶唐既谢,天历在虞”之誉;而此时吴国灭亡、天下一统,以之与尧舜平乱之功等视,明显是彰帝功,较之受禅之行也更加实至名归。
讨论至此,有一个现象尤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次赋诗活动中,赋诗者不再去替晋室受禅寻找合理性,而是单纯地赞颂武帝一统功业,王济、程咸、闾丘冲三人的诗作莫不如是。无独有偶,张载《平吴颂》也是这种调子。究其原因,还是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武帝登基迄今已过十六载,离首次华林园赋诗也已逾十三年之久,随着天下一统,晋祚愈发稳固,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美化受禅之事。赋诗者对于皇室赋诗动机以及政治时局的审度,这一次无疑又是准确的。
三、太康盛世与太康六年后园赋诗及其他
平吴后,虽然局部地区时有天灾发生,但是社会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更有周边诸国不断进献或内附,晋宋时人孔琳之描述当时的状况是“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④孔琳之:《废钱用谷帛议》,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27,第3册,第2584页下。。史家亦有“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之表述⑤房玄龄等撰:《晋书》卷36,第4册,第1071页。。身处“太康盛世”,登基初恪守礼数、力行节俭的武帝骄奢之心渐起渐深,“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⑥房玄龄等撰:《晋书》卷3,第1册,第80页。。
从“耽于游宴”可窥太康年间武帝游宴之频繁,今存张华《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即产生于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上迄曹魏、下至西晋,洛阳皇宫内的后园充备珍异之物,奢华无度,皇室成员常享乐于此⑦后园的奢侈建造与享乐属性,从魏晋时臣对尊主的上书进谏中可窥一斑,如张茂谏魏明帝书有言:“而乃奢靡是务,中尚方纯作玩弄之物炫耀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耳目之观,然亦足以骋寇雠之心矣。”(张茂:《上书谏明帝夺士女以配战士》,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40,第2册,第1281页上)又如晋时江统谏愍怀太子书云:“窃闻后园镂饰金银,刻磨犀象,画室之巧,课试日精。”(江统:《谏愍怀太子书》,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106,第2册,第2068页上)后园享乐之举,据载:“景初元年,帝(案,魏明帝曹叡)游后园,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6,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8页)。这更为武帝“耽于游宴”找到了依据。从“会诗”来看,此次宴会所赋之诗不止于此,然余皆不存,且引张诗一首以窥豹一斑。
暮春元日,阳气清明。祁祁甘雨,膏泽流盈。习习祥风,启滞导生。禽鸟翔逸,卉木滋荣。纤条被绿,翠华含英。
于皇我后,钦若昊乾。顺时省物,言观中园。燕及群辟,乃命乃延。合乐华池,祓濯清川。泛彼龙舟,溯游洪源。
朱幕云覆,列坐文茵。羽觞波腾,品物备珍。管弦繁会,变用奏新。穆穆我皇,临下渥仁。训以慈惠,询纳广神。好乐无荒,化达无垠。
咨予微臣,荷宠明诗。忝恩于外,攸攸三期。犬马为慕,天实为之。灵启其愿,遐愿在兹。于以表情,爰著斯诗。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3,第616—617页。
从诗题来看,此诗作于张华复归洛阳服膺太常期间,末章“忝恩于外,攸攸三期”两句亦可为证。“顺时省物,言观中园。燕及群辟,乃命乃延”四句交代了此次宴会的主题,其所命者概为诗文之事。首章属于渲染气氛与描绘后园美景,第二章后半部分和第三章前半部分系铺陈宴会盛况。“穆穆我皇”数句,赞颂武帝仁慈惠化之风,较之前论两次赋诗活动的主旨侧重点明显不同。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据末章所表之情,可见张华对于此次重新归洛任职心怀愉悦与感恩。应诏赋诗表己之情,不见于前两次赋诗活动。从“言志”到“表情”,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赋诗者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可以说威严与肃穆在逐渐被消解,当然这是受太康盛世的政治生态影响所致。从宏观体悟三次赋诗活动的氛围,初次重肃穆,复次彰宏大,此次偏欢娱。
产生于后园的文学作品,又有潘尼《后园颂》一首,虽名曰颂,从文体形态观之实与张诗无别。其文曰:
芒芒在昔,悠悠结绳。太仆未散,玄化沾凝。羲皇继踵,三代相承。五德更王,文质迭兴。天命匪谌,祐谦辅信。乃眷我皇,光有大晋。应期纳祚,天人是顺。和气四充,惠泽旁润。神祗告祥,四灵效质。游龙升云,仪凤翳日。甘露晨流,醴泉涌溢。华夏既宁,八荒静谧。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从皇以游。长筵远布,广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岩岩峻岳,汤汤玄流。翔鸟鼓翼,游鱼载浮。明明天子,肃肃庶官。文士济济,武夫桓桓。讲艺华林,肆射后园。威仪既具,弓矢斯闲。恂恂谦德,穆穆圣颜。赐以宴饮,诏以话言。黍稷既登,货财既丰。仁风潜运,皇化弥隆。征夫释甲,战士罢戎。遐夷慕义,绝域望风。无或慢易,在始虑终。无或安逸,在盈思冲。②严可均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94,第2册,第2002页下。
颂有“赐以宴饮,诏以话言”一句,暗示此颂当为应诏之作。从“华夏既宁,八荒静谧”“征夫释甲,战士罢戎”处可知此颂作于平吴之后,“人亦有言,吾何以休?乃延卿士,从皇以游”四句又可看出社会太平年间君臣欢游之旨趣。那么,结合潘尼的仕历就可进一步判断出作颂的大致时间。据本传记载,“初应州辟,后以父老,辞位致养。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历高陆令、淮南王允镇东参军”③房玄龄等撰:《晋书》卷55,第5册,第1510页。。潘尼前期为父养老,而司马允徙封淮南王并统军事事在太康十年(289),加之中间县令之掌,此颂只能是其任太常博士期间所作。太康十载(280—289),大致以每三年划分,太康六年亦在太康中之列,故张诗和潘颂的创作时间相隔不会太久。巧合的是,二人分别赋诗作颂时的官职也有关联,潘尼为太常博士,张华亦为太常,甚至极有可能张华曾为潘尼的上司。而“黍稷既登,货财既丰”“遐夷慕义,绝域望风”描摹的正是“太康盛世”的社会画卷,与前引史载之言吻合。其实,通过与张诗细致比照,二者亦多相近表述:如分别以“乃命乃延”与“赐以宴饮,诏以话言”点明欢游之主题;再如描写宴会场景的“长筵远布,广幕四周。嘉肴惟芳,旨酒思柔”与“朱幕云覆,列坐文茵。羽觞波腾,品物备珍”;又如称颂君王时颂言“恂恂谦德,穆穆圣颜”“仁风潜运,皇化弥隆”,而诗云“穆穆我皇,临下渥仁。训以慈惠,询纳广神”,均是颂扬武帝的仁惠之风。将其视为同时之作或许稍显草率,但保守点说二者的创作背景相同倒无不可。
另外,颂文结尾有“无或慢易,在始虑终。无或安逸,在盈思冲”四句,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这与其说是代君训诫臣下,倒不如说是对各级权贵的忠告,是士人对当下政治生态的独到体悟与自觉反思。可惜如此忠言并没有让武帝觉察到自己日渐骄泰之心和奢靡之行,这也是其为后世诟病之处,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对其平吴后的行为评价道:“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以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①房玄龄等撰:《晋书》卷3,第1册,第81页。
不可忽略的是,武帝时期不惟有君王组织的宴会赋诗活动,根据现存诗歌进行考察,晋惠帝司马衷作皇储时(267—290)亦曾在宴会上诏令侍从文士赋诗。今见此类应诏诗有王赞《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诗》《三月三日诗》《皇太子会诗》三首,当作于王赞任太子舍人期间。《李胤列传》载胤薨于太康三年(282),“皇太子命舍人王赞诔之,文义甚美”②房玄龄等撰:《晋书》卷44,第4册,第1254页。,前贤据此将王赞迁太子舍人系于本年③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703页。,其说可信。更加严谨地说,王赞至迟于此年服膺东宫。另言其诔文“文义甚美”,与西晋职官制度吻合,如《晋书》有“(太子)中舍人四人,咸宁四年置,以舍人才学美者为之,与中庶子共掌文翰”之说④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4,第3册,第743页。。以上所举三诗,《皇太子会诗》仅存四句,其他两首相对完整且主旨相类,但诗中所呈现的内容与君王宴会诗明显不同。以《三月三日诗》为例:
招摇启运,寒暑代谢。亹亹不舍,如彼行云。猗猗季月,穆穆和春。皇储降止,宴及嘉宾。嘉宾伊何?具惟姻族。如彼葛藟,衍于樛木。郁郁近侍,岩岩台岳。庶寮鳞次,以崇天禄。如彼昆山,列此琚玉。巍巍天阶,亦降列宿。右载元首,左光储副。大祚无穷,天地为寿。⑤⑥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8,第760,760页。
从“具惟姻族”看出宴请的均为具有姻亲关系的皇室成员。而较之君主宴会所赋之诗,此诗虽然对尊者亦有赞扬,但是已经不是重点,颂美的焦点集中到了被宴请者身上。“如彼葛藟,衍于樛木”系化用《诗》句以彰族亲和睦之情,《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诗》亦言“乐此棠棣,其甘如荠”⑥。最后,诗尾言“右载元首,左光储副。大祚无穷,天地为寿”,道出了宴请族亲的真实目的,即通过宴会拉拢与团结姻族以期得到拥护。作为太子的司马衷拉拢与团结姻族,也是形势所驱。由于其资质平平,立为太子以来并没有展现出能够担荷帝位的潜能,王公大臣多不看好其继承皇位,甚至废弃之声不绝于朝。宴请族亲,显然是为改变这种不利状况所作的努力。
四、王公大臣出京与皇室祖饯赋诗
晋武帝时期的皇室赋诗活动,就场合而言又不止于公宴,为王公大臣外出就任、将军出镇或出征等饯行时亦多赋诗之举。《文选》亦专辟“祖饯诗”一类,李善注引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⑦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20,第292页。随之“祖道”就演变为古代为出行者举行祭祀道神以祈求平安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又逐渐加入设宴饯别的环节,故又有“祖饯”之称。晋武帝时期皇室成员祖饯赋诗频繁,与武帝即位后大规模的王室分封与频繁的征伐平乱密切相关。据《武帝纪》所载,武帝在位期间曾于泰始元年、咸宁三年、太康十年进行过大规模的王公分封或徙封,期间个别的分封或徙封更不计其数;另一方面征讨平叛亦甚为频繁。皇室祖饯赋诗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和前论宴会赋诗一样,组织赋诗活动的皇室成员也有皇帝与皇储之别,故分而论之。
(一)君王祖饯赋诗
武帝祖饯赋诗,据今存此类应诏诗考察,最早一次当系祖饯徙封赵王后即将就国的司马伦,前贤结合史书记载与诗歌内容将其作年系于咸宁三年⑧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673—674页。,此说可信。张华《祖道赵王应诏诗》前大半部分赞美司马伦之德行与气质,而从“百寮饯行,缙绅具集。轩冕峨峨,冠盖习习”可观饯行场面之盛大,最后“恋德惟怀,咏叹弗及”在颂德之余又表露出宽慰、安抚之意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3,第616页。。其实根据《赵王伦列传》记载,司马伦素质庸下且生性贪冒,而在君王祖饯场合极力颂赞其德,安抚之意甚明。
今又存王浚《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与何劭《洛水祖王公应诏诗》两首,诗题相近,根据诗歌内容进一步观照,二诗作于同一场合无疑。《王浚列传》载曰:“太康初,(王浚)与诸王侯俱就国。”②房玄龄等撰:《晋书》卷39,第4册,第1146页。另据二诗分别有“朱颜感献春”“春风动衿”之句,赋诗当在春季。前引《武帝纪》云:“赐王公以下吴生口各有差。”概为诸王公受赐后各自就其国,武帝设宴祖饯之。王浚诗云:
圣主应期运,至德敷彝伦。神道垂大教,玄化被无垠。钦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邻。皇舆回羽盖,高会洛水滨。临川讲妙艺,纵酒钓潜鳞。八音以迭奏,兰羞备时珍。古人亦有言,为国不患贫。与蒙庙庭施,幸得厕太钧。群僚荷恩泽,朱颜感献春。赋诗尽下情,至感畅人神。长流无舍逝,白日入西津。奉辞慕华辇,侍卫路无因。驰情系帷幄,乃心恋轨尘。③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8,第774—775页。
诗歌起首系垂教化,何劭诗亦云“穆穆圣王,体此慈仁”④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4,第648页。,另外王诗“钦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邻”更是为王公分封与就国提供合理性支持。而分别依二诗中“神道垂大教”与“通于明神”观之,当时的祖饯依旧保留着向道神祈求平安的仪式。“古人亦有言”句以下所言主要为群僚感皇恩,一派和睦气氛。最重要的是,两首诗的结尾颇值得细细品味,前言王浚是要与诸位王公大臣一起离洛,“奉辞慕华辇,侍卫路无因。驰情系帷幄,乃心恋轨尘”四句是以出行者的口吻道出了对君王的不舍,同时也不难看出表忠之意;而何劭明显是为君王代言,以送行者口吻赋出“我皇重离,顿辔骖騑。临川永叹,酸涕沾颐。崇恩感物,左右同悲”,教化作用不言而喻。
武帝诏命赋诗,祖饯对象不惟就国之王公,大臣出京就任亦有祖饯赋诗之举。《晋书》载:“密有才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密官。”⑤房玄龄等撰:《晋书》卷88,第7册,第2276页。作为出行者,君王于东堂为其饯行,足见待遇之高,结合之前李密数次拜官不就的先例,此次似有安抚之意。而李密非但没有像前面提到的王浚那样感恩戴德,反而将牢骚与不满诉诸诗端。这也从反面衬托出君主祖饯赋诗的动机之所在。
(二)太子祖饯赋诗
太子司马衷祖饯赋诗,今存应制诗有王濬《祖道应令诗》和王赞《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两首,依据诗歌内容二者各表其事。王濬诗云:
侯谁在矣?东宫诜诜。曰保曰傅,弘道维新。前疑协衡,顾问翼轮。岂伊张仲,专美前津?涣乎唐德,钦在四邻。齐轨上叶,永垂清尘。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2,第591页。
诗歌开头即言“侯谁在矣?东宫诜诜”,“东宫”是太子的代称,主事者遂明。据《晋书》记载,王濬卒于太康六年(285),而武帝一朝未曾改立太子,那么此处的“东宫”就指司马衷无疑。从“曰保曰傅”“岂伊张仲”看,送别的对象系另有所任的太子府傅、保。“涣乎唐德,钦在四邻。齐轨上叶,永垂清尘”四句除了对出行者寓以期望,又不失团结之心。
而《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一诗的作年和饯行对象结合相关史事便可确定。太康十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王室改封,其中南阳王司马柬改封秦王,始平王司马玮改封楚王、濮阳王司马允改封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①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3,第1册,第79,81页。。三王改封的政治背景是,武帝晚年与心腹大臣共图后事,然众说纷纭而不能定,遂采纳王佑之谋,目的是让二王“镇守要害,以强帝室”②。作为太子的司马衷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祖饯即将出镇的二王,并令侍从文人赋诗。
同样是祖饯赋诗,帝王在场多垂教化、偏安抚,而皇储主持就以拉拢为最终目的。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取决于尊位,另一方面又与各自所处的政治生态有关,如平吴后太康二年祖饯王公归国时帝功、帝威正值顶峰,故垂教化;但太康十年各种政治势力暗流涌动,太子本身又处于舆论漩涡,故在祖饯赋诗时表现出拉拢之意也就不难理解。
结 论
产生于皇室赋诗活动的应制诗,以往对其的认识多以“歌功颂德”笼统概括,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是负面评价居多。这也无可厚非,毕竟这类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上均存在巨大缺陷。但是作为一种反映特定社会文化的文体形态,将其置于生成的场景并结合当下具体的政治生态进行细致考察,就会发现其主旨也并非绝对单一,甚至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价值可供挖掘。通过对晋武帝时期的皇室赋诗活动的论析,可以发现几乎每次赋诗活动的动机或主旨侧重点不一,具体体现为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场域)而异等。因人而异者如君王和太子举行赋诗活动的动机就不一样,因时而异者如武帝时期三次公宴赋诗主旨呈现各有侧重,因地(场域)而异者如公宴赋诗与祖饯赋诗中就会各言其志。概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皇室赋诗活动深受当时政治生态的影响,赋诗活动的动机、主题、气氛等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反言之,正是由于这类文学活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使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历史认识价值,甚至可以作为史料补充与完善历史。如通过王赞《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安二王诗》便可知太康十年作为太子的司马衷曾在祖饯二王时赋诗以拉拢,当史书都在记载各股政治势力暗流涌动,将舆论聚焦到司马衷身上时,素质平庸的司马衷也并非毫不“作为”;再如在生成背景与文体形态均与应诏诗无异的潘尼《后园颂》中对平吴后“太康盛世”的经典概括与居安思危的谆谆告诫,以后的政治家、史家不论评价还是记载这段历史均难出其右。
《论语·阳货》载孔子言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③程树德:《论语集释》卷35,《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12页。晋武帝时期的赋诗活动,从泰始四年“赋诗观志”到以后各个场合安抚、拉拢之意不同程度的表达,可以说有效实践并充分发展了“诗可以观”与“诗可以群”的文学观念。就实践与发展“诗可以群”这一观念层面,前贤已经结合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多种文体创作形态进行了阐发,其中公宴赋诗即占一席④吴承学、何志军:《诗可以群——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形态考察其文学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又收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3—102页。。晋武帝时期的宴会赋诗作为典型自然也体现了这种观念。如果将范围扩大到当时皇室祖饯赋诗进行观察,不难发现对这种文学观念的实践与发展更加彻底和纯粹。前已论及,在西晋皇室的赋诗活动中,用诗者并不在创作层面率先垂范从而奠定基调,所观之“志”自然就失去了赋诗者自由表达的空间,而是沦为大同小异的政治态度与素养的宏大呈现。笔者认为,从创作心理的视角进行分析,“赋诗观志”之说其实是双向互动的,当赋诗者无法自由抒发时,言志之前必然就要观察赋诗活动的社会政治生态以及体悟主事者赋诗之政治意图,可以说所言之志凝结着赋诗者的政治经验与社会洞察力。简言之,赋诗者观政,用诗者观志。当赋诗者“观”之表达与用诗者“观”之动机高度契合时,就会像应贞诗那样被誉为“最美”,如若“观”之不当,就会像李密那样招来免官之祸。这无疑实践并扩大了“诗可以观”观念的内涵。用诗者与赋诗者在“观”上的有效互动,促进了晋武帝时期皇室赋诗活动中不同动机或主旨的呈现,同时也使得此类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高的历史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