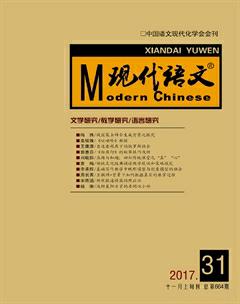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摘 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代表作之一。在父权制社会的背景下,茨威格的作品表现出了对女性的关怀,不经意间也表露出了为女性发声的思想。但茨威格终究是受父权制影响较深的男性作家,对他来说,女性依然是他观望的对象,是“他者”,女性依然是失语的。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可从作品中看到女性话语权的架空和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
关键词:茨威格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批评是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之一。女性主义批评产生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女权运动,所以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它的研究中心主要是妇女,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主张从女性视觉出发,重新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并对以往歪曲女性形象的男性视角进行了批判;它还致力于发现与男性文学传统相异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它也研究女性写作和表达方式的特点,对女作家的创作状况极为关注,并尝试挣脱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从而提倡一种女性主义的写作方式。女性主义批评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
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饱受父权中心文化压制的女性形象。文中的女主人公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可以说她是叛逆的,但是她面对爱情又是那样懦弱,脑袋里有太多父权中心文化的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像枷锁一样束缚着她,所以她只敢远远看着自己心爱的人,不敢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女主人公之所以如此,不仅有自己的原因,更是因为她处于一种父权中心文化的社会中。本文将从女性话语权的架空和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及其原因三个方面对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进行分析。
一、女性话语权的架空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采用了书信的形式,书信有两个特征:一是收信者的主动性。也就是说,收信者可以决定自己收不收这封信,收了信之后又可以自己决定看不看信,让不让写信者发声其实就是由收信人所决定的。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一切主动权都掌握在R先生手中,他可以不看这封信,让陌生女人失语;也可以打开这封信,让陌生女人开口说话。也就是说女性的话语权被牢牢的掌握在了男性手中。这就显示出当时女性话语权的架空,以及女性地位的低下。二是书信是单方面的诉说与倾听,和对话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整部小说都是陌生女人的独白,她径自讲述自己的故事,不期待回复,也不需要回复,就像她的“我爱你,与你无关”的爱情一样。 这独白式的写作方式,不可避免地让R先生这个被陌生女人深爱的对象被动地成为了故事的旁观者、被参与者。 这从侧面展示了陌生女人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要强调的是这说话的权力依旧是R先生赋予的。陌生女人给R先生写的这封信,似临终遗言般的吐露着自己的心声,她这一生的感情以这样的方式也算有了归宿吧。这封信让她在生命终结的一刹那终于有了自己“开口说话”的机会。
这个机会让读者误以为陌生女人掌握了话语权,也让陌生女人自认为自己掌握了话语权,但实际上她仅仅是在形式上借助于书信这种叙述模式而掌握的话语权。从R作家来看,他掌控着陌生女人的一切,他可以让陌生女人说话,也可以让她失语。最终R先生打开了那封信,让陌生女人开口说话了,看起来R先生是尊重女性的,至少愿意倾听女性说话,但是我们真的能确定R先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打开信的么?其实不然,从文本中的开头,我们就能看出,R先生打开这封信是在偶然的、闲来无事的情况下,以及好奇心的趋势下打开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女性的话语权就这样随意的掌控在男性手中,可见女性话语权的缺失。从陌生女人自身来看,在她的思想和内心深处,她还是把自己放在了男性地位之下,并没有将自己与男性放在平等的地位,甚至她还是屈从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结构中。比如在文中她不断地重复这样的意思:“亲爱的,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要是我写的话里出现了一些抱怨的语气,请你原谅我的举动。”[1]她是这样的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话的语气不好让R先生不高兴,而要常常事先做出道歉。
陌生女人是整部小说的叙述者,但很明显,她是一个没有真实自我的人,她的所有观点都完全依附在一个男性身上,她的生命意义完全由一个男性灵魂所滋养。这个男性就是作家茨威格。茨威格作为一个男性作家,虽然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也给这些女性以极大的尊重,但是,他还是未能摆脱男权主义的思想,《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说到底还是一个浸润着男权文化思想的关于女性的故事。在文章中我们能很明显的感受到“父权”制对茨威格的影响。比如,文中流露出女性的道德标准要为男性的利益服务这样的思想。不管是对R先生的描写,还是对陌生女人的描写,作者十分明显地赞许女人为男人默默奉献的精神和义无反顾的爱情。茨威格把陌生女人塑造成一个人女性美德的化身,她所有存在的意义便是对作家的忠贞。
所以,茨威格虽然用书信形式和把女性作為第一叙述者的方式,从形式上将女性的话语权还给了女性,但是,他并没有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而是依然站在男性的视角来描述这个故事。而女性也只是从形式上看起来是掌握了话语权,她的思想内核以及她所传达的价值观都受男性的支配,陌生女人的话语权依旧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
女性话语权的架空,也必然包含着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女性最重要的就是清楚地认识自我,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找到不足,才会有能力和勇气去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从而创立一个新的自己。
显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陌生女人并没有认识自我,她身上自我意识的缺失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自我价值的认知缺失
陌生女人的身上承载着女性所有的美好特质:美丽、善良、坚韧、执着等等,但就是这样的女性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自身的价值,甚至她认同当时父权制对女性的教育,她认同女性是为男性服务的这一思想,她认为女人的一生都是要托付给男人的。这种自我价值认知的偏差导致了她对爱情只是一味的付出与忍耐,也注定了她的爱情不会平等。endprint
(二)理性与独立性的缺失
同样,陌生女人也具有所有女性的弱点与局限,比如感性多于理性,过分依附男性而不够独立等等,这种理性与独立的缺失,正是那个年代女性的一种特质。陌生女人近乎迷狂地爱着R先生。她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R先生,她的生命轨迹深深地烙刻着R先生的印记。在13岁时,对R先生充满好奇,产生爱慕之情;16岁时,对R先生是难舍之情;18岁时,决心献身于他。以后的人生她都是为R先生而活,甚至当有了R先生的孩子,她也没有告诉他,而是自己一个人承受生产之痛,抚养之苦。R先生却从未用真挚的感情对待过陌生女人。对R先生来说,陌生女人只是他享乐的工具。在这样的对比下,陌生女人就更加地悲惨,但是究其原因,也只能怪她自己太缺乏理性,让感性高高的凌驾在其之上。
在陌生女人18岁重回维亚纳后,她过着清苦的生活,她曾经靠自己打过一些临工,但是她终究还是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和孩子,因此她去做男人的情妇,依靠男人活着。她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也认为靠做别人的情妇而活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这些就表现出陌生女人独立意识的缺失,这也是那个年代所有女性的共同写照。
(三)扭曲的爱情观
纵观陌生女人的一生,她似乎只做了一件事——爱R先生。但是她的爱是卑微的、不平等的,甚至是不健康的。陌生女人信奉爱情至上的爱情观,她所做的一起都是为了爱情,在爱情里她只懂得一味的付出和忍受,她永远在期待R先生能够认出她来,却从来没想过去主动追求R先生,她主动地把自己放在男性之下,遵守着父权制度,她不明白真正的爱情是如舒婷的《致橡树》里所写的那样“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虽然她在执着地追求爱情,但追求的却不是平等的爱情。而她的那份所谓的执着,也许更应该当做一种愚昧的坚持。
陌生女人的这些自我意识的缺失,是那个时代所有女性的共性,这不能完全的怪罪于女性,这也是由深刻的社会现实所影响的。
三、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的原因
(一)女性经济地位低下,依附性较强
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婚姻和感情中卑微的地位。陌生女人的母亲在婚姻中一直是战战兢兢的状态,一切都听从丈夫的安排,在女儿面前不断地夸自己的丈夫,以此来说服女儿。而陌生女人面对自己的爱情则是一种狂热且懦弱的态度,其实无论哪一种状态,都是失衡的,反映出的则是女性在实际生活中经济地位不独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是经济压迫造成了让她处于被征服者地位的社会压迫。是男女两性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以前,平等地位不可能重新确立;但要获得这种政治权利,全体女性就必须参与公共行业。”[2]也就是说女性想要在社会活动中追求一种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在经济上就必须要独立。显而易见的,陌生女人和她的母亲都没有经济独立,所以注定了她们在感情中的卑微。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茨威格也透露出这样的观点。陌生女人自幼生活清苦,母亲是个终日沉浸在沉重压抑中的寡妇,在她成年后,返回维也纳初期的日子也很清苦,勉强够自己生活。而R先生,是集才华、金钱、社会地位于一身的近乎完美的男士。他们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造成了陌生女人在爱情中的低三下四和卑躬屈膝。后来,陌生女人为了能让她与R先生的孩子过不那么糟糕的生活而做了别人的情妇,以此来获得物质生活。像陌生女人这样只有依附男人才能生活,是无法取得爱情中的平等和独立的,她必须要破除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才能得到平等和独立的权力。
除此以外,爱情是她的所有,即使她能在经济上独立,却未必能在精神上独立。这种就算经济独立了,精神上却依然依附着R先生的情况,在小说中随处可见。“走在饭馆门口,你问我是否忙着回家,是否还有点时间。 我怎么能瞒着你,不告诉你我乐意听从你的意愿呢?我说,我还有时间。”[3]我们完全可以预料这样的情形最终可能导致的后果,即自己不仅丢失了自我,很可能最后还会因为这样的不平等而下场凄惨。小说也有着大段这样的描写,“我感到很痛快:我把一切全對你讲了,现在你就知道,不,你只会感觉到,我曾经多么爱你,而你在这爱情上却没有一丝累赘。我不会让你痛苦地怀念的。”[4]这些都反映出女性薄弱的经济基础导致在物质和精神上对男人的依附。
(二)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塑造的结果
毫无疑问,男性是社会的主体,他们掌握着绝对的、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与决定权,并习惯性的把女性塑造成温柔乖巧的形象,所以一旦女性表现出一丝的叛逆,就必定会受到谴责和压迫。茨威格所描述的陌生女人的爱情是一种典型的单相思,尽管从一开始陌生女人就见识到了R先生的双重人格———作为作家的博学多识、彬彬有礼和作为男人的放荡不羁、纵情恣欲,但她仍将自己彻底地抛向了R先生。她沉迷于R先生,并期待通过与众不同的方式引起R先生的注意。但可悲的是R先生却完全意识不到她的存在,不管他们曾在身体上,心灵上有多么接近,在他眼里每一次见面,每一次交往,都是第一次,他从来不曾记得陌生女人。“那个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对于你的心灵来说,无论是相隔无数的山川峡谷,还是你和我的目光只相隔你窗户的一层玻璃,其实,都是同样的遥远”。[5]这是多么的荒谬啊,陌生女人执著一生的爱情就像一个缥缈的梦,实在太过于虚幻了。
陌生女人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命运独立的攥在自己的手里,她把自己完完全全地都交给了R先生,那是她生存的全部意义。她一次次地错过过上幸福日子的机会,她对周围的人和事视而不见,把自己埋进一个晦暗的、孤独的世界里,她把自己的心紧紧地关了起来,只为R先生开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见到这样的情况,在虚构的小说中,陌生女人的选择也近乎疯狂,甚至失去了现实的依据。那么在小说中她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陌生女人早就被从现实生活转换成了作者笔下的陌生女人,她早就不是我们看到的完整的女性形象了,她是在单一的男性视角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陌生女人。作者对陌生女人的爱情和行为的设定是基于男性的心理需要的,而不是遵从女性的生命逻辑来塑造的。所以“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多为其审美视野中的对象和客体,她们折射出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其自我意识已被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抹煞和压制,因此,她们实质上只是男权文化境域中没有自身主体‘声音的‘空洞能指”。[6]endprint
由此可見,茨威格还未能摆脱男性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作品中我们之所以看到陌生女人是一个一厢情愿为男性默默付出而不求回报的形象,就是因为她是在男性书写传统下塑造陌生女人的形象的,这还包括他所使用的习惯性的、高高在上的男性的观察视角、男性的叙述模式、男性的话语。他把陌生女人塑造成一个符合父权中心文化的女性形象,其实在根本上这造成了对女性欲望的误解和扭曲,忽略了女性自身的生命价值、人生追求,更是严重压抑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因此陌生女人是男性希望的而非女性真实的符号。她是茨威格从男性性别出发,一厢情愿地诠释出来的女性。
(三)女性自身的原因
女性自我认知的缺失,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妇女长期受父权文化的熏陶,逐渐地认同了父权文化,并不自觉地将父权文化所要求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因此,社会就只存在着一种价值取向,那便是男性的价值标准。那些完全按照男性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女性被伍尔夫称为“房间里的天使”。正是因为这些“天使”的存在,形成了一种阻碍自身创造力并阻止其他妇女进行创造的“反面本能”。由此以往,女性便渐渐的失去了和男人一样成为具有自主选择和自我设计能力的主体权利,在“天使”的推动下,女性也渐渐最终丧失了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
这是让陌生女人缺失自我意识的原因,也是那个时代的广大女性缺失自我意识的原因。女性虽然处于弱势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妥协,我们要认清现实,树立远大的信仰和人生目标,实现自我。
四、结语
茨威格的创作中,成功地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他也十分擅长描写女性的心理,尤其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对陌生女人的恋爱心理的描写,细腻入微,就像高尔基所说的:“我不知道有哪个艺术家会怀着这么多的敬意,这么多的柔情来描写妇女……我想不起有哪篇小说像它那样充满了纯净贞洁的抒情性。”[7]他虽然对女性充满了尊重,但依旧没有摆脱父权制的枷锁,他依然是站在男性主义的视角来写女性的,他让陌生女人在他的支配下开口讲述故事,他也在文中透露了些许关爱、同情女性的思想,但他笔下的女性还是缺乏自我意识的。
注释:
[1]张玉书译,[奥]斯台芬·茨威格著:《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页。
[2]韩建荣:《爱得如此豁达——用女性主义分析<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天府新论,2009年,第6期,第188-189页。
[3]张玉书译,[奥]斯台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18页。
[4]张玉书译,[奥]斯台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
[5]张玉书译,[奥]斯台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6]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妥斯陀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6页。
[7]范信龙,井勤荪:《三人书简——高尔基 罗曼·罗兰 茨威格书信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页。
参考文献:
[1]张玉书译,[奥]斯台芬·茨威格著.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2]杨荣.茨威格的小说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3:08.
[3]吴晓雷译,[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一间自己的屋子[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4]周也君.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女性主义[J].群文天地,2012,(05):236-237.
[5]叶晓勤,姜诚.从女性视角解读《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5,(08):76-77.
[6]肖英.男性意识下的女性世界——解读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J].名作欣赏,2010,(06):107-108.
(马兰 四川成都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61004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