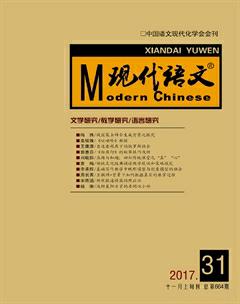战国策士辞令生成背景之探究
摘 要:战国时期,策士辞令的生成是有着深刻社会背景的。战国策士辞令作为一种时代文体,和当时的学术背景密不可分,百家争鸣的学术热潮则是其学术背景。文章重点通过文体背景、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三方面来综合论述战国策士辞令的生成背景。
关键词:文体背景 政治背景 学术背景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春秋时期大量的诸侯国几经兼并而合并成七个大国,于是,原来相对繁琐的辞令逐步演变成相对直接、有效的陈词奏对,这就是策士辞令生成的文体背景。同时,为了争霸称雄,诸侯国纷纷变法图强,逐步在社会大势下崛起的策士们,前赴后继地在庙堂之上一展治国方略,社会形势的转变,也无形之中构成了策士辞令产的政治背景。
一、文体背景
毋庸置疑,战国策士的横空出世不是社会的突变,而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因此,对战国策士辞令研究就必须从时代文体背景出发来探索其出现、发展的成因,挖掘其内在的文学之美。就辞令本身而言,各时期名称不已,孔子曰“命”,唐代刘知几称为“辞令”,清代章学诚等人谓之“辞命”。虽名称不同,但由此可以看出,辞令的一般功能是传递信息、沟通有无。《周礼·春官》曰:
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笑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褚,四曰禁,五曰攻,六曰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语,四曰会,五曰祷,六曰沫。[1]
为了彰显周礼的丰富性,辞在这里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整套的六祝之辞为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依据,同时,辞也作为一种表达而出现历史的文献中。对于“一曰祠”的表达,注家们作了很好的诠释,东汉初郑众曰:“当为辞,谓辞令也。”郑玄则进一步解释道:“‘一曰辞者,交接之辞。《春秋传》曰:‘古者诸侯相见,号辞必称先君以相接。”[2]由此可见,“辞”是诸侯国之间互通有无、进行邦交的礼仪性辞令。而在春秋时期,负责邦交的大臣被称为“行人”,因此,行人辞令作为春秋时期辞令的研究主体,就成为战国策士辞令继承、发展的直接源泉。
春秋行人辞令有着显著的时代特点,它的发展成熟为战国策士辞令的生成、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了更好地解读春秋行人辞令的特点及影响,就必须对春秋行人进行解读。“行人”作为列国的外交官,其出访一般都涉及邦交大事,因此,“行人”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实力,从而对“行人”的自身素养就有了时代最高要求。
首先,守“礼”。自周武王分封八百诸侯王天下以后,公、侯、伯、子、男爵位的设定使得整个社会等级森严,同时又颁布《周礼》,为各个阶层制定了不同的礼节,因此,守“礼”就成为贵族们的身份象征。出使他国的行人,就更需要做到知礼、守礼。诸侯邦交意义重大,在不断兼并的过程中,邦交礼仪就显得更加重要,尤其小国接待大国、弱国接待强国,大而言之,失礼灭国;小而言之,无礼丧身。
其次,通《诗》。诵《诗》是春秋时期外交场合的特殊语言。《汉书·艺文志》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3]邦交之时,双方诵《诗》开启平等对话,同时以《诗》论道彰显才情,个人才学、气度以及国家地位尽在其中,这种空前绝后的文化现象为后世学者所关注。《诗经》是外交人员的必修课。因为,精通《诗经》可以帮助行人提升口才。孔子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4]因此,无论是社会风气,还是自身需要,通《诗》都成为行人们必须具备的素养。
再次,为“公”。行人们出使他国,一般而言,都是关乎本国的大事,国家尊严、君王荣誉都会在外交活动中得到彰显。因此,行人们出访都是为了本国利益,而不是谋取私利。孔子说过,在言行上避免遭受耻辱,出使四方的过程中能够不辜负国家的托付,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士。在社会约定俗成的风气中,为“公”的社会意识已经形成,并且沉淀到行人的思想之中。
综上所述,行人形象大体凸现出来。才学、修为、忠君报国是春秋行人必备的素养。他们的素养决定了他們的外交辞令是以本国利益为重,而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一般而言,春秋行人都是贵族,家族利益通常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作为世家大族,他们必须为家国谋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了解行人的特点,有助于对行人辞令特点的更好把握,因为行人特征是行人辞令的反映。刘勰《文心雕龙·书记》说:“行人挚辞,多被翰墨。”[5]烛之武的慨然陈词可谓春秋行人辞令的代表: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6]
郑国面临亡国之危,烛之武临危受命,一席话使得秦穆公退兵,郑国得以保存,可谓善于辞令。事实上,春秋行人虽然多有君子风范,但是在涉及国家利益时也是当仁不让、寸土必争的,这些主要体现在“令”中。出使他国,难免发生突发事件,这就给行人展现辞令技巧提供了机会。齐国宰相晏子出使楚国,楚人在城门口凿一狗洞以羞辱晏子和齐国。然而,晏子义正词严,使得楚国自取其辱,并礼遇自己和齐国。因此,在“辞”表达的过程中,“令”就彰显出行人自身的素养,同时为行人的自我发挥提供了空间。对于战国策士辞令而言,春秋行人辞令当中的“令”影响最大。
战国策士相对于春秋行人而言,已经不再是纯粹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外交人员,而是分化为社会中的多种角色。春秋时代的“士”多指做官的贵族,而战国策士则是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是一个融汇的群体,而不是一类纯粹的个体。虽然战国策士成分驳杂,但是游说君王、权贵需要的辞令多是从春秋行人辞令转化而来,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春秋行人辞令中的成功案例是战国策士揣度、学习的经典教材。因此,战国策士辞令的生成是建立在春秋行人辞令基础之上的。endprint
《汉书·艺文志》曰: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7]
战国策士辞令首先也是作为策士游说诸侯王时的一种外交语言出现的。由于战国策士不再单纯代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礼仪性互访,更多是推行个人的执政主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战国策士辞令就从春秋行人辞令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型辞令。
二、政治背景
战国是大争时代,各诸侯国忙于变法图强,纷纷求贤纳士,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人才能够迅速崛起,其前提在于君王赏识,而若能很快得到庙堂认可,那么策士本身的辞令就在无形中发挥重要优势。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战国策士辞令就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一)大争时代
历史进入战国以后,由于铁制农具和私田的出现,整个社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列国之间对土地、城池、人口的争夺也就更加惨烈,于是战争不断,兼并成风,一个崭新的时代——大争时代——到来了。各国为了应对时局,纷纷展开变法,以图富国强兵,面对大争之世:
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拉开战国变法大幕。
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吴起变法,从打击大贵族入手。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变法,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基础。
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公元前357年,齐威王即位后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变法。
公元前312年,燕昭王即位后,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维新图强。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17年开始“胡服骑射”,变法图强。
变法图强要的就是国富民强,需要在列国当中争得一席之地,赢得应有的荣光,这也就为各国求才取士提出了标准: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在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中,国家数量锐减,从战国初期的百余小国渐渐演变成七个大国,而大国之间亦是杀伐不断。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解读了战国独特的时代背景:
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盛,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俟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竟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8]
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周天子的权威逐步丧失,各诸侯大国已不再视周天子为名义上的共主,社会进入诸侯争雄的时代。随着周天子对诸侯国约束能力的削减,新兴地主阶级渐渐强大起来,“六卿分晋”的结果是韩、赵、魏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掌权的大国,而“田氏代齐”更是说明了在大争的时代,无论对内对外都需要依靠实力。权势相争的时代已对道德相对疏离,道德信义逐步远离庙堂,列国之间以“利”相争,政权之内,以“利”相斗,无论庙堂内外,抑或市井街巷,都形成“谈利”之势。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世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9]
顾炎武通过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对于“礼”“信”的不同态度来深刻解读战国时期的因大争之势而造成的社会变革。“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是最真实的社会写照。在大争的乱世中,“礼崩乐坏”更是不可改变的社会现象。战国时代的急剧变革使得上层建筑已经逐步丧失了春秋时期士人“诗礼唱和”的贵族风雅,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权势之争。
战国作为社会急剧变革的大争时代,不仅造成了列国博弈的态势,而且列国对人才也达到了疯狂渴求的状态,如: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提出,如果能够使秦国强大,可以与他同分国土。于是,士人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崛起。而最为引人注目的则是士人中被称为“策士”的一类,他们在乱世风云中谱就了一曲英雄悲歌。
(二)策士纵横
随着社会各阶层的分化,世卿世禄制逐步被打破,士人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角色而诞生,并渐渐发展为左右时局的重要力量。在看到士人巨大的影响力后,为了巩固政权和加强权势,王侯将相纷纷“招贤养士”。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了当时“养士”之风:“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10]养士之风充分说明了士人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功能。随着大争时代的到来,策士也注定成为时代的宠儿,在时代大潮中迎风破浪,书写时代传奇。
策士的出现,为战国策士辞令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而策士之中,最为天下瞩目者当属纵横策士。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中提到:
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端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数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是则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肆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11]endprint
纵横之学出于邦交之学,纵横策士也是从一般外交人员中演变而来的,成长为与时俱进的新生力量。由于“逐利”思想已蔚然成风,策士们为了谋取更高的爵位、更大的利益,在言辞上过分夸张,新鲜之感层出不穷,以博君王赏识,从而攫取富贵。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策士取得卿相之尊,越发鼓动了更多的士子学习纵横之术,成就大者,如苏秦身跨六国相印;成就小者,如冯谖出入权贵之门。寒门策士尽得其妙,在言辞中大肆渲染,“以动人主”。纵横策士以《鬼谷子》为理论依据,在辞令中最大限度融入“捭阖之道”,使得战国策士辞令整体呈现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文风。《资治通鉴》载:
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余苏代、苏厉、周最、楼投之徒,纷纷遍于天下,务以诈辨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为最著。[12]
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人们对于纵横策士不但羡慕,而且仿效。无论王侯还是士子,都对纵横策士畏惧三分,如此,策士辞令就在整个社会当中散播开来,形成富有时代特色的战国策士辞令。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对纵横策士做了经典概述:
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13]
由于时代的召唤,纵横策士在列国之间长袖善舞、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们在游说过程中,绣口一吐,就是卿相之尊。这类人,虽然在道德上或有瑕疵,但是的确有着普通士人无法企及的权变智慧和过人的胆识,以及对列国之间关系亲疏的掌控能力。同时,变法策士、门客策士和高义策士的出现,使得策士这一群体更加立体,凸显时代感。他们或为君王所用,庙堂之上决策天下;或为将相所重,门第之内谋划荣辱。所以,战国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策士时代。简言之,大争之世,策士纵横。
三、学术背景
战国时代既是社会大动荡时代,又是思想大爆炸时代,可以称之为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这期间,发生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第一次思想大汇合。无论是孔孟儒家,还是刚正不阿的法家,抑或“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道家,或是因“围魏救赵”而声闻列国的孙膑所代表的兵家,还是高扬“兼爱、非攻”大旗的墨家,各种学说纷纷出现,一时间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由于各种学说都有创始人,都有着自己的政治理念,所以彼此之间相互诘难、辩论,以此来弘扬自家学说。于是,战国策士辞令就此发展起来,成为一个时代的独特文体,同时为战国时期文学注入一脉清泉。
刘泽华曾在《战国时期的“士”》一文中写道:
士的主要产品是精神,是理论。士以他们的精神产品与社会上其他人发生劳动交换或产品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也有统治者参加。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必须有精神力量,而且物质力量也需要由精神加以指导。由于这种情况,统治者不仅需要与士对话,而且需要求救于士的帮助。于是就出现了礼贤下士的场面,士也会一跃而成为统治行列中的成员。这时,士由认识而走向实践,由后台走向前台。[14]
面对统治者的需求,各种学说代表人物不停地周旋于列国王宫,以求自家学说能够引起君王重视,从而抬高学说声誉。因此,策士们清醒地看到君王所需,于是游说就成了策士——也是所有士子们施展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但是学术氛围是自由的,各家皆可立论,在这样的语境中,各家学说都能通过彼此论辩而得到充分的发展。策士作为士子中的一类,能够充分吸收各家学说精华,为我所用。所以,百家争鸣的社会语境就构成了战国策士辞令的学术背景。
注释:
[1][2]《十三经注疏·周禮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08—809页,第809页。
[3][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55—1756页。
[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5页。
[5][南朝]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6页。
[6][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3页。
[7][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40页。
[8][汉]刘向:《<战国策>附录·刘向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6页。
[9][清]顾炎武:《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67页。
[10][汉]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54页。
[11][清]章学诚著,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61页。
[12][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9—100页。
[13][汉]刘向:《<战国策>附录·刘向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7页。
[14]刘泽华:《战国时期的“士”》,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杨柳.先秦游士[M].北京:当代出版社,1996.
[2]张彦修.纵横家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3]郑杰文.中国古代的纵横家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4]彭永捷.中国纵横家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6]熊宪光.战国策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7]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梅伟 河南郑州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4512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