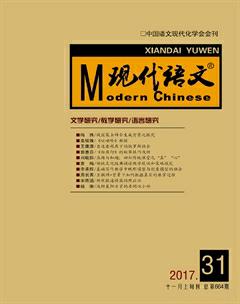说“中国式孤独”: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摘 要:《一句顶一万句》借杨百顺和牛爱国寻找“说得着”的故事和“喊丧”“社火”“喷空”等带有地方色彩活动展现国民“说不着”的困境和对“说得着”的寻找,描画了国人孤独的精神狀态和生存困境。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发现这种“孤独”是中国传统世俗文化的产物,源自民族文化的底层,因此被称为“中国式孤独”。
关键词:说得着 说不着 寻找 中国式孤独
刘震云长于写世俗人情和生活中的琐屑,作品多描写底层群众的世俗生活,如早年的《单位》《一地鸡毛》等。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以河南延津为故事背景,以社会底层小人物为主角,刘震云一反将其定位为“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愚昧麻木的传统,走进这群小人物,挖掘他们的精神及生存状态。
一
小说人物繁多,职业五花八门,如卖豆腐的、打铁的、杀猪的、剃头的……他们被称为三教九流。刘震云通过刻意模糊时代背景和剥离重大历史事件,将表面的时间抹掉,从而使这群小人物成为故事的绝对主角,探讨他们细碎琐屑的世俗生活背后孤独的精神困境。
作品分上、下两部。上部以“出走”为主题,杨百顺(也就是吴摩西)的妻子吴香香给他戴“绿帽子”,与老高私奔。他其实与妻子“说不着”,不想去找,但为了面子,只能带着唯一“说得着”的养女巧玲假装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巧玲被人拐走,他从最初的假装找私奔的妻子变为真正去寻找养女巧玲,走出了故乡延津。下部以“回归”为主题,曹青娥(被人拐卖的巧玲)的儿子牛爱国与杨百顺经历相似。他与妻子庞丽娟也“说不着”,但却一直拖着不离婚,因为怕离婚后连“说”都不得。而后妻子与人私奔,他在假装找妻子的过程中,为摆脱孤独,回到了祖父杨百顺当年出发的地方——延津,寻找他留下的那句话,并受到启示:“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最终明白自己真正寻找的是什么,决定回乡找回“说得着”的情妇章楚红,踏上了真正的寻找之路。
杨百顺和牛爱国都是为寻找“说得着”的人奔走在路上,饱受寻找之苦。小说通过祖孙两代横跨近百年的寻找,实现了“出走”与“回归”的轮回。贯穿这一轮回始终的是“说不着”的苦闷和对“说得着”的苦苦追寻。
剥离纷繁琐屑的故事表象,发现推动人物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说得着”。遭遇妻子背叛的原因是夫妻之间“说不着”,没法交流,而偷情者和私奔者恰恰“说得着”。作品在偷情和私奔这里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两人说了一夜还不停歇,一个说:“咱再说点别的?”另一个说:“再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出现,如牛爱国与章楚红、吴香香与老高、庞丽娜与小蒋。
研读文本,发现作品中每一个人都处于“想说”但“说不着”的困顿之中,都处于“说”与“听”的不对称语境下,杨百顺和牛爱国只是这一孤独群像中的两个代表,在他们现有的生存语境下找不到“说得着”的人。这种孤独感裹挟着作品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延津本地人杨百顺、牛爱国、曹青娥、老杨、老马、老曾还是外来者老胡、老史、小韩,他们想说但都“说不着”,为了对抗令人绝望的“说不着”的孤独,每个个体都以自己的方式与“说不着”进行抗争。
杨百顺和牛爱国的抗争方式是漂泊在寻找的路上。书中还有一类特殊的存在——偷情和私奔者。对待这类人,作品充满了宽容。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裹挟着每一个人的孤独中,“说得着”成为判断远近亲疏的唯一标准,也是精神归宿的唯一标准。牛爱国在与章楚红的私情中才开始明白妻子的私奔,作品最后受到启示决定回乡找回章楚红。杨百顺(即吴摩西)在寻找巧玲时,在郑州火车站看到了私奔的吴香香和老高,本想要杀了他们,但看到“为吃一个白薯,相互依偎在一起;白薯依然是吴香香拿着,在喂老高。老高说了一句什么,吴香香笑着打了一下老高的脸,接着又笑弯了腰。[1]”之后拔出的刀又放了回去。他突然意识到所谓的绿帽子只是一种表象,问题的关键是他跟自己的老婆没话“说不着”,而老婆与给自己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得着”。从“说得着”的角度来看,私奔者倒是正确的。所以绿帽子不是别人给自己戴的,而正是自己亲自戴上去的。
作品借对偷情和私奔的谅解实现了主题的升华,揭示了“说得着”的终极意义。“说得着”隐喻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找到“说得着”的人就是找到朋友和知己,而现实生活中朋友和知己多是缺位的,人人“说不着”,正因如此,“说得着”才愈发弥足珍贵。因“说不着”而背叛,因“说得着”而私奔,所以吴香香、章楚红、庞丽娜都不是所谓的潘金莲,尽管他们抛夫弃子,依然能够得到宽容和谅解,因为私奔是他们对现有孤独的生存困境的一种反抗。
关于孤独,刘震云做了这样的解释:“一个人的孤独不叫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叫孤独。”以这样的标准判断,书中每个人都处于孤独中,有人为了“寻找另一个人”奔波在背井离乡的路上,有人为“寻找另一句话”踏上私奔之路。
小说开头借私塾先生老汪之口对《论语》“有朋自远方来”的解读揭示了作品“孤独”的主题——“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有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2]如果身边有朋友,有“说得着”的人,那么杨百顺等人不用苦苦追寻,吴香香等人也不用私奔。通过这一解读,作品展现了以杨百顺为代表的普通大众对交流和倾诉生生不息的渴望,同时以“寻找”来反衬弥漫作品中渴望交流而不得的孤独。
二
细读文本发现文中“喊丧、社火、喷空”等一系列带有地方色彩活动的背后也体现了国民“说不着”的困境。
杨百顺少年时期喜欢听罗长礼“喊丧”,并梦想成为像罗长礼一样的“喊丧”者。因为“喊丧”能够“让谁上前谁上前,让谁退后就退后”。杨百顺的这个梦想源自现实生活中“说不着”的交流困境。在现有的生存环境中,他找不到一个可以“说”的对象,一个愿意听的对象。因为生活中“说不着”,所以才会痴迷“喊丧”。他将“喊丧”视为“说”,既然无处“说”,那就“喊”出来吧。在这种极端诉说形式中,虽然“喊”出的也不是所谓的“知己话”,但也是一种表达,能够收获一定的回应。对“喊丧”的痴迷是对现有生存状态的反叛和宣泄,这种宣泄的背后隐藏的是无处诉说的苦闷和无处不在的孤独。endprint
“社火”是杨百顺的另一个爱好。所谓的“社火”即一个人扮成另一个人,类似一种化妆舞会。在这类活动中,个体的身份得到了超越,他们超越了世俗生活。在集体的喧哗中,个体孤独得到消解,琐碎生活中淤积的孤独感得到一次性的释放。“喷空”是延津话,意思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接上,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杨百利喜欢“喷空”,因为“喷空”与牛兴国成为朋友。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两个人说的都是虚妄之言,说得激情澎湃,在外人看来却都是无关紧要、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干脆就是“一腔废话”。而正是这种“废话”成为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终极密码,使两人成为“说得着”的知己。透过“喷空”这种带有荒诞色彩的“说”,发现其实重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说得着”。即使“喷”的都是“空”也无关紧要,因为他们“说得着”,因为他们在“说”,在倾诉中不孤独。“喊丧”“社火”和“喷空”成为作品人物消解“说不着”的孤独感的利器。分析发现,这些民俗活动有两个共同之处:一、“虚”(延津话)。“喊丧”说的不是“知己话”,甚至不是一种表达,因为这种“虚”能收到表达所期待的“听”和“回应”,因此,不管形式多么荒诞,杨百顺都将其视为“说”。“社火”本身就是一种角色扮演,更是一种虚无。“喷空”说的本身都是一种“空”。第二个共同之处是“短暂”。“喊丧”只有丧事发生时才会举行,不能当成一种营生。“社火”更是一年一次。所以人们在社火和“喊丧”中获得的释放其实是短暂的,仪式结束后,不得不回归到原来的生活轨迹。
人们在“喊丧”“社火”和“喷空”这些活动中获得释放和短暂的“交流”。通过“交流”的短暂和“虚”更反衬了现实世界孤独的漫长和“实”。看似喧哗的活动展现普通群体的生存困境和对“说得着”的渴望,透着一股生命的悲凉。
三
作品展现了一个个“说”的困境,同时为摆脱无处诉说的孤独而不断找寻精神归宿。在众多孤独者的身影中,我们发现一个特殊的存在——意大利传教士老詹。
传教士老詹26岁时来到延津传教,在长达五十多年的传教生涯中,仅发展九名信徒。传教事业失败,在中国无依无靠(本来有一个叔父,但叔父后来去世了),与上级教会教义分歧而导致关系紧张,教堂被多任县官长期霸占。与杨百顺等一众相比,他更有理由孤独。但在作品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的孤独。这是因为老詹与延津百姓有本质的不同,他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载体。
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世俗的,不依赖于彼岸世界,现实世界是唯一的存在。对于普通的中国人而言,人与世界存在三种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人類的所有问题只能在这个世界解决,我们只能依靠自己,交流和倾诉的对象只能是人,如果找不到“说得着”的人,个体必然会陷入孤独。
而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多了说话和倾诉的对象。神是宽容的,被视为永恒的绝对倾听者,他无处无时不在,关照着自己的子民。因此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倾听者永远在位。即便人和人之间来往不多,“说得着”的个体缺位,因为有神的存在,他们并不孤独。
西方宗教文化中倾听者是神,中国文化倾听者是人。而人神的最大区别在于,“神的嘴是严的”,不会将人的罪孽或抱怨诉诸他处,所有的一切在他那里终止和消解。而人则不同,只有找到一个“说得着”的人,才能放心大胆地吐露心声,否则“说话”是会带来困境和灾难的。
杨百顺跟着老曾学杀猪,后来独立杀猪后依然只分到三个猪下水,在贺家庄抱怨了师娘几句。后来这话转了几道弯传到老曾那里,竟然变成了他对师傅的抱怨,杨百顺与老曾的师徒缘分也到此为止。牛爱国和冯文修从儿时开始便是好朋友,但因为冯文修喝醉后和清醒时完全两样,牛爱国不敢向他倾诉,怕说出去的话被他醉酒后传出去,越来越“说不着”,后来反目成仇。倾诉对象的不安全性造成的“说”的严重后果不言而喻。
中西文化的另一个不同是,与绝对存在的神相比,人则是相对且处于不断变动中的。杨百顺本来有一个“说得着”的人——养女巧玲,但是后来巧玲被拐卖,“说得着”的人发生了变动,不得不踏上寻找之路。牛爱国认为自己在三十五岁之前有三个朋友:冯文修、杜青海、陈奎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全部沦为陌路。为此,他不得不重新寻找“说得着”的人。
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发现,“说不着”的孤独和对“说得着”的寻找是中国特有的,是中国世俗文化孕育的产物,“说不着”的孤独是民族宿命,所以我们把这种孤独称为“中国式孤独”。就像曹青娥说的“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挑,就是日子没法挑”。对于中国普通大众来说,孤独又在孤独中不断地寻找,就是“日子”,就是“命”。因为这种孤独源于我们民族文化的最深层,这一生存状态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命”。
注释: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0月版,第198页。
[2]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0月版,第22页。
参考文献: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2]张颐武.书写生命和言语中的“中国梦”[J].文艺争鸣,2009,(8).
[3]李书磊.刘震云的勾当[J].文学自由谈,1993,(1).
[4]刘雪明,刘震云.探寻中国式孤独[N].乌鲁木齐晚报,2009-6-18.
[5]周新民.《一句顶一万句》:书写“说得着”的终极价值[J].文学教育,2010,(5).
[6]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鸣,2009,(8).
[7]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干叙事新面向[J].南方文坛,2009,(5).
[8]王雪伟.“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J].理论与创作,2009,(6).
[9]汪杨.我们还能怎么“说”?——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读札[J].小说评论,2010,(4).
[10]曹霞.滔滔的话语之流与绝望的生存本相[J].文艺争鸣,2009,(8).
[11]孟繁华.“说话”是生活中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鸣,2009,(8).
[12]李存.寻找那出动心神的一颤——浅析刘震云新作《一句顶一万句》的知己意识[J].当代文学,2010,(5).
(黄培培 江苏昆山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外训系 235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