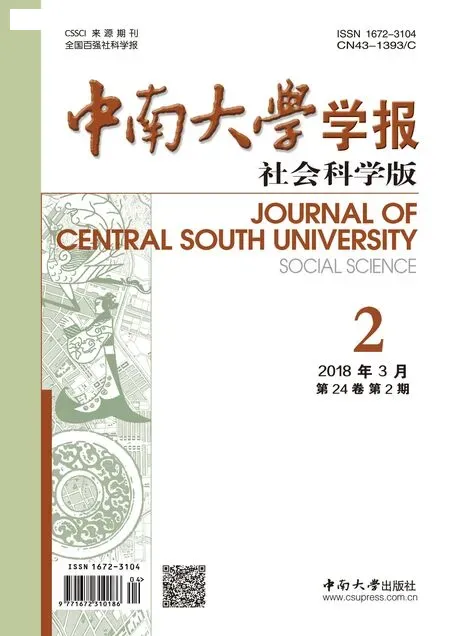民事诉讼中书面证言的效力探析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民事诉讼中,证人原则上需在审判法庭前口头陈述证言,书面证言仅于例外情况下使用。现行《民事诉讼法》第73条明确了书面证言的使用情形,但对书面证言的证明效力缺乏可量化的操作标准,导致各地法院和不同法官采信书面证言的差异化现象,增加了司法的不确定性。书面证言在何种情形下可以使用,究竟有何效力,与证人出庭证言发生龃龉时是否一概无效?毋庸置疑,明确民事诉讼中书面证言的效力不仅直接关系到具体个案中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也侧面影响民事诉讼庭审制度改革的实际成效。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紧张对立:民事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与书面证言的使用
(一) 言词原则要求证人口头陈述证言
在民事诉讼中,言词原则的内涵是唯有法庭上相关人员以口头的方式陈述或报告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诉讼资料方能构成法院判决的基础。因此,言词是审判法庭内所有诉讼参加人之间的基本沟通方式,审判法官、当事人之间须如此,审判法官、当事人与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沟通交流也不例外。证人进行口头陈述时,审判法官不仅注重证言的内容,而且关心证人表达时的语音语调、表情语言、肢体语言等丰富的背景材料,也即察言观色,以此形成对证言的全面感受。故而,口头陈述是对证人作证方式的基本要求。
所谓口头陈述,是指证人以口头表达的方式不间断地向法庭陈述其过去感知的事件始末。因此,当事人提交证人的书面证言以代替证人出庭作证显非口头陈述。常有证人事先写就证言,以便在出庭时于法庭前朗读,因该种做法对于法庭省时省力,司法实践对该类证言趋向于认可并加以提倡。但是,朗读不同于陈述。朗读是口头复述阅读的内容,复述乃照本宣科,证人真实的情感在复述的过程中被压抑和隐藏。而口头陈述是临时和现场表达证人记忆的内容,通过回忆展现其亲身经历的事件始末,这种回忆往往能够引起证人的情绪波动。从效果上看,朗读书面证言只能传递给审判法官有限的信息,不利于法官察言观色。
概言之,言词原则要求证人通过口头陈述的方式作证。口头陈述有两方面要求:一者要求“口头”,即言语表达,而非书面表达;二者要求“陈述”,即通过言词将自己对所体验事实的记忆表达出来,不能是“朗读”或“背诵”。书面证言阻断了法院与证人直接交流的渠道,有违言词原则的要义。
(二) 直接原则对证人科以出庭作证的义务
在民事诉讼中,言词原则是用来规范审判庭上诉讼参加人的沟通方式,直接原则系澄清法院与证据的关系。直接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形式的直接性,即作成判决的法院须自己审理案件,不得将证据调查工作委托其他法院或个人完成;二为实质的直接性,即法院须调查原始证据,不得用证据的替代品作为法院证据调查的对象。实质的直接性禁止法院任意转换证据方法,具体到人证这种证据方法,法院的证据调查程序受到人证优于书证的限制。
直接原则的目的在于确保法官能基于直接体验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证据的价值作出客观妥当的评价,以最大限度地发现事实真相。较之于言词审理,直接审理对证据的调查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官必须亲自调查原始证据,而不得代之以二手证据或者说原始证据的替代品。就证人证言这一证据资料而言,证人在法官面前之陈述本身,属于原始的证据方法;记载证人陈述的书面证言,属于由证人证言派生而来的证据替代品。
在出庭作证的情形下,证人出庭陈述证言,法官询问证人并察言观色,通过全方位观察证人的口头语言、表情神态和肢体动作等,综合判断证言的真实性,进而形成言词辩论的全部意旨,作为裁判之基础[1]。审判活动具有亲历性的特征,而书面证言是第二手的证据材料,以书面证言作证排除了法官直接辨识证言真意及其可靠性的可能。作为证据替代品,书面证言的作成与法庭取证质证分属于不同的时空,不符合直接原则对原始证据的要求。
(三) 证据调查参与权赋予当事人质询证人的权利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关于证据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不仅能自行主张、搜集和提出证据于法院,且能适度参与到法院的证据调查程序中,享有包括在场权、质询权和异议权在内的一系列权利。当事人的证据调查参与权在各国民诉立法中皆有反映[2]。法院如果没有依法通知当事人参与调查证据(这种参与调查通常表现为参与开庭),就不允许以此次证据调查的结果作为裁判依据,否则审判即属程序违法之一种[3]。
当事人的证据调查参与权不仅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利,也能纠正证人证言的偏颇,促进案件真相的发现,有助于证据调查程序的顺利推进。其一,证人证言的本质是将对事实的证明建立在证人的感知之上,感知带有人的主观色彩,受限于证人观察事物的特定角度,出错可能性较大。其二,证人陈述证言是对过去所感知事实的回忆,而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差在所难免。并且,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人的记忆往往只能记住故事的梗概,但证言要求人们就自己体验过的事实正确回忆细节。这种冲突迫使证人通过“常识”和“意义”填充记忆,甚至生成与实际体验不同的记忆。当事人作为事件的亲历者,了解讼争事件的始末,知晓证人证言的真伪及偏颇所在。因此,通过当事人对证人证言的主询问、反询问以及证人的回复等,有利于辨清证人证言的内容与真伪,并在这种互动中使审判法官得以窥探讼争事件的全貌。当事人的质询是发现事件真相的重要工具。鉴于此,证人证言必须经过法庭上的质辩,才能成为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
显然,在证人以书面证言作证的情形下,证人作证和法庭质证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空,当事人无法对证人进行直接的质询。当事人只能质疑书面证言承载的内容且无法得到证人的有效反馈,当事人和证人之间无法就证言内容形成良性互动,证言的真伪难以辨明,当事人的质询权即因证人不到场而无法得到贯彻和保障。
概言之,书面证言阻塞了法官通过察言观色直接辨明证人证言真伪的渠道,侵害了当事人的质询权,不利于有效发挥人证这样一种证据方法的作用。证人作证的基本形式是在审判法庭前口头陈述证言,使用书面证言作证是例外情形。这既是贯彻言词原则、直接原则的应有之义,也是保障当事人的证据调查参与权的必要举措。书面证言作为证人证言的替代品,获得证据能力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二、可信度不高:书面证言的固有缺陷
(一) 书面证言具有形式上的间接性,导致内容上的有限性和封闭性
语言固然是人类交流表达的重要方式。但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言语时所伴随的肢体动作、表情神态、语音语调等更能反映人的真实情感,传递丰富具体的细节信息,且这种信息能为听众所感受和察觉。在证人于审判法庭前口头陈述证言时,法官可以通过观察证人的神情和语言的连贯性、条理性等获得更多信息。在书面证言情形下,证人证言由书面文字承载,法庭通过阅读书面文字而非聆听本人陈述来了解讼争事件的信息。书面证言由文字作成,具有形式上的间接性。书面文字在承载与固定口头证言基本内容的同时,省略了人们言语时丰富的动作神态等背景信息,造成内容提供上的有限性。审判法官不能了解证人作证时的肢体动作、表情神态、语音语调等信息,丧失了通过解读这些信息来印证和判断证人证言真实性的可能,导致信息来源上的封闭性。
简言之,书面证言具有形式上的间接性,导致内容上的有限性和封闭性,该种特性为证据调查者扭曲甚至捏造证人证言提供了可能。
(二) 书面证言的作成主体不具有中立性,影响内容的真实性
在司法实践中,书面证言往往是由一方当事人搜集、作成和提供的。毋庸讳言,因为利益相关性,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会寻找对自身有利的证人,并作成和提供对己方有利的证言。诉讼角色及其代表的利益往往会决定取证的角度和方式,也会选择和取舍证言证明的内容。因此,当事人的利益相关性不可避免地投射到证言内容上来,造成书面证言内容的片面性。
书面证言提交到审判法庭后,由于证人不出庭,当事人无法行使质询权发现和揭露证言内容上的缺陷,审判法官亦不能通过询问证人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当事人只能质疑书面证言承载的内容,不能与证言的作出者直接对话,书面证言内容上存在的遗漏、矛盾与模糊不清等问题无法得到说明和解决。这种书面证言的片面性会影响甚至改变证言所欲证明事件内容的细节甚至全貌。
(三) 书面证言的形成场域在法庭外,有损证人证言的可信度
法庭是规范的证据调查空间。高耸的建筑、黑色的法袍、音质透亮的法槌、庄严的国徽、肃立的法警、权威的法官、严格执行的法庭规则等,都是法庭的“布景”与“道具”,属于法庭“场域”的构成要素。该“场域”所具有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形成了有利于证人如实陈述的法庭环境。
法庭也是有效的证据调查空间。证人在法庭作证,必须进行诚实宣誓、具结保证等环节[4]。法庭宣誓是证人作证的仪式。这种仪式有利于增加证人如实陈述的可能性,亦是对证人证言可信度的背书。在法庭这个场域内,当事人激烈对抗,因此证人的错误证词有可能被当事人当场发现,证人需要面临当事人的当面质询与交叉诘问。法官公正威严,居中裁判一切,审视法庭内每一个诉讼参与人的行为,证人如果虚假作证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庭形成了讼争事件相关人的“集合”,相关人等的法庭互动有利于查清讼争事件的全貌。
书面证言的搜集和作成脱离了法庭空间,缺乏法庭的构成要素和规范程序,既不能激发证人道出实情的义务感,也未能使证人产生作伪证要遭受处罚的危机感,难以形成有利于证人诚实作证的场景。不仅如此,书面证言形成在非公开场合,具有私密性,增加了金钱购买证言或强力逼迫证言的可能性,由此而获得的书面证言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概言之,由于书面证言形式上的间接性、搜集主体的非中立性和作成程序的非规范性,书面证言的内容不可避免地省略、扭曲甚至伪造某些信息,容易出现证言内容的失真。因此,书面证言具有先天性的缺陷。
三、可用性分析:书面证言的相对优势
在证人不能、不宜或者无需出庭陈述证言的情形下,为发现案件真实计,书面证言有使用的必要性。如前所述,相较于证人出庭作证,书面证言在内容上具有封闭性和片面性,在中立性上大打折扣,在真实性上不能令人信服。但不可否认,通过文字记载证人证言的书面证言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证人真意。这种证明案件事实的功用是书面证言可用性的基础所在。又因为证人出庭作证耗费甚糜、耗时甚巨,若能在保证证言可信度和真实性的前提下,部分使用书面证言,必能促使民事诉讼迅速推进,实现诉讼经济。
(一) 书面证言的形成时间较早,证人记忆更加清晰
证人作为一种证据方法,实质是对事件的证明建立在证人的感知之上。而人对过去事件的感知,以记忆为基础。人的记忆力,往往随时间流逝,渐趋薄弱。因此时间间距愈短,记忆越清晰;时间间隔愈久,记忆越模糊,出错可能性越大。并且,记忆不仅因为遗忘而消失,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原貌。诚如学者所言,记忆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地生成与实际事件毫无关联的幻想。但是,记忆肯定也不是能把我们的体验原封不动地珍藏起来的牢靠的仓库。记忆像是酿造库,使我们的体验发酵,一点点地发生变化[5]。书面证言作成于法院开庭前,先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时间,距待证事实的时间间距较短。对于事件真相,开庭前作成的书面证言或许比证人出庭作证更加清晰明了,更有助于法院查明事实。且诉讼前的书面证言,尤其是案件初发时获取的证言,受利益因素影响较小,证人更趋向于如实陈述。
譬如在交通事故现场,为分清双方责任、避免日后纠纷,交通警察邀请在场目击者形成一份书面证言,现场陈述其所体验的事件始末。因为距讼争事件的时间很短,证人记忆十分清晰,且案件尚未进入讼争阶段,在场目击者受到利益掣肘的空间和范围较小。加上书面证言的制作者是交通警察,具有中立性和公信力,该书面证言的可信度较高。
(二) 书面证言能固定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更改性
证人证言乃当事人以外之人在审判法庭供述自己过去所体验事实而形成的证据。因其具有随意性和可变更性,可信度较为薄弱。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通知出庭的证人,开庭时不到庭、到庭后拒绝发表证言或者临时改变证言的情况。该种现象不仅致使当事人措手不及,也会延滞诉讼进程,打乱审判计划,最终影响司法审判的质量。从真实性上考量,一个随意改变证言的证人往往可靠性不足。
书面证言是用文字记录证人证言。文字能够明确和固定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更改性。书面证言往往也会提前呈交法庭,有利于快速有效地推进审判进程。且相较于法庭,书面证言作成场合具有私密性,证人不必担心对方当事人的压力,氛围较为轻松,或许更有助于证人真实意思的表达,从而促进事实真相的发掘。
(三) 利益相关性是影响书面证言真实性的重要因素
在特定情形下,由于证言作成的时间、地点、环境、作证者自身情况、待证事实的性质等因素,书面证言的证明力甚至优于当庭证言。经验证明,某些书面证言具有高度真实性。如前文提到的现场陈述、在先前的诉讼或法院听证程序中提供的证词、陈述人在相信其死亡迫近时,就死亡之原因或情况所作出的临终陈述、于己不利的陈述、关于个人或者家族史的陈述[6]。
利益相关性是影响书面证言真实性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利益相关性越低,书面证言的真实性越高。于己不利的陈述之所以具有高度真实性,缘于从陈述的效果推导出该份书面证言不具有利益相关性。又例如临终陈述需满足三个要件,一者要求作出临终陈述的证人在案件审判阶段已经死亡,出庭作证已不可能;二者要求陈述人在作出陈述时必须意识到自己已经“大限将至”;三者要求陈述的内容限定为就死亡的原因或情况所作的陈述。表面上看,临终陈述建立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人情伦常基础上,究其实质,是因为临终陈述能够最大程度地摆脱自身利益的束缚。
上述书面证言的内部可用性特点决定了书面证言在民事诉讼中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甚至于书面证言与当庭证言相冲突时,具备了取代当庭证言的可能性[7]。从外部效应上看,书面证言具有保证证言的稳定性,实现证据调查主体的诉讼意图,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等功能。对书面证言可用性的评价,当委诸审判法官之自由判断。判断的依据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书面证言作成的时间、地点、程序以及待证问题的性质;外部因素包括当事人的意见,证人的利益相关性和人格品性等[8]。
四、制度构建: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
(一)《民事诉讼法》第73条评析与重塑
关于证人以书面证言作证,1991年和2007年的《民事诉讼法》第70条第1款第3项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对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其作出了目的性限缩解释:①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②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③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难以出庭的;④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无法出庭的;⑤其他无法出庭的特殊情形。
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73条基本上沿袭了之前的规定,仅于行文和内容处稍作调整。主要表现在三点:其一,“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替换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虽然表述有异,但两者的着力点皆集中于“不能出庭”。其二,第1项的“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替换为“因健康原因”,年迈体弱或者行动不便属于健康原因之一种,修改后涵盖范围全面,立法相对周延。其三,删去了第2项的内容“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
《民事诉讼法》的历次修改所遵循的思路是:证人不能出庭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方式作证”的前提条件。该一以贯之的思路包含两个基本判断:第一,证人不能出庭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方式作证的必要条件。易言之,若证人能够出庭,则没有书面证言使用的余地。第二,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是可以书面证言方式作证的充分条件,人民法院许可的依据是证人不能出庭的原因是否属于《民事诉讼法》第73条通过列举式规范规定的正当理由之列[9]。
相应地,该种立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证人能够出庭的情形下,书面证言缺乏使用的空间。书面证言的使用与证人能否出庭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在一些情况下,即使证人能够出庭,也可以使用书面证言作证[10]。这是缘于书面证言具有内部可用性和诉讼经济性的特点。另一方面,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并非可以通过书面证言方式作证的充分条件。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固然应当免除其出庭义务,但并不必然导致证人可以书面作证的结果。证人作证应当贯彻言词、直接原则,该种情形下审判法庭亦可以采取法庭外证据调查的方式进行[11]。使用书面证言这一证据替代品作证,不仅有违民事诉讼法的证据法理,亦侵害了当事人的证据调查参与权。
从法理上讲,出庭作证是证人对法院所负的公法上义务[12]。出庭与作证是两个不同的行为,也是证人所负两项独立的公法义务。依常理而言,出庭是作证的前提,作证是出庭的目的,出庭作证构成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最普遍方式。惟出庭行为与作证行为虽然在时空上具有经常的重合度,但于法理上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性。法庭是最常用的证据调查空间,但不是唯一的证据调查空间。证人口头陈述证言不仅可以在法庭上进行,也可以采取法庭外的方式进行。从法律后果上观之,书面证言与证人不出庭并非同一个问题。证人不出庭作证是对证人义务的违反和审判秩序的违背,可能产生公法上的制裁效果,于法院而言兹事体大[13]。书面证言作为证人证言的证据替代品,涉及证据自身的效力问题,直接关涉该证据所欲证明的事实能否被证明,进而影响到法院对事实认定的结果,攸关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并不必然导致书面证言具备证据能力。
在《民事诉讼法》第73条所列情形下,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但仍负有作证义务。为保证言词、直接原则的贯彻,应采取法庭外的证据调查方式,由审判法庭到证人所在地进行询问以获取证言,同时将该项法庭外的证据调查信息告知当事人,以保障其证据调查参与权。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此类情形下证人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有违言词、直接原则的精义,失之草率。同时,书面证言具有内部可用性和外部经济性的特点,书面证言取得证据资格并不以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为必要条件。简言之,书面证言的适用并不与证人不能出庭作证发生必然的逻辑关系。
(二) 特定情形下赋予书面证言证据能力
在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大量证人同意作证,但不愿出庭的情形。不愿出庭的理由是多层次、多方面的,这种现实困境决定了书面证言有使用的必要性。因鉴于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第2款后半段规定: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根据该规定,在证人未出庭而提交书面证言作证的情形下,法庭不判断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直接宣读并使之呈现于法庭。从证据属性上讲,书面证言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方具备证据能力。该种对书面证言不作限制的立法,值得商榷。
从域外立法来看,书面证言的使用条件极为严格。根据德国民诉法第377条第3款前段的规定,如果考虑到证人作证的内容与证人的人格,法院认为由证人提出书面回答即为已足,可以命令证人提出书面回答。据日本民诉法第203条后段规定,法院认为证人书面回答证明主题具有相当性并且当事人双方对此均未提出异议,可以让证人提出书面回答代替到场陈述并接受询问。证人因年龄、病伤及其他身体上的理由而导致在法院出庭不可能或存在显著困难,并且从证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作为证明主题的询问事项来看,预定其能够作出正确的回答,没有必要特意对其进行嘱托询问与临床询问的场合,可认为具有相当性。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第305条第2款规定:证人须依据文书、资料为陈述,或依事件之性质、证人之状况,经法院认为适当者,得命两造会同证人于公证人前作成陈述书状。该条第3款规定:经两造同意者,证人亦得于法院之外以书状为陈述。
考察域外立法通例,书面证言的运用主要集中于以下情形:第一,证人依据文书、资料进行陈述,例如须依据会计报告、病例为陈述者[14]。第二,证人不能出庭,且依事件之性质、证人与当事人间之关系,预定证人能够作出正确回答者。第三,双方当事人同意者。需要注意的是,允许书面证言这一证据替代品进行作证属于法院诉讼指挥权范围内的事项,前述情形需经过法院的斟酌同意,证人方得通过提交书面证言的方式作证。
依德国民诉法第377条第3款后段的规定,证人提出书面回答时,应同时表示,其可以接受法院传唤以备询问。如果法院认为有必要命令证人就书面回答中的问题作进一步陈述时,法院可以传唤证人到庭接受询问。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05条第4款亦规定:依前两项为陈述者,如认证人之书状陈述须加说明,法院仍得通知该证人到场陈述。因此,证人得通过书面方式回答法院询问,不代表其出庭义务就彻底免除。究其根由,乃因为出庭作证是民事诉讼言词、直接原则的贯彻,亦是对当事人证据调查参与权的保障,对案件事实的发现和程序公正的保障具有显著的功效,在规则设计上应当特别强调。
(三) 提高书面证言的可信度以增强书面证言的证明力
证人通过书面证言的方式作证抑或是出庭作证,虽是作证的形式问题,但形式是内容的载体,且不同的表达形式直接涉及证言的实质内容,更涉及如何保障证言真实性的根本问题。书面证言作为证人证言的替代品,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因此,欲提高书面证言的证据力,需着重增强书面证言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真实性是可信度的客观基础,可信度是审判法庭对证人证言真实性的主观评价。
第一,必须规范其书面证言收集制作、审查判断和复审复核的流程。就书面证言的收集制作而言,应当发挥律师的规范作用和公证机关的监督功能,提高书面证言作成过程的可信度,或者由中立的第三方进行见证。就书面证言的审查而言,书面证言须在法庭上展示,经过当事人的合理怀疑,在必要时法庭可以传唤证人到庭接受询问。书面证言的证据资格及证明力的裁判说理、判决理由公开等制度则为书面证言的使用提供了进一步的复核机制,由此形成了一个书面证言的完整使用体系,从而将由于书面证言的缺陷带来的风险尽可能地减少以至消除。
第二,证人作证应当尽可能满足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考虑到书面证言的书面性和间接性,当事人提供证人的书面证言作证时,可以同时提供作成证言时的录音录像。录音录像用来表现书面证言作成时证人的精神状况、神情神态、表情动作等,可为法官判断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资料。
第三,书面证言的提交并不当然免除证人的出庭义务。在当事人已对书面证言提出合理质疑时,法院仍得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对于关键证人不得以书面方式作证,可采取法院外的证据调查方式,由审判法庭到证人所在地进行询问以获取证言。
注释:
① 现代诉讼中,法官的“自由心证”被允许和承认。法官心证的主要根据便是基于直接审理而来的主观印象。
② 关于在场权,参见德国民诉法第357条第1款、日本民诉法第94条第1款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前半款: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在开庭 3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关于质询权,我国《民事证据规定》第55条第1款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
③ 当事人知情是参与证据调查的前提条件,为此,德国民诉法第364条第4款、第365条分别规定了在外国调查证据和调查证据的受托法官转托情形下当事人知情权的保障问题。
④ 若国家具有宗教信仰的背景,证人出庭作证时,需履行宣誓义务,但不理解宣誓意义的人和未成年人除外。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需签署保证书。
⑤ 关于证言的脆弱性与记忆的网络化特征,可参见(日)高木光太郎:《证言的心理学——相信记忆、怀疑记忆》,片成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⑥ 例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4条。
⑦ 在有些情形下,与当庭陈述不一致的诉讼前陈述比证人的出庭证言具有更大真实性。因为诉讼前陈述与所涉事件的发生时间更加接近,而且受到诉讼争议影响的可能性更小。
⑧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807条对传闻陈述的采信作出概括性的规定,委诸法官的自由判断。德国民诉法第377条第3款规定:如果考虑到作证中问题的性质与证人的人格,法院认为证人提出书面回答为已足,可以命令证人提出书面回答。日本民诉法第205条规定:在法院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当事人没有异议时,使当事人提出书面证言代替询问。
⑨ 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民事诉讼法》第73条属于典型的例示性规范。该条所列举前三项情形是第四项中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例示情形,其作用在于为法官判断是否属于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情形提供参考依据。
⑩ 例如德国民诉法第377条第3款规定:如果考虑到待证事实的内容与证人的人格因素,法院认为证人提出书面回答已足,可以命令证人提出书面回答。又例如日本民诉法第205条规定:在法院认为适当的情况下,当事人没有异议时,使当事人提出书面证言代替询问。
法庭外证据调查的方式是指审判法院将证据调查的场所由法院所在地转移到证人所在地。与书面证言相比,法庭外证据调查的方式更有利于贯彻言词、直接原则,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证据调查参与权。
从性质上讲,尽管出庭与作证同属证人义务,但出庭是事实行为,作证乃法律行为。
例如德国民诉法第380条规定了对证人不到场的公法上的制裁措施,依其强度分别是负担费用、违警罚款、违警拘留。为了强制证人到场,可以采取拘传的强制措施。
例如原告为证明其因遭受某一事故而受伤的主张,申请主治医生为其作证。在该种情形下,医生可以根据书面诊断资料陈述证言,但该陈述仅限于回答原告的病性问题。
[1]占善刚.论民事证据调查的应有法律规制——以证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为视角[J].学习与探索, 2014(2): 79−85.
[2]龙宗智.论书面证言及其运用[J].中国法学, 2008(4):128−144.
[3]李峰.传闻证据规则, 抑或直接言词原则?——民事诉讼书面证言处理的路径选择[J].法律科学, 2012(4): 139−145.
[4]王上仁.两岸刑事审判中证人庭外陈述之证据能力比较——以传闻法则与对质诘问权为视角[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87−94.
[5]吉村德重, 竹下守夫, 谷口安平.讲义民事诉讼法[M].东京:青林书院, 1982.
[6]备藤秀夫.注解民事诉讼法(5)[M].东京: 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杜, 1983.
[7]伊藤真.实验对象讲座民事诉讼法[M].东京: 弘文堂, 2005.
[8]小室直人.新民事诉讼法(Ⅱ)[M].东京: 日本评论社, 1983.
[9]高木光太郎.证言的心理学——相信记忆、怀疑记忆[M].片成男, 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10]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M].周翠, 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11]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M].汤维建, 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12]姚瑞光.民事诉讼法论[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3]陈计男.民事诉讼法(上).台北: 三民书局, 2002.
[14]王甲乙, 杨建华, 郑建才.民事诉讼法新论[M].台北: 三民书局,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