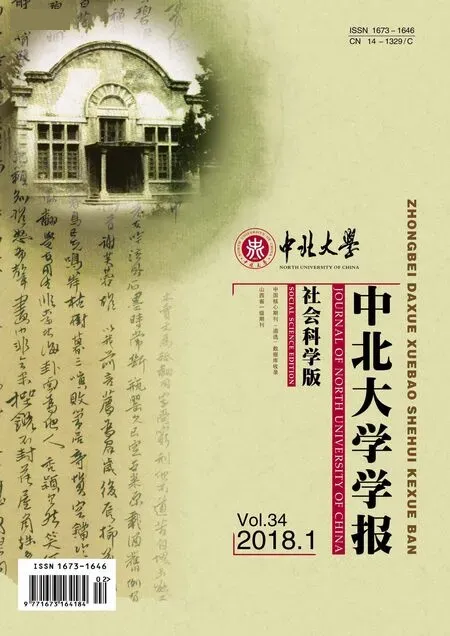“非遗”语境下的村落话语及文化表述
——以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为例
黄孝东, 加 俊, 刘 慧
(1.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2.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51)
0 引 言
21世纪初至今, “非遗”作为转型发展和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 越发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除了少数“非遗”项目之外, 现在被我们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种文化和艺术门类, 大多由乡村社会创造或延伸而来, 由此, “非遗”也成为我们窥探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绝佳视角。 乡土社会中的传统技艺、 风俗、 信仰承载着地方社会的历史记忆, 凝结着民众的智慧与情感, 与生活其中的人构成一个不可剥离的整体, 人们对己文化的表述具有生活性、 常态性、 真实性等特征。 然而, 当这些文化事象被纳入到“非遗”体系后, 地方社会逐渐将其视为可资利用的“资源”, 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包装和再创造, 这种文化商品化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的文化表述失真, 使区域社会中的村落之间产生话语权力的争夺, 对传统文化价值观、 文化形态以及区域文化的整合发展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本文采取个案分析方法, 选取的调查对象是山西省洪洞县羊獬—历山地区的“三月三”走亲习俗, 通过田野调查资料, 深入探讨在“非遗”语境下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村落之间通过怎样的方式表达和争夺话语权力, 并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产生此种现象的社会动因及深层逻辑。
1 研究背景
1.1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的基本情况
洪洞位于山西省南部, 临汾盆地北端, 距离省会太原228公里, 是山西省第一人口大县。 洪洞县甘亭镇羊獬村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羊獬村原名周府村, 四千多年前, 周府村的一户村民家的母羊生了一只非常奇特的羊羔, 这只羊羔只有一只角, 且有分辨善恶是非的本领。 这件事被恰好路过周府村的尧王大臣皋陶撞见, 于是上报尧帝。 定都平阳的尧王带着怀孕的妻子前来视察, 发现这只羊并非普通羊羔, 而是传说中的神兽獬豸。 而就在此时, 尧王妻子在生獬之地生下了二女儿女英。 尧王见此地连生神兽、 圣婴, 便举家搬来居住, 并将村名改为羊獬。 不久之后, 尧王历山访贤遇到了舜, 出于对舜的赏识和对他的考验, 尧王决定将两个女儿娥皇、 女英嫁给舜。 于是, 羊獬和历山就分别成了娥皇、 女英的娘家和婆家。 娥皇、 女英庇护百姓、 造福一方, 逐渐被后人奉为祖先神(当地人称娥皇、 女英为“姑姑”, 有时也称“老人家”)。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 羊獬人都会组织几百人的迎亲队伍, 鸣锣开道, 仪仗护持, 一路敲打威风锣鼓, 前往历山接“姑姑”回乡省亲。 农历四月二十八, 历山人以给尧王拜寿为契机, 再将二位“姑姑”接回婆家。 整个走亲仪式跨越洪洞县、 临汾市尧都区五个乡镇, 途径二十余个村庄, 穿越汾河东西两岸, 波及五万余人,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走亲活动。 2008年,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的行走路线中, 有两个村庄非常特殊, 其中一个是西乔庄村, 据当地人说, 1936年, “姑姑”化身为两条蛇给西乔庄的一位“马子”*从人类学的视角看, “马子”类似于萨满, 是人和神灵之间的沟通者与信息传递者, 属神职人员。 在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中, “马子”具有仪式功能, 迎亲队伍进入指定村落前, 前来村口的迎接人员中总会出现被神灵“附体”的“马子”, “马子”手持香火, 将迎亲队伍领到村子中的“娘娘庙”, 协助完成仪式。 在日常生活中, “马子”还具有治病救人、 化解困境的能力。传话, 让西乔庄村民在村里建一座庙。 第二年, 历山“娘娘”庙就被日本人炸毁了。 因此, 当地人一直视西乔庄为“姑姑”的避难所, 羊獬村民和西乔庄村民的关系也更为融洽。 另一个较为特殊的村庄是万安村, 从“三月三”走亲习俗最早的路线来看, 迎亲队伍并不路过万安村。 当地人给出的解释是, 二百多年前, 羊獬人到历山接“姑姑”, 那一年发生了很严重的蝗灾, 历山“亲戚”拿不出食物来招待羊獬人, 距历山不远的万安镇北门有一位姓乔的老者接待了羊獬人, 从此万安村人和羊獬人也结成了“亲戚”。 然而近些年, 万安人和羊獬人却因为两村走亲戚的起始时间以及舜王的寝宫在何处等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申遗”成功后, 两村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对传说、 仪式的不同阐释和界定, 下文详述。
1.2 理论背景: “非遗”语境下的资源与权力
从本质上讲, 羊獬村与万安村之间矛盾的核心是对资源的争夺, 这种争夺是“非遗”这种外部力量作用于原本是当地人生活一部分的风俗后而产生的, 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相关利益主体对传说和仪式的重塑和再生产。 正如霍布斯鲍姆(Hobsbawm, E.)所说, “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 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至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 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 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1]2-5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把资源划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 其中, 权威性资源是指对人类自身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 在所有集体情境中, 支配都表现为控制模式、 凭借控制, 某些能动者致力于实现并维护他人对自己的服从, 这是一个权力产生的过程。 在吉登斯看来, 权力即“改造能力”, 这种能力是指能够对一系列既定事件进行干预以至于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它们。[2]7-10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用“场域”指代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领域, “场域”中的位置是由不平等的资本分配决定的, 争夺“场域”中的地位的斗争, 使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实施资本分配与界定的有垄断性权力的人, 与那些想要篡权的人相互对抗。[3]142-144在对抗过程中, 人们所使用的往往不是身体暴力, 而是以文化资本为基础的“符号暴力”这种特殊权力形式。 这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即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认识主体、 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是权力—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4]29-30
关于资源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中国乡土社会中的体现, 费孝通认为, “资源和权力”是差序格局社会中的两个重要元素, 在对资源的不断开发过程中, 权力的作用也会表现得愈加明显。*费孝通将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形态划分为三种, 分别是“同意权力” “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 具体内容可参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分析。在中国乡土社会中, 资源必须同权力联系起来, 二者关系紧密。[5]在当下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市场化冲击的中国乡村, 则体现为基于理性计算的“权力的利益网络”, 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面临着经济利益的拷问, 这种拷问会瓦解传统的宗族、 亲情、 面子、 声誉、 道德、 信仰以及共同的是非标准。[6]105
2 羊獬—万安之争: 田野调查实例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属于信仰型“非遗”项目, 是一种民俗宗教。*日本人类学家渡边欣雄认为, 中国汉民族宗教的特征含括在“民俗宗教”之中, 这种宗教是民众基于生活惯例和信条而成立的, 主要依托地域社会中现存的各种生活组织而存在。 在这种宗教中, 各种传统制度化的价值与结构都渗透进具有超自然特征的民间传说中, 整个社会环境充满了神圣气氛, 激发了人们的一种感觉, 即神、 鬼和人共同参与构筑了现有的生活方式。这种民俗宗教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是自发地经由历史性传承在地方社群中逐渐形成的信仰现象。 当地人并不认为他们的信仰是源自于神话传说, 相反, 他们坚信这种信仰源于实实在在的历史, 几千年来, 仪式圈内的当地百姓严格遵守仪式程序和文化禁忌, 人们对此习俗的由来以及相关程序没有体现出任何异议。 然而, 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 万安人却对羊獬人和历山人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08年以后, 羊獬人与万安人的矛盾不断升级, 主要体现在对万安究竟是舜的“行宫”还是“寝宫”这一问题的争论上。 2015年, 两村的矛盾在一次仪式上对禁忌的触碰而达到顶点, 最后以一纸协议暂时解决了争端。
2.1 万安人: 《内陆九三》凭什么不来万安拍摄
20世纪60年代以前,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在晋南大地上像四季一样自然地发生和行进着, 很少有仪式圈以外的人关注。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 “三月三”走亲习俗经过了十几年漫长的“压抑期”, 80年代初期得以恢复, 仪式规模和人们的热情程度都是空前的, 这个古老而独特的习俗也渐渐进入“外来者”的视野。
据羊獬村的老人讲, “三月三”走亲习俗第一次被媒体关注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山西分会曾在羊獬地区对“三月三”进行过拍摄。 由于只在羊獬地区取景且技术设备相对落后, 因此没有形成多大的影响。 1993年, 洪洞电视台拍摄了大型系列纪录片《内陆九三》, 其中有一集拍摄的就是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 片名为《接姑姑》。 由于《内陆九三》拍摄组没有到万安取景, 纪录片里只有羊獬人和历山人出现在镜头里, 因此引起万安人的不满, 万安社*“社”是羊獬—历山地区管理庙事的民间组织, 成员由村民组成, 分为社首和普通社员。 原则上, 村委会与“社”互不干涉, 但二者时有交集, 例如每年“三月三”走亲习俗的启动仪式上和四月二十八的祭尧大典上, 都有村干部代表讲话, 村里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也会请庙上的人协助处理。里派出两个人来到羊獬村进行交涉。
当年与万安人进行交涉的羊獬村社员杨振辉*本文对访谈对象的姓名均做了技术化处理。 杨振辉, 男, 70岁, 羊獬村村民, 原北羊獬村支部书记, 现任羊獬“总社”成员兼顾问。 访谈时间: 2016年7月26日上午; 访谈地点: 羊獬村唐尧故园办公室。回忆说: 《内陆九三》播出后, 万安来了两个人找我, 一个姓杨一个姓杜, 他们都是万安社里的。 他们两个的意思是, 万安和历山一样是羊獬人的“亲戚”, 应该一视同仁, 可是《内陆九三》拍摄组只在羊獬和历山拍而不去万安拍是什么意思?同样都是“亲戚”为什么待遇不一样?要搞宣传就一起宣传嘛, 干嘛要把万安排除在外!我和他们说是他们误会了, 第一个, 拍摄组的人从杨家庄出来后说太原那边还有事, 时间来不及所以就没有去万安。 再一个, 是拍摄组找的我们, 又不是我们雇人家来拍摄的, 要是我们雇人家来拍, 肯定会去万安。 我和他们这么说, 他们不信。 回去以后那个姓杨的还给我写了一封信, 我也没理他(访谈编号: C20160726A)。
这件事虽然后来不了了之, 但从那以后万安人对自己在“三月三”走亲习俗中的地位产生了一种疑虑心理, 而真正的争端则由“申遗”引发并延续至今。
2.2 羊獬人: 万安就是个“歇马粮店”
2007年, 万安人曾针对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申遗”文本提出异议, 万安村“娘娘”庙理事会于2007年5月28日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对山西省洪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代表作的几点看法》*羊獬村唐尧故园“总社”成员提供的内部资料(内容有删减)。的声明, 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1.原文25页上写道: “队伍来到万安行宫”, 我们觉得万安“娘娘”庙是具有历史可考的庙, 是大小“娘娘”神居的寝宫, 而不是行宫。
2.原文题目《关于山西省洪洞县羊獬—历山三月三、 四月二十八接“姑姑”送“娘娘”民俗文化活动的普查报告》一文, 整个篇章写的都好, 但就是有一点不符合历史事实, 有些偏见。 自古四千七百年羊獬、 历山、 万安三者有着不可分割、 缺一不可的神亲关系, 书面根本没提万安……
然而, “申遗”文本并未因上述声明而有明显改变, 2008年,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同年, 省里向洪洞县划拨专项款43万, 具体分配为: 县文化馆13万, 羊獬15万, 历山十万, 万安三万, 西桥庄二万。 当笔者问及“申遗”成功后万安人较之从前有什么变化, 大多羊獬社员认为, 万安人对地位的争夺更甚了, 他们既想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又想获得实际利益, 主要做法是利用媒体和著书立说来“歪曲历史”。 近些年, 万安人有意识地在媒体宣传时凸显自己, 例如: 在临汾电视台播出“三月三”走亲习俗的画面时故意突出万安迎亲队伍, 将羊獬和历山的相关场景剪辑掉等。 针对万安人的做法, 羊獬“姑姑”庙总社在2016年7月12日发布了一份声明《针对临汾市电视台最近播放的“魅力临汾”栏目“万安四月二十八迎‘娘娘’活动”的几点看法》*同上, 主要内容如下:
“洪洞‘走亲’习俗”活动的两个重要端点是“羊獬唐尧故园”和“历山舜庙”, 其他所经过的村庄都是整个活动中的一些停留点或祭祀点。
“万安”庙执事大肆宣传, 舜建都在万安。 众所周知, 尧都平阳、 舜都蒲坂、 禹都安邑, 史成定论, 请问如果舜都在你们万安, 那史学界定论的舜都蒲坂如何解释?
总之万安“亲戚”一贯不尊重历史和事实, 早在万安刘宝山“亲戚”在世时, 就曾胡编臆造, 说什么万安翁儿疙瘩就是舜耕历山的地方, 我们希望临汾市电视台能够深入生活、 深入群众, 多做调查研究, 不要武断臆造, 做出一些有悖历史和事实的荒唐事来。
著书立说方面, 近些年万安人的确出版了一些论证舜生于万安、 长于万安、 建都万安的书籍以及其他文字材料。 2016年, “三月三”走亲习俗中一个万安人送给笔者一本非正式出版物《虞舜文化新探》, 其中有一小节内容——又是一大奇观, 就描述了万安与二位“姑姑”的关系, 笔者将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民国六年版《洪洞县志》介绍的那座“万安娥皇女英庙”, 是一座以“有虞二妃”为主神的综合型多殿之庙, 据多人反映说当初就名叫“娘娘庙”, 如今延缘而承, 仍命名为“娘娘庙”的。 这是万安的先民们, 为体现该姐妹二人“国母”的社会地位……
面对这种情况, 羊獬社员们表示也很无奈, 正如一位社首对笔者所说的那样: 万安人多, 有才华的人也多, 人家也比咱富裕, 他就要胡说八道, 你拿他也没办法。 实在不行我们就不和他们过亲戚了, 本来就是一个歇马粮店(歇脚的地方)!
2.3 突破底线: 一场闹剧、 一份协议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 历山人以给尧王拜寿为契机, 到羊獬村将二位“姑姑”接回“婆家”。 这一天万安人也会来羊獬, 但在到达次序和仪式上都有严格的禁忌, 例如: 四月二十八当天只有在历山人抬着“姑姑”的驾楼离开羊獬走过汾河之后, 万安人才能从河西赶来。 再如: 万安人来到羊獬“姑姑”庙应当先从圣德门进入来到英皇双凤殿, 而不是先到“尧王寝宫”拜寿。 2015年四月二十八, 万安人和以往一样等待历山人过河后来到羊獬村“姑姑”庙, 可是他们抬着驾楼从圣德门前走过直奔“尧王寝宫”, 这一行为使羊獬社员感到很愤怒, 认为这严重地破坏了规矩, 而其目的还是争夺地位。 在羊獬社员看来, 只有历山人才有资格在四月二十八这一天接走“姑姑”, 万安只是一个“歇马粮店”, 万安人在仪式中扮演的是仆人的角色。 万安人则认为, 他们并非只是来“干活儿”的, 而是和历山人一样是来接“姑姑”的, 既然有权利接“姑姑”, 自然就有权利给尧王拜寿。 这次事件在双方社首和村干部的调解下得以平息, 为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双方于2016年2月18日召开会议, 会议上双方签下了一份协议, 内容如下:
1.三月三, 羊獬迎亲队伍到万安, 万安接亲人在万安粮站门口等待迎接。 见面后, 羊獬威风锣鼓走前, 万安威风锣鼓随后, 按传统路线到“娘娘”庙。
2.四月二十八日, 万安“亲戚”到羊獬迎亲, 到达汾河西岸等候历山、 西乔庄迎亲队伍过河后, 方可过河。
3.羊獬迎亲锣鼓在“将军”庙等候万安“亲戚”到来, 万安“亲戚”在前, 羊獬锣鼓随后, 到达舜王庙祭拜, 祭拜后进入故园, 万安迎亲队伍, 经入圣德门进入“姑姑”庙, 将驾楼食箩放至献厅。
4.四月二十九日, 万安迎亲队伍按习俗进行祭拜, 祭拜后羊獬威风锣鼓在前, 万安随后, 到达“将军”庙, 祭拜后送万安“亲戚”返程。
5.以上条款共同遵守, 永不反悔, 空口无凭, 以字据为证。
羊獬主事人:
万安主事人:
从以上五点不难看出, 羊獬—万安之争是在外部力量介入之后产生的, “三月三”走亲习俗成功“申遗”后, 文化/习俗被视为一种凝结着财富、 权力和声望的资源, 在此基础上村落间展开了话语权力博弈, 其主要方式是对文化表述方式的重塑和再造。 人类学家往往更重视现象背后的社会和文化要素, 面对羊獬—万安之争笔者继续追问的是, 导致争端的深层因素是什么, 其他“非遗”项目同样会引发村落内部或村际之间的矛盾吗?
3 “非遗”项目属性与新乡土社会的实践逻辑
据上述田野调查资料可知, 从表面上看, 羊獬—万安之争是在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村落之间对名和利的追逐, 但从深层次上看, 羊獬—万安之争折射出的是在全球化、 市场化大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变迁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的转变, 这一过程又受到“非遗”项目属性的深刻影响。
3.1 信仰型“非遗”项目的独特性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非遗”项目划分成民间文学、 传统音乐、 传统舞蹈、 传统戏剧、 曲艺、 体育与杂技、 传统美术、 传统技艺、 传统医药、 民俗十个类别,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属于民俗类, 但是其中的尧舜传说和威风锣鼓又可以划在民间文学和传统音乐名录之下。 不论怎样划分, 这些内容都是由地方社会的独特信仰延伸而来, 因此笔者将这一类“非遗”项目称为信仰型“非遗”。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的“申遗”过程由洪洞县文化馆一手操办, 对其特殊性和存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发言权。 因此, 笔者对洪洞县前文化馆馆长闻存良进行了深度访谈, 从而对村落之争和“非遗”属性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闻存良*闻存良, 男, 62岁, 山西省洪洞县原文化馆馆长。 访谈时间: 2016年8月12日下午; 访谈地点: 羊獬村唐尧故园戏台后台。说: “三月三”走亲习俗牵涉到四家, 一个历山, 一个万安, 一个西乔庄, 一个是这(羊獬), 你说这个项目放在谁家?放在谁家另外几家都有意见, 最后为了免于争议就把它放在文化馆申遗办公室, 县上统一管理。 但是问题又来了, 文化部拨的保护经费该归谁、 怎么分?有的村会说, 我们的事碍你文化馆什么事?碍你县上什么事?再一个是传承人问题, 和老百姓打交道传承人最难弄, 这个说他是权威是社首, 那个又说他才是权威他也是社首, 那到底谁是呢?搞不清楚。 “三月三”不像戏剧, 传承人好说, 我就是导演, 你就是编导, 他就是团长, 这是非常明确的; 还有就是服务社会的问题, 像洪洞剪纸, 剪个什么我都能卖, 剪个年画可以吧, 皮影可以吧, 剪个龙剪个鸟都可以吧, 而且我可以把它印在杯子上、 T恤上、 本本上, 这种“非遗”可以渗透到各种市场经济中。 “三月三”不一样, 不仅不容易搞市场化, 而且村子之间、 村民之间很容易相互扯皮(访谈编号: 20160812B)。
从以上访谈内容可以看出, “三月三”走亲习俗之所以容易引发村落内部和村际之间的争议,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不易确权, 而之所以确权难, 是因为“三月三”走亲习俗这类信仰型“非遗”是处在“活生生的语境”中的, 它镶嵌在地方社会的各个层面, 与人们的价值观、 生死观以及伦理道德紧密地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承载着历史知识和文化记忆, 以仪式的方式不断地重复, 强化和形塑着人们的行为。 正如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所说, 历史、 记忆、 文化遗产, 它们是不可互换的, 或者说是不可相互化约的。[7]169-170因此, 当人们试图将它作为一种“器物”或商品将其“去语境化”时, 矛盾也就随即产生了。
3.2 市场化冲击下的差序格局理性化
由于无法对从前的“三月三”进行参与观察, 所以笔者只能在田野调查中对当地的老人进行深度访谈, 以此来了解从前“三月三”的相关情况。 报道人钱兵*钱兵, 男, 67岁, 羊獬村村民, 原北羊獬“社首”, 现为羊獬“总社”成员。 访谈时间: 2016年8月15日上午; 访谈地点: 钱兵家。说:
解放以前“三月三”招待亲戚讲究几个盘子几个碗, 那时候村里经济条件不好的人家都没有资格招待亲戚, 人们总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亲戚。 现在亲戚见面了也很亲, 但是总觉得哪里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今年的“三月三”你也看到了, 比去年的人数少了不少, 人都出去了, 要么打工要么做生意, 离得远的回来一趟就得五六天, 他得算一算值不值得回来, 要是实在回不来, 他就往庙上交一二百块钱, 也算是招待亲戚了。 “申遗”以后, 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外面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有的人思想就变了。 就说万安吧, 以前他怎么不说舜王在他们那儿?还不是看着名声了, 然后他们就花钱雇人写东西篡改历史……(访谈编号: C20160815A)
费孝通先生认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注重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乡土社会, 其基本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 即按照关系距离谱系来选择交往方式和处事原则, 这高度概括了中国儒家学说对处理人伦关系的“亲亲”和“尊尊”原则。 按照儒家学说, 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属于工具性关系, 依照公平法则即公事公办的法则进行处理; 熟人之间的关系是情感性的, 按照需求法则进行处理; 处于两者之间的是一种混合性关系, 人情法则是其核心。 从上述访谈资料及前文论述内容可知, “三月三”走亲习俗较之从前已经发生了变化, 当地社会已不再是纯粹的传统熟人社会, 仪式中掺杂进了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 更重要的是, 当地人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准则逐渐由需求法则转向人情法则, 即以人情和面子为出发点, 以不触碰对方根本性利益为底线。 个体利益的追求同社会义务的履行混合在一起, 最高水平的算计必须在经济回报和富有人情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8]221所以, 外出的人即使“三月三”无法返乡参加仪式也会用金钱来弥补, 万安人和羊獬人之间屡次产生矛盾却未有彻底撕破脸。 究其根本, 形成这种微妙平衡的原因正如贺雪峰*贺雪峰认为, 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建立在情法理的基础上。 但是, 当前中国农村权力的动作的情法理基础或文化基础正在消解, 形成了“权力的利益网络”。 详细内容参见加雪峰《新乡土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第102~105页。所指出的, 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结构已经解体, 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使人们精于理性算计, 人际关系和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了钩, 从而形成了差序格局理性化的局面。
3.3 村落正式权力失灵
前文多次提到“社”这个概念, 指的是洪洞“姑姑”信仰圈中专门管理庙事的一种民间组织, “社员”都是本村村民, 大部分是具备一定声望的、 对村庙事务积极热心的村民, 个别“社员”是退休的村干部, 他们是“三月三”走亲仪式最重要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虽然“社员”推动和维持着“三月三”走亲习俗的秩序, 但是这种独立于正式组织(村委会)之外的非正式组织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非期然后果”*由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K.Robert King Merton)20世纪30年代提出, 意指出于良好愿望得到的却是不符合期待的后果。,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凡涉及庙事, 如“社”里的安排和所做的决策, 村干部无权干涉, 村落权力出现“内卷化”, 非正式团体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9]53-55
据田野调查可知, 在羊獬—万安之争的整个过程中, 引发矛盾和回应矛盾的都是“社”里的人, 他们对仪式中的禁忌非常敏感, 对信仰背后的文化表述方式也极为在意。 为此, 笔者从观察和访谈中对比了与“三月三”走亲习俗相关的行动主体的态度。
3.3.1 普通百姓
在羊獬村, 笔者访谈了近50位庙上值班的妇女, 当问及是否知道“三月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 只有六人表示知道有这么回事, 但并不知道“非遗”到底是什么。 当被问到与信仰相关的传说以及村落关系时, 笔者得到的回答都是: 这个我也不知道, 问庙上的人吧, 他们最清楚!
3.3.2 村干部
羊獬、 历山、 西乔庄、 万安的村干部都表示, 村里很少干预庙上的事, 在仪式上只是象征性地出席和讲话, 只有当“社员”实在解决不了问题并影响村落、 村际正常秩序时, 村干部才出面协助解决。
3.3.3 县域文化精英
闻存良认为, “社员”无法以更高的格局看待问题, 他们注重眼前的权力和利益, 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手段是人情、 面子这样的乡土逻辑。 由于“三月三”规模庞大, 流传几千年的信仰使当地人形成了较强的思维和行为惯性, 所以县里不能冒然对“社”采取强制措施。
综上可知, “社”在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中占据着核心和主导地位, 支撑它存在的是浸润在人们生活和思想中的特殊信仰, 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的象征和规范, 这在塑造“社”的权力合法性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 每年的“三月三”, “社员”对仪式的每一个细节都加以界定和规范, 当地人上香、 磕头、 布施、 许愿还愿等行为都被纳入到一张无形之网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 村落的正式权力是“失语”的。
4 结 语
本文以“非遗”带来的村落间矛盾为切入点, 分析和探讨了当中国传统村落遭遇外部力量侵入时, 既有制度、 结构及其行动者所作出的反应和应对策略, 以此勾勒出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在全球化、 市场化、 城市化冲击下的变迁图景。 笔者的核心观点是, “非遗”虽然能够对传统文化起到保护和传承作用, 但是要实现真正的生产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需要在不同性质的“非遗”形态和不同村落类型、 区域社会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1] [英]E.霍布斯鲍姆, T.兰杰. 传统的发明[M]. 顾杭, 庞冠群,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2] [英]安东尼·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M]. 胡宗泽, 赵刀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3] [美]戴维·斯沃茨. 文化与权力: 布迪尔厄的社会学[M]. 陶东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4] [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5] 周大鸣, 石伟. 遗产旅游与乡土社会——关于灵渠文化遗产的旅游人类学研究[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2): 72-78.
[6]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7] [英]迈克尔·罗兰. 历史、 物质性与遗产[M]. 汤芸, 张原, 编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8] 阎云翔.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 陆洋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9] [美]杜赞奇. 文化、 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