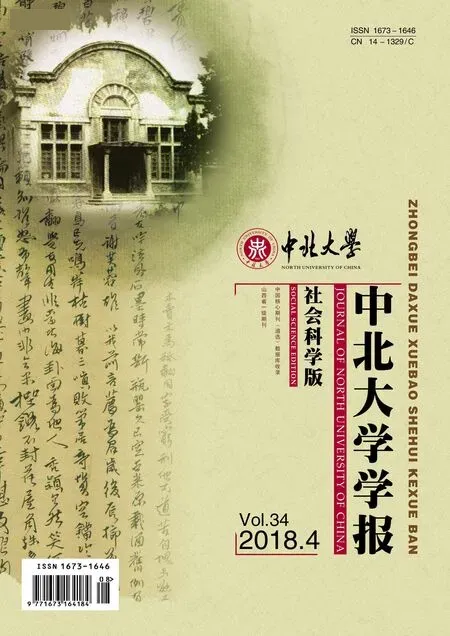金元易代白华、白朴的政治态度与内心世界
张建伟,刘文朝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隩州(今山西河曲)白氏家族伴随着金元王朝而崛起,不仅在金代出了白贲、白华两个进士,而且在元代仕宦不绝,并出了白朴这样的文学巨匠。*关于隩州白氏的世系可参胡世厚:《白朴世系考》,收入《白朴论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版;及《白朴与〈白氏宗谱〉》,《文学遗产》 2002年第5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白氏家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白朴,相关论文超过六十篇,包括文集整理、生平考证、政治态度、处世心态和文学成就等方面,白朴的杂剧、散曲与词更成为研究的热点。*参见胡世厚:《二十世纪的白朴研究》,《东南大学学报》 1999年第3期;李修生、查洪德:《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学者对白氏家族的研究仅仅限于世系的考证,尚未深入。 作为生活于金元易代之际的北方文人,白华、白朴父子的政治态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们在作品中展示了丰富的内心世界,值得研究者重视。
1 金元之际白华与白朴之政治态度
白华在金朝末年成为金哀宗的亲近大臣,但金亡之前他随邓州节度使移剌瑗降南宋,曾任宋官,后又于蒙古太宗八年(1236年)降蒙*《金史·白华传》:“华亦从至襄阳,宋署为制干,又改均州提督。 后范用吉杀均之长吏送款于北朝,遂因而北归。”,这种有悖于忠义的行为遭到了人们的批评。 《金史·白华传》说:“士大夫以(白)华夙儒贵显,国危不能以义自处为贬云。”修《金史》的史臣还在赞中说:白华“从瑗归宋,声名扫地”。 那么,所谓“夙儒贵显”的真实情况如何?白华的选择又有什么隐情呢?
《金史》说白华为“夙儒贵显”,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仕途。 白华中进士后初为应奉翰林文字,正大元年(1224年)累迁为枢密院经历官。 据《金史》卷五十五《百官志》,枢密院经历官为正七品。 白华后升为枢密院判官,最后升至右司郎中,据《金史》卷四十二《仪卫志》,尚书左右司郎中为正五品。 由此可见,白华的官职并不高,称不上“贵显”,只不过他在金哀宗身边针对很多时政大事提过很多建议,因此显得似乎深受重用。
白华确实为保全金朝殚精竭虑,但是他的很多正确建议并未被金哀宗采纳*《金史·白华传》:“上(哀宗)平日锐于武事,闻(白)华言若欣快者,然竟不行。”,甚至于还引起其他官员——尤其是女真族官员的嫉恨。 比如正大二年(1225年)九月,宋将彭义斌乘金朝经理河北之机,遂由山东取邢、洺、磁等州。 白华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宽。 今彭义斌招降河朔郡县,骎骎及于真定,宜及此大举,以除后患。”当时院官不愿意,就派遣白华去彰德视察,实际是借机排挤他。 白华的这一重要建议最终未被实行。 白华的另一次经历则更为危险,正大八年(1231年),驻守桃源界滶河口的合达、蒲阿二军要求增兵,哀宗派遣白华传谕,二人不满意,蒲阿遣水军令白华坐小船顺河而下视察,“(白)华力辞不获,遂登舟。 及淮与河合流处,才及八里庄城门相直,城守者以白鹞大船五十溯流而上,占其上流以截华归路。 华几不得还,昏黑得径先归,乃悟两省怒朝省不益军,谓皆华辈主之,故挤之险地耳”。
白华在金朝危亡之时积极出谋划策,连批评他变节的《金史》史臣也承认“白华以儒者习吏事,以经生知兵,其所论建,屡中事机”,然而,对于白华的正确建议未被采纳一事,史臣是这样解释的:“然三军败衄之余,士气不作,其言果可行乎?”
事实上,作为汉族文士,白华在金代朝廷中的地位并不高,根本不能决策国家大事。 这缘于金朝的女真族统治之本质,“朝政大权始终掌握在女真贵族手里,文士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1]278。 金末文人刘祁在总结金亡教训时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2]137他认为区分女真与汉族的政策是金亡的重要原因。 《金史》卷一百二十四《忠义传》长公主对金哀宗说:“近来立功效命多诸色人,无事时则自家人争强,有事则他人尽力,焉得不怨。”说明金亡之时各民族的不平等待遇依然没有得到改变,汉族等民族的人士尽管为国立功,但是其政治地位依然远不及女真人,因此对这一政权并不满意。 白华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白华一心为国谋划却不受重视,甚至遭人陷害,他的遭遇让很多人不满。 天兴元年(1232年),首领官张衮、聂天骥奏:“尚有旧人谙练军务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见军中事体,此为未尽。”[3]2511哀宗问未用者何人,都说是院判白华,哀宗由此任命白华为右司郎中。 然而,哀宗并未采纳白华出城决战的奏议,而是不顾反对逃奔归德(今河南商丘)。
了解了汉族文士在金代的处境,对白华在金亡前后降宋投蒙的行为便可以理解了。 既然金代政权并未把汉族文士当成值得倚重的力量,那么,从整体上讲,汉族文士自然不会效忠于这个朝廷。*当然也有少数汉族文士在金末殉难,比如路铎、李革、李复亨、周昂等,参见《金史》卷九十九《李革传》、卷一百《路铎传》 《李复亨传》、卷一百二十六《文艺传》。因此,白华并不是个例,而是汉族文士较为普遍的选择,比如王磐为正大四年(1227年)进士,河南被兵时,为避难,入南宋为议事官,襄阳兵变后北归仕元。 杨弘道也有类似的经历。 王鹗为正大元年(1224年)状元,入元后任翰林学士承旨,同样为正大元年进士的杨果也出仕元朝。 即使是不仕元朝的元好问、李俊民等人,也频繁与元朝皇帝、权贵交往。 白华的行为从本质上讲与他们没什么区别。
白华之子白朴尽管在金亡时年仅九岁,但他终生没有出仕元朝,关于他的政治态度,学术界多有不同看法。*参见胡世厚:《试论白朴拒仕元朝之因》,《中州学刊》 1986年第1期;张志江:《也谈白朴拒荐之因》,《中州学刊》1987年第4期;杜桂萍、于建慧:《论白朴拒荐原因及对其杂剧创作的影响》,《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1997年第1期。实际上,白朴既不属金代遗民,又与元朝权贵多有接触,明初人孙大雅对白朴这种复杂的心理有深入的分析,他在《天籁集序》中说:白朴“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 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污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4]207。 而这一切缘于汴京陷落,国破家亡,壬辰之难,尤其是母亲失踪对白朴一生的政治态度与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参见赵维江:《隐士的隐衷——论白朴词隐逸倾向的文化心理成因》,《暨南学报》 1999年第4期。
2 易代之际白华与白朴之痛苦心灵
尽管白华投宋降蒙行为的背后有着自己的苦衷,但他还是承受着舆论对其节操的指责。 白华自己推崇忠臣之义,比如《题仲植长史斋诗》曰:“杜陵文章光万丈,政自爱君心不已。 鲁公若无忠义气,屋漏锥沙一技止。”赞美杜甫和颜真卿的忠义精神。 然而,这段辗转三朝的经历给他的心灵带来惭愧与痛苦,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多有反映,比如《题靖节图》曰:“咄哉灵运辈,危坐衣冠辱。 何如五柳家,春雨东皋绿。”谢灵运与陶渊明都是由东晋入刘宋的诗人,白华将为官受辱的灵运与归隐自得的渊明相对比,鲜明的取舍中饱含着自己的仕途荣辱,尤其是易代之际未能守节的惭愧。 《送陈外郎还燕》也写到贵知几的陶渊明,思考地是人间是非与仕途之愧。 《题何天衢安常斋》写了一种随时而动的思想,流露出自己在金元之际几经辗转、宦海浮沉的感慨。 《送马云汉还燕二首》之一回忆起孤臣在邓之时,自己如同等待赎身的百里奚,“恐成三虎世多疑”,谗言可畏,内心的苦楚能向谁人述说呢?
除了书写仕途的不堪回首外,白华对金亡后自己的处境也有描写,《满庭芳·示刘子新》喜于自己儿女生还,勉励对方建立勋业。[5]603《示恒》:“忍教憔悴衡门底,窃得虚名玷士林”,写的是归隐后的困苦生活与仕途反思。 《是日又示恒二首》其一写年老多病,又羁留异乡的痛苦;其二则表明他对前途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唯一的期望是勉励儿子事业有成。 《示恒》诗也说:“一经真胜万黄金”,勉励子白恒(即白朴)努力学业,振兴家族。
白朴的作品同样有着金亡的痛苦烙印。 他的杂剧《梧桐雨》“融入了家国沦亡的切肤之痛,但更为显明的是借助这桩演说不尽的帝妃爱恋悲剧,倾诉了掩抑深重的荣枯难料、人生命运难以自主的悲剧体验”[6]。 白朴晚年所作的金陵怀古词“兴废古今同”(《水调歌头》“苍烟拥乔木”)包含着金与南宋相继灭亡的现实慨叹,尤其是亲身经历金朝灭亡的苦痛,成了他一生难以磨灭的惨痛记忆。
蒙古军队灭金的过程伴随的是杀戮与掳掠。 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说蒙古军“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7]。 史籍中记载的蒙古军队屠城与掳掠之事甚多。 例如,元人王恽在《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八《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记载,真定有人叛蒙古从武仙,蒙古主帅笑乃发怒,将杀万人以示威,在史天泽的反复劝谏之下才作罢。 张好古《知常姬真人事迹》说:“辛巳,天兵下河东,泽、潞居民半为俘虏。”[8]344辛巳为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所谓“天兵”指的正是蒙古军,蒙古攻打金朝,起初并不以占地经营为目的,而是以掳掠抢夺为主,“泽、潞居民半为俘虏”说的并不夸张。 田茂实之父谈到蒙古灭金时说:“金将亡,城郭蚁溃四出,马尘南驱,躏藉争死,枯骼野燐,千里一色。 丰州为路冲,荒墟败砾,白日无人行声。”[9]
金朝首都汴京的沦陷也一样,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五记载次年宋军进入汴京,发现这座当年的金朝都城被蒙古军占领过之后,“荆棘遗骸,交午道路,止存居民千余架,故宫及相国寺佛阁不动而已”[10]78。 刘祁《归潜志》卷十一记载,崔立降蒙后,“搜选民间寡妇、处女,亦将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众。 又括刷在京金银,命百官分坊陌穷治之,贵人、富家俱被害”。 汴京遭受了崔立的残杀掠夺后,又遭到蒙古军队的洗劫,“北兵纵入,大掠”。“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2]129,据《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崔立传》记载,连投降蒙古有功的崔立家眷也被蒙古军队掳掠。 当时白华跟随金哀宗出奔,困在汴京城的白朴母子情势危急。 叶德均先生《白朴年谱》认为白朴失母当在汴京破后,幺书仪先生《白朴年谱补正》(《文史》第17辑)进一步补充证实,白朴的母亲或被崔党送奉于北兵,或被元军剽掠、荼毒,或以不受辱而自尽。 白朴因被元好问收留才幸免于难,父亲生死未卜,母亲又下落不明,这给年幼的白朴造成了严重的心灵创伤。 王博文序说:白朴“自是不茹荤血,人问其故,曰:‘俟见吾亲则如初。’”这种心灵创伤还显现于白朴的作品中,其《沁园春》曰:“羡东方臣朔,从容帝所,西真阿母,唤作儿郎。”[4]191,192据张华《博物志》卷八《史补》记载,东方朔所见为西王母,白朴称之为“阿母”,可见其内心的恋母情结,因此,清无名氏《天籁集序》说:白朴“痛兵燹失母,见凡有母,如见阿母也”[4]210。
蒙古攻南宋,遭到的抵抗不如攻金时强烈,即使这样,白朴词中依然有“兵余犹见川流血” “几度生灵埋灭”等语句*参见白朴:《满江红·用前韵,留别巴陵诸公,时至元十四年冬》 《念奴娇·题镇江多景楼,用坡仙韵》。,可见白朴对生灵涂炭感慨之深。 金亡三十三年后*据《石州慢》小序,该词作于丙寅,即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距金亡已三十三年。,白朴重游汴京,《石州慢》曰:“千古神州,一旦陆沉,高岸深谷。 梦中鸡犬,新丰眼底,姑苏麋鹿。”[4]12多年过后,其故国之思依然萦绕心中。
白华、白朴父子的作品反映了金元易代之际文人的痛楚。 尽管白氏子孙仕元者不少,尤其是白恪一支,但是家族在王朝更迭的战火中付出的代价还是深深烙在白华父子身上,他们的作品正是其心灵世界的写照。
[1] 牛贵琥.金代文学综论[C]∥刘毓庆.国学新声(第二辑).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
[2] [金]刘祁.归潜志(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元]脱脱.金史(白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元]白朴.天籁集编年校注[M].徐凌云,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
[5] 唐圭璋.全金元词[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 张大新.传统人格范式失衡境遇下的悲怨与风流——白朴的心路历程与其剧作的泛人文内涵[J].文学评论,2008(6):95-103.
[7] [元]姚燧.牧庵集(卷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8] 李修生.全元文(第22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9]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6.
[10] [宋]周密.齐东野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