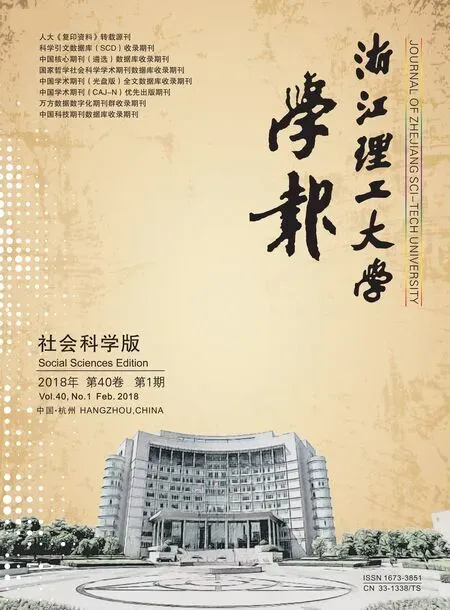书写和隐喻的力量
——从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角度解读《黄色壁纸》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郑州 450001)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是美国最早的女性主义先锋作家之一,曾担任《先驱》月刊出版人,同时身兼社会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演讲人、商业艺术家、教师等多重职业身份。除曾入学罗得岛设计学院之外,吉尔曼所受正规教育并不多。但她的家族却是女性先驱辈出:姨祖母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Tom’sCabin)被称为“引发了南北战争的女人”,其作品具有十分深刻的社会影响。吉尔曼的作品中渗透着她痛苦的生活体验:两段婚姻,困扰终身的产后抑郁症,折磨身心的乳腺癌。罹癌三年后,吉尔曼在加州帕萨迪纳自杀,那里也正是吉尔曼短篇小说代表作《黄色壁纸》(TheYellowWallpaper)的诞生之地。
《黄色壁纸》和凯特·肖班(Kate Chopin)的《觉醒》(TheAwakening)被视为女性文学经典必读之作,也是吉尔曼的成名作,初版发表于1899年。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美国中上阶层的一位知识女性由于患上轻微的精神抑郁症而被内科医生丈夫约翰安置到一座偏僻孤立的深宅大院里进行“休养治疗(rest cure)”[5]。这种疗法使她不得不与刚出生的孩子分开,不得随意出门,不得做任何与思考有关的事情(譬如写作),只能整日呆在贴着黄色壁纸的育婴室中。为了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约翰让自己的妹妹珍妮“照顾”“我”。珍妮尽职尽责,把“我”的一举一动都如实地报告给约翰。“我”的精神在监狱般的生活中走向崩溃,渐渐对墙上的黄色壁纸产生了幻想。“我”总觉得有很多女人藏在壁纸的图案后面,她们挣扎着想出来却又被阻隔拉扯。最终,“我”决定帮助女人从壁纸中出来,甚至融入了她们。“我”撕碎壁纸,把房门锁起来,在地上四处爬动。匆匆赶来的约翰费力打开房门,却被“我”的怪异行为吓得晕倒在地。“我”从他的身体上爬了过去。
小说从女性的视角,以日记的文体和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女性是怎样在男性看似关心尊重,实则被压制被消声,被剥夺身心自由,逐渐陷入癫狂的心理状态。吉尔曼以她个人受诊于心理医生并接受“休养疗法”的经历为基础,真实地反映了在十九世纪初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以往对《黄色壁纸》的解读往往从女性主义批评和哥特文学批评的角度分析小说内容和人物形象,或者从精神病治疗与女性话语的关系,以及使用福柯“权力与规训”的理论来细读文本。但是对文本内容的解读很容易产生主观倾向,使得带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渗透痕迹。因此,本文希望从女性主义文体学这一比较新的视角,通过将文本分析和语言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新审视吉尔曼的这篇杰作,希望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
一、女性主义文体学
1995年,英国语言学家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出版《女性主义文体学》(FeministStylistics)一书[13],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系统论述女性主义文体学相关理论和分析方法的著作。在引言中,米尔斯不仅阐述了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还指出了传统文体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存在的一些问题。米尔斯认为“语言和读者是文本意义产生的一部分,每个读者或评论家因个人背景、经历或关注点的不同会对同一文本的解读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为何大部分文学评论倾向于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实际上也显示出菲勒斯中心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很难真正摆脱因意识形态对文本产生的割裂。因此,女性主义文体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多少能有一套系统的方法、理论的建构,使得批评变得客观起来,使得‘即使不同读者阅读也能产生一个相同结论’变得可能”[2]。因此,米尔斯详细分析了阅读阐释对文本意义建构产生的影响,提出应该更加重视女性读者对某些文本的阐释,允许多种结论的产生。
西方女性主义文体研究是女性主义理论与语言学多个分支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批判性语言学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12](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结合。米尔斯拓展了女性主义的内涵与文本的选择范围,认为“女性主义文体学不仅描述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而且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审视文本,揭示叙述视角、能动作用、隐喻及物性系统等是如何出乎意料地与性别问题相联系。……同时,我也建议女性主义文体学的分析对象应不仅局限于文学文本,而应包括其他一切能够服务于论点的文本形式,比如广告或新闻报道”[12]。这种广阔的视角为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近年来,女性主义文体学飞速发展,已“自然成为了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一个分支”[13]。
《女性文体学》分为理论和方法两大部分,系统的结构也反映出米尔斯希望女性主义文体学能够作为一种有理论支撑的文学批评方法真正被运用于实践之中。在理论部分,米尔斯讨论了女性主义文本类型、语言的性别区分以及性别和阅读的关系。之后从语词层面、句子层面以及语篇层面进行了丰富的文本分析。通过将语言学分析方法与文学批评方法相结合,女性主义文体学试图从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重理论轻文本的倾向中另辟蹊径,从语言的细微之处发掘出女性阐释与表达的可能性。同时,米尔斯所选用的文本不拘泥于文学作品,还有大量的广告、海报等其他文本形式,大大拓宽了女性文体学的研究范围。
而《黄色壁纸》作为女性主义著名的代表作,自1892年发表以来就被许多文学批评家进行解读,文中“我”的形象更是在此过程中被定义、反思以及重塑,成为某种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英雄”。
二、日记体:文学、性别、身份
苏珊·兰瑟在其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出:“《黄色壁纸》是许多因意识形态原因险些被埋没的众多作品之一。意识形态往往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内容是否具有冒犯性,是否会引起争议。比如《黄色壁纸》最早投稿的《亚特兰大月刊》的编辑就拒绝了这部短篇小说的刊载,原因是‘如果(他)使得读者变得跟读完了这篇小说的自己一样痛苦,那么(他)将无法原谅自己’。”[8]但是,类似于“让人绝望”或者“给人痛苦”的评价也同样被给予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然而坡的作品却一直再版,并拥有为数众多的学术研究者。
兰瑟的评论将问题的关键聚焦于为何相似主题的作品会因为作者的性别而受到不同的评价。实际上,对《黄色壁纸》感到恐惧和焦虑的多数是男性评论家,而正是众多女性批评家对《黄色壁纸》从女性主义角度做出的解读将其中的“我”塑造成了19世纪反抗男权的“女英雄”。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单单以性别歧视简而话之,需要考虑吉尔曼所处的时代和她的女性身份。但吉尔曼在《黄色壁纸》中毫不掩饰地对女性写作者和读者的心理进行了探讨,利用最隐私的日记体手法对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份意识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揭示。虽然是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但是《黄色壁纸》包含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仿佛吉尔曼在邀请着女性读者和她一起在私密的空间中(即日记体小说特有的私密性语言)展开一场对文学、性别和身份的精神分析。
吉尔曼利用日记体对“我”最深刻最隐私的身心体验进行细致的公开叙述。在中国五四期间,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利用日记体的形式描述出处于边缘状态和弱势地位的个体,具有某种异己性质。和吉尔曼的小说作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两部作品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属不同的性别,他们的作品却具有某种内在的共通性:在一般情况下,不论是“女人”还是“疯人”,他们都被剥夺了在公共领域发言的权力;反过来说,他们讲出任何大逆不道或荒诞不经的话语,也因而都拥有了某种合理性[6]。
在写作日记的过程中,读者和作者二者合一,形成了一个独特、封闭的阐释循环。日记的内容不会进入公共领域,又赋予了日记作者某种程度上的言说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吉尔曼会让囚徒般的“我”使用日记这一文体来呈现隐含作者的心理状态:书写本身成为一种对男性压制的反抗,“我”也得以在日记中发声,写出对约翰所代表的男性力量最真实的感受。
在小说开头,“我”便告诉读者“约翰是极其现实的。约翰对信念这一说法无法忍耐,对迷信怀有强烈的恐惧,而且言及任何无法感知、未经目睹且无法以数字记录的诸事,都会遭其公开嘲笑”。由此可以看出,约翰的性格使其对妻子的病情具有先在的偏见和无知,在他看来,妻子的病是源于她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源于她“编故事”的能力。所以,他面对妻子的质疑“感到好笑”,“我”也认为或许“我”无法更快好起来的一个原因正是:“你瞧,他不相信我生病了!”[10]205-206。
在这句感叹句中,吉尔曼使用了“你瞧”来直接引起读者的注意,而句尾的感叹号加深了句子讽刺又无奈的意味。在此,吉尔曼想要“拉拢”的读者显然是女性,因为在她的时代,女性被认为是脆弱的,敏感的,和“歇斯底里”天生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吉尔曼自己正是这种观念下的受压迫者。因为产后忧郁症,她被丈夫送到当时著名的心理医生威尔·米切尔(也就是“休养疗法”的创始人)处接受诊治,被迫放弃一切与精神活动有关的工作。因此,《黄色壁纸》也正是吉尔曼自己真实的心理写照。正如小说中的“我”无法被理解一样,吉尔曼在现实生活中也因为这次治疗濒临崩溃。
日记体在文本内部消除了除“我”之外的存在,因而能够最有效地作为个体的“我”发出自己声音的媒介,探讨在面对男性的物化和拒绝时,“我”作为女性内心真正的愿望和反应。日记体由此被认为是女性私语式的情感话语,它为女性大胆表达自己提供了一种“私人场域”。但另一方面,日记体又因这种隐蔽性使得其话语内容的权威性岌岌可危。其太过自我的表达很容易让读者质疑其客观真实性而将其置于边缘。
这种二重性也同样成为小说中“我”之处境的隐喻。一方面,日记是她在丈夫的剥夺监视下唯一能够保有的言说途径;另一方面,又因为它的私密性无法成为和外界沟通交流,诉说自己的媒介:“我不知道缘何要写这些。我不愿去琢磨。我琢磨不透的。我还晓得约翰会觉得荒唐。但我必须用某种方式来诉说我的感想——这将如释重负!”[10]216句尾的感叹号再次展现了“我”矛盾压抑的心情,寻求理解,寻求自由,又没有办法表达这种诉求。和约翰几次的沟通都以失败告终,这也预示着日记体虽可为女性表达自我却又在无形中成了男性权力的帮凶,不断消解压抑着“我”的话语和诉求,再次显示出女性被剥夺和压制的边缘地位。
日记体成了女性写作受制于男性主导的文学创作传统、女性被赋予的从属地位的一种体裁表征。小说中的“我”虽然意识到丈夫对自己看似关心,实则强迫和忽视的真相,但仍旧因为在言语中的弱势和对自身意义的不明确而不能真正打破丈夫和其所营造的空间的束缚。因为“我”不停告诉自己“亲爱的约翰!他特别疼爱我,不愿我生病”,所以在每次谈话的对峙中最终都是“我”在约翰的强势和拒绝中败下阵来,“我又没能给自己找出充分的理由反驳”[10]216。
而约翰的“爱”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对于“我”这个个体的爱?这是“我”无法区分清楚,也不想去揭示的。“我”的日记中,只有约翰的话以直接引语的形式保留下来,伴随着和约翰一次次沟通的失败,“我”的病情也一步步加重,陷入“倾诉——拒绝——自我安慰——倾诉”这一没有结果的循环中。
在“我”最后一次尝试告诉约翰自己的情况,希望他能带自己离开时,他答道:“(1)家里的维修还没完工,我此刻也离不开镇上。(2)当然了,若是你病得厉害,我定能而且也会带你走,但亲爱的,不管你自己意识到没有,你的确好多了。(3)我是位大夫,亲爱的,所以我看得出。(4)你在长胖,也有气色了,胃口也好多了,我确实对你要放心得多”[10]219。
这段话可谓层层推进,揭示出男性语言对于女性表达的压制和解构:第(1)句中表明约翰不带“我”走的真正原因。但是为了维护自己“好丈夫”的形象,他在第(2)中又强调了自己的拒绝是为“我”考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句中,约翰使用了“真的”和“的确”,暗示他根本不相信妻子的话,也不相信妻子拥有描述自己客观病情的能力,他的判断全部是基于他的自以为是。第(3)句进一步以“大夫”的身份来压制妻子,巩固自己作为男性的权威性和正确性。最后,在第(4)句中,他再次以自己所认为的事实来解构妻子的主观感受,并用“我确实对你要放心得多”给“我”进行心理强化。自始至终可以看出,约翰一直掌握着话语的主导权,其看问题的角度完全是处于他自身的考虑,并没有真正去关心和理解妻子的病情。
“我”想以“或许身体上好些了——”来继续谈话时,约翰因为睡眠持续被打断显示出了不耐烦的神情,并且“打量我的目光里含有那么一股怨嗔苛责的意味”。破折号的使用表明“我”的谈话被打断,同时表现出“我”对约翰那带有苛责的凝视产生的恐惧。“我”感受到了约翰的拒绝,“以至于我吐不出一个字来了”[10]219。
约翰之后的一段话更使“我”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完成了对“我”的消声:“(5)‘亲爱的,’他说,‘我求求你了,看在我的份上,也看在我们孩子的面子上,同样也是为着你自己,你绝不要有一瞬间让那想入非非的念头蹦到你的脑子里去!(6)对于像你这般性情的人,这是再危险、易入迷不过的事儿了。(7)这是某种虚幻不实的愚蠢幻觉。(8)我作为一名医生这么嘱咐你,难道你连我都信不过么?”[10]220
第(5)句中,约翰用恳求的语气放低了自己作为男性的姿态,动摇“我”渴望诉说的决心。之后先说“看在我的份上”,提醒“我”意识到自己“妻子”的身份和责任;再用孩子提醒“我”作为母亲的身份和责任,最后才是“我”作为个体的身份。对“妻子,母亲,女人”三个身份的先后排列不仅表明约翰并没有将“我”作为一个独立女性个体来看待,更一步步解构了“我”作为个体女性的独立性,再次使“我”符号化,模糊化。句尾的叹号暗含命令的语气,显示出男性对女性的规约欲望;第(6)句的主语不是表示个体的“你”,而是“像你这般的人”,暗示了男性对女性的高人一等的姿态;第(7)句中将“我”的病情等同于“愚蠢的幻想”,充满了贬义,显示出男性权威对女性的蔑视;第(8)句中则再次强调自己“医生”的权威地位,同时,反问句又提出了自己作为丈夫和男人的压倒性的力量。至此,“我”的话语权被彻底剥夺,“所以我当然说就此不再提及”[10]220。这段对话是小说中为数不多“我”以直接引语的方式进行转述,表明了这段话对“我”精神产生的难以遗忘的冲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鼓起勇气向约翰表明自己想要离开的愿望,但却遭遇了约翰最粗暴和直接的忽视与拒绝。“不再提及”既表明“我”完全失声,也表明了“我”对约翰不再抱有希望。“我”更加退入内心世界,是之后“我”精神状况失控的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我”在日记中使用了大量的感叹号,直观地表明“我”内心的不安与愤怒。日记写作通常是平静的回忆式陈述,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多为句号。其写作通常与叙述之事间有一个时间沉淀,也意味着一段感情沉淀的时间。再者,写作日记通常是在比较私密放松的环境之中,比如夜晚的卧室或书房,因而下笔相对也更从容。但“我”的日记却既要偷偷地写,又是在近乎封闭、充满监视的环境里——“我”丧失了情感沉淀的时间和来自私密空间的安全感——感叹号提醒着读者去揣摩“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同时,对转折词如“但是”“却”“然而”等的运用也鲜明地展现了“我”真实想法与外界现实的反差:转折词前经常是约翰或珍妮认为、希望“我”能如何如何,而在下一行的转折词之后往往会是“我觉得”、“我想”。“我”的真实诉求被长期搁置、延宕,这才是“我”生病的根本原因。
作为日记体呈现出来的小说不仅呼应了作为病人的“我”像日记一样无法被他人阅读和理解,也因为“我”的女性身份表明男性的压制和束缚中,女性最终将陷入沉默,所有的自我书写都相互抵消,自我的存在面临消失和分裂的困境。日记体既像女性作家面临的语言困境的隐喻,又像整个女性身份错位与缺失的隐喻:女性写作无法以男性语言进行构建,也无法传达女性真正的心理需求,因为她既不被允许写作,写出的日记从本质上来说也不会被他人看到;同时,女性身份意识的觉醒在19世纪是痛苦的,因为这些写满诉求的日记除了让她更加陷入自己的困境之外,没能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黄色壁纸的隐喻:伴随阐释的重构
如果说读者从小说中看到的是“我”作为女性个体一步步崩溃的解构过程,那么透过“我”对壁纸孜孜不倦的阐释尝试却表现出一个新的女性形象以读者和解码者的身份进行重构。苏珊·兰瑟认为:“《黄色壁纸》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种解读文学文本的新途径,这篇短篇小说实际上是这种修正性阅读的一个认知过程。因为叙述者本身就亲身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女性主义解读——她一直试图弄清壁纸的意义。”
这实际上是将叙述者和读者的关系进行了转换和类比。面对复杂难辨,迷惑人心的壁纸,叙述者“我”就像面对复杂文本的读者,想要通过自身的认知和思考,将自我建设投射到对文本意义的解读中。但这个过程往往并不那么顺利,特别是在充斥着男性主导权的语言结构中构建起女性独立的言语阐释空间更加困难。正如女性主义文体学家所提出的:“女性读者应当秉持这样一种阅读理念,即不应把文本当做意义承载的容器,而是作为作者所留下的一系列充满模糊可能性的踪迹,读者需要不停地质疑和询问,去试图抓住这些踪迹”[1]。
之所以在此强调女性读者的地位,是因为《黄色壁纸》巧妙地展现了男女之间在阅读和写作行为上的差别。《黄色壁纸》详细展现了吉尔曼完成这篇文稿的过程—即作为女性作者的心理—这是一篇女性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写下的故事,从中读者可以窥视到吉尔曼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对女性写作的看法。同时,她笔下的“我”对壁纸的研究与解读又仿佛是女性读者阅读行为的一个镜像,其描写深刻地反映出在面对男性语言主导的文本时女性读者感到的迷惑、压抑以及愤怒。如果把文中的“我”对壁纸意义一步步的构建解读为写作的过程,那么“我”最后的癫狂则表明了吉尔曼自己对女性作家身份的矛盾态度:癫狂究竟是源于对创造力的压抑还是过分纵容?
在《女性文体学》中,米尔斯认为女性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总是以某种类型的隐喻出现,比如鸟,尤其是笼中鸟。[2]40娇小、柔弱、美丽、顺从,这些特质似乎总是被反复类比于女性,而且是某种理想的女性。她们需要依附于饲主并要尽力赢得饲主的欢心,以期被给予更舒适的生活,却从不会想要从笼子里出来。即便有些冲出笼中的鸟儿,她们的下场也往往以悲剧告终,成为某种反面教材—更加巩固了“笼中鸟”的形象。吉尔曼所处的19世纪正是第一次女权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女性获得了相对多的教育权,同时也引发了对女性是否适合工作的争论。而写作,作为女性在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前提下首先想到的职业,首当其冲受到了社会传统观念的质疑。在中产阶级男性的意识中,“女士发表作品只为三种理由:爱听赞扬,爱金钱,或是有做好事的愿望。”[11]51写作,会从精神和经济上赋予女性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而这无疑会威胁到男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正如在发表了上述言论之后,女作家夏洛特·扬的父亲似乎做出了某种让步,表示“如果夏洛特愿意写教诲性的小说,并把挣到的钱赠送出去,那么他会不吝赞赏之词并克制住怒火。”[11]51但很显然这是种以退为进的妥协,因为“教诲性的小说”是小说创作中最不需要想象力、最容易被反过来利用为宣扬某些男性传统道德的类型,而分文不取则意味着要求女作家自愿放弃经济自立的可能性。
写作与家庭生活之间存在的某种对立自1850年后就让许多立志于成为作家的女性感到焦虑。[11]60这种焦虑也经常反映在女作家的创作中:比如作品反复出现的和房间(比如伍尔夫讨论女性写作的《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房屋(比如《黄色壁纸》一开始就对房屋的外观进行了详细描写),土地以及大海(伍尔夫《到灯塔去》中大海的象征意义)相关的描写。这些重复的意象既暗示了她们对家庭生活的重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显示了家庭生活对女性经验的束缚,即她们只能写她们所熟悉的东西。壁纸也是这一系列“房屋隐喻”中的一个。但《黄色壁纸》中的“壁纸”意象需要和那个“壁纸背后的女人”意象联系起来理解:两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演变,显示了“我”在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精神运动。
初始时“我”想勉力以所谓的理智来思考壁纸的图案,以克服对它的厌恶和恐惧,此时壁纸的图案在“我”看来是“折断的脖颈”和“两颗眼白上翻的眼球”[10]212,分别象征着“扼杀”和“监视”。我虽然不喜欢壁纸,但是又庆幸图案阻隔了它们接近“我”的企图。而在“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约翰表明想要离开却遭到拒绝,壁纸成了“我”唯一的兴趣对象,“我”不再厌恶它。上面图案也产生了变化,“凭借月色,花纹的肌理演变、幻化成了栅栏!”[10]221月色在文学传统中经常和女性与癫狂联系在一起,这里表明了“我”精神的进一步崩溃。而“栅栏”则隐喻着“禁闭”与“隔离”,此时“我”肯定地认为“那个图案里朦胧黯淡的暗纹是一个女人。”[10]221图案从监护者开始转变为镇压者,“我”开始同情“栅栏”后的女人。最终,“我”认同了她们,此时所有原本是“那个女人”的动作开始以“我”为主语,读者慢慢不再能够分辨描述的究竟是“我”还是壁纸后的女人。壁纸已经完全变为邪恶的存在,是“我”必须要“一点一点,尽力尝试着褪去的束缚。”[10]226
“我”对壁纸进行了一系列的认知重构,隐喻的一系列变形既是“我”精神状况不断恶化的显现,伴随着“我”对与约翰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和建构;也象征了在创作和意义生成过程中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我”即吉尔曼作为女性对艺术的渴望与受到的压抑。壁纸既是叙述者形象和生活的隐喻,又是其打破封闭,建构自我的突破口。最初的厌恶是因为壁纸肮脏沉闷,模糊不清的状态正好影射着叙述者不能掌控的生活现状。“我”此时还寄希望于约翰身上,相信他对自己的爱护,相信他最终会带自己脱离这种生活。但是随着言语交流的一步步崩盘,“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和约翰身份上的不对等,他不可能理解“我”,也不可能帮助“我”痊愈。
壁纸上的图案会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它慢慢变成“我”无所事事的生活中唯一和思维与精神活动相联系的部分。当“我”把精神投注在壁纸上时,它便开始具象化为“我”的形象,和叙述者的状态形成一种对应:
夜里,在任何光线下,于黄昏的薄暮中,烛光下、灯火里,还有最糟糕的便是凭借着月色,花纹的肌理演变、幻化成了栅栏!我的意思是指壁纸外在的图案,而隐藏于其后的那个女人简直呼之欲出,再清晰不过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壁纸背后呈现的影像是何物,那个图案朦胧暗淡的子模式,但现在我可以很肯定那暗纹是一个女人。在白昼的天光下,她显得柔韧克制,安宁平和。我以为是那时呈现的图形使得她能如此沉静。好生奇怪。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持守缄默。[10]
在隐喻结构中,日光象征着男性的力量,理性和活力,而月光则总是和女性相对应,预示一种潜在的疯狂的力量,温柔和神秘。同时,两种时间与心理状态上的呼应也和“我”的抑郁症状表现产生对照:白天病情相对稳定,晚上则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时段,伴随着失眠和幻觉。
不论是“我”的病症还是对壁纸的解读,实际上都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根源——男性权威的束缚和压制。小说中作为“我”的对立面的女性形象,约翰的妹妹珍妮,即是传统社会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她是位理想完美、尽心尽职的女管家,看来没啥职业比这个更适合她了。我完全相信,她肯定认为正是写作让我惹病上身的!”[10]珍妮对待壁纸的态度和约翰如出一辙,她与“我”的关系正如壁纸和图案后面的女人。
珍妮代表着认同男性统治传统的女性,她们顺从命运,安于做男性身后沉默模糊的影子。《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详细描述了19世纪小说中“屋中天使”的女性形象,她们没有自己的个性,存在的意义在于体现出男性心目中女性应该具备的勤奋、贤淑的理想品德。女性天生就该属于家庭,属于丈夫,属于孩子,她可以成为任何身份除了她心中真正的自己。因此,与“屋中天使”相对应的“疯女人”形象其实象征着镜子另一边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让男性权威感到恐慌,也让珍妮这样的传统女性感到恐惧。小说中珍妮对“我”的不认同并帮助约翰对“我”进行监视实际上表明了女性在内外语境中对自我的双重异化,她们既是两性关系中的“他者”,又是自我的“他者”。
显然,珍妮代表的传统女性和约翰代表的男性权威都不是女性主义文本的理想读者。他们不可能理解壁纸真正的奥秘,因为壁纸已经成为一种质疑男权,反抗传统对女性禁锢的隐喻,唯有具有相同认知结构的“我”(也代表着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读者)才能解开壁纸的秘密。
因此,虽然大多数的解读认为小说最后“我”最终进入疯癫的状态,但在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视角下却可得出另一种不同的结论。“我”在最后终于和壁纸后面的女人合二为一,象征着“我”完成了在男性权威中对女性文本含义的独立构建,“我”终于打破了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束缚,从“壁纸”后走入现实的生活。
黄色本是生命力和活力的象征,但是文中壁纸的黄色却是“种极陌生的黄色……它让我联想起一切我见到过的黄色的东西——不是像毛莨那类漂亮的植物,而是些老旧污秽、腐败恶劣的黄色。”[10]223壁纸的黄色隐喻着女性在封闭的家庭生活中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萎缩,女性写作很难在这种受到限制的环境中产出有意义的作品,甚至连她们独立的精神个性都开始走向崩坏。吉尔曼曾在杂志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论述繁琐封闭的家庭生活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她本人也极力想要摆脱这种无形的幽闭,希望到户外去创作、去建立和他人(尤其是女性之间)的社交关系。正如文中的“我”最终和壁纸后的女人融为一体,得以“到了外面,一切事物都是绿色而非黄色了。”[10]230绿色和衰败的黄色再次在视觉和心理寓意上形成对比,表达吉尔曼对打破家庭生活束缚和压抑的渴望。
在现实生活中,吉尔曼最终下定决心结束原先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她与丈夫华特协议离婚,结束了“休养疗法”。此后,她热衷写作并出版自己的作品,在各大社会集会进行宣讲促进社会福利、妇女权力等相关议题,并在《黄色壁纸》发表二十五年后出版了探讨女性乌托邦可能性的著作《她的国》(Herland)。吉尔曼已然从身心的折磨和痛苦的逃避中的涅槃,以文字为利刃一点点撕破了覆盖在自己身上的壁纸,重获新生。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在《黄色壁纸》中,吉尔曼展示了女性话语的缺失和重建的必要性及其对女性突破束缚和压迫的重要意义。而女性主义文体学为《黄色壁纸》提供了一种紧密联系文本的解读方法,使得理论分析得以以文本为依托,从文本最基本的语词构成处切入吉尔曼对男权社会的批判;之后再从隐喻的选择、生成和发展中分析女性作家对特定意象的关注,揭示出更大层面上女性写作的局限和困境。可以说,在女性主义文体学的解读下,《黄色壁纸》既是女性主义经典文本,也是关于女性通过写作与阅读争取自由的珍贵史料。
[1] Mills S. The Gendered Sentence[C]//CAMERON D. The Feminist Critique of Language: A Reader. London: Routledge,1990:65-78.
[2] Mills S. Feminist Stylistics [M]. London:Routledge, 1995:40,97-164.
[3] Goodman L. Approaching Literature: Literature and Gender[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4] E.安.卡普兰.两种妇女乌托邦——吉尔曼和皮尔西的两部小说[C]//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2-116.
[5] 洪流.规训权力与反抗权力[J].外国文学,2006(3):59-64.
[6] 宋晓萍.公共性和私人性:丁玲前期创作的悖论[J].妇女研究论丛,2004(3):53-57.
[7] 玛丽·塔尔博特.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M].艾晓明,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0-78.
[8] 王淑芳.壁纸与疯女人:女性之境:美国《黄色壁纸》文学评论综述[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7(5):76-80.
[9] 王志伟.论女性主义文体研究[J].时代文学,2012(8):142-143.
[10]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她的国[M].朱巧蓓,王骁双,康宇扬,等,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205-231.
[11] 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M].韩敏中,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51-64.
[12] 张平.文体学中的性别政治:《女性主义文体学》简介[J].妇女研究论丛,2008(6):85-87.
[13] 张平,刘银燕.《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中女性在场的缺席[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36-141.
[14] 张平.女性话语的力量:《同命人审案》的女性主义文体学分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54-57.
[15] 周翔,吴庆宏.《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女性主义文体学[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4):208-209,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