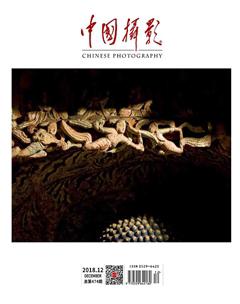人工智能,质询人工之能
郑萍萍
一
10月25日,一个胖嘟嘟的、身穿黑色礼服、面目模糊的男子肖像赢得了艺术界的关注。当天,这幅由人工智能创作的《埃德蒙德·贝拉米的肖像》在纽约佳士得拍出43.25万美元(约合3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比预期的1万美元高出了几十倍。
这幅画—“如果这是正确的术语”—是由一个来自巴黎的3人团体,使用“生成式对抗网络”(GAN)“创作”的。他们将1.5万幅创作于14至20世纪的肖像画输入“发生器”中,“发生器”通过学习不断地炮制出大量作品,再交由“鉴别器”去识别,直至鉴别器误以为计算机创作的图像是由人工绘制完成的。
这三位25岁的年轻人希望证明,人工智能不仅能操作无人驾驶汽车,或者改变制造业,还拥有艺术家的“创造性”,而这也许正是人类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了—李开复在2017年5月接受Quartz采访时都还确信:“艺术和美很难被人工智能取代……现在是转行人文艺术学科的最佳时机。”
其实,这不是人工智能第一次试图踏入艺术的领地,不过这一次资本给出了它的答案。
二
2017年初,罗格斯大学的艺术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在GAN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一套名为“创造生成网络”(CAN)的系统。和只会模仿的GAN不同,在CAN模型中,“鉴别器”要求“发生器”最大化地偏离已知的艺术风格。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CAN果真开始生成极富创造力的抽象艺术品。该实验室主任艾哈迈德·埃尔加迈尔(Ahmed Elgammal)决定组织一场图灵测试:不知情的受试者被邀请观看四类作品,分别是CAN和GAN生成的图像、2017年巴塞尔艺博会上的人类艺术家作品,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的作品。
结果53%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被认为是人类作品,而在对照组,也就是艺博会展出的艺术家作品中,只有41%被认为是出自人类之手。不仅如此,人工智能作品的各项评分都超过了艺博会上的参展作品,尤其在创新性和复杂度上。值得欣慰的一点是,那些五六十年代的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的作品以85%的优秀成绩领跑测试,在喜好程度上也高于人工智能的创作。
代表人类参战的艺术家几乎全部拒绝评论此事,他们更愿意相信,源于“理性”的人工智能至多可以替代艺术创作里“劳动”的成分,却不可能完成源于“感性”的自由意志的创作。正如一位获得了无数点赞的网友留言:“伦勃朗的伟大不是那些精湛技术的定制画,而是那些浸透了人生苦楚的自画像,即使人工智能能画的一样,我们也并不会感动。”
但是,一方面,正如上面的实验所显示,大众并不能准确地分辨谁才是“伦勃朗”;另一方面,在“创新性”的生成模式中,人工智不再是复制已知的艺术风格,而是通过学习摸索出艺术的“自然”之道,对艺术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它很有可能比艺术家更了解大众对艺术的喜好。
三
回顾历史,艺术家对科技一直抱有谨慎的批判态度,回想19世纪初,摄影术的诞生引来的一片质疑。今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样的谨慎不无道理:作为机械之眼的胜利,摄影技术消弭了人类观看的多样性,世界日益被简化为技术式的观看,而这正是今天人工智能技术“观看”的起点。
但科技一直都在影响着艺术的发展,新材料、新工具、新技术的出现不断地改变着艺术的样貌。未来,人工智能是会淘汰一部分艺术家,还是会像摄影一样,作为一种语言,帮助另一些艺术家成为新的大师,我们难以预料。
不過,不同于19世纪初,科技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自我迭代”逻辑不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而人工智能企图改变的是底层的社会结构。
今年10月,抖音国际版Tik Tok击败了Facebook、YouTube等巨头,成为当月社交应用排行榜上的下载冠军。而为应对抖音的威胁,Facebook在10月底,悄悄发布了一款功能同抖音类似的应用,名为Lasso。相比谨慎的艺术家,乐观的大众正沉迷在技术的狂欢之中。借由数字、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曾经在文字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终于登上了自己的舞台。
7月,社交电商平台“拼多多”的上市,照亮了它背后的近3亿活跃用户。透过买家秀的照片,人们看到了一个“隔壁的中国”:裸露着红砖的房间里,废弃的缝纫机便是这家人的电视柜,上面摆放着一台399元购买的“4k高清智能网络液晶电视”;一个售价29.9元的简易衣柜被放在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照片下是买家诚恳地留言“高端实用,上档次”……
关于“拼多多”最多的讨论莫过于社会对“消费升级”的误解。对此,创始人黄铮表示:“消费升级不是让上海人去过巴黎人的生活,而是让安徽安庆人有厨房纸用,有好水果吃。”所谓的误解,只是长期以来,主流社会对“隔壁中国”的忽视。
由人工智能算法主导的社交平台,让我们认识了尬舞的“红毛皇帝”、直播农村生活的“欢子”、每天吃竹鼠的“华农兄弟”……他们被视为触网率普及后,涌入互联网的第二、第三波人口红利。技术赋予了他们便利与平等,并教会了他们观看之道。在视觉传播时代,他们凭借“不修饰”“接地气”的民间影像打破了以一二线城市为主的较早一批网民的固有阵地,在绝对数量上获得优势。在2018年8月短视频平台活跃用户数排行榜TOP10中,快手以活跃用户数21939.34万人位居榜首。
不过事情也正在发生变化。“欢子”购买了单反、滑轨和无人机,“华农兄弟”请来了航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农村过着隐居生活的90后四川女孩李子柒,凭借制作精良的视频获得了1500万粉丝。视频里,李子柒妆容精美、服装考究;她的家被精心布置成田园休闲风,甚至还有秋千;大光圈下的每一帧画面都在有意识地选择性地营造着一种田园之美。
大众陷入影像生产与消费的狂热,科技为大众打开便捷之门。
而风,继续吹向大洋彼岸。
四
全球化的过程,就观看而言,正是视觉的殖民化、标准化的过程(《图像与观看》,谢宏声)。以为驾驭了“看与被看”的自由,大众忽略了技術织就的更大的一张网。
利用公共视频记录的影像创作的电影《蜻蜓之眼》,显然是一个隐喻:那些一个个隐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习以为常的监控器摄像头,共同组成了一个巨大、锐利的“复眼”,“我们每天被它看到300次”,所有的行迹都被计算、分析,甚至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捕捉的“情感”,也可以轻易地被数据化、进而标准化。
在导演米夏埃尔·克利尔(Michael Klier)看来,这种时刻存在的泛电影方式,不知不觉地让我们的日常行为沦为一种同质化的电影行为,成为视觉的新型设备。(《天真的摄像机》,保罗·维利里奥)。他导演的电影《巨人》(Der Riese),拿下了1984年在法国蒙贝利亚尔举行的第二届国际视频博览会大奖。同样,这部电影里的图像是由安装在德国城市街头的自动监控摄像头拍摄的。
我们正像当年失去独立的观看能力一样,一步步地将自己的感官、欲望、隐私让渡给不断扩展边界的技术—无论我们是时刻警惕的艺术家,还是心无芥蒂的普罗大众。徐冰借《蜻蜓之眼》质疑技术的边界,但制作的每一步又何尝不处在这张巨大的网络之下。艺术试图通过技术把握现实,但在技术的作用下,现实的定义和认知却在不断发生变化。
当然,这一切不仅仅关乎科技,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也许,真正能将我们解救出技术之手的只有自己,正如Google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所言,技术是推动者,但人类必须处理人类自己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视频编辑,毕业于南京大学,长期从事新闻摄影一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