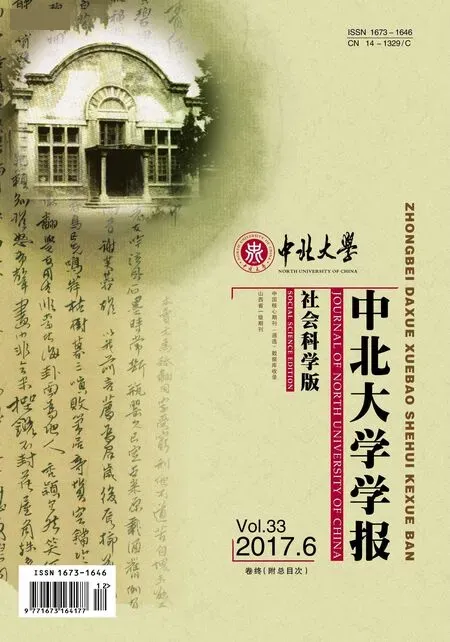国际援助协调的多中心治理研究*
王 微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国际援助协调的多中心治理研究*
王 微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作为援助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援助的协调性在本世纪受到了空前重视。 本文剖析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国际援助协调中的适用性, 并从国际组织层面、 援助主体之间、 援助方与受援方之间、 民间力量等方面阐述了国际援助协调事务的“多中心治理”框架, 这也是推动国际发展事业由资源动员走向全球治理的内在要求。
国际援助; 国际援助协调; 多中心治理; 援助有效性
0 引 言
随着本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援助有效性问题的空前关注, 援助的协调性作为援助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受到广泛重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援助协调性定义为:“受援国政府从援助国获得援助并将其纳入国家发展目标和战略之中的过程。”[1]也就是说, 国际援助要能支持受援国的国家目标、 优先事项和发展战略, 其强调的是援受双方的协调。 21世纪以来, 援助协调日益强调捐助者和受援国整合各方资源的共同努力, 它不仅包括捐助者之间对援助行动的共同安排, 也包括援助活动与伙伴国国家战略、 发展进程的一致, 还包括援助系统与其他系统的集体效益。 援助协调日益成为新时期国际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议题。
援助协调自20世纪60年代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并成立了两大国际援助协调组织: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1960年)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65年)。 在七八十年代, 由于冷战的原因, 援助协调性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1992年, 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高级会议上, 援助国提出了援助政策的“一致性”概念。 “一致性”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传统援助国开始重新重视援助的协调性议题。 在这一时期, 还诞生了日后在国际援助协调上起重要作用的财政主体——欧洲发展基金EDF(1993年)。 2000年以来国际社会举办了关于援助有效性问题的多伦国际磋商并出台了一系列全球性文件: 《罗马宣言》(2003年) 《巴黎宣言》(2005年) 《阿拉克行动议程》(2008年) 《釜山宣言》(2011年)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 其中, 《罗马宣言》 《巴黎宣言》最明确提出要提高捐助者协调的重要性, 《阿拉克行动议程》 《釜山宣言》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则使援助协调性具有了援受双方协调和援助系统与其他系统协调等更丰富的内容。 近20年中, 人们对协调性认识的逐步深化也使得协调性从“捐助者协调(Donor Harmonization)”扩展到了全方位的“援助协调(Aid Coordination)”[2]。
1 国际援助协调的挑战与困难
正如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家摩根索所说: 无论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其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3]尽管援助协调性近二十年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但由于各国的对外援助政策通常还是首先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利益, 然后在此基础上关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整个援助系统的效果, 而各个援助国由于历史和国情的不同, 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同和追求的领域、 方式都不相同, 再加上整个国际援助系统缺乏一个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权威机构, 因此使得援助的协调事务变得错综复杂, 困难重重。 这主要表现在双边援助与国际协调之间的矛盾上。
由于双边途径能够较好地贯彻援助国的理念与意图, 便于援受双方的沟通与合作, 故各国之间的双边援助是国际援助的主要形式。 这些双边援助的项目主要来自23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国(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 到2011年, 官方发展援助的双边援助总额为160.748亿美元, 其中, DAC国家双边援助额为134.411亿美元, 占援助总额的83.62%, 较2000年总额增长了167.83%。 当前的对外援助, 百分之八十的比重还是采取国家对国家(stat-to-state)的双边援助形式, 其动因就是为了让援助服务于援助国的理念与意图, 实现援助国的国家战略, 而援助协调常常是为了应对各种全球问题和人道主义危机, 实现全球战略, 这里就有一个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矛盾冲突与调和问题。 同时, 双边援助中援助国具有主导权与话语权, 而援助协调行动的顺利进行要求援助国让渡部分主导权和话语权, 而国际援助领域缺乏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协调主体, 往往使得这种要求难以落实, 国际援助领域“各行其是”的局面暂时还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2 国际援助协调的可能性
在国际援助协调问题上, 最大的困难是存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矛盾冲突与调和问题, 但这并不代表国际援助协调是不可能进行的。
第一, 《罗马宣言》(2003年) 《巴黎宣言》(2004年) 《阿拉克行动议程》(2008年) 《釜山宣言》(2011年)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年)等一系列全球性文件的颁布, 体现出全球国际援助正趋于网络化和协调一致的趋势。 虽然这些协议只构成了一个指导性框架而不是保证援助效果的唯一发展手段, 但其为各援助方之间的合作、 相互信任以及联合行动提供了一个制度性指导, 其所倡导的核心思想代表了未来国际发展援助的趋势, 援助协调性是援助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已在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
第二, 近20年中, 人们对协调性认识的进步也使得协调性成为对外援助的核心原则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关于协调性的理念、 原则、 做法越来越被国际发展界各主体所接受, 并在援助实践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指导作用。 援助机构已采取了各种行动来实现共同安排, 并不断努力采取新的方法和措施来促进援助的分工与协作, 如开展更多的联合行动, 建设援助同盟等。 在《阿拉克行动议程》(2008年)中, 援助国和发展中国家一致同意在2009年6月前就援助的跨国分工启动对话, 援助国之间将实施更多统一的援助安排, 将建设更多的类似于世界银行学院的全球性交流和学习平台或国家性、 区域性的协作平台。 欧盟采用了联合融资安排(Joint Financing Arrangements for EU Donors, JFAs)的方式来帮助成员国协调其援助方式和程序要求, 并促进与非欧盟捐助者的协调。 目前, JFAs已在玻利维亚、 莫桑比克、 尼加拉瓜等国使用。[4]
第三, 受援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援助的协调性, 把援助与财政、 金融、 贸易等纳入统一的国家发展战略, 并采取各种行动来配合援助国的援助项目, 以尽量降低援助成本, 提高援助实效, 已取得一些成效。 OECD-DAC在14个伙伴国进行了关于协调性和一致性进程的调查研究, 调查发现, 14个国家中有9个已经完成了协调行动计划的制定, 其他5国正在筹备或即将完成。[4]*这些国家有孟加拉国、 莫桑比克、 玻利维亚、 尼加拉瓜、 尼日尔、 柬埔寨、 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亚、 赞比亚、 塞内 加尔、 斐、 越南、 吉尔吉斯共和国、 摩洛哥等。
援助协调困难重重但又是大势所趋, 为了提高援助协调的效果和效率, 下面引入多中心治理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3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涵及其在国际援助协调中的适用性
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创立者是美国的奥斯特罗姆夫妇(Vincent Ostrom and Elinor Ostrom), 是多元社会中公共事物的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 打破政府作为唯一管理主体的现状, 实现管理主体多元化, 从而形成权力分散、 管理交叠、 存在于政府之外充满竞争、 富有效率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3.1 内涵
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强调参与者的互动过程和能动创立规则的治理形态。 在这里, 多中心是指许多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或组织机构。 权力分散、 管辖交叠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因发挥自治能动性、 充满竞争而富有效率。 多中心治理理论包含如下几个层次的涵义: ①多中心治理以自主治理为基础, “自发性的属性可以看作是多中心的额外的定义性特质”[5]78; ②强调各个主体的参与和协调, “它们在竞争性关系中相互重视对方的存在, 相互签订各种各样的合约, 并从事合作性的活动, 或者利用核心机制来解决冲突”[6]11; ③公共事务供给的多元化, “‘多中心’意味着有许多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6]12; ④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政府不再是单一治理主体, 主要以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的方式对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提供进行间接管理。[7]11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Ostrom)教授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V.Ostrom)教授共同创立的多中心理论是多元社会中公共事物的治理理论, 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 强调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社区组织均可成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 从而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来。 打破了以往学者认为只有国家或市场是解决公共事务治理之道的定式思维, 提出了政府与市场之外新的可能性方式, 即在政府、 市场两个中心之外引入社会, 作为“第三个中心”, 这是该理论的贡献与创新之处。[8]18
3.2 适用条件
3.2.1 公共产品——多中心治理理论适用性的逻辑起点
多中心治理理论根本目的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存在基础和逻辑起点。 多中心治理理论能否被运用于国际援助协调问题中, 首先取决于国际援助是否属于公共产品。
20世纪60年代中期, 美国学者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 ard J Zeckhauser)、 约翰·平库斯(John Pincus)、 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就已经把对外援助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了。 进入21世纪, 随着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世界银行(WB)等多边援助机构对援助有效性的关注, 对外援助的国际公共产品属性日益获得人们的共识。 拉维·坎布尔(Ravi Kanbur)和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指出, 以国际公共产品形式提供的对外援助会增加作为发展援助的比重。[9]55-94托德·桑德勒将对外援助归类为公共产品中的连带产品(joint products), 亦即能同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出且各自的公共性程度有所不同的产品。 马克·费罗尼(Marco Ferroni)强调, 官方发展援助的作用之一是促进市场或受援国政府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供给, 国际组织和官方发展援助可起到为区域性公共产品融资充当催化剂、 来源和渠道的作用。[10]93,157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 由特定援助国或多边援助机构提供的对外援助是可供其他援助国或非援助国及其民众获益的国际公共产品。 例如, 以维护和平、 减少贫困、 防治疾病、 保护环境、 改良教育、 扩散技术等为目的的对外援助, 至少能从两个方面让国际社会受益: 一是有利于消除或降低由国际危机引发的国际风险, 如战乱、 冲突、 传染性疾病、 难民潮等, 二是有利于消除或降低各国企业在受援国的投资风险, 从而保障其正常的投资收益。[11]
3.2.2 多个治理主体——多中心治理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基础
“我们不指望发现充分整合的命令结构, 而指望发现权威充分分散并且有许多不同的命令结构。”[12]116国际援助领域, 没有一个绝对的一元权威, 其治理主体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 欧盟(EU)、 世界银行(WB)这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也包括主权国家对外援助机构, 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 德国经济合作部(BMZ)、 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等及各受援国政府(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 还包括大量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如美国卡特基金会(Carter Center)、 福特基金会(Ford Fundation)、 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 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 全球抗艾滋病、 肺结核及疟疾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 应对千年挑战团体(MCC)、 全球环境基金(GEF)、 国际行动援助(Action Aid)、 国际红十字协会(Red Cross)、 英国乐施会(Oxfam)等等, 还有大量的企业和个人。 即使像UNDP、 DAC、 EU、 WB这样有影响的组织, 他们的主要职责也只是协调和监督, 而不能发布命令和指挥。 因此, 这样的格局符合多中心治理的条件。
3.2.3 利益相关者多元化——多中心治理理论适用性的支撑条件
利益相关者是指与某一特定组织或事件存在利益关系, 能够影响其决策和行动并受其决策和行动所影响的任何相关者。 援助协调具有因素复杂、 影响范围广等特点。 当援助国之间面对某一影响显著的全球性问题商讨协调机制时, 受到影响的不仅包括具体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国际危机具有链发效应, 灾难性后果往往不可估量。 本文认为, 凡是与援助协调存在一定的利益联系, 能够影响援助协调或被援助协调所影响的个人或团体都是援助协调的利益相关者, 其中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 国际非政府组织、 相关国家政府、 企业、 NGO、 民众等。 对于国际援助协调机制来说, 利益相关者多元化是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国际援助协调中应用的有力支撑。
3.2.4 民主——多中心治理理论赖以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
“每个人都有资格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12]133, “命令性权力的范围限制在最小范围内”[12]165, “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留给所有社群成员以及他们所选择的代表考虑”[12]165。 奥斯特罗姆夫妇认为:“民主社会的重要特质是, 决策权能够广泛分散, 从规范的观点来看, 民主社会的活力取决于社会治理中存在着实质的多中心因素。”[5]76显然, 援助协调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援助协调机制的参与者不应该仅仅是某一组织的单独行为。 当前, 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援助协调形式是国际磋商, 成员国政府通过相关主题的国际磋商, 形成有约束力的文件, 以各种“集体的力量”对援助国和受援国施加影响, 使一些问题在发展进化过程中有了外援的介入, 如难民救助、 气候援助、 卫生防疫和控制恐怖主义等, 从而以较小的成本和社会代价促成问题地解决。
4 国际援助协调中的多中心治理
事实上, 随着国际援助主体的多元化, 各援助主体加强彼此间的合作和协调已经成为未来发展援助的趋势。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差距问题工作组在2008年的报告中提出, 捐助者和受援国, 包括新增的捐助国, 应当加强合作, 以提高援助的一致性、 协调性, 改善可预测性。 援助相关方的行动能够决定援助协调规模的大小和它的成败。 对国际援助协调事务进行“多中心治理”, 构建多层次协调机制应围绕以下几方面重点展开。
4.1 国际组织层面
作为发展援助领域重要的国际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 EU、 世界银行(WB)等有影响力的主体应该切实履行其成员国发展合作政策的协调领导者的作用, 在优先合作领域和区域, 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确立有广泛的援助国参与的联合行动, 联合行动主要指通过援助各方开展更多统一的援助安排、 更多的联合任务和联合培训, 建立更多联合实践小组, 使援助的提供形式集约高效, 从而降低援助过程的行政管理成本和交易费用, (ARNE BIGSTEN and SVEN TENGSTAM, 2013)以DAC国家为主要对象, 以其2009年的对外援助成本为依据, 发现通过援助协调行动将使援助行政费用下降14%, 可以节约8.56亿美元的行政费用(2009年总行政费用为61.13亿美元)。[13]同时, 使相关各方能明确一定时期内将要达到的援助目标、 应遵循的行动原则、 要完成的明确任务、 即将采取的工作步骤和相关的评估、 监督、 问责方式等。 同时, 正视自身缺乏命令指挥这种刚性权力的事实, 善于运用开放式协调法。 开放式协调法由欧盟首创和力推, 主旨是在缺乏国际权威、 各国存在多样性的领域采用广泛参与、 同侪评议、 非约束性立法等“软”性治理工具以寻找最佳的政策实践, 实现政策趋同。 采用这种方法, 政策实施的责任和权利仍然保留在主权国家手中, 它们可以根据国内的情况自行决定实施规则的具体办法。 但是, 它们需要对外公布在相关政策领域中采取的基本政策措施和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 这既让主权国家之间互相学习, 又对其施加了无形的压力。 同时, 由于合作援助需要取得伙伴国政府的支持, 对于一些在合作过程中有种种困难的政府, UNDP、 DAC、 EU、 WB等应该为其提供支持, 帮助其履行责任。
4.2 援助主体之间
发展援助的超国家理论认为, 援助国集团内部各成员国之间在援助方向和内容上需要整体协调和整合, 超越国家界限, 避免内部竞争, 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 实现相互补充。[14]在战略层面, 主要是制定国家联合援助战略。 国家联合援助战略指就某一议题、 区域、 项目进行援助的伙伴国之间共同制定关于援助的根本长期目标和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必需行动序列和资源配置方案, 具有目标导向、 长期效应、 资源承诺和冲突互动的一般战略特征。 国家联合战略的制定有助于确保捐助者形成一个共同愿景, 使援助活动在共同的原则和框架下运行。
在行动层面, 具体来说, 首先, 在成员国内部分享共同的发展目标、 前景、 价值观和原则, 以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 形成共识是采取共同行动的基础; 其次, 尽量在合适的领域建立具有公共属性的计划和项目, 比如环保、 治污、 气候等关乎整个人类福祉的项目, 以减少早期协调的阻力; 再次, 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分工, 援助分工要注意利用成员国的相对优势, 优势不只是建立在财源的基础上, 同时也涉及更广泛的事项, 如历史、 地缘、 经验等, 尤其是新兴援助国和国际NGO的独特作用应予以重视。
4.3 援助方与受援方之间
由于各国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环境和不同的道路和特色, 故国际援助项目的设立和运作要估计各国社会制度的异同对于援助项目运作造成的影响。 正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 多维度的权力问题和接受国所具有的特点对于援助项目取得积极的成效至关重要。[15]国际援助必须关注受援国的国家主导权问题, 如果单向度的基于西方援助国的价值观来提出要求, 其项目运作所预期的许多目标可能并不现实, 无疑会影响援助的效率。 例如, 通过对尼泊尔、 卢旺达、 科特迪瓦和秘鲁四国的案例研究发现, 由于援助国的控制, 受援国在项目运作时几乎没有政策空间做自主的决定。[16]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类型、 难度、 重点等具有巨大差异, 因此, 发展援助必须强调受援国自身发展潜能的挖掘, 并且应该将能力发展置于发展议题的核心。 同时, 国际援助项目的实施不仅是人力物力的跨国转移, 也伴随着价值观和制度的传播, 二者间的关系十分微妙。[17]这就使如何很好地把当地文化和制度的特点与援助项目所带有的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之间进行融合, 如何减少援助实施过程中与受援国当地的政治宗教制度和社会习俗的差异而产生的排斥和抵制, 如何使国际援助项目能够适合当地的国情和民众的需要, 成为新时期国际援助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新时期的援受关系来说, 援助国应加深对受援国社会传统、 政治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的研究, 避免过度干涉受援国的国内政策制定, 充分保护受援国的自主权, 使受援国有充分的政策空间来发展适合国情的援助机制并满足国家的特定需求; 援助国应在受援国领导下, 支持该国实现其发展目标, 其扶持应随受援国本国的变化而灵活变动, 并为受援国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支持和帮助。 受援国应认识到发展的实质是加强本国的机构和制度, 以此达到治理目的, 而不是照搬援助国的模式, 也不是通过削弱所有权的方式实施援助, 而应在工作分配、 减少援助微观管理和加强结果管理方面进行改善。
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 应明确自己在援助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 首先应该向捐助者表明自己需要的援助项目的性质和数量以及愿意合作的领域, 确定本国希望捐赠者在其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其次, 受援国需要在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方面负起更多的责任, 深化地方政府、 公民社会组织和议会各方的能力建设, 因为未来更多的援助将通过受援国的体制和机构来开展, 因而受援国完善的政治、 经济体制以及良好的政策和公共治理能力将受到更多重视, 并可能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援助决策特别是援助分配的因素。
4.4 注重民间力量
多中心治理理论以自主治理为基础, 强调各个主体的参与和协调, 因此注重民间力量便是这一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 对外援助的私有化正是民间力量兴起的标志。 这一趋势体现在参与援助的私人资金、 私人企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三个方面。 当前, 私人援助增长快速, 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外部援助总额的主要部分, 2014年DAC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网络援助达到了4 117亿美元, 非DAC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网络援助也达到24亿美元(见表 1); 流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投资也从2005年的3 730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7 500亿美元。*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文件:《秘书长的说明:可持续发展筹资和2015年后发展议程方面的一致性、协调与合作》,E/2015/52,第9页。

表 1 2010~2015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网络资金总量 百万美元
总之, 越来越多的主体对国际发展感兴趣, 使得援助的提供和管理更加复杂, 同时还造成一定程度的援助重复、 无序竞争及受援国的高管理成本等。 一方面是由于新的捐助者的出现使得援助更加分散, 进一步增加了协调的难度; 另一方面是需要协调的援助主体也随之增加, 而每个主体对有效性援助的兴趣可能不同。 各种援助主体之间在项目、 资金、 对伙伴国政府影响力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竞争, 这就为援助带来了更多的协调问题。 尽管如此, 竞争的存在对于国际援助事业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在多中心治理框架下, 援助协调要思考的不是消灭竞争, 而是如何引导竞争, 使之发挥积极的效应。 奥斯特罗姆认为:“如果多中心体制能够解决冲突,并在适当的约束之内维持竞争, 那么它就能够是富有活力的安排。”[5]128
在新时期的援助协调中, 可以倡导成立由政府外援部门和本国私营部门共同参与的公共基金, 将私人援助基金整合进官方发展框架, 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与雪佛兰公司共同设立尼日尔三角洲伙伴关系倡议基金, 双方每年各投入2 500万美金, 制定了为期四年的发展伙伴计划, 推进针对该地区的技术合作和人道主义援助。 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 发达国家政府可以利用资金供给者的优势对其加强引导, 发展中国家政府则通过对其提供足够的支持, 使其不再采用传统的避开受援国政府对贫困群体提供服务的形式来提供援助, 而是依靠受援国政府来提供援助, 受援国政府在提供支持的同时扮演倡导者、 监督者、 协调者和引导者的角色。
[1] UNDP Policy Division. Aid Coordination and Management by Government: A Role for UNDP[EB/OL]. 1994-08-01[2017-03-15]. http:∥www.adb.org/projects/ta2419/main#project-overview.html.
[2] 武晋, 张丽霞. 国际发展援助的协调:回顾与述评[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4): 102-108.
[3] 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2, 56(2): 301-309.
[4] OECD-DAC. Overview of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on Harmonization and Alignment. The findings of the survey were used to report progress to the Second High-Level Forum on Harmonisation and Alignment of Aid Effectiveness (early 2005)[EB/OL] . 2012-04-04[2017-03-15]. http:∥www.oecd.org/document/61/0, 3746, en_2649_3236398_31659517_1_1_1_1, 00. html.
[5] [美]迈克尔· 麦金尼斯. 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 毛寿龙, 李梅,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6] [美]奥斯特罗姆, 帕克斯, 惠特克. 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都市警察服务的制度结构[M]. 宋全喜, 任睿,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7] [美]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 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 余逊达, 陈旭东,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8] Elinor Ostrom, Larry Schroeder, Susan Wynne.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 Boulder[M]. CO: West-view Press, 1993.
[9] Ravi Kanbur, Todd Sandler. The Future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on Pool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Goods [M].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1999.
[10] Marco Ferroni, Ashoka Mody.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ncentives, Measurement, and Financing[M].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11] 姜默竹, 李俊久. 朋友与利益——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对外援助[J]. 东北亚论坛, 2016(5): 40-49.
[12] [美] 文森特· 奥斯特罗姆. 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M] .毛寿龙, 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13] Arne Bigsten, Sven Tengstam.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J]. World Development, 2015(69): 75-85.
[14] 肖曾艳. 从“援助”到“发展”: 发展援助理论的演变轨迹——基于文献综述的角度[J]. 西部发展评论, 2012(00), 186-195.
[15] Mavrotas, Nunnenkamp. Foreign aid heterogeneity: issues and agenda[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07, 143(4): 585-595.
[16] 黄梅波, 李子璇. 2015年后国际发展援助展望, 厦门大学国际发展论坛, 2013.
[17] 蒋华杰. 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J]. 外交评论, 2015(4): 61-81
OntheMulti-CenterGovernanceofInternationalAidCoordination
WANGW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the coordination of aid has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in this centu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Multi-center Governanc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aid coordination and expounds the multi-center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aid coord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in aid bo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nors and recipients, and the usage of private sector forces. Meanwhile, these are also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rom resource mobiliza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id coordination; multi-center governance; aid effectiveness
1673-1646(2017)06-0057-06
2017-09-12
王 微(1974-), 女, 副教授, 从事专业: 国际援助、 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
D815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6.011
——来自中国对外援助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