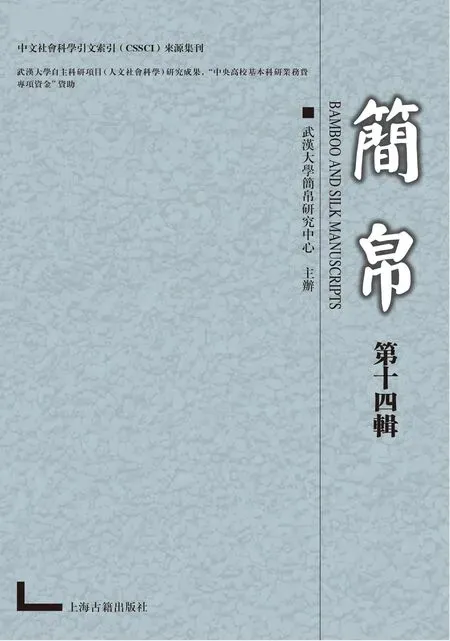《鄭文公問太伯》與中國古代文獻抄寫的問題
[美] 夏含夷
《鄭文公問太伯》與中國古代文獻抄寫的問題
[美] 夏含夷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於2016年年初公布了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所藏戰國竹書中的又一批文獻。這一輯的文獻多與春秋時代的鄭國有關,一共包括五種文獻。其中,《鄭文公問太伯》與清華收藏的其他文獻相比,相當獨特,存在兩種抄本,稱作《鄭文公問太伯(甲)》、《鄭文公問太伯(乙)》,下面簡稱《甲》、《乙》兩本。正如清華大學編者馬楠所指出的,兩個抄本“係同一書手根據不同底本進行抄寫,爲目前戰國簡中僅見的情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中西書局2016年,第118頁。這種僅見的證據爲了解中國古代文獻的抄寫過程提供了極其難得的信息,下面對這個問題作初步討論。
《甲》本與《乙》本的形式與内容都非常相似,但是也存有個别明顯的不同。兩種寫本的竹簡都長45釐米,寬0.6釐米,原來都由三道編綫編聯。清華簡的整理者雖然没有記載編綫確切的位置,但是從圖録可知兩個寫本也都相同,上面編綫離簡首約3.5 釐米,中間編綫離簡首約22.5釐米,下面編綫離簡尾約3.5釐米。《甲》本保存相當完整,一共包括14支簡,唯有簡3中斷,只存有下面一部分。《乙》本相對而言保存稍差,原來應該包括12支簡,但是現在只存有11支簡,原來第三支簡不存。另外,簡2和簡4都中斷,只存有下面一部分。簡 1、9、12的簡首都殘缺,簡1失去了一個字,簡9和簡12都失去了兩三個字。兩個寫本背後都没有標題。從《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的照片看,《乙》本多數簡簡背存有劃痕,《甲》本就不見劃痕。
上面已經指出,清華大學編者馬楠認爲兩個寫本“係同一書手根據不同底本進行抄寫”。儘管没有科學方法證明這一點,可是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看,很容易看出兩個寫本都是一個人抄寫的。兩個寫本的形式非常相似,每一個字佔的位置都一樣,字跟字之間空格的比例也差不多。書法的筆勢也非常相似,大多數的字幾乎一模一樣,顯然是一個人寫的。雖然如此,也有少數文字寫法不一樣。有的僅僅是一個寫本較之另一個寫本或多或少了一個部件,諸如: 《甲》本作“綣”,《乙》本作“綤”(即“穀”字);《甲》本作“綥”,《乙》本作“幽”;《甲》本作“肰”,《乙》本作“然”;《甲》本作“庚”,《乙》本作“康”;《甲》本作“酥”,《乙》本作“衛”;《甲》本作“俑”,《乙》本作“揅”(即“寵”字)等。也有個别例子,兩個寫本用不同的字,諸如《甲》本作“争”,《乙》本作“請”;《甲》本作“綧”,《乙》本作“遺”;《甲》本作“綨”(即“次”字),《乙》本作“事”。《甲》、《乙》本也各有個别漏字,譬如《甲》本第9簡漏一個“其”字、第14簡漏一個“曰”,《乙》本第9簡漏“及遨”(即“及吾”)兩個字,第 11簡漏一個“也”字,第12簡漏“戒之哉”三個字等,都可以根據相應的抄本補充。兩本也似乎含有個别錯字,諸如《甲》本第10簡“色”應該以《乙》本第9簡之“孚”爲正,《乙》本第12簡之“綩”應該以《甲》本第14簡之“綪”(即“殷”字)爲正。除了這些少數不同之外,兩個文本還有一種系統性的不同。文本的内容往往牽涉到地名,地名的名字多半都含有“邑”旁,可是兩個抄本的寫法迥然不同。《甲》本一律都將“邑”旁置於字的左邊。與此不同的是,《乙》本將“邑”旁置於字的右邊,如下:
疲 疳 鄶





《乙》

從“邑”旁的位置,我們大概可以確定兩個抄本是根據兩個不同的底本抄寫的,兩個底本反映了兩個不同的書寫傳統。楚國的書寫習慣一律都將“邑”旁置於字的左邊,正像《甲》本那樣。與此不同的是,秦國的習慣是將“邑”旁置於字的右邊,正如《乙》本那樣。我們當然不能確定《乙》本的底本就是從秦國(抑或秦國的系統)來的;也有可能中國早期其他的書寫習慣,諸如三晉或是齊魯系統,也將“邑”旁置於字的右邊。我們也不能排除這僅僅是兩個抄手自己的習慣。然而,《鄭文公問太伯》的兩個文本如果像馬楠所説的那樣是“同一書手根據不同底本進行抄寫”的,我們很難想像這樣好的書手會隨意地改變他的習慣。我們只能同意馬楠所説,他很細心地抄了兩個不同的底本,每一個抄本都如實地反映了兩個底本的原來面貌。
《鄭文公問太伯》的兩個寫本爲了解中國古代文獻的抄寫過程提供了極其難得的信息。中國古文字學家對這個問題向來注意得不多。西方學者相對來説非常關心這個問題,早已經發表了各種詳細的討論。在西方漢學界最有影響的討論應該算是柯馬丁(Martin Kern)在2002年發表的《異文分析與中國古代文本製造: 方法論的反思》。*Martin Kern,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Analysis of Textual Variants and the Modes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 in Early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4.1-4 (2002),PP.143-181. 特别見第167頁。本文有中文譯文: 柯馬丁,《方法論反思: 早期中國文本異文之分析和寫本文獻之産生模式》,李芳、楊治宜譯,載於陳致主編,《當代西方漢學研究集萃: 上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9—385頁;特别見第375頁。在這篇文章裏,柯氏對戰國秦漢寫本引用《詩經》的情況作了概述,將引文和傳世本《毛詩》作比較,發現三分之一的字都不同,儘管它們原來表示的詞應該相同。根據這一點認識,他説古代抄寫文獻過程當中可能會有三種不同的抄寫模式:
● 抄手複製他面前的底本,因此可以對照底本和抄本
● 有一人拿底本,給抄手念書,抄手一邊聽一邊寫
● 抄手按照記憶來寫,抑或按照他人唱誦,没有一個底本
柯馬丁説按照他的分析第三種抄寫模式(即抄手按照他自己的記憶來寫,抑或按照他人唱誦)更有可能。因此,他强調説文獻的抄寫通常没有底本:
假如承認在早期中國既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字規範又有大量的同音詞,一個抄本和與之對應的傳世文獻有三分之二的字相同,同時有三分之一的字(通常是比較難寫的字)不同,我們大概應該考慮這符合於没有底本的文本製造模式。*Kern,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P.171;另見柯馬丁,《方法論反思》第379頁。
柯馬丁的結論是根據詳細的統計學的分析,對西方學者相當有影響。譬如,麥迪(Dirk Meyer)經常根據柯馬丁的研究提出同樣的看法,在他2012年出版的《竹上的哲學: 中國古代的文本以及意味的創造》一書裏,他甚至説:
製造一個文本的新抄本,抄手是按照他所聽到的,不是按照他所看到的文字。*Dirk Meyer, Philosophy on Bamboo: Text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in Early Chin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xts 2 (Leiden: Brill, 2012),P.150.
爲了支持這種推論,麥迪還提出“與歐洲文本製造進行對比”。中國古文字學家和文獻學家雖然對這個問題没有給予多少注意,過去也没有具體證據可供討論,但是我的印象是大多數中國學者大概默認的是柯馬丁所提出第一種抄寫模式,即有一個抄手複製他面前的底本。第二種模式也很有可能。不但有文字學證據可以説明,即“讎”字及其用法,並且也或多或少有一點物質證據,即1958年在湖南長沙金盆岭9號墓葬所出的兩個瓷俑,一個拿書念誦,一個執筆抄寫。這兩個模式雖然不一樣,可是都假設有一個底本。
幸運的是,在柯馬丁2002年發表文章和麥迪2012年出版書之間,中國就發現了一些文獻證據説明古代文獻的抄寫確實是從一個底本到一個抄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載有《天子建州》兩個文本(編者稱作《甲》本和《乙》本),很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抄手分别書寫的,而且有證據説明《乙》本很可能是《甲》本的底本。李孟濤(Matthias Richter)對這兩個文本做了詳細比較,説:
對比兩個文本的時候,第一個特點是“也”字的特殊寫法。在整個的文本裏,這個字出現四次,後三次都是戰國文字常見的“也”字,然而兩個文本裏第一次出現的“也”字的寫法從來没有見過。如果僅有一個文本含有這種特殊寫法,我們很容易理解。然而,兩個文本都同樣有特殊寫法只能説明一個文本是另一個文本的底本,第二個文本的抄手應該是模仿第一個文本的字型。僅僅從這一個例子,我們仍然無法判斷哪一個文本是底本,哪一個是抄本,但是我們可以肯定一個受到了另一個的影響。*Matthias L. Richter, “Faithful Transmission or Creative Change: Tracing Modes of Manuscript Production from the Material Evidence,” Asiatische Studien /Etudes Asiatique 63.4 (2009): P.897.
李孟濤還做了相當大膽的推論,説《天子建州(乙)》應該是底本,《天子建州(甲)》是抄本。他説:
《乙》本抄手的筆墨雖然很不整齊,並且在整篇文本裏也不能保持統一的書法,可是也不能説他是完全没有經驗的。字型的構造和筆勢都正確。有的時候,他似乎不知道怎麽寫一個字。我們大概可以看出他不是一個常常寫作文本的人,但是他仍然明了所寫的内容。根據《乙》本的書法,我們大概可以判斷他寫得很快,也没有太用心。
《甲》本明顯是《乙》本的抄本。《甲》本的形式很整齊,文字的構造都寫得很正確,很容易看懂。雖然如此,這個抄手不是很識字,不能判斷哪一個特殊文字正確,也不知道《乙》本的特點都有甚麽意思。這不是説他不是一個好抄手。《甲》本的美觀特點比内容更爲重要。無論是《甲》本還是《乙》本,文字的正確性並不重要。同樣的現象也可以見於中國古代許多寫本上。讀者如果知道一個文本,他不需要統一文字,因爲他並不僅僅依靠所寫的文字知道文本的意味。文本只是爲了提醒讀者的記憶。因爲文本的作用並不是爲了公布新的内容,文本外貌的重要性並不在乎它的可讀性,而是在乎它的象徵價值。*Richter, “Faithful Transmission or Creative Change,” PP.904-905.
無論李孟濤的這種看法有多少説服力,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天子建州》兩個文本之間的互相關係,也可以肯定一個是底本,一個是抄本,抄寫過程是按照視覺來抄寫。*墨子涵(Daniel Morgan)在未發表的文章裏,指出這兩個文本多處都使用同樣的特殊寫法,不但是文字如此,並且兩個文本的非文字部分,諸如標點符號和文字的飾筆也正好相同。他得出結論説:“根據這些相同點,我們可以肯定兩個文本的關係只能是根據不斷的視覺的抄寫而産生的。”見Daniel Morgan, “A Positive Case for the Visuality of Text in Warring States Manuscript Culture,” “The Creel-Luce Paleography Forum”論文,芝加哥大學,2010年4月24日。
《天子建州》兩個文本的關係與《鄭文公問太伯》兩個文本的關係雖然不一樣——《天子建州》的兩個抄本是由兩個抄手製造的,《鄭文公問太伯》兩個抄本是由一個抄手製造的——然而抄寫過程應該相同: 無論是一個抄手還是兩個抄手,抄手都是一邊看底本,一邊抄寫。這不一定説明柯馬丁所提出第三個抄寫模式,即“抄手按照記憶來寫,抑或按照他人唱誦,没有一個底本”完全不可能,但是至少到現在爲止,較多的證據説明,在戰國時代,文本的製造方法通常是從一個底本到一個抄本抄寫的。當然,我們還需要更多的證據出來才可以得到更廣泛的結論。不過,除非有新的反證出現,我覺得一個底本一個抄本應該算是中國古代最可能的文本製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