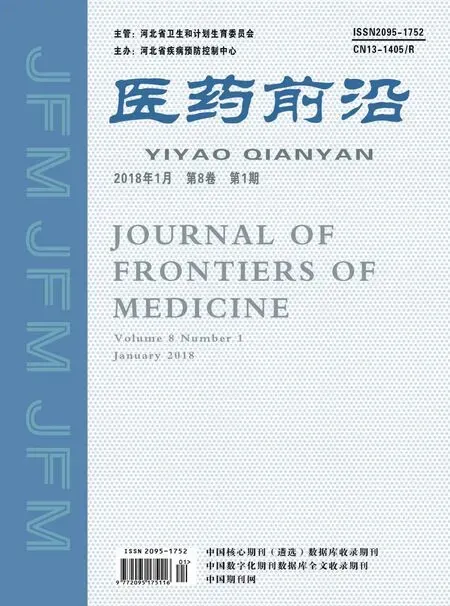5-甲基胞嘧啶
——高等生物的主要表观遗传标记
刘卓 潘攀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 江苏 张家港 215600)
引言
DNA中碱基的化学修饰近年来一直是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主要的DNA修饰包括腺嘌呤的甲基化和脱氨基,胞嘧啶的甲基化、羟甲基化和羧基取代,鸟嘌呤的氧化等,虽然这些修饰碱基的比例较低,但它们或者是细胞的生理活动所必需的,或者与细胞的病理发生密切相关,而且在物种间具有高度保守性和独特性[1]。DNA甲基化主要形成5-甲基胞嘧啶(5mC)和少量的N6-甲基腺嘌呤及7-甲基鸟嘌呤[2]。其中,胞嘧啶第5位碳原子上的甲基化动态修饰研究得较为深入。在上世纪早期,科学家首次用实验证明甲基化胞嘧啶是生物体内天然存在的化合物[3],修饰之后的碱基称为5-甲基胞嘧啶,简称为5mC。1951年,DNA中5mC的存在被Wyatt第一次报道[4]。
1.5mC和5hmC在基因表达调控中的基本作用
5mC是高等真核生物表观遗传修饰的主要形式,5hmC是5mC的羟基化形式,被称为DNA的第6种碱基,它最早于1952年在噬菌体DNA中被发现,它能被糖基转移酶介导糖基化修饰,从而使噬菌体基因组在进入宿主后能抵抗宿主限制酶的降解[5]。5hmC与5mC一样参与基因表达调控。一系列成果证实Tet1蛋白能调控CpG富集启动子处的DNA甲基化与羟甲基化水平,进而能促进干细胞中与多能性相关的因子的转录,使干细胞保持多能性[6]。为了具体探明甲基化与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科学家在基因组层面测定了5mC和5hmC的存在位点[7],结果表明5mC主要导致基因的沉默,5hmC主要导致基因的激活,这可能因为5hmC是基因去甲基化的先兆。
在基因启动子区内CpG位点上,甲基化可能通过3种方式影响该基因转录活性[8]:
(1)DNA序列甲基化直接阻碍转录因子的结合。
(2)甲基CpG结合蛋白(methyl2CpG2bindingproteins,MB Ps)结合到甲基化CpG位点,与其他转录复合抑制因子相互作用或招募组蛋白修饰酶改变染色质结构。
(3)染色质结构的凝集阻碍转录因子与其调控序列的结合。
以上三种抑制转录的途径均需要通过改变染色质构型来实现。目前已经证实,在CpG岛上的DNA甲基化能够改变染色质的构型[8]。在决定DNA构型的诸多参数中,DNA二级结构中大沟、小沟的宽度和深度参数对DNA-蛋白质、DNA-小分子结合有重要影响,如果这些参数改变,蛋白质或小分子的识别及与DNA结合的强度都会发生变化[10]。
2.5mC表观遗传修饰标记的优越性
2.1 生命活动的能量
BER通路是在原核生物中就已经存在的DNA修复机制,用于修复由于水解脱嘌呤、胞嘧啶及其衍生物的脱氨、鸟嘌呤的氧化、胞嘧啶和腺嘌呤特定位点上的甲基化等造成的单个碱基损伤[11]。然而在高等真核生物的基因表达调控中,这种修复机制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可以看到以上所提的两种已经被证实的去甲基化途径中,均利用了这种碱基配对修复机制来实现甲基化与去甲基化之间的动态变化。这种运用已存在的通路实现新的生物学功能,拓展原有通路的方式,能够节约生物体进行基本生命活动所需的能量。例如,如果细胞要建立一个主动去甲基化的新通路,假设原有通路的蛋白及其他小分子对新通路没有任何作用,那么新通路需要生物体合成全新的蛋白质和小分子,效率明显不如拓展原有通路高。
就5-甲基胞嘧啶而言,进一步脱氨或氧化均可以启动BER通路,即可运用已有的胸腺嘧啶-DNA糖苷酶切除甲基化的胞嘧啶,实现去甲基化。
2.2 对细胞正常稳态的影响
相比于胞嘧啶脱氨基、鸟嘌呤氧化和发生在碱基其他不同位点的甲基化等化学修饰而言,5mC修饰的优势在于不影响DNA的一级结构,主要通过影响二级结构来影响基因表达,不影响碱基配对和DNA的稳定性,不会对生物体造成明显的危害。
前文中已提到,在CpG岛上的DNA甲基化能够改变染色质的构型。甲基化通过改变DNA二级结构中大沟、小沟的宽度和深度参数,影响蛋白质或小分子的识别及与DNA结合的强度。同时,对C5-MeC…G的电子占据数和授受体作用的二级微扰能量E2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胞嘧啶5-C位甲基化没有改变GC 碱基间的氢键授受体作用方式,对G…C碱基间的氢键结合没有显著影响,不影响碱基配对,故不会降低DNA的稳定性。随着去甲基化的进行,这种对蛋白质或小分子的影响随之消除,具有高度的可逆性和无损伤性。
此外,如图所示,胞嘧啶可以在亚硫酸根的介导下实现脱氨基,从而生成尿嘧啶,造成基因突变。研究表明,5mC具有抵抗各种亚硫酸氢根介导的脱氨基作用的能力,这一特性被用于检测全基因组中5mC的存在[12]。
因此胞嘧啶的甲基化修对于遗传信息的保存没有影响,不影响碱基配对,不具有毒性,甚至能够一定程度上抑制C→U的基因突变,是一种理想的表观遗传标记。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另一种化学修饰,6-甲基腺嘌呤,它在原核生物中是限制性修饰系统的重要标记,使得自身DNA不和外源DNA一样被降解,除此之外,6-甲基腺嘌呤还能起到重要的调控作用,具有成为新的表观遗传修饰的潜能[13]。

下面笔者总结了其他常见化学修饰对细胞的影响:
(1)如果把胞嘧啶脱氨基作用作为表观遗传标记,则生成尿嘧啶,改变了遗传信息,甚至不可称作表观遗传修饰,不可行。
(2)如果把鸟嘌呤氧化作用作为表观遗传标记,那么鸟嘌呤氧化生成的8-氧鸟嘌呤不仅能够与腺嘌呤配对,导致复制后碱基序列出错,不利于遗传信息精确地传递,还具有毒性[14],不适宜在机体内作为表观遗传标记以一定数量存在。
(3)N3-甲基腺嘌呤可以阻止DNA的正常复制;N1-甲基腺嘌呤和N3-甲基胞嘧啶会阻止碱基对的形成;O6-甲基鸟嘌呤和O4-甲基胸腺嘧啶可能引起基因突变[15]。以上修饰均对细胞具有很大的毒性。
以上这些修饰都是不适于作为表观遗传标记的。综上,5mC相比于其他修饰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笔者推测这也是5mC成为高等真核生物的主要表观遗传标记的原因。
[1]Yi, C., & Pan, T. (2011). Cellular dynamics of rna modification.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 44(12),1380-8.
[2]Dodge, Jonathan E.; Bernard H. Ramsahoyeb,Z. Galen Woa,Masaki Okanoa, En Li:De novo methylation of MMLV provirus in embryonic stem cells: CpG versus non-CpG methylation(2002)Gene,289(1-2):41-8.
[3]Treat Baldwin Johoson, Robert D. Coghill.
[4]Wyatt, G.R. (1951)Recognition and estimation of 5-methylcytosine in nucleic acids. Biochem. J. 48, 581-584.
[5]COHEN, S. S., & WYATT, G. R. (1952).A new pyrimidine base from bacteriophage nucleic acids. Nature, 170(4338),1072-1073.
[6]Ito, S., D'Alessio, A.,C., Taranova, O. V., Hong, K.,Sowers, L. C., & Zhang, Y. (2010). Role of tet proteins in 5mC to 5hmC conversion, ES-cell self-renewal and inner cell mass specification. Nature, 466(7310), 1129-33.
[7]Kriaucionis, S., & Heintz, N. (2009). The nuclear DNA base 5-hydroxymethylcytosine is present in purkinje neurons and the brain. Science, 324(5929), 929-930.
[8]Attwood JT;Yung RL;Richardson BC(2002)DNA methyla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gene transcription. CellMo. 59(2):241-257.
[9]F. Antequera, J.Boyes: High levels of De Novo methylation and altered chromatin structure at CpG islands in cell lines.A Bird-Cell, 1990.Volume 62,Issue 3,10 August 1990, Pages 503-514.
[10]Remo R, Ean M, Sean M. West, Alona Sosinsky, Peng Liu,Richard S. Mann, B Honig :The role of DNA shape in protein - DNA recognition[J]. Nature,2009,461:1248-1253.
[11]Lindahl, T. (2013): My journey to DNA repair. Genomics、Proteomics & Bioinformatics, 11(1),2-7.
[12]Yu, M.; Hon, G. C.; Szulwach, K. E. … Jin, P.*; Ren, B.*;He, C.* Cell 2012, 149, 1368-1380.Also see oxBS-Seq in Science 2012, 336, 934.
[13]Luo, G., Blanco, M., Greer, E., He, C., & Shi, Y.(2015). DNA N-6-methyladenine: A new epigenetic mark in eukaryotes?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16(12),705-710.
[14]Bret D. Freudenthal, William A. Beard, Lalith Perera,David D. Shock, Taejin Kim, Tamar Schlick & Samuel H.Wilson,Uncovering the polymerase-induced cytotoxicity of an oxidized nucleotide,Nature517,635-639
[15]Thomas E S,Douglas E L. Structure of the hydrogen bonding complex of O6-methylguanine with cytosine and thymine during DNA replication[J]. Nucleic Acids Research,1997,25(16):3354-3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