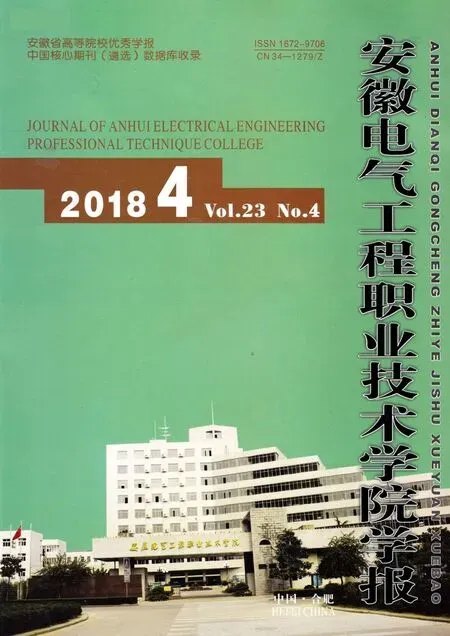宗白华对中国绘画美学传统的诠释与拓新
陈祥明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2)
宗白华美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艺术美学,是对中国诗书画艺术传统的诠释、拓新和转型而建立起来的。他的艺术美学参照和借鉴了西方哲学美学,却不是西方思辨式美学的翻版与推演;他的艺术美学传承和坚守了中国美学传统,但不是中国古代评点式诗论、书论、画论和乐论等等的承袭发挥。他的艺术美学是在中西审美文化的相互比较参照下,对中国美学传统的再发现、再诠释和再创造,而对中国绘画美学传统的诠释与拓新,是他对艺术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一、中国画艺术特征:诗书画乐“本一体”
近代以来,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强势进入中国,在西学东渐大潮中,中国民族文化已成弱势而失去往昔辉煌,作为极富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画艺术,其画学体系遭到致命冲击。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降,带有强烈政治功利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美术革命”思潮,更是直接解构着中国传统画学体系,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文人画传统。
美术史论家李铸晋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绘画史的发展,从宋代以来一直为文人画观点所支配,以为艺术的最高成就,便是诗、书、画三绝的结合。”关于艺术功能问题,“传统文人以为诗、书、画乃是抒发个人情感的媒介”。关于艺术风格问题,“在文人画全盛时期,书画一向保持其特定的风格,没有太大的起伏,其基本的要求为:一方面要师造化,另一方面要讲求古意而中得心源;在笔墨方面,最高的表现在于气韵和意境,要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绘画观,在近代受到西方思潮的质疑和考验。[1]在西方科学主义、写实主义为引领的新美术思潮冲击之下,“诗、书、画三绝结合”这一中国文人画根本传统被彻底动摇,中国画所特有的抒情性、写意性被严重损害。
当所谓“美术革命”已形成时代思潮,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已成为艺术潮流,中国画与西洋画相融合已成为画学重要价值取向的情势下,宗白华对中国画艺术的根本传统作了探究、揭示和诠释。
宗白华认为,中国画和西洋画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哲学传统,其根本差异不仅在于外在表现形式之不同,更在于内在精神灵魂之迥异。宗白华从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之比较的特定维度,对中国画的表现形式与精神灵魂予以揭示和诠释。
从表现形式看,中国画有以下主要特点:中国画超脱了刻板的立体空间、凹凸实体及光线阴影,于是它的画法乃能笔笔虚灵,不滞于物,而又笔笔写实,为物传神。笔不滞于物,笔乃留有余地,抒写画家自己胸中浩荡之思、奇逸之趣,“而引书法入画乃成中国画第一特点”。“中国特有的艺术‘书法’实为中国画的骨干,各种点线皴法溶解万象超入虚灵妙境,而融诗心、诗境于画景,亦成为中国画第二特色。”“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乃将心灵的情韵表现于书法、画法。书法尤为代表音乐的抽象艺术。在画幅上题诗写字,借书法以点醒画中的笔法,借诗句以衬出画中意境,而并不觉其破坏画景,这又是中国画可注意的特色。”[2]101-102
宗白华进而从“境界”的高度加以揭示:
因中、西画法所表现的“境界层”根本不同:一为写实的,一为虚灵的;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中国画以书法为骨干,以诗境为灵魂,诗、书、画同属一境层。西画以建筑空间为间架,以雕塑人体为对象,建筑、雕塑、油画同属一境层。中国画运用笔勾的线纹及墨色的浓淡直接表达生命情调,透入物象的核心,其精神简淡幽微,“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唐代大批评家张彦远说:“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遗形似而尚骨气,薄彩色以重笔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这是中国画宋元以后的趋向。然而形似逼真与色彩浓丽,却正是西洋油画的特色。中西绘画的趋向不同如此。[2]102
从表现对象和取法手段看,中国画以“气韵生动”即“生命的律动”为始终的对象,而以笔法取物之骨气,所谓“骨法用笔”为绘画的手段。[2]103谢赫六法以“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之模仿自然,“经营位置”之研究和谐、秩序、比例、匀称等形式美问题,被列在三四等地位。然而这“模仿自然”及“形式美”问题,却是占据西方美学思想发展中的二大中心问题。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画虽然强调书法特点,突出骨法用笔,但它只是手段,目的是表现“生命的律动”即达到“气韵生动”。他说:“中国画运用笔法墨气以外取物的骨相神态,内表人格心灵。不敷彩色而神韵骨气已足。”西洋画各人有各人的“色调”,以表现各个性所见色相世界及自心的情韵;中国画以墨调色,其浓淡明晦,映发光彩,相等于油画之光。西洋画是色彩的音乐,而中国画是点线的音乐,“色彩的音乐与点线的音乐各有所长”。[2]108在这里,宗白华揭示了一个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问题:在中国画中,笔墨世界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世界,它是物象世界或色相世界的意象性、象征性表现,更是“生命律动”、“人格心灵”的延伸与表达。而笔墨之“意”、笔墨之“舞”、笔墨之“乐”,是诗化的、鲜活的、韵味的生命律动与心灵弦响。这是晋唐肇始,宋元以来中国画走上“写意”之路,形成独特“写意”体系的深厚画学根源。
二、中国画艺术造型:非科学的“灵的空间”
如果按照现代艺术分类,建筑、雕塑、绘画都属于造型艺术,而空间问题则是造型艺术的根本问题。单就绘画而言,西洋画艺术造型与中国画艺术造型根本不同,西洋画是写实的、科学的“实的空间”,而中国画是虚拟的、非科学的“灵的空间”。在宗白华看来,非科学的“灵的空间”是中国画艺术空间最重要特点,而这一特点根源于华夏民族独特的宇宙观、生命观与心灵世界。
宗白华认为:“中国画自有它独特的宇宙观点与生命情调”。[2]102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宇宙观点”和“生命情调”,决定了中国画艺术造型的总体面貌以及发展演变的总体趋向,这就是非写实的、虚拟的、诗化的空间造型与艺术意象。
宗白华指出:
中国绘画里所表现的最深心灵究竟是什么?答曰:它既不是以世界为有限的圆满的现实而崇拜模仿,也不是向一无尽的世界作无尽的追求,烦闷苦恼,彷徨不安。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体合为一”。它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因为顺着自然法则运行的宇宙是虽动而静的,与自然精神合一的人生也是虽动而静的。它所描写的对象,山川、人物、花鸟、虫鱼,都充满着生命的动——气韵生动。但因为自然是顺法则的(老、庄所谓道),画家是默契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着一层深深的寂静。就是尺幅里的花鸟、虫鱼,也都像是沉落遗忘于宇宙悠渺的太空中,意境旷邈幽深。至于山水画如倪云林的一丘一壑,简之又简,譬如为道,损之又损,所得着的是一片空明中金刚不灭的精粹。它表现着无限的寂静,也同时表示着是自然最深最后的结构。有如柏拉图的观念,纵然天地毁灭,此山此水的观念是毁灭不动的。[2]44
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画的空间观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宇宙观,两者紧密相关而不可剥离。中国人感到这宇宙的深处是无形无色的虚空,而这虚空却是万象的源泉,万动的根本,生生不已的创造力。老庄名之为“道”、为“自然”、为“虚无”,儒家名之为“天”。万象从虚空中来,又向虚空中去,所以纸上的空白是中国画真正的画底。中国画在一片空白上随意布放几个人物,不知是人物在空间,还是空间因人物而显。人与空间溶成一片,呈现无尽的气韵生动。我们觉得在这无边的世界里,只有这几个人,并不嫌其少;而这几个人在这空白的环境里,并不觉得没有世界。其实,中国画底的空白处在整个画的意境上并不是真空,乃是宇宙灵气往来、生命流动之处。笪重光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这“无画处”的空白正是老庄宇宙观中的“虚无”。中国画无论表现万里江山、浩茫云山,还是表现一山一石、一树一木,都以无画处之空白而思接大千,朝向无限虚无之境;画家无论挥写高山泉响、松风鹤鸣,还是抒写原野荒寒、柴门寂静,也都以留白而洞达幽微,旨向虚灵之境。由此可见,不理解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就难以理解中国画独特的空间观。
宗白华认为,《易经》的天地“阴阳”思想,老庄的宇宙“虚无”思想,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与中国画的空间观。中国画是虚拟的、非科学的“灵的空间”,而非像西洋画那样是写实的、科学的“实的空间”。用西洋画的空间意识、空间感型之概念范畴来解读、诠释中国画的空间构成、造境等,只能是误读误解。
西洋画的三个主要空间透视画法即几何学的透视画法、光影的透视法、空气的透视法,其所构造的空间都是科学的、写实的空间。宗白华指出:“每一种艺术表出一种空间感型。并且可以互相移易地表现它们的空间感型。西洋绘画在希腊及古典主义画风里所表现的是偏于雕刻的和建筑的空间意识。文艺复兴以后,发展到印象主义,是绘画风格的绘画,空间情绪寄托在光线彩色明暗里面。”[2]142-143
在宗白华看来,与西洋画根本不同,中国画里的空间构造,既不是凭借光影的烘染存托,中国水墨画并非光影的实写而是一种抽象的笔墨表现;也不是移写雕塑立体及建筑的几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所引起的空间感型。确切地说:是一种“书法的空间创造”。
宗白华指出:
中国的书法本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它具有形线之美,有情感与人格的表现。它不是描绘实物,却又不完全抽象,如西洋字母而保有暗示事物和生命的姿势。中国音乐衰落,而书法却代替了它成为一种表达最高境界与情操的民族艺术。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我们几乎可以从中国书法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时期,像西洋艺术史依据建筑风格的变迁来划分一样。[2]143
中国绘画以书法为基础,中国书法所特有的空间表现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画的空间意识,创造了中国画“灵的空间”。
中国书画的神采气韵皆生于用笔。中国字如果写得好,用笔得法,就成为一个有生命、有空间立体味的艺术品。如果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能够“偃仰顾盼,阴阳起伏,如树木之枝叶扶疏,而彼此相让。如流水之沦漪杂见,而先后相承”。这一幅字就是一股生命之流、一回舞蹈、一曲音乐。“书法中所谓气势,所谓结构,所谓力透纸背,都是表现这书法的空间意境。”而“一件表现生动的艺术品,必然地同时表现空间感。因为一切动作以空间为条件,为间架。”[2]144如果状物生动,像中国画绘一枝竹影,几叶兰草,纵不画背景环境,而一片空间,宛然在目,风光日影,如绕前后。像八大山人在白纸上画一条生动的鱼,别无所有,然而让人觉得满纸江湖,烟波无尽。可见,中国画的气韵生动,是用笔得法抒写的结果,而中国画“灵的空间”是书法所创造的。
宗白华进一步指出:
画境是一种“灵的空间”,就像一幅好字也表现一个灵的空间一样。
书境通于画境,并且通于音的境界,我们见雷简夫一段话可知。盛熙明著《法书考》载雷简夫云:“余偶昼卧,闻江涨声,想其波涛翻翻,迅駃掀磕,高下蹙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所想,尽在笔下矣。”作书可以写景,可以寄情,可以绘音,因所写所绘,只是一个灵的境界耳。
恽南田评画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邱一壑,皆洁庵灵想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这一种永恒的灵的空间,是中画的造境,而这空间的构成是依于书法。[2]144-145
在这里,宗白华深入揭示了中国画的空间是一种“灵的空间”,中国画的境界是一种“灵的境界”,而这灵的空间与境界,其构成依于书法,其奥妙源于书法,其“灵想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的无尽魅力也在于书法。宗白华还深刻揭示了书境通于画境,并通于音乐境界,故作书如同作画,可以写景,可以寄情,可以绘音,都是构成“灵的空间”而创造“灵的境界”。
可见,宗白华并不重复古人“书画同源”的结论,也不照搬近人“以书入画”的主张,而是通过揭示中国书画的空间构成的奥秘,进而揭示中国画的意境创造的奥妙,直至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相结合的层面,揭示中国绘画的空间意识与哲学基础。
三、中国画艺术精神:空灵与充实
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空灵与充实”是作为中国艺术的根本精神而被揭示和描述的。
在讨论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特点时,宗白华说:“空灵和充实是艺术精神的两元。”[2]348“中国文艺在空灵与充实两方面都尽力,达到极高的成就。”[2]353在宗白华看来,就艺术家个体而言,空灵是艺术心灵诞生的奥秘所在,是艺术美感形成的根本缘由。他说:
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2]348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所以周济说:“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2]349
在宗白华看来,艺术家心境的虚静、空灵,不滞于物,静观万象,心游八荒,自由无碍,人之生命灵性浸注入世界万物,人之精神灵魂往来于天地之间,这是诗情画意产生的心理条件,也是艺术意境形成的内在根据。南朝画家宗炳强调“澄怀味象”,即涤除心灵的尘埃,体味万物的真谛。认为画家“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才能心游物外,畅神无阻,达到“万趣融其神思”之境界。[3]苏轼诗曰:“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虚静和空灵是诗之妙境产生的所以然,也是万象灵动、万境充盈的所以居。
画家和诗人都一样,其审美心境应是空灵的虚静的,同时也应是充实的丰盈的。空灵纳万境后的充实,虚静动万象后的丰盈,是心灵对自然造化的洗礼与收获,是情思对自然意象的浸染与凝聚,是从眼中丘壑到胸中丘壑、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的升华与积淀。因此,画家的“胸中丘壑”“胸中之竹”等,是情致化、诗意化的,而非纯客观、纯实在的。因此,审美心境中作为审美意象(而非物象)的山川丘壑、虬松秀竹、风花雪月、斜阳飞鸟等等,是“化景物为情思”“万趣融其神思”的结晶,是“万物皆备于我”的充实,又是不滞于物、超以象外的虚灵。
从眼中丘壑到胸中丘壑再到手中丘壑,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是眼中的自然物象到胸中的审美意象再到画面的艺术形象的创作过程,是一个从实到虚、以虚化实、以虚拟实、虚实相生的艺境生成过程。对此过程历史上一些画家都作过揭示或描述,譬如,郑板桥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存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4]
宗白华将“空灵”与“充实”作为一对范畴,以揭示艺术心灵诞生、诗画艺境诞生的奥秘。它激活了一系列沉睡的中国绘画美学范畴,如“造化”与“心源”(唐代王璪语“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景物”与“情思”(清代范晞文语“化景物为情思”)、“虚”与“实”(清代笪重光语“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质”与“灵”(南朝宗炳语“山水质有而灵趋”)以及“阴阳之道”(《易经》语)、“意存笔先”(唐代王维语)等等。特别是对“虚实”范畴的激活唤醒,对“虚实相生”画理的解读诠释,开辟了中国绘画美学新境界。
宗白华通过对“空灵”与“充实”范畴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虚实关系的诠释,重新恢复了中国画学传统,同时也校正了中国文人画学的偏颇。关于中国古典绘画虚实关系,董欣宾先生曾诠释:在中国画中,虚与实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一种相对的存在性的互为虚实。任何中国画作品,必既有虚处,又有实处。有虚无实不成其为画,有实无虚也不成其为画。最实处也有虚,使人感到空灵;最虚处也有实,使人感到充实。虚,可以指无笔无墨处,也可以是用笔松动处,用墨轻淡处,构图疏朗处,形象隐含处;相对于这种种虚,实可以指笔墨沉着处,用墨浓重处,构图繁密处,形象显实处。虚实相生,方成艺术。这些原理完全出自于老庄哲学。他进一步分析解释:“由于老庄哲学认识论的影响,文人画长期居统治地位,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文人画观念认为虚灵胜于充实(尽管虚灵中有充实)、简淡胜于繁密。这既是中国绘画美学的高度成就所在,但同时也是中国画的误区。”[5]98-99确实,在中国文人画观念里,虚灵胜于充实、简淡胜于繁密,以虚灵、简淡为上为妙为美。而宗白华在强调空灵之必须时,也同时强调充实之重要,辩证地看待虚与实的关系,将虚实相生看作中国画艺术的真谛所在,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中国文人画画学传统的局限。
四、中国画艺术妙境:虚实相生
在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虚实结合和以虚为美的理想境界”问题,是中国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6]
宗白华先生认为,虚实关系问题是中国艺术的根本问题,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与此密切相关。虚实相生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古典美学的意象说、意境说、境界说的形成和发展与之关系密切。
虚实相生思想来源于老子。老子哲学充满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主要表现在有无相生、虚实相生、对立转化、循环运动等方面。他关于有无、虚实的论述对后来诗书画的发展影响甚大。[7]
“虚实相生”思想是从老子“道”论中生发出来的。在老子那里,“道”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道”有虚有实,虚实相生;有阴有阳,阴阳相调;有气有象,气象相和。老子上述思想中,关于“道”“气”“象”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虚实相生的思想,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董欣宾先生指出,在中国绘画范畴中,“虚实”对“疏密”、“繁简”、“有无”等具有统领性,而“虚实”范畴和“虚实相生”的中国画艺术原理,完全出自老庄哲学,受老子哲学影响尤深。[5]97-100
关于艺术中的虚实问题,宗白华曾反复援引晋唐诗文,宋代诗人范晞文的诗论,清代画家方士庶、恽南田、范玑、笪重光等人的画论加以诠释。然而,他对于古人诗论、画论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从中拟出了一条清晰的线索,即虚与实范畴如何理解、虚实关系如何处理、虚实处理又如何臻于妙境,以及虚实与构图、布白、笔墨等等。可以说,他以对虚实范畴和虚实关系的诠释为中心,重新建构了中国画学诠释体系,重新恢复了中国画学传统。
那么,艺术中的虚与实,应作何理解呢?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注]参见方士庶《天慵庵笔记》上,载《题画诗·天慵庵笔记·画梅题记》,书林书局1935年版,第21页。客观存在的描写对象——自然或社会是实境,而经艺术家创造性的艺术构思具体表现于作品的是虚境。艺术虽来自生活,但毕竟不等于实际生活,而是艺术家“惨淡经营”的虚构之境。这种虚境,蕴含着艺术家的主观情思,是“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注]参见方士庶《天慵庵笔记》上,载《题画诗·天慵庵笔记·画梅题记》,书林书局1935年版,第22页。;是“皆灵想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注]参见恽南田《题洁庵图》,载《瓯香馆集》卷五,西泠印社2012年版,第101页。。
艺术中的虚实关系,应如何处理呢?范晞文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否则偏于枯瘠,流于轻俗,而不足采矣。”[注]参见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对床夜语·滹南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页。在范晞文看来,以实为虚,化实为虚,虚实结合,才能避免“虚者枯,实者塞”之弊端,创造出“非人间所有”的艺术奇迹。宗白华从中引出关于艺术意境创造的一个重要原理:
化景物为情思,这是对艺术中虚实结合的正确定义。以虚为虚,就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唯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就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意境。[8]436
绘画中的虚实处理,又如何臻于妙境呢?范玑在《过云楼画论》中说:“画有虚实处,虚处明,实处无不明矣。人知无笔墨处为虚,不知实处亦不离虚。即如笔著于纸有虚有实,笔始灵活,而况于境乎?更不知无笔墨处是实,盖笔虽未到其意已到也。瓯香所谓虚处实,则通体皆灵。至云烟遮处谓之空白,极要体会其浮空流行之气,散漫以腾,远视成一片白,虽借虚以见实。此浮空流行之气,用以助山林深浅参错之致耳。若布置至意窘处以之掩饰,或竟强空之,其失甚大,正可见其实处理路未明也。必虚处明,实处始明。”[9]
范玑赞成恽寿平(瓯香)所说的“虚处实,则通体皆灵”。恽寿平《南田画跋》说:“古人用笔,极塞实处愈见虚灵,今人布置一角,已见繁缛。虚处实则通体皆灵,愈多而愈不厌,玩此可想昔人惨淡经营之妙。”“气韵自然,虚实相生,此董、巨神髓也。”[10]140,147
关键在于处理实景与空景、真境与虚境的关系,实中有虚,虚中见实,虚实相生,充实而又空灵,妙境得以生发呈现。笪重光《画筌》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11]宗白华从这里引出中国画与戏曲、诗、书法相通的艺境生成的重要美学观点和规律。他说:
笪重光这段话扼要地说出了中国画里处理空间的方法,也叫人联想到中国舞台艺术里的表演方式和布景问题。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是有独创性的,我们愈来愈见到它的优越性。而这种艺术表演方式又是和中国独特的绘画艺术相通的,甚至也和中国诗中的意境相通。中国舞台上一般不设置逼真的布景(仅用少量的道具桌椅等)。老艺人说得好:“戏曲的布景是在演员的身上。”演员结合剧情的发展,灵活地运用表演的程式和手法,使得“真境逼而神境生”。演员集中精神用程式手法、舞蹈动作,“逼真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动,就会使人忘掉对于剧中环境布景的要求,不需要环境布景阻碍表演的集中和灵活,“实景清而空景现”,留出空虚来让人物充分地表现剧情,剧中人和观众精神交流,深入艺术创作的最深意趣,这就是“真境逼而神境生”。这个“真境逼”是在现实主义的意义里的,不是自然主义里所谓逼真。这是艺术所启示的真,也是“无可绘”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美。“真”、“神”、“美”在这里是一体。[8]388
在这里,宗白华通过对笪重光观点的诠释与引伸,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画“艺境”—“妙境”生成的奥秘,即“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也揭示了中国画艺术表现的最高旨趣,即追求“真、神、美一体”境界。
在宗白华看来,“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不仅仅是“经营位置”或“布白”的结果,还关乎画家情感、笔墨意蕴、审美观照。恽寿平说:“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笔墨者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10]141“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笔中之笔,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10]162“川濑氤氲之气,林风苍翠只色,正须澄怀观道,静以求之,若徒索于毫末间者离矣。”[10]147戴熙说:“画在有笔墨处,画之妙在无笔墨处。”[注]参见戴熙《习苦斋画絮》卷九,《戴文节公画絮》光绪十九年刻本。因此,肆力在实处,而索趣在虚处。中国画讲究“妙在无处”,亦即“无画处皆成妙境”,旨在创生画面的空灵境界,给人以无穷的想象。
艺术所特有的因素是创造性的想象。艺术家化实为虚、化景为情,旨在通过虚构之境去唤起欣赏者的自由想象。八大山人画一条生动的鱼于纸上,别无一物,却令人觉得满幅皆水;白石老人画一枯枝横出,站立一鸟,别无所有,但使人感到小生物背衬丰实无比的空间;而石涛的巨幅画《搜尽奇峰打草稿》,愈满愈使人觉得虚灵动荡,富有生气;黄宾虹晚年多画阴面山或夜山,满幅皆黑却墨气淋漓,透出虚灵之光,弥漫虚灵之气。马远画山水,常常因画一个角落而得名“马一角”,剩下的空白并不填实,是湖泊,是天空,却并不感到空,空白处更有意味,此可谓“无画处皆成妙境”。齐白石画的荷花往往枝叶错落,横斜逸出,画得比较密,但密中又有疏,给人一种生机勃发之感;就全幅看往往留有空白,但空白处有时或画晴蜓,或画翠鸟,虚和实的对照不独十分明显,而且十分和谐,表现出一种清新典雅的意境。仔细玩味,白石老人绘画的美妙,既不在画的实处,也不在画的虚处,而在虚实相生处。
艺术家化实为虚,化景为情,使他的艺术形象具有最大的概括性,艺术境界虚灵化;反过来,观赏者却能从虚境当中看到实境,并以自己的想象去充实它、丰富它、再创造它。正如美学家李泽厚所说:“一方面,虚自由地扩大实,丰富实,充实实;另一方面,实又必然地制约虚,规范虚,指引虚。”[12]从而使人发生审美愉快。
总之,抓住“虚实关系”这一中国绘画艺术的根本问题,宗白华从宏观哲学层面,探讨和揭示了中国古老哲学尤其是《易经》、老子对艺术意境生成的深刻影响;从微观技法层面,探讨和揭示了中国画构图、布白、笔墨等等对艺术意境创构的巨大作用;又从宏观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和揭示了中国画“虚实相生”的审美心理根据,以及中国画意境追求“真、神、美一体”的根本价值取向。
结语:宗白华绘画美学的独特贡献
宗白华一生致力于探索艺术意境,他说:“人生有限,而艺境之求索与创造无涯。”[8]623因此,有论者将其美学界定为“艺境美学”或者“探索艺术意境的美学”。[13]作为他整个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绘画美学以探索绘画艺术意境为旨归,以解决中国绘画的虚实问题为中心,以对中国传统画学的创造性诠释,建构起了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中国绘画美学体系。他因此开启了中国绘画美学的民族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宗白华绘画美学是对20世纪西学东渐的一个回应,是对现代中国画学西化的一个矫枉,是对中国画学优秀传统的一种恢复与回归。宗白华的独特贡献在于:一是重新发掘了中国绘画的深厚的“文化—哲学”渊源与基础,尤其是揭示了中国画艺术意境诞生的“哲学—心理”根据与特点。特别是他打通了艺术意境与道境、佛境之关系,更是发前人未所发。二是重新诠释和彰显了“诗书画合一体”的中国画学传统,突出了中国画所特有的“写意”精神。尤其是他将书法作为创造“灵的空间”之首要手段,大大深化了对中国画“空间感型”的认识和把握。三是重新激活了中国传统画学的特定范畴及其命题,如“虚实”范畴及“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命题,如“造化心源”范畴及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命题,如“情景”范畴及“化景物为情思”命题等等。四是校正了以西学误读误解中国古典画学画理的问题,譬如,不用西方科学透视方法来解释中国画空间造型方法,不是将沈括的“以大观小”的山水之法、郭熙的“三远”(平远、高远、深远)的构形之法解释为所谓的“散点透视”“动点透视”,而是将其视作中国古典绘画所特有的空间造型之法,即刘继潮先生所谓的“游观”之法。[注]参见刘继潮《游观:中国古典绘画空间本体诠释》,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三章“山水”空间秘蕴,第71-148页。如此等等,都对新时期中国绘画美学的学术风貌和发展趋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白华以中西比较的视野和方法,将中西画学互为参照,相互比较,进行互释,并且以中化西,以西补中;借古开今,熔古铸今。这与黄宾虹、潘天寿等人在绘画实践中的沟通古今、借古开今相契合,也与张大千、林风眠等人的融合中西、以西补中相呼应。因此,宗白华的绘画美学在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都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