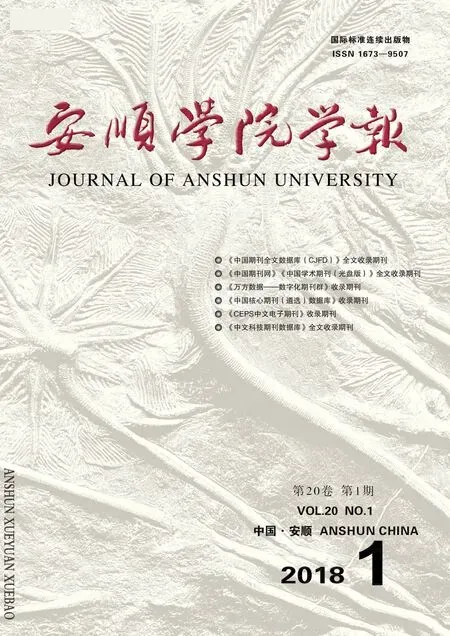清代改卫归流研究刍论
(安顺学院人文学院;贵州省屯堡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安顺561000 )
引言
明朝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的实土或准实土的卫所(不含羁縻卫所),通常被时人或后人视作流官政治的一部分。相对于土司而言,明代卫所因其表征王朝正统的身份而被归入流官体制似无疑义,但由于卫所职役世袭制度的推行,它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流官政治。相较于从土司制度到经制州县的“改土归流”而言,清前中期对前朝卫所的裁撤、归并及改置州县,同样属于裁汰消解世袭制度的范畴。在未裁撤废除之前,卫所与土司一样,都是以世袭制度为支撑的地方管理制度,兼具辖土治民的地方政府职能,皆具地方政区(准政区)性质。在淘汰消解世袭制度的层面上,裁撤土司与取消卫所的目的一样,都指向地方管理的流官体制。因此,废除土司可谓“改土归流”,裁撤卫所亦可称之“改卫归流”。
相对于“改土归流”而言,“改卫归流”的提法可能值得商榷甚至受到质疑。但是,不仅土司职官具有世袭特点,卫所职役同样具有世袭的特点。因此,在消除世袭制度的意义上,卫所亦存在“归流”问题。清政府裁撤前朝所设卫所,以其土田、户口归并或改置州县的过程可称之为“改卫归流”。卫所同土司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明朝问题在清代的延续,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改卫归流”并没有同“改土归流”一样得到学界认可并予以高度重视。已故明史研究专家顾诚先生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将清代卫所裁撤问题等同于“改土归流”提出来,顾氏谓:
史学界对于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一直非常注意,发表的文章很不少。可是,对于雍正年间基本完成的并卫所入州县、改卫所为府、州、县这一触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却很少有人注意。主要原因看来还是对明代的卫所制度缺乏研究,因而史籍中经常出现的卫所材料往往被忽略过去。[1]
时至今日,不仅明代卫所已成为明史研究的热点,卫所的清代变革及其后世影响也逐渐受到学界重视。明代卫所的后世影响并不因清代卫所的裁撤而结束。在卫所裁撤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原卫所造成的插花地问题仍持续且大量地存在,屯田赋役与州县民田在输纳方式与水平上仍存在较大差别,卫所基层社会结构与组织在其归并州县以后仍在相当程度上继续存在,基于卫所移民及其在地化发展而形成的族群和文化仍然得到延续。关注明代卫所及其清代延续问题,不能至卫所裁撤为止,而应以之为新的起点,继续讨论卫所制度的长期实践对基层社会所造成的深刻而持续的影响。本文提出“改卫归流”的概念,并认为卫所的裁撤并不标志“归流”的完成,其后续影响在经制州县管理框架下的基本消弭才是“改卫归流”完成的体现。
一、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
明代的卫所在清代仍然延续了很长时间,是因为大部分卫所皆有其管辖的地盘,它们对辖区内军、旗、舍、余征收的子粒同行政系统的州县征收的赋税在数量上和方法上相距甚远,力役制度也有很大差别[2]。面对卫所辖地与州县辖地在赋役制度上的巨大差别,清政府对于前朝已经逐渐失去军事职能的卫所只能暂时采取维持现状的的办法。针对卫所在清代的延续,顾诚先生指出:
卫所作为同州县类似的地方管辖单位在清代大约存在了80多年,在此期间,都司、卫、所经历了一个轨迹鲜明的变化过程。其特点是:一、都司、卫、所官员由世袭制改为任命制;二、卫所内部的“民化”、辖地的“行政化”过程加速;三、最后以拼入或改为州县使卫所制度化作历史陈迹,从而完成了全国地方体制的基本划一。[1]15
顾氏着眼于明代卫所在清代的变革,指出清政府将卫所裁并或改置州县,不仅明代卫所制度化作历史陈迹,更是全国地方体制基本划一的体现,标志着明朝政府所建立的在疆土管理方面的军民二元体制的终结。李巨澜强调清代卫所的存在,指出清代卫所制度是对明代卫所制度的改造和调整,其官员由世袭改为任命,职能由原先的军事、经济相结合转变为纯粹的经济职能。卫军改为屯丁和运丁,专事屯田与漕运,另外卫所还承担着一定的民事职能[3]。顾、李二氏都在探讨清代卫所变革问题,但出发点却不相同。前者以明代卫所为出发点,落脚于清政府对前朝卫所的处置;后者以清政府借鉴和调整前朝卫所制度为出发点,旨在整体评价清代的卫所制度。清政府裁撤明设卫所的同时,在西北关西和湘黔苗疆等局部民族地区仍新设诸卫,仍以屯田支撑京畿漕运系统。
讨论清代“改卫归流”问题,其关注点在明代卫所制度及其实践的清代延续,并非清代新设的关西或苗疆诸卫,也非清代的漕运诸卫。明代卫所作为地理管辖单位(或者说政区、准政区单位,实土、准实土单位),清代撤卫所实即以其土田、户口归并或改置州县。
二、卫所裁撤与改置州县
卫所裁并、裁撤或改置州县的过程,《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一文已有梗概地梳理:清顺治年间,卫所官员虽仍被视作武职,但其职责范围同行政系统的府州县官越来越接近,沿边和在内卫所常有裁并之举;清康熙时期,一方面保留了卫所名称,另一方面又继续了明后期的势头,把部分卫所改为州县;而大规模的改卫所为州县是在清世宗统治期间进行的[1]。
目前,对于卫所归并或改置州县问题,除了顾氏的整体论述外,大多是局部或个案的实证研究,例如明清潼关卫——潼关县——潼关厅,蔚州——蔚州卫——蔚县,九溪、永定二卫——安福县——安福、永定二县的变迁个案,都是清代卫所裁撤与州县改置的典型案例。
台湾于志嘉以潼关卫为例,指出潼关废卫改县,其初犹为兵饷供应、屯粮征收之便保持原潼关卫屯的完整性,然终究难抵屯地分散两省十一州县所带来的困扰,逐步缩编成仅掌管潼关、华阴两境内屯地的潼关厅,明初以来以“犬牙相制”为目的建立的机制一步步迈向土崩瓦解的境地[4]。
邓庆平以明清蔚州为中心,梳理了明代蔚州州、卫分立到清代蔚州卫改设蔚县的过程。明代蔚州与蔚州卫同城而治,二者在在户籍编制、赋役征派方式等方有明确的区分,而在公共设施、文化资源、经济利益的共享方面又打破了州——卫隔离的特点。清初,蔚州卫改为蔚县,原州——卫系统下疆界纠葛、资源共享的状态被打破,资源在新的蔚州一蔚县系统下进行重新配置,矛盾和纠纷亦因之而起,这使得清廷几次进行政区调整,最后以并蔚县入蔚州的方式解决[5]。
孟凡松梳理湘西北九溪、永定二卫裁撤设县的历程,认为经过初设安福县、再设永定县等连续两次设县,才在田土、户口归属的意义上最终完成了该地区的卫所裁撤问题。设置于雍正七年(1729年)年底的安福县是直接裁革九溪、永定二卫的结果,它并未改变原卫所田土、户口错杂分布于各属州县境内的格局,也使得新设安福县难以对其辖境实施有效管理。因此,雍正十三年(1735年)增设永定县,完全打乱原存民、屯田地原有的管辖格局,以保证州县辖境的相对完整性为基本原则,在州县之间对土地和户口的归属作了相当彻底的调整[6][7]。
卫所裁并固然属于清代行政区划与地方行政管理体系调整的重要举措,然而这一清代行政史上重大的改革,统治当局并无统一的规划,也没有与之配套的实施预案。在大多数情况下,卫所的归并、裁撤或改置州县都是分省进行的,甚至同一省区的卫所裁撤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先易后难,分步实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种先裁撤卫所后解决具体问题的被动局面。裁撤卫所归并或改设州县,最初仅涉及“上层建筑”层面,原卫所田赋、徭役的征解额度、方式以及因之而构建起来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等“经济基础”领域并未涉及。因此,这就带来了卫所裁并、改置州县的后续调整问题,如插花地划拨、屯赋调整与基层社会组织重构,都是“作为地理单位的卫所成了历史遗迹”[1]之后,“改卫归流”进一步深化的体现。
清代裁撤卫所并以其土田、户口归并或改设州县,涉及明代沿边、沿海、内地和在内卫所,从清初至雍正年间,属于持续性、全国性的改革行为。据杨晨宇统计,有清一朝共有817个卫所被裁并,其中21个卫所经历了裁并——复设——裁并的历程,22个卫所为清代新设但之后也同样被裁并,67个卫所被改置为府、厅、州、县,卫所改置州县主要集中于康雍乾三朝,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区[8]。关于清代卫所裁并、改置州县的研究,诚如杨晨宇所言,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少数几个史料记载比较丰富的区域和时段,而对于其他一些卫所裁并资料相对欠缺的地区和时段则少有问津,仍缺乏从全国范围和整体角度来看的宏观研究[9]。实际上,不仅全国范围和整体角度的宏观研究缺乏,且区域性、时段性的个案研究也仍不充分。有鉴于此,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宏观视野下的微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总结都应该得到重视。
三、插花地及其划拨
清代裁撤卫所,或将之归并州县,或以之改设州县,都要面临原卫所田土与人口管辖权属的转移和管辖制度的调整问题。问题在于,明代卫所辖地多与邻近州县相互插花,其在边疆、海疆与省际交界地区尤其严重。在清代裁撤卫所,归并或改设州县,插花地划拨问题相应而生。
因卫所原因造成插花地在明代属于相当普遍的现象,其在贵州表现尤其突出。马琦等通过探讨清末贵州插花地认为:清末贵州81%的县级政区存在插花地,其中以安顺、贵阳、镇远、思州、黎平等府亲辖地及其附郭县的插花地最为集中;贵州插花地众多与其政区设置的方式有关,贵州府、县政区或在原卫所屯田之地,或在土司所辖领地,或在剿抚土著居民聚居区设置,卫所、土司与原住民聚居区域相互穿插导致贵州插花地的产生[10]。杨斌认为明代的卫所、元明土司及“地随人走”的地权转移传统等都属于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产生的原因[11]。
明代卫所在腹里地区的土地多通过开垦荒地、隙地,占种籍没地等方式获得,土地难以连片故多插花形态;而在沿边民族地区,亦多垦辟强占原住居民或土司土地,故与土司、原住民土地呈插花形态分布。总之,由于明代卫所土地来源的特殊性和卫所曾长期存在的结果,插花地并非个案,也非裁撤卫所便可直接解决的。裁撤卫所,以其土田、户口并归州县或改置州县,插花地都是需要充分考量的存在。
无论是基于卫所、土司还是雕剿、投献而来的州县土田,之所以作为插花地问题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及附着于土地的户口,其承载田赋、徭役的水平及输纳、佥派赋役所依托的基层社会因应体系的差异。插花地不仅关乎政区辖地的空间问题,更在于辖地所彰显的制度与身份差异。换句话说,若插花地仅是空间问题,以山川形便为前提,遵循就近划拨州县原则即可解决之;但若插花地是一个制度和社会问题,涉及田赋多少、徭役分担、基层社会组织系统和地方精英利益及民众的政区认同心理等,大多数情况下就不是区区州县亲民官所能调解的,非地方大吏亲自主持且历有年月难以成功。明代卫所造成的插花地问题,在卫所裁撤之后,仍历至清代中后期乃至民国以后方渐次解决,其原因即在于此。关于明清插花地延续及其划拨、消解的研究,仍有待于更多的分省研究或个案研究为基础,方能作全国性和长时段的整体观察。
四、屯田与屯赋调整
前述清代民国插花地划拨的主要困难在其所承载的赋役水平和方式与邻近土地的参差有别上。具体地说,在卫所裁撤之后,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卫所屯赋水平的调整与屯丁的归并问题。
对于明清卫所屯田的所有权形态问题,毛亦可认为应以清代雍正五年至七年(1727—1729年)的屯田私有化政策为界,之前完全为国有制,之后转以私有制为主。屯田国有制时期又可区分为领种制和租佃制两个阶段,在明代宣德十年至正统二年(1435—1437年)“诏免正粮上仓”之后,屯军逐渐拥有屯田的永佃权、田面权,这对屯田私有化起到关键作用。清代雍正年间,朝廷颁布屯田私有化政策,并在归并州县的卫所屯田中切实推行[12]。
从贵州的案例来看,卫所的土地包括屯田和科田,且卫所田土的私下交易在明中期已俨然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以故嘉靖《贵州通志》感叹贵州土田的“欺隐之弊,逋负之奸”[13]卷3《土田》,277。“欺隐”针对土地权属而言,诡寄飞洒,化屯作科,私相授受,皆谓欺隐;“逋负”针对钱粮而言,迁延不纳,逃亡难追,皆属逋负。雍正年间屯田买卖合法化,屯田交易由地下的、变相的形式转变为公开的、合法的形式。据所见,不仅福建省的屯田契约文书展示了屯田交易实态的变迁[12],贵州黔中屯堡地区存在的关于水田、旱地的交易同样体现了这一实态[14]。
但是,针对裁撤之后的卫所土地而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其是否存在私下的或公开的交易行为,而在于卫所屯田、科田与州县民田及土司土民秋粮田之间存在的税则、徭役上的差别。同一地域之内,若田制科则及输纳方式、水平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民间社会就会在彼此之间进行比较权衡,趋利避害,避重就轻,以此达到赋役规避的目的。孟凡松通过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证明,不同类型的政区意味着不同的赋役制度与管理方式,在土司、卫所与州县权势彼此消长的背景下,导致土司与州县、土司与卫所、卫所与州县之间彼此交织的种种土地纠纷与赋役规避问题。清雍正间,通过改卫归流与改土归流,三者之间的土地与赋役纠纷随着卫所、土司的取消与州县政区主体地位的确立而逐渐消弭[15]。
为了避免或减少民间社会的赋役规避现象,调整民、屯赋役水平及征派方式,使之相近甚至相同就有了政策上的必要。但是,受定额财政体制的限制,州县地方在赋役调整方面的主动性是相当有限的。屯赋的调整,除了自上而下地执行相对简单外,自下而上的申报常常难上加难。清代湖南宝庆屯赋调整一案,经历顺康雍乾四朝,多任督抚申报才最终实现就是最好的证明①。清代贵州安平县(后改平坝县)也存在严重的“改屯作科”问题,屯田赋重而科田赋轻,赋重则价低,赋轻则价高,屯田拥有者为追求较高的土地售价,遂将之当作科田售卖,而自己承担改屯作科造成的田赋差额,是即“改屯作科”,“甘纳空粮,以图受价”者也[16]卷4《田赋》,77-78、82。
屯田赋役调整水平和征收方式,使之与州县民田所承载的赋役相一致,是清代康雍乾时期地方赋役制度改革与调整的重要内容。清代州县赋役多列有“屯赋”名目,但大多研究者对于屯赋、民赋之间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对地方社会的意蕴却不甚留意。施剑等在关注贵州卫所裁撤的同时,已注意其屯田的处置问题[17]。相对于卫所裁撤而言,屯田处置其实是脱节和滞后的。这种滞后性恰恰凸显了州县民田和原卫所屯田、科田之间的差别。民、屯科则及户丁徭役的差别,给地方政府征收田赋、派发力役等皆造成了一定的困境,也为民间社会的赋役规避提供了契机,这也是因卫所等原因造成的插花地问题长期存在且在卫所等裁撤以后仍难以解决的根本所在。州县官员在应对这一问题时,除了一再呼吁、个案处置或想方设法使田赋有具体村寨及户丁承担以保障足额征解钱粮外,在均平赋役、调整科则方面则受制于定额财政制度和“旧例”“旧额”的传统约束,几乎难有作为可言。
目前,诸如宝庆府或安平县之类基于府州县等局部视域的屯赋调整案件的研究仍相当缺乏,而这类事件在内地、沿海与沿边仍有较多的存在,尚有鼓励个案研究的必要。当然,以个案关注为基础,进一步对屯田赋税及户丁徭役变革作分省区或全国性的宏观探讨也是值得期待的。
五、卫所基层组织的因袭与里甲重构
卫所撤并或改设州县之后,原卫所辖区以屯旗、屯堡为单位的基层组织或被编入州县里甲体系,或因卫所原有基层组织体系而整顿调剂之。在卫所改设州县或卫所影响地方社会较为深远的地区,归并或改设州县之后,原卫所基层社会组织体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下来。考察这类地区的基层社会结构与组织形态,仍需要溯源卫所制度的明代实践。
因应于地方政府在户籍、赋税与征役等方面的制度差异,诸如里甲之类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对应赋役征发而存在的。因此,改卫归流落实到基层社会的时候,原卫所的基层组织体系也要作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州县管理体制和理念。在西北、西南不少地区,由于卫所基层组织曾长期存在,即使它们经历过清代里甲组织体系重新改编整顿,但至今仍有大量乡镇村寨的地名保留了卫所基层社会组织留下的痕迹。清代改卫归流体现在基层社会组织体系上,就是原卫所屯堡组织的里甲重组。明代卫所相当部分屯、科土地交错在州县、土司境内,二者科则不同,输纳各异,归属不同的管理系统。清代以之归并或改置州县,必然重建或调整里甲系统以接纳、消化这部分田土、户口,就不得不面对原来卫所的基层组织系统,并只能在此基础上因革损益而为之。
前述于志嘉、邓庆平等人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卫所裁撤之后,其原有基层组织的沿袭、变革及州县里甲体系在此基础上的整顿重构问题。然而,卫所裁撤导致的州县里甲重构作为康熙、雍正以后相对普遍的存在,仅有边疆或民族地区的少数个案研究显然不够,讨论卫所影响的逐步消解问题也必然将视角“下移”基层社会,从里甲组织乃至民间社会的因应上进行观察。
六、明代卫所的后世遗产与清代改卫归流的历史评估
明初所构建的军、民二元管理体制以及与之相辅而行的汉、土二元管理体制,秉持“军民分际”与“汉土分际”的统治原则执行了二百数十年,即使明中后期卫所行政化(州县化)与土司政治中的流官渗透在整体上不断加强,但该二元体制仍长期存在,该统治原则长期执行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却不能因改朝换代或改弦更张而被低估或忽视。明朝疆土管理体制是由军事和行政两大系统构成的,这种二元体制自有其建立、延续和消解的过程。明代卫所在清朝的阶段性存在及其最终裁撤,实际上是明朝疆土的二元管理体制在清代延续和消解的体现。裁撤政区(地理)意义上的卫所仅仅是二元体制在“上层建筑”(政区)层面的消除,但并不意味着其在“经济基础”(社会)层面的结束,这就是清代“改卫归流”研究的起点和价值所在。
前文所述清代“改卫归流”所涉及的州县政区调整、插花地划拨、基层社会的赋役调整和里甲重组等,归根结底都是清朝中央与地方为消除前朝军民二元体制所作的努力。明朝的疆土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也即军事与行政系统的二元体制,这个问题顾诚先生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等文中已有充分的论述。然而,如何接收消化这种体制,巩固其既有成果,并消解其消极影响,却成为清朝前中统治者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清代“改卫归流”,对政府而言,即废除明代军民二元体制并消解其消极影响过程;对于民间社会来说,即军民二元体制从制度层面瓦解之后,面对州县管理体制如何应对和调适的问题。
清代的改卫归流,不应该仅仅被看成是裁撤卫所归并或改设州县的行政行为,它应该包括上述卫所插花地划拨、屯科赋役调整、屯堡到里甲的社会组织重构等“落地”于基层社会的诸多体现,而这些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变革必须通过长期渐进的因应、调整方能实现。
讨论清代改卫归流问题,必须将之置于整个明代二元体制建立、延续及其清代调整、消解的整体性、连续性视野中考察。至明朝中后期,这种军民二元体制已然造成持续而严重的消极影响,诸如川滇黔、湘黔桂等省区交界区域的犬牙相制不再具有预期的制度成效,“黔府湖卫”或“州卫同城”“司卫同城”导致的矛盾冲突难以调节。但是,所有这些也不能否认它在维系明朝疆土管理及拓展中国地理与文化边疆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清代改卫归流正是消弭明代军民二元体制的消极影响,巩固其既有统治成果的自然趋势。可以说,更加积极地评价明代卫所与卫所制度的后世遗产,评价明代军民二元体制发生的必然性与阶段性,评价清代改卫归流“落地”于基层社会的历史价值是必要的。
注释:
①道光《宝庆府志》等诸种地方志均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原宝庆等卫屯赋在清中前期艰难调整的历程,而相关研究成果则仍未刊布。
参考文献:
[1]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2):15-22.
[2]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J].中国社会科学,1986(4):193-213.
[3]李巨澜.清代卫所制度述略[J].史学月刊,2002(3):36-40.
[4]于志嘉.犬牙相制:以明清时代的潼关卫为例[A].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9(80—1).
[5]邓庆平.卫所制度变迁与基层社会的资源配置——以明清蔚州为中心的考察[J].求是学刊,2007(6):150-155.
[6]孟凡松.安福、永定二县的设置与清代州县行政管理体制在湘西北的确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1):81-86.
[7]孟凡松.卫所沿革与明清时期澧州地区地方行政制度变迁——以九溪、永定二卫及其属所为中心[J].历史地理,2008(1):53-64.
[8]杨晨宇.清代卫所裁并总论[J].史志学刊,2017(3):6-13.
[9]杨晨宇.清代卫所裁并研究综述[J].史志学刊,2017(6):83-91.
[10]马琦,韩昭庆,孙涛.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22-128.
[11]杨斌.明清以来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12]毛亦可.论明清屯田的私有化历程[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2):35-48.
[13]嘉靖《贵州通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14]孙兆霞.吉昌契约文化汇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5]孟凡松.赋役制度与政区边界——基于明清湘鄂西地区的考察[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2):60-69.
[16]道光《安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4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
[17]施剑.清前期贵州卫所之裁撤及其屯田处置[J].历史档案,2014(2):5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