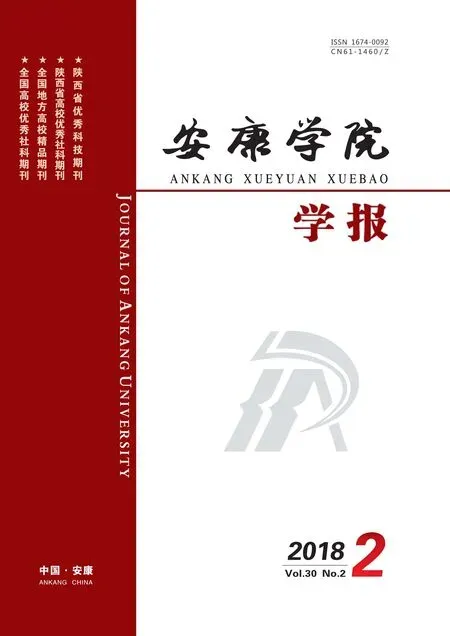战争背景下对小说《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的生态解读
张 珍
(西安航空学院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7)
《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创作的以阿富汗历史为背景的两部小说,曾分别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榜首。因其独特的背景和深刻的主题,揭示了战争前后阿富汗人民在自然、社会及精神上的变化和迷茫。其中,《追风筝的人》以阿米尔和哈桑的关系为主线,《灿烂千阳》以玛丽娅姆和莱拉为线索,讲述在灾难深重的阿富汗大背景下,人们对人性的救赎和幸福和平生活的渴望。胡塞尼向读者展现了处于战争中的父子、母女、手足之间的爱,以及创伤、背叛、性别阶层歧视和牺牲等主题,这些也成为诸多读者研究这两部小说的切入点和热点[1]。此外,作者在这两部作品中也详细地展现了对战前阿富汗诗意的自然、丰富的文化生活及和谐社会的深爱,这与小说中处在战争及塔利班恐怖主义下的阿富汗及人民的遭遇形成强烈对比。胡塞尼通过小说关注战争中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旨在唤起人们的生态意识。身为一名美籍阿富汗人,胡塞尼认为有义务将真实的阿富汗呈献给读者——战前乐土和战后荒园,以及在重压下维持着苦难生活的人们。
一、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是文学研究与当代生态思潮的结合,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是90年代英美兴起的批评浪潮。生态批评通过文学文本考察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不仅要解救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大自然,而且还要还人性以自然,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它的终极关怀是重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家园和物质家园,天人合一[2]。生态批评可以简要地定义为本着拯救环境之精神研究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态批评”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曼于1978年首次提出。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中,他以“生态批评”概念明确地将文学和生态结合起来[3]。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态批评从刚开始的边缘批评理论发展到在文学批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外文学评论家们也对生态批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大致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生态批评理论主要研究文学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本文将从广义的角度解读胡塞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 《灿烂千阳》这两部作品。
二、自然生态
(一)战前的诗意家园
自然无处不在,它是人类生存环境中现实存在的事物和环境。战前的阿富汗,大自然充满生机与活力,是人们快乐的诗意家园。那时的天清澈透亮,花儿竞相开放,草翠绿繁茂。两部小说中都描述了各种具有生命力的树木。在《追风筝的人》中,作者描写了石榴树、白杨树、樱桃树等。《灿烂千阳》中,茂密的柳树围绕着玛丽娅姆和莱拉的家。
在《追风筝的人》中,石榴树长在离阿米尔父亲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房子北面不远的山丘上。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山顶有已废弃的墓园,墓园的入口边上有株石榴树。某个夏日,我和哈桑在树干刻下我们的名字。这些字宣告:这棵树属于我们。放学后,哈桑和我爬上树枝,摘几个血红色的石榴。吃完,我们用杂草把手擦干净,之后我会念书给哈桑听。他盘腿坐着,阳光和石榴叶的阴影在他脸上翩翩起舞,心不在焉地摘着地上杂草的叶片。我们坐在石榴树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直到太阳西下。我们分享着书中的故事,感受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4]27
山丘和石榴树是阿米尔和哈桑的乐园。他们开心时跑去那里玩儿,在树下读书,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石榴树上,象征他们友谊长存,这是他们儿时最快乐的回忆。他们不开心时,也会去那里,从大自然中寻找安慰。当阿富汗政治发生动荡后,哈桑怕自己要和阿米尔分离,他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乐园,只有在大自然这个秘密乐园里,他们才能忘记所有的担忧和不快,享受片刻的儿时乐趣。
他们也经常爬上白杨树,坐在高高的树枝上,光脚吊在空中。裤兜里装满风干的桑葚和坚果,用吃完的核掷向对方,空气中到处弥漫着他们的欢笑声。温暖的阳光从树叶间泄下,照在脸上。阿米尔和哈桑在大自然中自由、开心地玩耍,仿佛他们也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
在《灿烂千阳》中,玛丽娅姆和母亲娜拉住在离市中心2000公里远的偏僻农舍里。去她们家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山路,路两旁是过人膝的草丛和亮黄色的野花,往上走是一片白杨树和棉花地,一条小河从山上流下。离山不远的地方,有一片环形的柳树群,在这一圈柳树中间的空地上坐落的正是玛丽娅姆的家[5]。虽远离城市,但她们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早晨起来,玛丽娅姆和母亲挤羊奶、喂鸡、收鸡蛋。两人一起做面包,跟母亲学习缝补。夏天的夜晚,母女俩躺在屋顶一起欣赏月光。冬日的夜晚,她们在家里一起读书。玛丽娅姆所有美好的记忆都是远离城市和战争的那段田园乡下生活。
(二)战后荒园
战争的到来让阿富汗人民深陷苦难之中,昔日美丽的大自然和生存环境遭到战火的破坏。冬季穷人砍树当柴火取暖,苏联士兵砍倒成片树木为了找到潜伏在树林里的狙击手。
阿米尔多年以后回到喀布尔,来到曾经和哈桑度过快乐童年时光的那个小山丘。往日充满生机的乐园如今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成堆的战后垃圾,炮火和地雷把地表的植被炸毁了,仅存的树干和干枯的草显得死气沉沉。通往父亲住所的道路两旁的柳树也基本被砍光了。玉米地里没有了庄稼,那株带给他们无限快乐的石榴树也多年不结果实,枯萎了。喀布尔河和美丽的湖水干涸了。空气里不再是甘蔗和烤肉串的香味,到处充斥着燃烧的柴油和炮火的刺鼻气味。
被砍伐的柳树,不再结果的石榴树,干涸的喀布尔河等景象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田园式美好生活的消失。受到战火的重创,大自然不再给人们提供美好的生存环境,人们也不能从中获取幸福生活和精神上的安慰。
三、社会生态
社会生态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研究社会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美国社会学家穆雷·布克金曾指出,生态问题的背后肯定存在深刻的社会问题,即生态问题是由非理性的社会生存方式和政治体系造成的[6]。理想的社会生态支撑自然生态,保护生命,实现自然的最大价值。相反,糟糕的社会生态导致自然生态的破坏并阻碍其生命发展。在《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中,阿富汗经历了10年战争和塔利班的统治,导致经济衰败、人性扭曲、女性遭受歧视、儿童被虐待等,种族矛盾更加尖锐。
苏联的入侵让阿富汗人民过上了朝不保夕的日子。两部小说中都描写了战争的场面和人们的恐惧:到处都是地雷炸弹,到处都是墓地和受伤的同胞。而苏联的撤军并没有给阿富汗带来希望,塔利班组织开始控制这个国家,并要求大家都遵从被曲解的伊斯兰教法:禁止人们各种活动和传统节日的开展,甚至看电视、放风筝和体育赛事中的欢呼鼓掌都被制止。塔利班的统治破坏了社会生态和阿富汗国家的文化生态。塔利班派“大胡子”在街上巡逻,他们手里的鞭子和武器随时都会找到发泄的对象,尤其对女性的严苛要求和惩罚程度令人发指。
在塔利班的统治下,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和人际关系矛盾异常尖锐。由于不同的信仰,哈扎拉人被认为是低等的垃圾人。哈桑和玛丽娅姆作为哈扎拉人,他们的悲惨命运何尝不是种族歧视造成的,即使阿米尔和莱拉,作为普什图人,被认为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但在关键时刻,他们并没有把哈桑和玛丽娅姆当做真正的朋友。哈桑对阿米尔全心全意付出,玛丽娅姆对莱拉的牺牲都证明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不平等的。
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下,妇女儿童受到极大的迫害。丈夫战死,女人不许外出工作,大批儿童要么营养不良,要么被饿死。苏联士兵和塔利班分子肆意骚扰,强奸妇女和儿童,甚至男童。在《追风筝的人》中,卡迈勒被四名士兵强奸,之后再也不和他人讲话。作为塔利班的官员,阿塞夫定期去孤儿院强迫院长给他提供女童或男童。其中索拉博(阿桑的儿子)就被阿塞夫选中,被打扮成女孩的模样供他娱乐,被他蹂躏。这在索拉博的心理留下了无法抹去的阴影。在《灿烂千阳》中,由于经济窘迫,玛丽娅姆的丈夫拉希德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孤儿院。孤儿院的环境恶劣,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在塔利班的统治下,没有男士的陪伴,女性是不允许一个人去孤儿院的。即使玛丽娅姆担心女儿,但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下,她也束手无策。
阿富汗在战争的摧残下,社会生态发生了扭曲。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生命都不能遵从自然的发展,诸多关系都发生了扭曲和恶化。
四、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以及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利用和改造环境而创造文化,从而说明文化特征、产生及发展规律。阿富汗遭受他国入侵,国内政治动荡,这些因素导致阿富汗人民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困惑。在极端的宗教教义下,人民已经失去了丰富的文化生活。阿富汗这种畸形的文化生态与被破坏的自然生态和病态的社会生态密不可分。
“身份”可以理解为区别于他人的有自己性格特质的品质和态度。文化身份(culturalidentity)主要指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特征,常由国家历史文化和人们的精神支柱等组成,如宗教信仰、种族价值观、人生观等[7]。
苏联的入侵导致很多阿富汗人逃到美国,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竭尽全力接受并适应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无形中与自己本国的文化身份形成对立和冲突。作为移民,他们成为美国底层人民,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靠政府的接济度日。阿米尔的父亲在加气站找到一份体力活,而他在阿富汗是成功的企业家,有体面的事业,过着富足舒适的生活。加气站的工作非常辛苦,他时常怀念自己在喀布尔的日子:那里的一草一木,街道上碰到的打招呼的熟人,和自己有着共同祖先的亲戚以及自己打拼的事业。在美国,出于自尊,他拒绝了好心的多宾斯夫人赠与的政府食物劵,并认为这是对他自尊的羞辱。作为孩子,阿米尔很快适应了美国生活,来到新环境,没有人在意他的过去和他曾经在阿富汗犯下的错。在这里没有回忆,没有折磨他心灵的罪孽感。然而,阿米尔仍然存在个人身份和社会身份的认同问题。在与拉辛汗通电话之后,阿米尔决定踏上回国之路。当回到阿富汗时,他感到自己的国家如此陌生:“我已经离开祖国这么久,早已忘记和被忘记,再次回来,在自己的国土上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游客”[4]220。这样的身份认同障碍体现了阿富汗文化生态的破坏和丢失。
在塔利班的高压统治下,阿富汗人民往日丰富的文化生活几乎被全面禁止。伊斯兰教法罗列出诸多严酷的禁止条文:人们不许看西方电影,不许看电视、听音乐、跳舞,更别说在阿富汗最令孩子们开心的风筝比赛了。阿富汗人民什么文化生活也没有了,只能祷告。他们整日苦闷、忧愁,身份认同问题和严酷的文化统治使人们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战争和国内扭曲的社会生态造成了阿富汗支离破碎的文化生态。
五、结语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主要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人们又通过审视自己的行为和人类文明来找寻对待自然和环境的正确方式。本文从生态批评的三个方面,即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分析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两部小说,探讨了战争和社会制度对生态的影响,为人类生态危机现状提供了丰富的生态主义内涵和启示。
参考文献:
[1]魏金梅.《追风筝的人》的生态批评解读[J].名作欣赏,2011(15):52-53.
[2]刘文良.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生态批评不可忽视的维度[J].理论与改革,2009(2):95-98.
[3]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1.
[4]HOSSEINI K.The kite runner[M].London:Bloom-sbury,2003.
[5]HOSSEINI K.A thousand splendid suns[M].New York:Riverhead Books,2007:68.
[6]BOOKCHIN M.What is social ecology? [M].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3:53.
[7]王诺.生态批评:界定与任务[J].文学评论,2009(1):6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