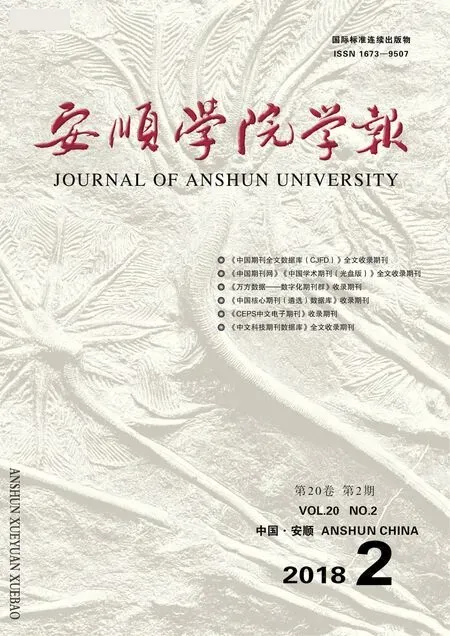玉汝于成:赋学文献研究的新境地
——评踪凡教授《赋学文献论稿》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当前,学界的赋学文献研究如火如荼,呈现总结集成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赋学文本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如2014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历时20年出版的《历代辞赋总汇》,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全的赋体文学总汇。而许结教授历时多年打造的《历代赋汇》(点校本)亦即将面世。二是赋论资料的选编,如王冠《赋话广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孙福轩《历代赋论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尤其是以首都师范大学踪凡教授《历代赋学文献辑刊》(全20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的出版最为卓著。中国赋学会会长、南京大学许结教授给予高度评价和期待:“有了这一鸿篇巨制,赋学同仁宜考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赋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如出版赋学文献系列点校、笺注本”。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石,离开文献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可以想见,对推动中国赋学研究的力度上,踪教授此举厥功甚伟。在长时期举力蒐辑、考辨甄别的摸索中,编者进一步深化提升,将近二十年赋学研究的创见与心得汇于一书,于是又有《赋学文献论稿》出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为学界的赋学文献研究呈上精彩典范。以笔者之见,《赋学文献论稿》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元典考论:中国赋学文献与批评史特征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1]赋学文献分散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十分不易搜集。有时某种文献的重要版本甚至需要跨境、跨国去寻访。踪教授利用各种途径,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不仅花费很大力气去搜集各种文献,获得第一手资料,还特别注重对各版本进行比勘和研究。如《会稽三赋》的注本与版本问题,经作者查考,目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10种版本,共12套;而国家图书馆则藏有该书的16种版本,共23套。而将两馆所藏诸本进行归纳、梳理后,进而又可揭示出三赋在宋元明清时期被解读和传播的情况。又如明代以来辑录的司马相如文集有十余种之多。《<司马相如集>版本叙录》一文在描述其版本状态的基础上,指出它们或本于《汉书》,或源出《文选》,或广蓃佚文,或详加校注,有的还汇集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对于司马相如作品的保存、研究、传播与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值得提出的是,早在2008年,作者即有《司马相如资料汇编》一书出版,可见该文深厚的文献基础。又《事类赋》现存不同版本达21种之多,踪教授一一说明其版式藏地等信息,指出是编既具类书功能,亦表现出鲜明的文学特色,是清代以来学者辑佚、校勘古书的重要资料来源,因此有着珍贵的文献价值。这种以元典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方式,论证有据,论点可信,路径可循,成果可期,是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和必由之路。诚如作者所说,“本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认真阅读赋学元典和相关史料,尤其注重对文献版本的考察和甄别,对出土文献的关注和研讨,对古代“小学”著作的挖掘和利用……以原始资料为据而得出的观点,自己心里感到踏实”(《前言》)。
是编以文献为基本线索,文献与批评结合,以点带面,考论并重,由此展示出中国赋学批评史的基本特征。作者并没有对中国赋论史作全面论析,而是将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或意义重大的赋学典籍进行深入挖掘与研究,或抉发其价值,或归纳其特点,或指摘其阙失,或胪列其版本,既能统筹赋学批评全局,又颇顾及个体价值地位。如对汉魏六朝时期的赋学批评,由于赋学文献十不存一,那么重点在辞赋的编集、传播、注释等情况。踪教授首先对赋体考镜源流,正本清源,突破了传统的诗源说、楚辞说、纵横家言说、隐语说、俳词说、多源说等固有观念,得出赋体文学源于先秦民间韵语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就贾谊、司马相如、檀道鸾等影响较大的赋家,或探讨辞赋的著录与传播,或考辨版本迷雾,或评析价值地位等,与此期赋学批评相得益彰。唐宋元三代赋集编纂成果不多,踪教授主要关注类书、韵书及大型诗文总集等对保存赋体及由此产生的意义和价值。明清时期历史风云的变化,文学形式也随之改变。在赋学研究领域,则以赋话的产生、评点的繁荣及赋总集的大量出现为特征,因此踪教授关注的重点又以重要作家、重要赋集如《辞赋标义》《赋海补遗》《赋珍》《赋略》《赋海大观》等文献为主。对于当代赋学著作,踪教授首先对龚克昌先生的《中国辞赋研究》《全汉赋评注》《全三国赋评注》分别进行介绍和评论。之后对新时期第一部专门研究唐赋的学术专著,广西师范大学韩晖先生的《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做了介绍。而赋论及赋集的编纂,则以湖北大学何新文教授的《中国赋论史稿》《中国赋论史》和中国赋学会第一任会长、湖南师范大学马积高先生主编,六十余位赋学研究者通力合作的《历代辞赋总汇》为代表。全书以文献为主,由一系列典型个案的研究自然形成中国赋学文献批评的历史进程与变迁,为学界赋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二、填补空白:赋学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突破
踪教授的赋学研究,不惧冷僻,不避热点,孜孜矻矻,开拓创新。其《论稿》对学界未关注或关注较少的领域均敢于耕耘,创获颇丰,代表着中国赋学文献研究的最新前沿。如对于先唐赋论,大都将眼光聚焦于扬雄、班固、刘勰等理论家,对于南朝宋檀道鸾,则几乎无人关注。踪教授从《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中钩稽出一段檀道鸾《续晋阳秋》的佚文,通过考辨与辨析,写出《檀道鸾赋论发微》一文,认为檀道鸾不仅极力主张诗骚传统,而且第一次将楚辞与赋分而论之,并率先从《诗经》、楚辞、诸子百家凡三个方面探讨了赋体渊源。这不仅在刘宋时绝无仅有,在整个中国赋学批评史上也难得一见。又如作为明代前七子中的重要作家,何景明的辞赋主要见于其《何大复先生集》,作者却在《(雍正)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发现了佚文《石楼赋》,该赋对了解何景明的复古理论与创作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唐宋以后,对于保存赋学文献较多的类书、韵书、赋集、文集等均有关注,如《艺文类聚》对中国赋学的贡献,从赋学视域看《韵补》,及明清时期的大型赋集《辞赋标义》《赋珍》《赋海补遗》《赋略》《宋金元明赋选》《赋海大观》等,前者看似与赋学无关,较为冷僻;后者多藏身京师,翻阅不易,故学界探讨不多。《论稿》或考察其编者,或辨析其版本,或挖掘其赋学思想,或考证其阙误,将赋学研究的触角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推进,因此均可称为嘉惠学林、导夫先路之作。
值得提出的是,现代学界关于汉赋的研究,有从文学史、制度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风俗史及考古学等多个角度进行考察,硕果累累。汉赋研究亟须寻求新的研究视野与方式,才能走向全面创新与发展。然汉赋大家多是小学宗匠,如司马相如作有《凡将篇》,扬雄作《训纂篇》与《方言》,班固有《续训纂篇》,可知西汉文人如扬雄、司马相如等,均洞明字学。“综两京文赋,诸家莫不洞悉经史,钻研六书,耀采腾文,骈音俪字。”[2]因此汉赋与小学的关系不容忽视,亦是汉赋研究的新亮点。台湾简宗梧先生,大陆学者易闻晓等均倡此论,并身体力行,试图开辟赋学研究新天地。因交叉学科涉及面广,又有专业差异,因此,非涉猎广博、学养深厚者不能为之。踪凡教授早在《汉赋研究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就已注意到古人汉赋研究的语言学视角,近十年后,《论稿》再次指出,赋体文学的研究,大多学者从史书、总集、别集、诗文评等各类著述中查找资料,却很少注意语言文字学著作。其《古代语言文字学著作中的汉赋资料》一文发现,文字学著作如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一书征引前代赋多达206条,全部集中在汉魏六朝赋,隋唐赋1条也没有。这些引文为后人研究汉赋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异文资料及阐释材料,十分珍贵;音韵学著作如吴棫《韵补》征引先秦至北宋赋多达682条,其所征引的汉赋并不限于名篇,常常涉及一些不甚知名的作家作品,是后人辑佚工作重要的资料库;训诂学著作如罗愿《尔雅翼》、方以智《通雅》等书对汉赋语词、名物有较多研究。此外,作者不仅对东汉时期赋注家及其赋注有详细考述,还对出土文献密切关注,并考证审慎,如《神乌傅(赋)》于1993年出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尹湾村汉墓,是目前唯一的一篇保持原始状况的汉赋作品。迄今为止,海内外研究者对许多问题都取得重大进展,但不少问题仍是聚讼纷纭,《神乌赋集校集释》一文不仅对十余年间《神乌赋》考释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还就学界争议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提出创见,深见功力。
三、赋境开拓:古今贯通与上下求索
在时间上,本书横跨先秦至当代,内容广及类书、方志、出土文献、小学文献及赋家、赋集等,视野广博,然又深入细致。业师许结先生曾说,古代文学的研究,已有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只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一步,哪怕是半步,就是好的。对某些常人较少问津的大部头赋学文献,踪教授都有认真的考证工作,考其阙误,评其价值,前进之路,远非可尺可量。
作为一代文学之胜,两汉时期的赋家赋作可谓彬彬日盛。班固《两都赋序》云:“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3]至《汉书·艺文志》著录四类78家共1004篇,汉赋已散佚良多。自汉至今,留存下来的汉赋更是十不余一。今人费正刚等辑校《全汉赋》(1993年版、2005年增补版)、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的附录《先唐赋辑补》、《先唐赋存目考》等均对汉赋存佚情况作了竭泽而渔式的整理,因此很难再发现一些新材料。然踪教授《严可均<全汉文>、<全后汉文>辑录汉赋之贡献及阙误》一文据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引文发现赋圣司马相如有《玉如意赋》,又据明解缙等《永乐大典》卷一二〇四三“酒”部“赐方朔牛酒” 条引《古今事通启颜录》录东方朔《大言赋》。如此之评功正讹,补益良多,《论稿》举不胜举,是学界赋学研究绕不开的重要参考文献。又《赋珍》一书,海内外有四家图书馆收藏,分别是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及西北大学图书馆藏本。踪教授根据程章灿《赋珍考论》一文中“卷五《机赋》,作者为汉代王逸而误为汉王起”,而国内三本皆刻作“汉王逸”,得出程先生所据的哈佛本必与国内三个版本不同。又通过考察发现,西北大学藏本在吴宗达序之下刻有《赋珍总目》,这是西北大学藏本与其他藏本的最大区别。继而对《总目》与原文作了比对,并正其讹误。作者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各版本的区别,还对是编的编纂、内容及批评有详细介绍,为《赋珍》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参考价值。众所周知,清末光绪年间鸿宝斋书局编印的《赋海大观》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收赋最多、分类最繁细的赋体文学总集,规模是清康熙年间陈元龙奉敕编纂的《历代赋汇》的三倍之多。如此体制宏大,内容浩博的赋体总集,虽一再影印,却石印袖珍,字如蝼蚁,实难观感。作为清代律赋渊薮,还存在着分类失当、次序错乱、篇目缺漏、误收重出、篇名错讹、作者阙误、内容阙误、体例混乱等问题,如作者标注之误,卷一“天文类”“风”目收有《飓风赋》1篇,题为苏轼作,据《宋文鉴》《古赋辨体》等书,当为苏轼之子苏过所作;篇名之误,卷三“地”目有唐钱起《益地图赋》,据《文苑英华》卷二十五和《历代赋汇》正集卷十四,赋题当为《盖地图赋》,“盖”“益”形近而讹;重出之误,如卷八“典礼”类“祭祀”目收录唐石贯《藉田赋》1篇,同卷“耕藉”目又收此赋,文字相同,只是未标出作者朝代;那么《<赋海大观>之阙误》一文对此一一校核辨析,需要何其大的耐心和毅力!
踪教授的赋学研究,谦虚宽容、严谨细致并持之以恒,其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独到而有远见,并不随着成果的问世而终止。如《<神乌赋>集校集释》一文原载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先秦两汉学术》,2006年第6期。在发表的同时及以后,又有数篇考释《神乌赋》的论文,未能吸收。然在本书出版时,踪教授将这些论文附录在文后。一方面为有兴趣的读者提供更多的线索和参考,另一方面表明其对此问题的长期关注。踪教授还在书中留下了自己赋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如《<艺文类聚>与中国赋学》一文,他在文后不仅罗列了研究类书与文学关系的著作,如方师铎《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唐光荣《唐代类书与文学》、田媛《隋暨初唐类书编纂与文学》等,还有专门研究《艺文类聚》的著作,如郭醒博士论文《<艺文类聚>研究》、孙翠翠硕士论文《<艺文类聚>》所引“艺文”研究》等,由此可知,踪先生在研究《艺文类聚》与赋学的关系时,不仅详细比较了《艺文类聚》《初学记》《文选》所载赋的异同,还将视角延伸到类书与文学的关系,以小见大,洞见随出。又作者在《<事类赋>版本叙录》文后指出,研究《事类赋》,首先应该参考冀勤等点校的《事类赋注》,(中华书局1989年版),研究论文有权儒学《宋刻本吴淑<事类赋>》(《文献》1990年第2期)等。或为读者指明路径,或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不失为学界赋学文献研究的典范力作。
参考文献:
[1](清)张之洞.书目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
[2]孙梅.四六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
[3](南朝梁)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