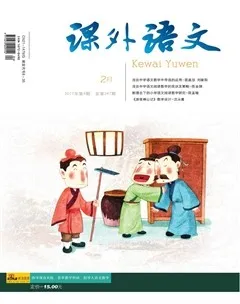试论嵇康悲剧命运的必然性根源
【摘要】嵇康,魏晋名士,“人以为龙章凤姿,天然自成”,遭司马氏所弑,然他的悲剧人生却为魏晋南北朝甚至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本文从当时政治、文化环境及其个人性情出发剖析其悲剧人生的必然性。
【关键词】嵇康;文化;政治;性情;悲剧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魏晋南北朝,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实在是个丰富多彩的时代,战火纷飞,枭雄辈出,才子风流,文化交融,儒释道三教相容相杀,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一段乱世,无数故事。对于时代的敏感度,文学家是最有体现力的群体,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而其中最有悲剧震撼力的人物当属嵇康了。
嵇康,字叔夜,魏文帝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出生,谯郡人,娶曹操子曹林之女长乐亭主为妻,补郎中,后拜中散大夫,景元四年(263年)被杀。
史书上对嵇康生平轶事多有记载描述。笔者对其品行形象归纳有四:一理想超尘绝俗、返归自然。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他说“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可见其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的理想人生。二其个性淡泊名利,但又愤世嫉俗、刚正切直。《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嵇康别传》中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俊,岂能免乎?”三是诗书琴画造诣高深,是一个很有艺术修养的名士。韦续《墨薮》中评嵇康书法如抱琴半醉,酣歌高眠。又若众鸟翱翔,群乌乍散。”唐人张怀瑾于《书断》中列康草书为妙品。他的《琴赋》《声无哀乐论》表现了他高深的音乐素养。他的诗作水平也可称得上大家。四是相貌堂堂,人中龙凤。《晋书·嵇康传》称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凤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然自成。”
如此才情横溢淡泊名利之士为何最终落得被诛杀的下场呢?他的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何?
其一,文化根源——“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为儒家所不容。
嵇康在《卜疑》中提出了二十八中处世态度,这几乎涵盖了当时士人出处的各种可能,而他自己的选择则是“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这样的选择也是他追求优游适意、自足怀抱的人生理想。这一理想承自于老庄思想。嵇康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中走向他与众不同的人生境界,他的悠闲垂钓、鼓楫泛舟,洋溢着浓重的庄子避世思想。也许在常人看来,嵇康的生存方式透露着颓废,他与竹林七贤在竹林中喝酒吃肉弹琴,扪虱而谈,过着常人难以理解的生活。这种荒诞无序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充满着庄子思想,与庄子所不同的是嵇康追求返归自然、心与道和,是一种真实的生活。
至于他最有名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惊世骇俗,与名教持完全对立的态度。这种对立最鲜明的表现就是他厌恶仕途,拒绝山涛的推荐,不愿入世为官,追求仕禄。他强烈地反对名教,在《绝交书》中,他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答难养生论》中,亦有他对孔子的非议:
且凡圣人,有损己为世,表行显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经营四方,心劳形困,趣步失节者……吾所不能同也。
如此犀利的言辞,可见在嵇康眼中孔子是一个趋名逐利的人,是他不认同的,这对名教中人而言,是极大的不尊重。
其二,政治根源——“欲起兵应毋丘俭”,名士争相入狱求为其替罪为司马氏所不容。
对于嵇康为司马氏所杀,还有一条根本性的根源是当时曹氏集团与司马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魏晋时期,权力争斗险恶,司马氏为夺取和稳定统治,杀戮异党,手段残忍,在嵇康生活的时期,正是曹爽与司马懿共同治政而司马氏渐逼曹氏放弃权柄的时期,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斗争最为惨烈、最为尖锐的时期。司马懿杀王陵夷其三族,司马炎杀张弘又夷其三族。嵇康认为当时已是“民之多僻,政不由己”(《幽愤诗》),国家内乱不停,百姓生灵涂炭,整个社会与其理想中的与自然相和的诗意社会完全背离,所以,他拒绝出仕为司马氏效力。嵇康因婚而仕,置身于曹氏政治联姻的婚姻圈,“而因姻戚之关系,以至影响其政治立场”。在《释私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中,他暗指司马氏及其追随者“匿情矜吝”,“或谗言似信,不可谓有 诚;激盗似忠,不可谓无私”;借论管叔蔡叔何以“姑为淑善”而又叛乱,暗指司马氏父子托周公之名以专朝政的野心;或者为被诬陷为不孝而入狱的吕安辩护,公然向司马氏所推行的“孝治天下”的方略挑战。司马昭杀之,一则是针对其本人的不为司马氏所用之心,介入毋丘俭起兵之大不忠,二则是司马昭想通过他打击名士们的对立情绪,杀鸡给猴看的意思更为浓重,这是司马氏权力斗争的需要,而借嵇康这个有大声望名士的性命。当嵇康被羁,有人争相入狱替罪,有人上书请以其为师,又怎不为司马氏所忌惮?而嵇康却在临刑之时,依然能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遗世,这又是何等的潇洒风流!
司马氏以“名教”为幌子,争权夺利排除异己,使得民生困苦。而嵇康公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這便从思想意识上对统治阶级提出了挑战。由此观之,嵇康此时已避无可避,既然不能放弃原则归顺司马氏,就只能坚持独立人格,冒牺牲生命之危险。
其三,个性根源——“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为政见相异者所不容。
嵇康幼年就成为孤儿,由父兄抚养长大,父兄待他又极为宠溺,所以养成了他任性恣肆的性格。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胸襟坦荡之士。他的性格刚直峻急,他在《与山涛绝交书》中自言“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与吕巽绝交,是因为吕巽诬陷吕安;与山涛绝交,是因为山涛的价值取向与自己的人生理想相背;与钟会交恶,是因为他不肯正眼与之相酬。甘露三年(258),钟会迁司隶校尉,“为大将军所昵”(《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九《钟会传》),志得意满,索闻康名,不料反遭难堪和冷遇。史载,嵇康正与向秀垄大树下打铁,及至钟会诸人来访,康犹“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会乘兴而来,见此番情景,自是无趣,遂起去。此时,康才开口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无论此中机锋何在,钟从此记恨于心,为日后嵇康系狱身死埋下祸根。钟会曰:
“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雅量第六》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司马氏所惧者无非“负才乱群惑众”人物,于是嵇康的人生悲剧避无可避。
嵇康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玄学人生观使得他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还是个体特性上都与当时的统治阶层格格不入,最终只能以悲剧告终,但也唯以此因,嵇康如竹如松如荷之高洁品行,才为千古士人所敬仰赞叹!山涛说:“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语·容止》)钟会言:“嵇康,卧龙也,不可起。”(晋书·嵇康传)政见相左者犹如是说,何况后人?黄庭坚语:“嵇叔夜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凡学作诗者,不可不成诵在心。想见其人,虽沉于世故者,暂得揽其余芳,便可扑去面上三斗俗尘矣。何况深其义味者乎?”(《书嵇叔夜诗与侄榎》)甚是。
参考文献
[1]罗宗强.嵇康的心态及其人生悲剧[J].中国社会科学,1991.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