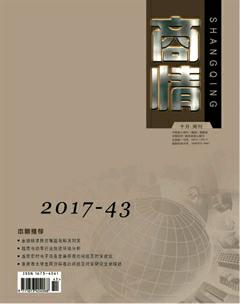反家庭暴力法实施难点研究
李宇
【摘要】2015年年末出台,2016年3月起正式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在我国防止和惩处家庭暴力问题的进程上可谓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司法实践,反家暴法存在的种种不足之处也都暴露了出来。本文对反家暴法在实践中面临着的家暴的范围界定不清晰,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难以及传统观念、文化漠视的阻碍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反家暴法 家庭暴力 实施难点 人身安全保护令
作为我国针对家暴问题的首次专门性立法,新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制化进程上,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经过了一年多的司法实践,反家庭暴力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如何?存在哪些阻碍或挑战?都已经有所反映。本文将就家庭暴力的范围界定问题、人身安全保护令、传统观念和文化漠视的阻碍等三个方面分析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式。
一、家暴的范围界定问题
在家庭暴力的界定问题上,国际上出台的相关公约以及外国的相关立法都早有界定。在1993年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是:“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的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而美国则认为“当一方亲密伴侣使用身体暴力、胁迫、威胁、恐吓、孤立隔绝以及情感、性和经济暴力试图保持对另一半亲密伴侣的权力控制时,即发生家庭暴力”。这一关于家庭暴力的定义较之《宣言》则更为广泛;英国法律中的家庭暴力通常被视为在身体、性、情感或经济等方面的伤害行为,其主体不仅包括现在有亲密关系的伴侣也包括曾有过亲密关系的伴侣,且家庭暴力发生的时间或地点并不影响其行为性质。在新西兰的《家庭暴力法案》中,家庭暴力的内容包括了对身体、性和心理等多个方面的伤害,而异性夫妻、“伴侣”和“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都可以成为家庭暴力的主体,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无论是缔结过婚姻关系还是没有。在日本,家庭暴力中的施暴者则只能是现时的丈夫或妻子,虽然在《家庭暴力防止法》中将事实婚姻也纳入了其中,却不包括离婚后的伴侣。而且在家庭暴力的内容上只有伤害罪、暴行等基本的身体性暴力,却没有将精神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范围。
我国新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在关于家庭暴力的范围界定上,相较于之前的婚姻法等法律做出了新的,突破性的规定。反家暴法第一章第二条:“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第六章第三十七条:“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和婚姻法關于家庭暴力规定相比较,新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沿用了婚姻法对家庭暴力这一概念的定义,但是在家暴主体上做出了突破,将共同生活人纳入了家暴主体范围内。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国际上一般将家庭暴力分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财产暴力四大类,
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虽然包括了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并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指明,但是却未能够将性暴力和财产暴力这两个在生活中越来越多出现的家暴类型纳入法条规定中。由此可见,新法在对家庭暴力的定义范围上,特别是和国际社会相关立法相比较,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
二、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可谓是不可忽视的一大亮点,在新法刚出台之际就备受关注,备受赞誉。诚然,同之前的立法相比,反家庭暴力法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从申请主体到申请条件,签发时间到有效期限,甚至包括相关的复议制度,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可谓是面面俱到。但面面俱到并不代表毫无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人身安全保护令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保护令在执行上存在问题,其次,缺乏一个统一的证明标准,最后,缺乏关于具体内容和流程的细则规定。
(一)保护令的执行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于法律条文的历届和具体的做法往往不一致,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反家庭暴力法在关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的执行上,缺少了具体明确可行的细则规定。除此之外,执行主体上,由于人身安全保护令存在法院、派出所、社区等多主体,实践中多主体之间常常由于职责划分不清,缺乏配合等原因,导致人身安全保护令无法真正落实,无法切实保护申请人权益等问题。法院、派出所等多主体之间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上如何协调,配合,不同主体在具体实行之际应当分别担任何种角色,才能最大程度地保障申请人的权益,才能最高效地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都有待实践中进一步的摸索,验证。
(二)证明标准问题
在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上,反家庭暴力法规定:“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这一规定包括两点要求,一是要求受害人提供相应的证据;而是这些证据需要足以证明家庭暴力发生的事实或者有家庭暴力发生的现实危险。但在司法实践当中,被家暴者或代为申请者想要提供充分的、能够达到上述证明标准的证据是有难度的。就被家暴者而言,他们遭受了身体上的伤害是事实,但轻微的身体伤害并不会留下明显的足以作为证据的伤痕。更何况精神上的伤害?基本无法取证,也就无法提供充足的证据;此外,在我国,受“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思想影响,家庭暴力较之别国更具有隐蔽性,因此对于代为申请者而言,想要提供家暴的证据更是难上加难。毫无疑问,这种过高的证明标准会严重阻碍对被家暴者的救济。此外,新法在对通常保护令和紧急保护令的区分上,仅仅只是签发时间上有简单的区分,对于二者在审理程序、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上都缺乏必要的区别对待,而在司法实践中,仅仅依靠单纯的时间区分,很显然,并不能将这二者很好的分别开来。
(三)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内容和流程问题
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四项有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前三项规定的禁止令和迁出令,主要对被申请人人身做出限制;第四项则是“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的兜底性措施。但是在关于其他措施的具体规定上,法条却没有说明,如此一来,基层法院在处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类案件时,不能确定具体哪些措施可以作为其他措施适用,也就缺乏更多更有效的手段,举措来对申请人进行保护。比如,在分居期间甚至离婚判决后是否还可以申请保护令?紧急状态下人身保护令的签发是否只能由公安机关来签发以保证及时性?是否应扩大申请主体范围,加大处罚力度等。人身安全保护令具体内容和流程规定问题上存在的不足,严重影响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施效果。endprint
三、传统观念和文化漠视的阻碍
通过网络检索,有关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信息有113万多条,去掉新法实施之前的,我们从中却仍然时不时能看到许多报道出来的家暴重案,以及許多反映新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使用度低的报道。而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受害人很少主动寻求国家机关的庇护,另一方面,很多基层的工作人员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也存在不足,关于家暴的理念没有能够与时俱进,甚至出现了责备受害人的现象。
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男尊女卑、“清官难断家务事”等封建糟粕至今仍根深蒂固,这也是我国家暴发生、且受害人很少想到对外寻求帮助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抱着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许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即使遭受了家暴,也没想过要主动寻求法律的帮助;另一方面,作为家暴案件知情人的亲友、邻居,也觉得这是别人的“家事”,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实上,非但寻常百姓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大,相当一部分的执法人员在新法出台之后对家庭暴力也仍然是抱着老一套的看法,认为家暴不过是“两口子吵架”、“大人教育小孩”,抱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想法不愿或消极地介入、对待家暴案件。
甚至由于对家暴案件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而对施暴者抱有同情,乃至对受害人寻求保护的行为表示不理解。
四、问题解决建议
(一)完善家庭暴力概念
毫无疑问,将性暴力和财产暴力纳入反家庭暴力法防范和惩处的范畴是非常有必要的,不仅如此,对这些行为应当制定出客观、明确的标准,且在运用到司法实践当中之后,能行之有效,更好地保护公民不受家暴伤害。相较于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性暴力以及财产暴力可能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但其同样属于家暴,虽然不见痕迹,但同样会对受害人造成严重的伤害。随着性暴力和财产暴力在现今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为了更好地防治家庭暴力,非常有必要将性暴力、财产暴力纳入反家庭暴力法的惩处范围。除此之外,对于家庭暴力的主体规定上,应当将“共同生活的人”所包括的具体情形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同时借鉴国际立法上对家暴范围的界定,将前配偶以及“任何按照”婚姻的本质关系共同生活的人都纳入家暴主体之中,尽管笔者并不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同性恋作为“共同生活的人”同样可能发生家暴。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
在前文中提到,在实践当中,人身安全保护令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保护令的执行问题突出,二是证明标准不尽统一,三是缺乏保护令的具体内容和流程。因此也应当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来完善。
首先,要明确反家暴工作需要多机构相互配合,协同开展,通过立法对各部门在反家暴工作中的具体职责,细化分工。地方性立法针对反家暴工作对法院、公安、妇联、社区居委会等反家暴工作核心单位进行分工,明确不同部门的职责及权利,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机制,尝试构建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上的多元化的执行主体体系。同时在加强各单位反家暴工作专业性只是培训的同时规定各单位失职应当承担的后果,完善相关的追责机制和其他相关的配套措施。其次,有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证明标准以及举证责任,应当结合家暴案件的特殊性做出特别规定,不仅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证据规则上也应当适用优势证据规则;作为一项以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为直接目的的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证明标准和一般案件审理中的证明标准保持一致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应当相对地有所降低。此外,立法应当加强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职能的要求,基于此建立合理实用的证据制度,包括相应的证明标准体系。最后,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具体内容和流程的规定应当进一步细化,对于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执行的流程、内容、格式、时限等问题都应当有具体可参照执行的规定。
(三)加强反家暴法的宣传和培训
要彻底实现反家庭暴力的法治化,实现反家庭暴力的制度化和常态化,就必须克服传统的“男尊女卑”“家丑不外扬”等落后观念以及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漠视等阻碍。而要突破着种种困难,就需要从多方面加强对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
对普通民众,一方面,要通过广泛宣传反家暴法知识,转变家暴受害人的观念,让受害人能主动站出来寻求法律的保护,同时,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科普,让受害人知道如何正确的利用反家暴法保护自己。另一方面,通过广泛宣传反家暴法知识,加强对整个社会的公众宣传教育,改变人们对家暴的认识误区,改变现存的文化漠视。而对公权力部门和针对家暴的专业社会组织,则要加强其在反家暴工作上的专业性,既要了解反家暴的专业知识,更要树立正确的、先进的反家暴理念,如此,方能真正地为家暴受害人提供他们需要的保护和帮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