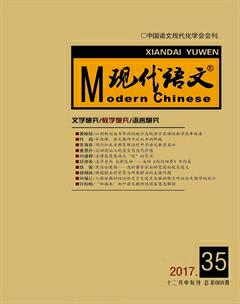中国式的《错误》
梁艳
台湾诗人郑愁予的代表作《错误》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诗歌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江南小镇的错误而又美丽的故事。《错误》一诗,借助中国式的意象,塑造典雅的形象;借助中国式的语言,营造动人的旋律;借助中国式的情感,构造生命的常态。杨牧曾经评价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而《错误》应当是郑诗“中国式”的典范之作。
笔者认为,他的“中国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式的意象,塑造典雅的形象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借用中国式的意象塑造人物形象是诗人们常用的一种手段。提到蒹葭,我们会想到伊人;提到雎鸠,我们会想到淑女;提到桃夭,我们会想到美妇……
关于《错误》一诗中的意象,不得不提的是“马蹄”。马蹄声响起的时候,马背上的男子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他也许潇洒风流,似那个骑着骏马的裴少俊;他也许春风得意,像那个骑着轻马游长安的诗人;他也许颓唐落魄,如那个骑着瘦马的断肠人……马蹄声几乎贯穿着整个中国文学史。
郑愁予童年有过一番逃难的经历。他说:“小时候母亲和我走过一个小镇,那时还在抗战,我们忽然听到背后传来轰轰声响,后来就见到马匹拉着炮车飞奔而来,母亲和我站在路旁,看着战马与炮车擦身而过,这印象一直潜存在我的意识里,后来写《错误》这首诗时,这个意象自然而然的就浮现在脑海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有此佳作的呈现。”
然而,在“达达的马蹄”响起的街口,那个骑马而来的人不是王子,更不是归人,只是一个过客。“马蹄”敲开了紧掩的窗扉,也敲击着她们的心。每一次马蹄声响都是一个希望,也是一次失望。每一次的马蹄都是“美丽”的,每一次的马蹄又都是“错误”的,于是便有了“莲花的开落”。
没有描摹,没有渲染,一朵莲花让“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跃然眼前:清如水、美如花。余光中笔下让“我”成为无悔地等在雨中的一池如红焰的“红莲”,红艳而热烈;席慕容笔下满腹心事的“夏荷”,缠绵而幽怨;《西洲曲》里,“清如水”的莲子,美丽而清新。“莲花”让一个个女子栩栩如生。
郑愁予笔下的开落的“莲花”,既写出了红颜的衰老,又写出了心情的起落,还写出了时光的流转。和下文向晚的“青石街道”连用,将等待的漫漫从时间上写到了极致:日复日、年复年……
这些还不够,诗人又将等待的心在空间上比作“寂寞的城”“青石的街道”和“窗”,范围越来越小,空间越来越窄,等待的女子的心也越来越封闭,直到“紧掩”。
诗人借助于这些中国式的意象塑造了一系列典雅的艺术形象:男子潇洒而决绝,而女子美丽而忧伤。
二、中国式的语言,营造动人的旋律
诗歌是最高的语言艺术。《错误》一诗,虽然短小,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却是独具特色的。
开篇一句“我打江南走过”,一个“打”字极具表现力。如果换成“从”,我从江南走过,就变得很普通。“打”字既说明了“我”骑马经过,更让读者听到马蹄敲击青石小路的达达之声。一声又一声,回响在青石街街道里,也敲在窗后女子的心上。一个“打”字让那颗等待的心不时悬起,又久久难以放下。既把等待中的女子的情感表現得淋漓尽致,又让读者的心在开篇就随着诗人的节奏跳动。
诗歌的语言是诗人的独白或是诗人的梦呓,所以它既具有感情性,又具有音乐性,还具有跳跃性。
“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按照现代汉语的逻辑顺序应当表述为: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所以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顺序一调整,达达的马蹄声就被突出了。在我的心如窗扉般紧掩之后,在这长长的向晚的青石街道上,又响起了达达的马蹄,那么清脆、那么响亮地又一次直抵心扉。窗后的那颗心又该乱了。而这时诗人却异常冷静地迸出一句: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窗后的失落与惆怅该如何形容?于是,我们看到那颗等待的心在瞬息之间百转千回。
跳跃的节奏、错乱的语序不仅营造了动人的旋律,还给我们留下无穷的回味。
三、中国式的情感,构造生命的常态
《错误》这首诗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的错误的故事。故事的四个要素是时、地、人、事。江南是一个多情的地方,也是一个生长故事的地方。江南三月,美丽的小镇,“我”和“你”因为一个“等”字,而产生了一段故事。一个“等”字将美丽的情感描摹得缠绵悱恻又如九曲回肠。
“我”和“你”的身份认定,可以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可能是情人,也可能是母子,还可能是朋友,更可能是陌生人,相同的是在我们之间都发生着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因为两人关系的不同,诗歌的主题也就截然不一了。
“你”在漫长的等待中,马蹄声响,马蹄声落。莲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柳絮飞了又落,落了又飞;跫音响起,跫音远去;春帷揭开,春帷放下;窗扉开启,窗扉紧掩。
人总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或出于主动,或迫于无奈,前方的诱惑始终存在着。“我”非常清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往往因为很多原因,回不到原点。正如顾曼桢所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打马走过的“我”也明白,自己已然走不进那座小小的城。人生的情缘恰恰如此,一错过就是一生。但于我来说,这是一次美好的经历。
“我”和“你”也许互不相识,而我们的背后又分别会有一个漂泊无依的归人和一个承受相思之苦的女子。打马走过的“我”凭着人生的经验,可以推断,每一扇紧掩的窗扉后都有一个等待的容颜在老去,每一扇窗里都有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
然而对于窗里的“你”,忧伤更在于,每次东风起时,都会春心流荡;每次马蹄声过,都会春心慌乱。可是,过尽千帆,都没有等来要等的人。但“你”又不愿错过这一切关于他的消息。席慕容说,长久的等待又算得了什么呢?假如,过尽千帆之后,你终于出现。“你”坚信当千帆过尽时,终能等来翩然来临的真实的笑容。
这种漂泊与守候在中国诗歌中已经流转千年,那么无可奈何,又那么心甘情愿。牛郎与织女,三百六十四天的等待只为一日的相聚,年复一年;白素贞断桥边千年的守候,只为一世的相逢;王宝钏寒窑的苦守,一等就是十八年……
郑愁予在《郑愁予的诗》的“序言”中如是说:诗中的人物都是我移情的替身,带有我对生命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悯。当我更进一步做横的检视时,令我瞿然心惊的是:我的诗作里,无论是哪一类的素材,都隐含我自幼就怀有的一种“流逝感”。这种“流逝感”在本诗中就表现为一种“漂泊感”。马上的男子在漂泊,楼上的女子也在漂泊。男子的漂泊是肉体的,而女子的漂泊是心灵的。本质上,他们都在流浪,都在寻找精神上感情上的一个安静的依靠。所以,那达达的马蹄注定会延续千年,不断地响起。
那段光阴的故事看似发生在过去,其实也发生在现在,还会发生在将来。这个中国式的故事是错误的,却又错得那么美丽。或许,这根本就是人生的一个常态!
参考文献:
[1]马梦原.诗歌语言的诗性解读[J].文教资料,2008,(7).
[2]郑愁予.郑愁予的诗[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