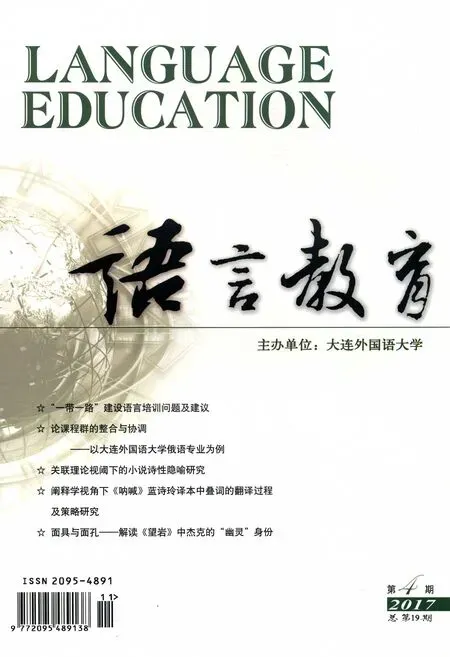从意向解读看含义研究
华鸿燕
(西南大学,重庆)
从意向解读看含义研究
华鸿燕
(西南大学,重庆)
语言交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说话人向受话人传递其意向,而受话人则要解读这一意向;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语用推理。在语用推理过程中,从话语中解读出来的意向就是含义;本研究中的含义是指受话人所获得的有别于话语语句真值的意义。含义是一种因果蕴涵的现象,也是从该话语中推演出来的若干能够想象的任何不包括逻辑矛盾的可能的思维内容;含义的解读可依“话语-含义因果蕴涵机制”而展开。
意向解读;含义;语用推理;话语-含义因果蕴涵机制
1.引言
本文研究含义(implied meaning)解读的认知过程;这就是说研究重点是语用推理的逻辑再现,而不是其心理实在。从意向解读(intentionreading)和含义关系的角度来说,对于有认知能力的交际者来说,把对方话语的意向解读出来就是做出了含义解读,本文的刻画就是含义解读语用推理的逻辑再现。把解读出来的含义内容用恰当简洁的文字写出来就是含义理论通常所指的含义,但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未涉及用文字写出来这一步骤。
2.语言转向与语用思维
我们将意向解读与语言运用特别是含义运用关系的研究放在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这一大理论背景下来考察,因为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最终使语用思维在学术研究中获得了主导地位。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为哲学研究自身乃至为语言研究、人文科学研究、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重大理论契机,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理论思考支撑点。正是语言转向及其内在包含的语用转向和认知转向的思维,为从意向解读切入含义运用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
以一个学科规模对含义进行研究的开创者是格莱斯(P. 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 (Grice’s theory of conversation implicature)。会话含义理论包括其后续的研究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有自己的特点,其影响广泛而深远,以致现在人们研究含义一般都会指向这一理论。格莱斯本人及其后继者对会话含义做出了很多重要的细致分类。但是,正如有学者对“格莱斯剃刀”(Grice’s razor)(Hazlett,2007: 669-690)的评论所说,其实违反或遵守原则或其他情况所得到的含义都是含义,在会话含义理论中做出精微的区分可能是为了学理研究的需要,但从语言运用来说,它们都来自同样的思维机制、认知过程。本研究是研究含义的思维机制,所以在本研究中含义是泛指交际话语中受话人所获得的有别于话语语句真值的意义,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把对方话语的意向解读出来,而不拘泥于会话含义理论所作出的各种细致的区分。
从哲学研究来说,语言转向发生在20世纪中叶,这使得在这以后的西方哲学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哲学的发展深深地打下了“语言”的烙印。这个转向现在还方兴未艾地向着纵深发展,回过头看语言转向在那大半个世纪的发展,可以观察到若干阶段,这些阶段采用不完全相同的语言分析手段进行研究,形成了一些不同的特征,例如以语形学为取向,形成逻辑论-语形分析;以言说内容为取向,形成本体论-语义分析;以语言使用者为取向,形成认识论-语用分析(殷杰,2003: 36-39);这些影响及至自然科学研究、科学哲学研究。
从语言研究这一视角看,语言转向对语言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表现出语言研究的哲学研究化以及哲学研究的语言学化的特征,许多大哲学家就做着深入的语言分析工作,著名哲学家奥斯丁(L. J. Austin)、格莱斯、舍尔(J. Searle)等人的名字在我国的语言学界变得耳熟能详;并使语言学的论述摆脱了单纯作为工具书趋向于抽象化、理论化、系统化的概括的特性,表现出整体性的承诺,以试图在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奠立语言学自身的实在的本体地位。但由于语言研究所触及的一切都是“语言”的,光是“语言转向”一个整体性的概括可能还难于表示这个过程各阶段的特征,因此需要有较为具体的说明。从语言研究的主题来说,这个转向大体有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起,集中注意的焦点是在句法上,其中,转换生成语法是这一阶段最杰出的代表;这样的关注焦点是同20世纪前半期展开语言转向的哲学家使用语言语形分析手段解决哲学问题的趋向是相呼应的;随后转换生成语言学也开始关注语义是后来的事情。
第二阶段语用转向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时语用研究异军突起,代表性的理论是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和以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其基础的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普遍语用学”理念;这些理论力图表明,言语的首要功用并不是表明所述之命题内容,而是通过言语行为来做事,即如言语行为理论所言:怎样以言辞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其中主要的“行事”是进行社会交往,以建立人际关系即主体间性的关系。同时,“语用思维的发展与哲学的演进历史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语用思维在哲学研究中的出现满足了解决哲学难题的需求,语用分析方法成为哲学家们可以有效使用的语言分析方法之一;另一方面,哲学家们对语用分析方法的借鉴也内在地促进了语用思维的发展,导致了现代语用学的诞生”(殷杰,2003: 36-39),并且“语用思维构成了‘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盛晓明, 2000: 2)。格莱斯就是在这一阶段提出了会话含义理论。
第三阶段出现在20世纪后期,进入到认知转向阶段;随着认知科学对语言学科的渗透,出现了广义的语言认知研究和以“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即首字母大写命名的语言学研究流派。认知科学发现,人的认知是认知主体的心智、身体、环境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不同情况、不同形式的身心相互作用、身心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认识集中反映为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4E+S”的认知科学: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内嵌认知(embedded cognition)、生成认知 (enacted cognition)、延展认知 (extended cognition) 和情境认知 (situated cognition)(卢找律,2012;李其维,2008: 1315-1321),因此,语言的认知研究尤其关注语言运用者的意识、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他的认知状态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语言研究的认知转向促成了语言学研究许多新的出发点和生长点,例如其中的“基于使用”(usage-based)的理论就是一种新的语言分析理论和新的语言习得理论。会话含义理论在这一阶段也有新的发展趣向。随着语言转向及其内在所包括的语用转向、认知转向的发生,近半个多世纪在语言研究中发生了三种趋向:弱化语义作用、强调语境平台建构和重视主体意向性的辐射。正是这三个趋向引导着我们研究意向解读与含义理论关系的思路和方法。
3.关于“意向解读”
将“意向解读”作为一项认知能力提出来的是从美国移居到德国的发展心理学家(developmental psychologist)托马谢鲁(M. Tomasello)。他所坚持的“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理论认为,从语言习得来说,人自小就具有两种能力:意向解读能力和句型认定(pattern-finding)能力。用“基于使用”的方法来处理语法规则的形成是认知语言学所坚持的一个信念(Langacker, 1987:46,411-412),但将“基于使用”这一理念专门用于语言习得并且做了系统研究的是托马谢鲁及其团队。据托马谢鲁及其研究团队人员的观察,在婴幼儿出生九个月大到十二个月大时这些能力就在同他人交往的意识活动中表露出来了(Tomasello,2000: 61-82; 2003: 3-5)。就意向解读能力而言,不到一岁大的孩子就能在与别人的言语交往中初步感知对方话语表达时所蕴涵的意图。最初这种能力是人作为人这个物种在与同类进行交往时表现出的生物性的适应能力,是一种生物属性,就像人的手天生会拿东西、脚会走路、眼睛会看东西、脑会思考一样,是人类生存的内在基础;在感觉到自己有某种心理状态,并且感觉到对方也表现出这样的心理状态时,就会掌握住这样的心理状态进行合作,从而达到交流的目的。这就是说,最初意向解读能力使婴儿能分享对话者语言运用时的意图,尽管他并不懂得说话人话语的语义内容,但是能按其意图作出反应,能从形式上、语气上、音调上、停顿上、抑扬顿挫等方面的句子形式上对讲话人所使用的话语进行辨识,尤其能从说话时对方的肢体语言和脸部受到情绪的感染而发生的变化,例如你抱着婴儿,你对她笑,她也会高兴地笑、你假装生气骂她她就会哭。心理学家艾克曼(P. Ekman)发现,生气、恐惧、愉悦、惊讶、厌烦、沮丧、不高兴等情绪表达有跨文化的共通性(艾克曼,2008: 12),因而这些情绪表达有人际间的共通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足一岁的婴儿虽然自己还没有语言能力,但已经能从同交际中观察、积累一些前语言交际的经验,初步表现出意向解读的能力。
托马谢鲁及其团队对这项能力的发现和总结的确是关键性的。在语言习得研究中总结并阐发了包括意向解读在内的认知能力是认知语言学语言习得理论对前人语言习得研究的一项突破:它一方面突破了行为主义的单纯的外在行为的“刺激-反应”说的束缚,转而重视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的研究;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乔姆斯基所持的天赋说,天赋说认为语言习得靠的就是人的大脑里语言习得机制(LAD)的普遍语法的生长。托马谢鲁所揭示的意向解读能力的启动和发展,为幼儿语言习得先天基础和后天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在条件。随着婴儿慢慢长大,他们的意向解读和句型认定同其他认知能力一起发展,逐步成为他们日后运用语言的基本策略和手段;这意味着在此时,意向解读能力从内在的基础发展为语言运用的认知能力。随着各方面能力的提高,这种意向解读的能力同语码运用能力结合起来,就发展成为运用会话含义的能力。
意向解读同语言运用特别是含义运用关系十分密切。当年格莱斯进行会话含义理论的研究,对说话人意向的关注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他认为,语言交际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说话人向受话人传递其意向,而受话人则要辨识这一意向(Grice, 1989: 36、86-116、117-137)。后来,“关联理论”提出者斯珀波和威尔逊(D. Sperber& D. Wilson)也认为,语言表达包含一种“明示”(ostention)信息;明示信息是说话人“明确地向听话人表示意向的行为”(Sperber & Wilson, 1986:49 ) ,而语用推理就是听话人根据说话人提供的明示信息推断出说话人的交际意向。由此可知“意向”在语言交际中占据着极端重要的地位。由于意向在语言交际中的地位如此重要,意向解读的能力在语言交际中的表达和理解就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里还要说一说在词源上同“意向”有关系的概念“意向性”。“意向”与“意向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多用于心理学,后者多见于哲学;但二者在语言研究中的关系变得逐渐密切起来,尤其在心智哲学视域下语言研究开展以来,意向性被引入到语言研究中,作为语言主体对意向内容指向的所在,以及指向这样的意向内容时的意向态度这两个维度的概括,它实际体现了语言主体运用一定的意向态度指向这一意向内容进行交际时的广泛的意向、意图、目的。徐盛桓(2013:174-184)发文提到的三个趋向之一的“重视主体意向性的辐射”,即语言主体的意向、意图和目的必定辐射到语言的表达,语言研究应把这方面作为解释语言运作的一个维度。
4.含义理论研究回顾
对于含义研究作学科理论形态的回顾要回到格莱斯,因为语用学讲到“含义”一般都是格莱斯的“会话含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格莱斯在William James Lectures陆续发表了三篇论述自然意义、非自然意义和会话含义理论的论文;1975年,载有会话含义理论“合作原则”的Logic and Conversation 一文在 Cole & Morgan的著作中,发表(以后该文在1989年又收集在格莱斯自己编辑的文集Grice,1989)。之后的三四十年里,会话含义理论及其运用成为语用学乃至语言学学科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受合作原则影响,后继的学者也归结了一些语用原则,包括李琦(G. N. Leech) 的“礼貌原则”、荷恩(L. Horn)的“数量原则”和“关系原则”、列文森(S.Levinson)的“方式原则”以及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关联原则”(Relevance Principle)等。
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各种机制和原则均体现了这一理论的发展。由于学科的进展以及相邻学科和新思潮的影响、研究者研究内容特点和倾向性的影响等,这些新发展的会话含义理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从而造成会话含义理论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再生形态等的演变。但是我们发现,会话含义理论所有形态都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把意向解读看成是一种推理,是同逻辑推理不同的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但没有明确提及“明示”(即语句所用的词语和所说的事物)同含义的逻辑关系;二、凡为推理所建构的理论框架都称为原则或准则;三、这些原则、准则基本上都具有演绎取向;四、所处理话语中提到事物的关系基本上都来自现实世界、必然世界的规则性、必然性的事务,例如格莱斯用康德的质、量、方式、关系四个范畴所建构的合作原则、列文森用常规关系(stereotypical relation)建构起来的信息性原则、荷恩所提出的等级含义(scalar implicature)的推理等都是这样;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关联原则所说的关联,实质是所推导出来的含义同说话人话语所表示的“意向”同语境的关联,而在现实世界的交际,说话的意向所涉及的多是规则性、必然性的事务。
在语言交际中,话语所体现的意向是多方面的,所得到的含义是丰富多彩的,下面举一些例子。
(1) Suppose that A and B are talking about a mutual friend, C, who is now working in a bank. A asks B how C is getting on in his job, and B replies,“Oh quite well I think; he likes his colleagues, and he hasn’t been to prison yet.”At this point, A might well inquire what B was implying, what he was suggesting, or even what he meant by saying that C had not yet been to prison. The answer might be any one of such things as that C is the sort of person likely to yield to the temptation provided by his occupation,that C’s colleagues are really very unpleasant and treacherous people, and so forth. It might, of course, be quite unnecessary for A to make such an inquiry of B,the answer to it being, in the context, clear in advance.It is clear that whatever B implied, suggested, meant in this example, is distinct from what B said, which was simply that C had not been to prison yet. I wish to introduce,as terms of art, the verb“implicate”and the related nouns“implicature”(cf.“implying”) and“implicatum”(cf.“what is implied”). The point of this maneuver is to avoid having, on each occasion,to choose between this or that member of the family of verbs for which“Implicate”is to do general duty.(摘自 Logic and Conversation)
这里的叙述可以改写为对话形式,就像语用学分析含义通常所展现的那样:
A. How is C getting on in his job in the bank?
B. Oh quite well I think; he likes his colleagues,and he hasn’t been to prison yet.
会话含义理论研究的,就是B为什么对A询问C在银行里工作情况时会做那样的回答,这里透露了他的什么意向,可以做怎样的解读。由于这些在上述引文中Grice 已做了简单的说明,这里便不再赘言。在Logic and Conversation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语用学教科书对这样的例子都作了解释,这里也不再赘言,如:
A: Let’s get the kids something.
B: Well, I veto I-C-E-C-R-E-A-M-S.
A: Where does C live?
B: Somewhere in the south of France.
A: What on earth has happened to the roast beef?
B: The dog is looking very happy.
下面例子的表述可能同语用学关于会话含义的研究中通常举出的例子表述不完全一样。
(2)【环球网报道 记者周旭】据英国路透社7月21日消息,联合国安理会21日将对涉及MH17航班的一份决议进行投票表决,……,报道称,路透社所得到的决议文本中使用了“坠落”(downing)一词,而非此前使用的“击落”(shooting down);报道称,“这是对俄国的某种妥协”,因为决议的通过需要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对该飞机如何坠落的说法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向,而从一种说法改换为另一种说法则体现了更改的意向。
(3) 凉夜金街[对街道的美称]天似洗。打叠[整理]银篝[金属的熏笼]熏透吴绫被。作剧消愁何计是?鬓丝扶定相思子[用相思子嵌制成的发卡]。对漾红绳低复起,明月光中乱卷潇湘水[翻动水绿色的裙子]。……(陈维崧,蝶恋花·跳索[跳绳])
这是这首词的上半阕的大意:天气变秋凉了,她们要熏秋被;熏被子时点燃熏笼就要关上房门,人无法待在房间里,所以就要商量到户外“作剧消愁何计是”。这首词告诉我们,她们商量好后紧接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鬓丝扶定相思子”。这是一个信号,但写词的人要卖个关子,只是预告了她们要“作”什么“剧”的大方向,具体做什么还需读者猜一猜。这是写作的一种手法,用这个明示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只有看到词的下半阕才弄明白她们是去跳绳,因为跳绳活动比较激烈,所以要把头发固定。这是设想读者具有一定的意向解读能力而安排的语篇行文,是制造悬念的一种手法。
我们可以把词改写为对话,设A、B已经谈到她们正商量做些什么活动,接下去:
A:那么她们要做什么活动?
B:她们没说,只见她们把头发上的发卡夹紧。
或者:
女孩A:我们等下做什么?
女孩B:你用发卡把头发夹紧了再说。
这样一改写,这些对话就都与会话含义要研究的语言现象相似。
(4) 在我国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问金正日是否已经到了中国,外交部言人回答说,我没有得到授权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之后另一记者问:我的问题与金正日访华有间接关系。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进行经济改革,而只是亲自来看看中国的改革成果,这有什么用处呢?
答:你是想间接地让我证实访问是否正在进行,这是我无法做到的,我没有得到授权向各位提供权威的信息。(news.zj.com/china/detail/.../531272.html.2006-1-17)
这是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的问答实录。发言人如果要在发言中不出现纰漏,就要努力解读提问者的意图。这位记者首先说他的问题与金正日访华只有间接关系,好像他并不关心金正日是否来访,只是想问金正日不在国内改革光参观有什么用。但是,不论回答参观有用或没用,都证明金正日已在中国参观了,这就上当了,因为进行参观就预设了人来到了参观地,这样的回答就等于“不打自招”。所以必须把提问者的意向解读出来才能应对得滴水不漏。
(5)【此前《新闻联播》对“老虎”被查曾有暗示】今年春节前夕,在《新闻联播》播出的领导人看望老同志通稿中,除江泽民、胡锦涛外,并未逐个列出老同志名单,改为:“春节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泽民、胡锦涛等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
而在2012年、2013年的新华社通稿中,均详细列出了领导人看望的老同志名单。通稿显示,去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共看望了76位老同志。其中包括14位退休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贺国强、周永康。
在中共权力传承的政治规则中,“老同志”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虽已不在一线,但仍不时以各种形式亮相各种重要场合。每年春节前夕,现任领导人看望“老同志”已成惯例。而每年一变的老同志名单以及排名情况,亦广受关注。而今年的《新闻联播》将诸多老同志的名单融入一个“等”字,实在意味万千。现在看,几乎可以肯定那时“周老虎”已经入笼,不再适合出现在公开报道中,因此采用如此模糊的提法,避免打草惊蛇。(news.sohu.com, 2014.8.1)
我们在这里用这些例子研究含义,一方面表明,研究主体不满足于停留在格莱斯提出会话含义理论。因为其只是关注交际中的会话含义、说话人含义(speaker’s implicature);这样的不满足当然不是本研究的首创,在过去研究会话含义的文献中用会话含义理论来研究各种修辞格的讨论已不少见,例如研究隐喻、夸张、讽刺、反语等。我们希望能在体裁、题材、含义被利用的方式上捕捉或解读意向的方式方法上有所发展,进而使含义理论有更大的研究空间;另一方面这些例子也表明,我们认为含义出现的话语空间是比较宽阔的,因为“现实世界不仅是自然世界、必然世界,而且也是概率世界、偶然世界(可能世界);现实世界既有规则性、必然性,也有不确定性。”(刘邦凡 王磊,2013: 114)。因此含义理论的研究空间也应该把各种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现象的规则性、必然性、可能性、不确定性、概率性等表现囊括进来。这要求我们要对含义的特点作出新的概括。
5.含义特点的新概括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上文所说的把对方话语的意向解读出来就是做了含义解读的工作,这是符合实际的,例如:话语将诸多“老同志”的名单融入一个“等”字(x),对此中的意向作出解读,得到其含义就是“几乎可以肯定”,“周老虎”已经入笼而不再适合出现在公开报道中(y);又如金正日不采取经济改革只是亲自来看看中国的改革成果,这有什么用处(x),其含义就是想让发言人证实访问是否正在进行(y);再如说女孩子要“鬓丝扶定相思子”(x),其含义就是她们会做比较激烈的活动(y)。这样来看待包含了说话人意向的话语同由此而得到的含义的关系(简称“话语-含义”关系),可以看到:
一、“话语-含义”关系是一种因果蕴涵(causal consequence)关系。
“话语”同“含义”之间现象是因果蕴涵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因果蕴涵关系,即二者的关系既是蕴涵的又是因果的,上面例子的x与y就是既有蕴涵关系又有因果关系。“所谓‘原因’就是产生某一现象并先于某一现象的现象;所谓‘结果’就是原因引发的某一现象,原因作用的后果。原因与结果之间是一种蕴涵关系,但从内涵与意义上看这种蕴涵又不同于传统的‘实质蕴涵’或者‘严格蕴涵’” (刘邦凡 王磊,2013:116);实质蕴涵反映的是由有关涵项真假所建立起来的蕴涵关系:真命题为任意命题所蕴涵,假命题蕴涵任意命题;而严格蕴涵的后件已逻辑地暗含于前件,即前后件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因果蕴涵是“专门刻画因果条件句的蕴涵推理形式”,而“因果蕴涵的蕴涵强度处于严格蕴涵与实质蕴涵之间”(刘邦凡 王磊,2013: 116),即前后件不但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而且这逻辑联系一定是因果关系。含义作为因果蕴涵的结果,它已暗含于话语里,“话语”同“含义”之间作为因果关系,前者用的是事物的本体,后者表现为对前者有关事态的认识。
二、从“话语-含义”关系看,含义是指能从该话语中推演出来的若干能够想象的任何认识,但在它们之间不应包含逻辑矛盾。
在“话语-含义”这一对前后件的“必然的逻辑联系”中,“必然是分等级的”(刘邦凡 王磊, 2013: 116),因此在含义解读中,话语与含义的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是分等级的。含义作为因果蕴涵的结果,它已暗含于话语里,但关于含义受何种因果必然律支配,这不是先验地定下来的,而是有律则的、可能的、偶然的、临时性的、经验直觉的,等等。对可能性的分析可以回顾莱布尼茨 (G. W. Leibniz) 提出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 理论。设A是包含A1、A2、A3、…… 这些它们之间没有逻辑矛盾但具有各种不同规定性、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事物所形成的“世界”,A就是一个可能世界;A1、A2、A3、…… 也可以看成是不同的可能世界。从可能世界看,含义就是从话语里产生的一个可能世界。对“必然”和“可能”的定义是:W是必然的,当且仅当W在一切可能世界是真的;Z是可能的,当且仅当Z至少在一个(或在一些)可能世界是真的。
综合这两个特点,含义的定义如下:
Y是相对于话语X的含义,当且仅当,Y不是X词语的真值,但是从X话语中推演出来一组有因果关系的认识。
6.对含义解读认知过程的刻画
根据含义的这个定义,可以利用徐盛桓参考了美国逻辑学家伯克斯(A.W. Burks)的“因果陈述逻辑”(logic of causal statement)(Burks, 1977)而提出来的“因果蕴涵思维机制”(a causal consequence apparatus of thinking)(徐盛桓 何爱晶,2014)来建构一个“话语-含义因果蕴涵机制”,以刻画含义解读的理性认知过程。伯克斯的因果陈述逻辑以“因果蕴涵”和“因果可能世界”为核心概念,将因果、概率和归纳-演绎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可以针对复杂世界的因果蕴涵的推理系统。这一推理系统是同当代语言解释的意向性解释(intentional explanation)相契合的。当代语言研究对语言解释的心智进路之一是意向性解释,它是把语言活动融入到运用主体的意向性之中,对话语的解释不仅是对其中的语法语义关系的解释,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对主体心智在一定情景下因事物而获得的感受的解释,话语表达要与语言运用主体在该语境下的意图相融合,因此,话语“解释的条件主要是由语境和说话者的兴趣决定的”(Fraassen, 2002: 66)。这样来看待语言运用,它主要涉及三个要素:语言现象;在场的使用者即语言主体;事件及事件所处的环境。这里可以借用科学哲学家基尔(R.N.Giere)提出的一个三元解释的公式(Giere, 2004:743):
主体S用X 表征W[即World —— 引用者注,下同]以达到一定的P[即purpose]
X是语言现象、W是事件及涉事的环境、P是主体的意向性。这三个因素可以进一步归并:一方面事件是客观存在的自在事件,但另一方面事件进入到语言表征又是主体认知的事件,为主体意识所加工,我们这是据此构建出“话语-含义因果蕴涵机制”。
含义的运用其实是以话语所描述的事件为“因”,通过主体在一定的语境(Con[context])下所持的意向性(Int [intentionality])作主导,主体的心智对该事件的认识发生格式塔转换,获得内省意识,或者称为反思意识,就是对这一事件的感受(徐盛桓,2012: 137-144),这就是“果”;这一(些)认识就是含义。刻画含义解读过程的“话语-含义因果蕴涵机制”是这样的:

设话语、含义分别表示为x和y;→表蕴涵,→c表因果蕴涵;□c、◇c分别表因果必然和因果可能,∨表析取。上式读如:在语境和意向性的审视下,话语x因果蕴涵y,这个过程可定义为:或者x可能因果蕴涵y,或者x必然因果蕴含y。这就是对从话语推导含义的认知过程的刻画,是这个过程的逻辑再现。例如:
“鬓丝扶定相思子”即用发卡把头发卡紧(x),是许多女孩子在做比较大的动作如跳舞、运动(y)前必选的动作,外人看到了x,就知道这些女孩子要做y了。在这个意义上说,x因果蕴涵 了y。但是比较大的动作不仅可能是运动和游戏,而且可能是劳动或其他可能的活动。这些都是可能从该话语中推演出来的若干能够想象的认识,而且它们在逻辑上都互不产生矛盾。因此,y作为词中所说的“跳绳”,只是x在此情此景中可能的一个结果,即x→c y =◇c(x→y)。
再如:话语将诸多“老同志”的名单融入一个“等”字(x),对此中的意向作出解读,得到的含义是:几乎可以肯定,“周老虎”已经入笼(y),所以不再适合出现在公开报道中。这个结果怎样推导出来?在过去的报道被看望的有76位老同志,其中包括列出名字的14位退休政治局常委;因此,将诸多“老同志”的名单融入一个“等”字的,只从文字上看,理论上说可以有多种可能性。但是,事实上,情势的发展已经让读者知道了“周老虎”的名字,因为“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经近乎盖棺定论,只是实操中步步为营罢了”(柳叶刀,周永康案后中国要打好“三大战役”,人民日报,2014.8.7);就是在春节后不久的2014年3月2日,全国政协发言人在回复记者问到周永康时说了三个意味深长但又是人人都能听懂的话:“你懂的”。因此,将“周老虎”作为“打虎”的目标,这已成为读者的认知内容、意向性的目标;听(读)到“新闻联播”这条消息就会对名单很敏感。因此,从这样的x得到的y,从总体来说,“必然”会联想到不一一提名字是同议论得沸沸扬扬的“周老虎”有关。这里y的推理认知过程应是必然蕴涵:x→c y =□c (x→y)。
7.结束语
人们对含有意向的话语进行意向解读,即从话语解读出含义,其思路是直觉地通达,通常是瞬间完成的;本研究的目的是解释、模拟、刻画这一直觉通达思路的认知过程。作为对逻辑再现的理性研究,是研究解读的推理过程及推理的有效性;所谓推理的有效性就是要获得在当前的语境下符合交际人意向的保真性判断。
格莱斯包括其后继者的研究,开创了从话语里解读其意向的会话含义理论研究;随着语言转向及其内在包括的语用转向、认知转向的发生,近半个多世纪在语言研究中所发生的语义作用弱化、强调语境和重视主体意向性的辐射的趋向,使含义研究的深化具有更切合人类认知特点的学术资源。伯克斯的“因果陈述逻辑”是逻辑研究资源中的一种;“因果蕴涵对于人类认知具有普遍适用性”(刘邦凡 王磊,2013: 118),我们希望参考因果陈述逻辑构建起来的“话语-含义因果蕴涵机制”能够将因果、概率、归纳-演绎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呈现人们解读含义的理性认知过程。
[1] Burks, W. 1977. Chance, Cause, Reason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Cole, P. & J. Morgan (eds.).1975.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3:Speech Acts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 Giere, N. 2004. How models are used to represent reality [J].Philosophy of Science, (5):742-752.
[4] Fraassen, B. The pragmatics of explanation [A]. Balashov, Y.& Rosenberg A. (eds.) Philosophy of Science [C]. Routledge,2002: 69-70.
[5] Grice, H. 1989.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In P. Grice (ed).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 Hazlett, A., 2007. Grice’s razor [J]. Metaphilosophy, (5):669-690.
[7] Langacke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Vol.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8] Sperber, D. & D. Wilson.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lackwel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9] Tomasello. M., 2000.First steps towards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2):61-82.
[10] Tomasello, M.,2003.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1] 艾克曼.2008.杨旭译.情绪的解剖[M].海口:海南出版社.
[12] 李其维.2008.“认知革命”与“第二代认知科学”刍议[J].心理学报,(12):1306-1327.
[13] 刘邦凡 王磊.2013.科学、哲学与认知融合视域下的因果陈述逻辑[J].哲学研究,(12):114-118.
[14] 卢找律.2012.“认知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系列讲座[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15] 盛晓明.2000.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M].上海:学林出版社.
[16] 徐盛桓.2012.从“事件”到“用例事件”——从意识的涌现看句子表达式雏形的形成[J].河南大学学报,(4):137-144.
[17] 徐盛桓.2013.意向性的认识论意义——从语言运用的视角看[J].外语教学与研究,(2):174-184.
[18] 徐盛桓 何爱晶.2014.转喻隐喻机理新论——心智哲学视域下修辞研究之一[J].外语教学,(1):1-6.
[19] 殷杰.2003.论“语用学转向”及其意义[J].新华文摘,(11):36-39.
A Note Study on Implied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ntion-reading
A noted feature of linguistic exchange is that the speaker will convey his intentions in his discourse, and the hearer will read these intentions; this process is called pragmatic inference. During the pragmatic inference, the intention read from the discourse is just the implied meaning. The present study regards the implied meaning as the meaning other than the meaning of the truth value of the words and sentences in the discourse. Implied meaning is seen as a phenomenon of causal consequence as well as the conceived possible non-contradictory thinking contents deduced from the discourse, and the reading of it can be conducted by the Causal Consequence Apparatus of Discourse-Implied Meaning.
intention-reading; implied meaning; pragmatic inference; Causal Consequence Apparatus of Discourse-implied Meaning
H0
A
2095-4891(2017)04-0056-07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隐喻性话语的具身认知研究”(项目编号:SWU170944)的最终成果。
华鸿燕,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用学
通讯地址:400700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