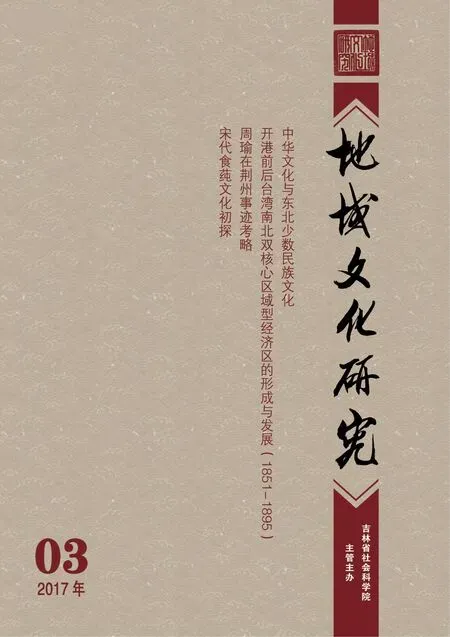高句丽建国史研究(下)
杨 军
高句丽建国史研究(下)
杨 军
朱蒙所部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是父家长制大家庭,但朱蒙所部却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血缘组织。朱蒙所部迁入地的通行的社会组织是“邑落”,即村落或村镇,作为传统血缘组织的部落,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完全退化,因此,不存在超越村落或村镇之上的地方行政组织。迁徙和移民征服造成朱蒙所部和迁入地的深刻社会变革,原有的社会组织被逐渐改造为地方行政组织,在此基础上,王权成长、社会分化加剧,最终导致了高句丽人的建国。
高句丽 建国 地方组织 王权
四、地方组织结构
在朱蒙迁入朝鲜咸兴附近之初,曾试图利用血缘组织,按朱蒙所部移民集团的模式,建立对新征服地区的管理机制,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最终形成了高句丽五部。但很快,面对高句丽人实力的迅速膨胀和对外征服的迅速发展,高句丽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这种模式无法适应高句丽政权迅速发展的需要,因而开始以另一种方式管理新征服的地区,最终逐渐建立起高句丽政权的地方行政组织。
(一)
朱蒙所部出自东夫余。史书对东夫余的地方行政组织没有相关记载。《三国志》卷30《东夷传·夫余》提到,北夫余“国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为奴仆。诸加别主四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①(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夫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1页。。夫余之官明显分为两类:加、使者。“使者”,是“诸加”派往各地管理与其存在隶属关系的“邑落”的亲信,他们因此也被称为“诸加别主”。“使者”是“诸加”的代表,可以看成是“诸加”的属吏。北夫余人的“邑落”应与沃沮人一样,就是指村落、村镇,其中的“豪民”,无疑是指村落、村镇的首领,也是实际的管理者。每个村落、村镇都有自己的管理者“豪民”,但由“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的规模来看,这里的“道”不会指村落、村镇,而是指一个“使者”或“诸加”控制的总户口数,则一个“使者”可能会同时负责若干个村落、村镇,而隶属于一位“大加”的“使者”可能也不止一人。北夫余的统治结构我们可以概括为:诸加(如马加、牛加、猪加、狗加)——使者(也称诸加别主,如大使、大使者、使者)——豪民——下户。东夫余的情况应与此类似。
从高句丽政权的早期发展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体制的影子。《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
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头著帻,如帻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①(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844页。
很明显,高句丽早期官职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三国志》称“诸大加”,可以与夫余人的“诸加”相对应,另一类《三国志》称“小加”,相当于夫余人的“使者”。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都是“大加”的称号,使者、皂衣、先人才是“小加”的称号。两者地位差异明显,在服饰方面也有明显的标志。“加”“使者”这两种称号,高句丽人恐怕都是自夫余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与夫余人的“使者”属于“诸加”任命的代表一样,高句丽人的“小加”,即使者、皂衣、先人,也是诸“大加”“自置”,即自行任命的,只是“名皆达于王”,要报高句丽王备案而已。
关于高句丽“小加”的职能,我们可以找到一例。据《三国志》卷30《东夷传·东沃沮》,高句丽征服沃沮后,“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②(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东沃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6页。显然,高句丽在沃沮人中任命的“使者”是直接隶属于高句丽“大加”的,其职能是管理沃沮人的邑落,这也与夫余人“诸加”和“使者”间的关系以及“使者”的职能是相同的。可证高句丽的“小加”其职能与夫余“使者”类官员类似,也是代表“大加”管理“诸加”属下的各个邑落。
高句丽的“小加”明确分为两类,一类是“诸大加”自行任命的“小加”,即“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另一类是高句丽王亲自任命的“小加”,也就是“王家使者、皂衣、先人”。两者虽然职能相同,但地位差异却相当大。“诸大加”任命的使者、皂衣、先人,其地位相当于中原政权的“卿大夫之家臣”,具有私臣的性质,其身份并不是纯粹的国家政府官员;高句丽王亲自任命的使者、皂衣、先人,负责管理高句丽王直接控制的地区,其身份才是政府官员。所以,“诸大加”任命的使者、皂衣、先人,“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③(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页。
由此看来,高句丽人对于其新征服的邑落,即村落、村镇,或者说自然的居民点,都是尽可能保留其原有的结构,并将其原来的首领任命为本村落、村镇的长官,另派出“小加”直接领导各村落的长官。不过,这些“小加”有的直接隶属于高句丽王,有的则隶属于高句丽五部中的某位“大加”。这反映出,高句丽早期征服的村落、村镇,有的是高句丽王的直属领地,有的则是五部贵族的领地。这从另一侧面证明,王族所在的桂娄部和其他四部是一种联盟的关系,尚未凌驾于其他四部之上;王族作为桂娄部的强宗大姓,与其他四部强宗大姓的区别也还不是十分明显,其特权也不十分突出。
高句丽政权早期统治体制图示如下:

五部体制的存在,使高句丽王对五部的部长及其中的强宗大姓具有支配权,但新征服的邑落却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高句丽王直辖,另一部分则被划为各强宗大姓的私属领地,由其自行任命“小加”进行管理。由高句丽太祖大王在位时,“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遣贯那沛者达贾伐藻那”①[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3页。的记载来看,各部强宗大姓控制的私属邑落,相当一部分是其自己出兵征服的。从这种地方统治体制来看,此时的高句丽政权尚处于早期国家的发展阶段,尚未步入成熟的国家形态。从《三国志》的成书时间来看,这应该是公元1—3世纪的情况,也就是说,高句丽人步入成熟的国家形态是公元3世纪以后的事情。
除了“相加”这个夫余语与汉语合璧的官名以外,见于前引《三国志》记载的官名明显分为汉语官名和非汉语官名两类,而且按顺序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第二组是优台、丞,第三组是使者、皂衣、先人。如果我们认为汉语官名与非汉语官名存在对应关系的话,那么,在第一组中,主簿是与对卢、沛者、古雏加相对应的汉语官名,在第二组中,丞是与优台相对应的汉语官名,而第三组则没有相对应的汉语官名。由此推测,在汉王朝设立高句丽县时,是在高句丽下属的部落首领中任命高句丽县的属官主簿和丞,由于并不是所有的部落首领都能够得到主簿或丞的称号,主簿和丞最初可能是高句丽所属各部落首领引以为荣的一种称号,而后逐渐演变成为对所有部落首领的一种尊称,也就成为部落首领的别名了。由于部落首领在高句丽早期的官制体系中都属于“大加”,所以主簿和丞也就成为高句丽“大加”的称号。使者、皂衣、先人因为是邑落首领的称号,而邑落首领是不可能被任命为高句丽县的属官的,所以这一组高句丽官称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汉语官名。
随着高句丽王权的加强,高句丽王越来越多地利用“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达于王”的传统,过问甚至是干涉“诸大加”私人领地上的使者、皂衣、先人等官员的任免,使这些私臣逐渐向政府官员转化。当最终高句丽王能够左右这些官员的任免,并从中提拔中央官时,这些官员也就由原来的私臣彻底转变为纯粹的国家政府官员,高句丽政权也就步入成熟的国家形态了。
(二)
公元30年,大武神王在位时,“买沟谷人尚须与其弟尉须及堂弟于刀等来投”,②[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7页。这里虽然出现了“买沟谷”,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是地方行政组织的名字,而不是自然地理名词。因此,最早见于史籍的高句丽地方官称是“栅城守”。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公元98年有“栅城守”,公元107年有“东海谷守”,③[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3页。公元296年有“新城太守”,④[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烽上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4页。证明高句丽人在1世纪以后派往新占领地区的地方官,是模仿汉王朝地方官名称称“太守”的,也省称为“守”。见于记载的高句丽太守共6处:新城太守、栅城太守、东海谷太守、海谷太守、南海(谷)太守、鸭渌谷太守。①杨军:《高句丽地方官制研究》,《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6期。这是高句丽最早出现的地方官。2世纪中叶至3世纪末,是其新兴的地方官制与传统的加—使者地方统治结构并存的时期,早期可能部落制传统发挥主导作用,但不晚于3世纪下半叶,新的地方统治体制已占居主导地位。
栅城通常认为在今吉林珲春,②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6页。韩国学者余昊奎把海谷首府敦城比定在朝鲜咸镜道的东海岸一带,③[韩]余昊奎著,李慧竹译:《三世纪后期—四世纪前期高句丽的交通道与地方统治组织——以南道和北道为中心》,《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2000年第1期。如果我们认为,东海谷与南海谷都是因海谷而得名,则东海谷应在敦城以东或东北,南海谷应在敦城以南或西南,上述四个行政单位都在高句丽人旧居地以东至海的范围内,由北向南依次为栅城、东海谷、海谷、南海谷。鸭渌谷在鸭绿江中游,新城位于今抚顺高尔山山城,所辖应是高句丽向西开拓的领土。上述六太守辖区散布在高句丽新拓领土的各处,如果考虑到其间还有采用传统的加—使者模式统治的地区,估计见于文献记载的这6个太守辖区就是此时期高句丽全部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了。
《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烽上王》记载,高奴子由新城宰升任新城太守,虽然这里的新城不是同一个地方,但可以证明,太守的下一级地方行政组织的负责人是“宰”。与此条史料基本同时,在卷17《美川王本纪》中还出现了鸭渌宰。作为新城宰的高奴子曾“领五百骑迎王”,证明宰有统兵权;鸭渌宰曾经审断美川王所涉案件,证明宰有司法权。宰作为地方二级行政组织的负责人,不仅有行政权,还有司法权、军权,权力是相当大的。其上级主管官员太守的职能应该与此类似。可证太守—宰是军政合一的地方长官。
《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美川王》记载,美川王流落民间时曾在鸭绿“江东”的思收村被人告发,审理此案的是鸭渌宰,说明城宰下辖村。村中的案件要由城宰来审理,证明村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不存在正式政府官员。同书卷16《山上王本纪》记载,在208年山上王曾微服出行、夜至酒桶村,酒桶村距国都很近,应属于五部辖区,证明沿用传统的加—使者统治结构的地区,基层行政单位已经与太守—宰辖区没有区别了,说明3世纪初开始,传统的部落体制也在向太守—宰这种新机制转化。只是限于资料,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
新旧体制的对照关系如下图:
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最基层的组织邑落或者村落、村镇的变化不大。最重要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原来其私属领地类似国中之国的五部强宗大姓的势力受到削弱,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一级行政建置是太守的辖区,而太守是直接听命于高句丽王的,这无疑是高句丽王权上升的结果。其二,原来负责管理各村落的“小加”现在为“城宰”所取代。一些由原来的大型村落发展来的城,成为“宰”固定的办公地点,“宰”也有了自己的机构与属吏,城周围的其他村落现在成为城的下属组织,同样接受“宰”的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城宰隶属于太守,这样就构成了太守辖区—城两级地方行政建置。完善成熟的地方管理体制的出现,意味着高句丽政权步入了成熟的国家形态。
自2世纪开始,高句丽逐渐形成谷(城)—城—村的地方行政体制,谷(城)的长官是太守,城的长官是宰,村则不存在正式的政府官员。但280年安国君达贾征肃慎后,“迁六百余家于扶余南乌川,降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①[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西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3页。仍在用部落制方式管理新征服地区,“国相”作为传统的加—使者统治体系的代表直存在到300年,②[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新大王》记载,公元166年,高句丽改左右辅为国相。见于《三国史记》的最后一位国相是公元300年废烽上王立美川王的仓助利。都可以证明,公元166年—300年是新旧体制的过渡时期,两种体制并存,但应该是新的地方统治体制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概言之,高句丽步入成熟国家,是公元3世纪末的事情。《三国志》约成书于公元285年,因此,《三国志》所载高句丽官制是2世纪中期至3世纪末期的情况,正是高句丽新旧体制的过渡时期。
高句丽地方管理体制的变革,其重要环节是对五部强宗大姓特权的剥夺,因此必然引发五部贵族的不满情绪,也许《三国史记》记载发生于公元190年的四椽那之乱,③[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2页。我们对其原因应该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五、王权的成长
高句丽地方统治体制由原来的“大加”—家臣体制,向新的谷(太守)—城(宰)—村体制转化,其关键环节在于削弱五部贵族的势力,而这显然是以高句丽王权的上升为前提的。因此,在高句丽向成熟国家演进的过程中,王权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一)
尽管在朱蒙神话中,北夫余的统治者被认为是“天帝子”“天帝太子”“天帝之子”,④《旧三国史》:“阿兰弗劝王移都,号东夫余。于旧都,解慕漱为天帝子来都。”“汉神雀三年壬戌岁,天帝遣太子降游扶余王古都,号解慕漱。”这个被称为天帝子或天帝太子的解慕漱显然就是北夫余的统治者,而《好太王碑》则称朱蒙“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朱蒙自称“天帝之孙”“天孙”,⑤据《旧三国史》,朱蒙曾对松让说:“寡人天帝之孙,西国之王也。”“松让以王累称天孙,内自怀疑。”似乎北夫余早已确立起“皇”权,但这些内容恐怕皆出自后世编造神话者的想象,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北夫余固然早已存在所谓的“王”,但《三国志》卷30《东夷传·夫余》记载:“旧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于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⑥(晋)陈寿:《三国志》30《东夷传·夫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2页。所谓“旧夫余俗”,说明这不是三国时期夫余人的情况。但由此推测,朱蒙所部自东夫余迁出时,恐怕夫余人的王尚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国王所应拥有的权力。三国时期,夫余“诸加”还拥有较大的权力,“尉仇台死,简位居立。无适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诸加共立麻余”。由此推测,说早期的夫余“诸加”可能曾经对夫余王权构成比较大的制约,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黜大臣仇都、逸苟、焚求等三人为庶人………欲杀之,以东明旧臣,不忍致极法,黜退而已。使南部使者邹壳素代为部长。”①[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7页。高句丽大武神王能够将三位不法的沸流部长黜为庶人,并任命南部使者邹壳素代为部长,可见高句丽王权相对于“旧夫余俗”时代的上升。
高句丽政权成立之初,王权也并不稳固,像夫余王一样,高句丽王的权力也受到“诸加”的制约。《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称沸流部的三部长:“资贪鄙,夺人妻妾牛马财物,恣其所欲”,②[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7页。可见部长对所部拥有行政管辖权;太祖大王“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遣贯那沛者达贾伐藻那”,③[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3页。桓那(顺奴部)、贯那(灌奴部)都拥有自己的部队,可以独立出兵,证明五部的部长拥有兵权;“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④(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4页。证明各部长有司法权。而且,下至东汉三国时期,五部的部长们对本部仍有比较大的控制权,涓奴加甚至能够率领本部民3万余人自行脱离高句丽降附中原王朝,并迁居沸流水流域;类似的例子还有蚕支落大加戴升,率领万余部民降附汉王朝。高句丽五部的强宗大姓,在各自的领地内拥有行政、军事、司法方面的全权,部民对部长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部长们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可以独立出兵对外征战。以此为后盾,五部的部长们对高句丽王权构成比较大的制约。
更为重要的是,在高句丽早期的政治体制中,形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诸加会议”制度⑤关于“诸加会议”,国外学者已经进行过比较充分的研究。参见[韩]琴京淑《高句丽初期的中央政治结构——以诸加会议和国相制为中心》,载《韩国高句丽史研究论文集》,首尔: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2006年。,为五部的大加们提供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机会。《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⑥(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4页。所谓“诸加评议”,自然是“诸加”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这条史料反映出,高句丽的司法权完全掌握在“诸加会议”手中。但是,都由什么人参加“诸加会议”,除司法之外“诸加会议”还拥有哪些权力,中国史书皆语焉不详。
《三国志》卷28《毌丘俭传》:
句骊沛者名得来,数谏宫,宫不从其言。得来叹曰:“立见此地将生蓬蒿。”遂不食而死,举国贤之。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⑦(晋)陈寿:《三国志》卷28《毌丘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62页。
《三国史记》卷17《东川王本纪》:
初,其臣得来见王侵叛中国,数谏王,不从。得来叹曰:“立见此地将生蓬蒿。”遂不食而死。毌丘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⑧[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东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0页。
学者们多数认为,高句丽的“诸加会议”也就是“群臣会议”,其成员就是《三国史记》中提到的“群臣”。对照上述两条史料可以发现,《三国史记·东川王本纪》的相关记载取材于《三国志·毌丘俭传》,在《三国志》中被称为沛者的“得来”,在《三国史记》中被称为“其臣得来”,由此可证,沛者以及与沛者身份类似的人,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被笼统地称为“臣”,就是这些人组成了高句丽早期的“诸加会议”或者说“群臣会议”。沛者为五部“大加”,据《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与沛者同属“大加”的还有相加、对卢、古雏加、主簿、优台、丞,其中主簿很可能是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等高句丽语官名的汉语称谓,丞很可能是优台的汉语称谓,因此,高句丽“诸加会议”或“群臣会议”的成员,就是高句丽五部的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优台等。“诸加会议”或“群臣会议”,其性质是大加们的议事会,这是高句丽早期的最高决策层。
既然参加“诸加会议”的诸位大加,在《三国史记》的记载中也被笼统地记载为“臣”或“群臣”,我们就首先将《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烽上王及其以前的记事中有关“群臣”的记载罗列如下:①下限之所以定在烽上王时期,是为了与《三国志》成书的年代大体相当,即截止于公元3世纪末。高句丽的五部官与中央官都经历着变化,我们无法断定在《三国志》成书的时代以后,《三国史记》中所载的“臣”是否还与五部的部长存在一定的联系,也就是不能断定其后的“群臣会议”的性质是否还是“诸加会议”,因此在我们下面的讨论中,不涉及《三国史记》美川王以后纪事中的“群臣”。
⑴王谓群臣曰:“鲜卑恃险,不我和亲,利则出抄,不利则入守,为国之患。若有人能折此者,我将重赏之。”(卷13《琉璃明王本纪》)
⑵扶余王带素使来……(琉璃明王)乃与群臣谋。(卷13《琉璃明王本纪》)
⑶扶余王带素遣使送赤乌,一头二身……(大武神)王与群臣议。(卷14《大武神王本纪》)
⑷王既至国,乃会群臣饮至。(卷14《大武神王本纪》)
⑸汉辽东太守将兵来伐。王会群臣,问战守之计。(卷14《大武神王本纪》)
⑹王薨。王后及群臣重违遗命,乃葬于石窟,号为闵中王。(卷14《闵中王纪》)
⑺及至栅城,与群臣宴饮,赐栅城守吏物段有差。(卷15《太祖大王本纪》)
⑻汉以大兵向我,王问君臣战守孰便。(卷16《新大王本纪》)
⑼群臣请立太子。(卷16《新大王本纪》)
⑽朝臣国戚谓(乙巴)素以新间旧,疾之。(卷16《故国川王本纪》)
⑾王以无子,祷于山川。是月十五夜,梦天谓曰:“吾令汝少后生男,勿忧。”王觉语群臣曰:“梦天语我谆谆如此,而无少后奈何?”(卷16《故国川王本纪》)
⑿延优从之,王后执手入宫。至翌日质明,矫先王命,令群臣立延优为王。(卷16《山上王本纪》)
⒀太后于氏薨。太后临终遗言曰:“妾失行,将何面目见国壤于地下?若群臣不忍挤于沟壑,则请葬我于山上王陵之侧。”(卷17《东川王本纪》)
⒁肃慎来侵,屠害边民。王谓群臣曰:“寡人以眇末之躯,谬袭邦基,德不能绥,威不能震,致此邻敌猾我疆域。思得谋臣猛将,以折遐冲,咨尔群公,各举奇谋异略,才堪将帅者。”群臣曰:“王弟达买勇而有智略,堪为大将。”王于是遣达买往伐之。(卷17《西川王本纪》)
⒂王谓群臣曰:“慕容氏兵马精强,屡犯我疆场,为之奈何!”(卷17《烽上王本纪》)
⒃王增营宫室,颇极侈丽,民饥且困,群臣骤谏,不从。(卷17《烽上王本纪》)
⒄助利知王之不悛,且畏及害,退与群臣同谋废之,迎乙弗为王。(卷17《烽上王本纪》)
从其讨论的内容看,史料⑴⑵⑶⑸⑻⒂讨论的是对外关系与对外战争;史料⒁既讨论到对外战争,也讨论到重要人事任免;史料⑽属于人事任免方面的事情,主要是群臣反对任命乙巴素为国相;史料⑹⒀讨论的是高句丽王与王后的丧事与葬礼,也就是国家最重要的礼仪性问题;史料⑷⑺是高句丽王与“诸加”举行仪式性宴会的例子,如果从礼仪的角度着眼,也可以与史料⑹⒀视为一类;史料⑺可以证明,在高句丽王出外巡视时,“群臣”也就是“诸加”是随行的,当然,从现有的史料中还看不出随行的是参加“诸加会议”的全体成员,以便在途中也可以召集“诸加会议”,还是仅仅有部分“诸加会议”的成员随行,但是,这种随行体现“诸加”对高句丽国内的行政事务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则是没有疑义的;史料⑼⑿⒄讨论的是王位的继承;史料⑾虽然讨论的是高句丽王有关得子的梦兆,但当时故国川王无子,直接影响到高句丽王位的继承问题,所以,此条史料应与史料⑼视为同类,讨论的都是与王位继承有关的问题;史料⒃反映的是在内政方面“诸加”对王的劝谏,从卷17《烽上王本纪》的记载来看,在“诸加”劝谏不被采纳之后,是国相仓助利的直言极谏,在烽上王对仓助利表示“冀无复言”之后,仓助利与群臣“同谋”废烽上王、立美川王,说明对“诸加”的劝谏,王是必须给予足够重视的,这是“诸加”在高句丽内政方面拥有发言权的重要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史料⒃应与史料⑺视为同类。
根据上面17条史料,我们可以将“诸加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及所占比例列表如下:

王位继承4 21%讨论内容次数所占比例对外关系7 37%人事任免2 10.5%国家礼仪4 21%内政2 10.5%
高句丽“诸加会议”讨论得最多的是对外关系与对外战争方面的事情,其次是有关王位的继承问题和一些关乎国体的礼仪性问题,人事的任免以及对高句丽王治国政策方面的干涉是比较少的。此外,《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头著帻,如帻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其国东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国中大会,迎隧神还于国东上祭之。”①(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4页。十月举行两次高句丽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一次是祭东明,一次是祭隧神。大加、小加都参与东明祭与隧神祭,且在祭祀活动中身着特殊的服饰,说明他们在高句丽的两次重大祭祀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由此看来,此“公会”虽然不是“诸加会议”,但反映出高句丽的诸加在祭祀方面也就是宗教领域是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的。《三国志》称涓奴部“亦得立宗庙,祠灵星、社稷”,反映的也是涓奴加作为大加在宗教领域的特殊权力,这从另一侧面证明,诸大加在宗教领域都拥有一定的权力。
《三国史记》的记载可以证明,“诸加会议”在外交与对外战争、王位继承和人事任免、关乎国体的礼仪问题等方面拥有一定的权力,也可以对高句丽王所实行的具体政策施加影响;《三国志》的记载可以证明,“诸加会议”还具有相当强的司法职能和祭祀职能。结合两种记载来看,“诸加会议”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在三个方面:外交、司法、祭祀与礼仪,其对高句丽内政的影响远不及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大,并且主要体现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其干涉高句丽王具体政策以及人事任免的例子是不多的。
前引的史料⑴⑵⑶⑸⑾⒁⒂都可以证明,“诸加会议”的召集人应该是高句丽王,认为“诸加会议”是以高句丽的国相为“议长”的观点,①[韩]琴京淑:《高句丽初期的中央政治结构——以诸加会议和国相制为中心》,载《韩国高句丽史研究论文集》,首尔:韩国高句丽研究财团,2006年,第155页。也有的韩国学者认为,左右辅、国相在群臣会议上是作为群臣的头目在活动的,从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来看,左右辅、国相的发言受到重视,但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拥有群臣头目的地位。参见[韩]李钟旭《高句丽初期的中央政府组织》,《东方学志》33,1982年。恐怕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们认为,“诸加会议”是高句丽早期国家中央机构尚不健全的时代存在的由高句丽王召集五部大加举行的议事会,也发挥着司法机构、外交机构和祭祀机构的作用,这是高句丽由酋邦时代向早期国家演进的过程中,构建其中央机构与中央官制过程中的过渡性机制。②韩国学者李钟旭称“诸加会议”为“群臣会议”,他对其性质的界定是:“一个由王主宰,以群臣构成的政策审议决策机构”。参见[韩]李钟旭《高句丽初期的中央政府组织》,《东方学志》33,1982年。正是由于“诸加会议”的存在,才使五部大加也具有中央官的身份,高句丽因此构建起最初的中央政府组织,形成最早的中央官制系统。但是,随着高句丽中央机构与中央官制的成熟健全,“诸加会议”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高句丽后期的群臣议事,已经是封建国家的中央官和中央政府机构各部门间就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其性质与早期的“诸加会议”是截然不同的,对《三国史记》后期记载的“群臣”我们不能作与早期“诸加会议”相同的理解。
(二)
在故国原王以前,高句丽的王位继承还不存在明确的世袭制度。虽然王位的继承者都是朱蒙的子孙,但五部的大加及“国人”在决定王位的继承者上还有相当大的选择权,通过这种方式对王权构成制约。
从《三国史记》卷23《百济本纪·始祖温祚王》的记载中可以发现,朱蒙与琉璃明王之间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父死子继,但在联盟内部反对的势力也很强,最终导致反对势力脱离联盟自行发展。据《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琉璃明王三十二年(13)十一月,曾派王子无恤率兵抵御夫余人的进攻,大获全胜,第二年正月,无恤就被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大武神王。可见,琉璃明王和大武神王之所以能实现父死子继,并不是父死子继已成为高句丽人的继承制度,而是琉璃明王有意地安排大武神王建功立业,使其得到国人的拥戴。总之,自朱蒙起,《三国史记》所载高句丽的前三王都是父死子继,但并不能证明高句丽人已经确立父死子继的王位继承制度。
大武神王去世后,“太子幼少,不克即政”,“国人推戴”其弟闵中王即位。③[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闵中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9页。但《三国史记》记载,大武神王生母松氏于琉璃明王二年(前18)秋七月被琉璃明王纳为妃,次年冬十月去世,则大武神王肯定生于琉璃明王三年(前17),④[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称其“琉璃王在位三十三年甲戌,立为太子,时年十一岁”,立为太子的时间与同书卷13《琉璃明王本纪》的记载相同。但依大武神王生于琉璃明王三年计算,至琉璃明王三十三年(14),大武神王应为31岁。正因如此,才能如《琉璃明王本纪》所说,可以“委以军国之事”。因此,上述《大武神王本纪》所载“时年十一岁”,当为“时年三十一岁”,《三国史记》原文脱“三”字。按《三国史记》推算,享年为61岁。说其死时“太子幼少”,似乎不可能。大武神王十五年(32),其元妃恐其庶子好童夺嫡,进谗导致好童自杀,此后立解忧为太子。好童已是成年人,此时解忧的年龄也不会太小。从此至大武神王去世又经过12年,解忧应为成年人了。解忧即位“立王子翊为王太子”①[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慕本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0页。,解忧已有儿子,也证明大武神王去世时解忧并不“幼少,不克即政”,这只是国人不肯拥戴他的借口而已。由此看来,当时决定王位更替的是国人的拥戴,只不过要从朱蒙的子孙特别是前王之子中选择而已。
解忧死于国人的行刺。其后,《三国史记》所载太祖大王、次大王、新大王这三王的世次明显有误,②刘子敏:《高句丽新大王伯固考》,《延边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朴灿奎:《高句丽太祖王宫考》,《东疆学刊》2000年第4期;《高句丽之新大王和故国川王考》,《东疆学刊》2001年第1期。对于是否存在山上王延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议,③杨通方:《高句丽不存在山上王延优其人——论朝鲜〈三国史记〉有关高句丽君主世系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3期;朴真奭:《关于高句丽存在山上王与否的问题——与杨通方同志商榷》,《世界历史》1989年第2期。皆反映出这一时期高句丽王位继承仍旧处于无序状态。故国川王是“伯固薨,国人以长子拔奇不肖”,立其为王。对此《三国史记》与《三国志》的记载是相同的。《三国志》称“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按《三国志》所载户口数推算,拔奇与涓奴加所率当是沸流部与多勿部的全部人口了,可见在此次王位更迭中,五部中的两部支持拔奇,另三部支持伊夷模。支持拔奇的两个部,沸流部是王族所在的部,涓奴部是前王部,这个支持力度是不小的。伊夷模“更作新国”,正是为了避开旧都中支持拔奇的力量。西川王得立为太子是因为“国人爱敬之”④[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西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2页。,此后的烽上王、美川王之间的继承,是由于仓助利的废立。我们可以说,直至第十六代故国原王以后,高句丽才出现比较规律的王位承袭。
在上述记载中,对高句丽王位继承发挥重要影响的“国人”究竟指哪些人呢?
《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国人有气力,习战斗,沃沮、东秽皆属焉”⑤(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4页。,证明未被编入高句丽王部而仅由高句丽的大加负责向其征收贡赋的沃沮、秽人,都不属于高句丽的“国人”。由此看来,所谓“国人”,指的是五部的部民。在高句丽早期国家时期,五部的部民对其部长还存在着比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拔奇时代因继承问题而导致的分裂事件中,涓奴部所有部民都追随部长涓奴加投降公孙康并迁居沸流水流域,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上述记载中对高句丽王位继承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人”,与其说是五部的部民,不如说是名义上代表五部部民即“国人”的大加们更为恰当。与前面我们提到的“诸加会议”对高句丽王位继承问题的讨论相结合,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此时期,五部的大加以及主要由五部大加组成的“诸加会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左右高句丽的王位继承。
(三)
在朱蒙所部迁徙之初,其最高首领的身边就已经聚集起一批亲信,成为高句丽政治生活中一股新生的力量,也是一个新生成的利益集团,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高句丽王的“亲信集团”。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前三位王的本纪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史料:
A.朱蒙行至毛屯谷,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乃告于众曰:“我方承景命,欲启元基,而适遇此三贤,岂非天赐乎?”遂揆其能,各任以事。与之俱至卒本川。(卷13《始祖东明圣王本纪》)
B.十九年秋八月,郊豕逸,王使托利、斯卑追之,至长屋泽中得之,以刀断其脚筋。王闻之,怒曰:“祭天之牲岂可伤也?”遂投二人坑中,杀之。九月,王疾病,巫曰:“托利、斯卑为祟。”王使谢之,即愈。(卷13《琉璃明王本纪》)
C.二十一年春三月,郊豕逸,王命掌牲薛支逐之,至国内尉那岩得之,拘于国内人家养之。返见王曰:“臣逐豕至国内尉那岩,见其山水深险,地宜五谷,又多麋鹿鱼鳖之产。王若移都,则不唯民利之无穷,又可免兵革之患也。”夏四月,王田于尉中林。秋八月,地震。九月,王如国内观地势,还至沙勿泽,见一丈夫,坐泽上石,谓王曰:“愿为王臣。”王喜许之,因赐名沙勿,姓位氏。(卷13《琉璃明王本纪》)
D.二十四年秋九月,王田于箕山之野,得异人,两腋有羽,登之朝,赐姓羽氏,俾尚王女。(卷13《琉璃明王本纪》)
E.四年冬十二月,王出师伐扶余,次沸流水上,望见水涯,若有女人舁鼎游戏。就见之,只有鼎,使之炊,不待火自热。因得作食,饱一军。忽有一壮夫曰:“是鼎,吾家物也,我妹失之,王今得之,请负以从。”遂赐姓负鼎氏……上道有一人,身长九尺许,面白而目有光。拜王曰:“臣是北溟人怪由,窃闻大王北伐扶余,臣请从行,取扶余王头。”王悦,许之。又有人曰:“臣赤谷人麻卢,请以长矛为导。”王又许之。
五年春二月,王进军于扶余国南……怪由拔剑号吼击之,万军披靡,不能支。直进,执扶余王,斩头。(卷14《大武神王本纪》)
F.十三年秋七月,买沟谷人尚须与其弟尉须及堂弟于刀等来投。(卷14《大武神王本纪》)
上述史料表明,高句丽王的亲信集团的成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亲信集团成员是其原来所属部族中的平民,原本没有任何权力。在他们投靠高句丽王之后,才在高句丽王所在的部族中拥有一定的权力与地位,并进而在五部所构成的联盟中拥有一定的权力与地位。第二,亲信集团的成员没有自己的领地,也没有拥护自己的部民,他们的权力与地位完全依赖于高句丽王,因此,高句丽王可以对他们随意进行任免、处罚乃至处死。第三,亲信集团成员的权力来自于高句丽王,早期其权力主要表现在军事与祭祀方面。第四,亲信集团成员在五部联盟中的地位虽然远比不上五部的部长们,但他们对高句丽王最终决策的影响力却是不容低估的。史料C证明,高句丽王最终做出迁都这一重大决定,显然是接受了亲信集团成员薛支的建议。大辅陕父曾说过“王新移都邑,民不安堵”,①[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0页。可见,在迁都问题上,作为曾随朱蒙迁徙的部长,陕父存在不同意见,但在此问题上,五部部长的意见显然没有被琉璃明王所采纳。陕父后来因劝谏而被免官,并在一气之下“去之南韩”,离开高句丽自行发展,当与此也有一定关系。
亲信集团是王权的附属物,是王权成长的获益者,他们绝不会成为制约王权的力量,因而,在高句丽王与五部部长的权力争夺中,高句丽王很自然地要利用亲信集团去排挤五部的部长们,这也使得亲信集团越来越成为支持王权的最重要力量。
随着高句丽对外征服战争的展开,高句丽王逐渐派遣亲信集团成员管理新征服的地区。由于他们没有依附于自己的部民,他们很难将新征服的地区演变为自己的私属领地,高句丽王仍旧有能力控制对他们的任免。因此,他们的身份逐渐演变为国家形态中的地方官员,这无疑推动了高句丽王权的进一步发展。大片新征服地区成为高句丽王的直属领地,完全改变了高句丽王与五部贵族的力量对比,五部的部长们所控制的地域与人力在整个王国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使五部的部长们不再具有制约高句丽王权的实力。因而,五部部长自身连同其所属的家臣,其身份也逐渐转化为国家形态中的地方官员,而不再是前国家形态下的血亲组织的首领。
由于高句丽王是五部联盟的最高军事首领,是征服行动的实际运作者,效忠于高句丽王的亲信集团又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被征服部族更多的是被划归高句丽王直接管辖。高句丽王直辖领地的迅速膨胀,使高句丽王通过占有被征服部族的贡赋而拥了巨额财富。琉璃明王十一年(前19),扶芬奴因战功被“赐黄金三十斤,良马一十匹”;琉璃明王三十七年(18),沸流部人祭须因找到王子的尸体,受赐“金十斤,田十顷”。①[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2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此为基础,高句丽王可以维持一个规模日趋扩大的亲信集团,而这又有利于高句丽王直辖领地的进一步扩大。因此,高句丽王成为对外征服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南迁之初,朱蒙家族的权力主要来自于五部中王室所在的沸流部,其所能得到的经济利益也局限于在沸流部的公共积累中其所能支配的份额。对五部联盟来说,虽然联盟的最高首领世代由朱蒙家族成员担任,但联盟最高首领的权利仅仅局限在组织战争与祭祀,并不能从中得到比较大的经济利益。因此王族的地位并不突出,沸流部与其他四部的实力与地位相差无几。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展开,情况出现了变化。朱蒙家族利用对高句丽王位的控制,掌握了大部分新征服地区,王族逐渐具有了凌驾五部之上的势力。在此基础上,王权也开始逐渐膨胀。
从现有史料分析,高句丽王权的膨胀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首先,高句丽王拥有了罢免有罪部长的权力。最早的例子应该是大武神王十五年(32)对仇都、逸苟、焚求等三位沸流部部长的罢免。虽然在此前,琉璃明王二十二年(3),有将大辅陕父罢职的记载,但“罢陕父职,俾司官园”,说明免去的是陕父的“大辅”身份,改任其他工作,而不是免去其部长的职位。而且,面对此决定,“陕父愤,去之南韩”,率所部出走了。可见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对部长的罢免。而仇都等三人是被黜为“庶人”,而且他们没有力量反抗大武神王的决定,只能留在沸流部内,改过自新,“不复为恶”。但在这一事件中,大武神王不是从沸流部的平民中提拔起新的部长,而是“使南部使者邹壳素代为部长”,②[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大武神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7页。说明高句丽王虽然已有权力罢免有罪的部长,但还不能把自己中意的人提拔到部长的位置上。但是,对有罪部长的罢免,是高句丽王权扩张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此前,五部的部长作为血亲组织的首领,其权力、地位都是高句丽王所无法左右的,他们依据本部血亲组织的支持,成为对高句丽王权的制衡力量。高句丽王一旦拥有了罢免部长的权力,不论理由是什么,都打破了王权与部长权力之间的平衡,部长的权力不再是王权的制衡而是受王权左右,这就为王权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
其次,高句丽王拥有了任命新部长的权力。据《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次大王》,次大王“以桓那于台菸支留为左辅,加爵为大主簿。冬十月,沸流那阳神为中畏大夫,加爵为于台,皆王之故旧”。①[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次大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7页。太祖大王在位时,阳神是“沸流那皂衣”,即皂衣先人,此次升职唯一的原因是“王之故旧”,可见高句丽王已经能够根据个人的喜恶提高五部部长的职位。至故国川王平定椽那部部长发动的叛乱以后,晏留推荐“力田自给”的乙巴素,“加爵为于台”,②[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2页。更是将平民任命为部长的例子。至此,高句丽王拥有了自由任免五部部长的绝对权力,五部部长的身份不再是血亲组织的首领,而是隶属于高句丽王的官员了。新任的部长们固然不必再拥有某一血亲组织的认可与支持,他们的地位与权力皆来自于王的任命,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管理相应血亲组织的权力,其具体工作完全听命于王,成为王权的附属。乙巴素被任命为部长后,并不负责任何部的管理,而是辅政。在这一点上,五部的部长开始与亲信集团的成员具有相同的地位,二者都演变为国家形态下受王权任免的官员。发展到这一步,部长的职权就不再是王权的制衡力量,而是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王权的新支柱。乙巴素当政的主要方针是“明政教,慎赏罚”③[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3页。,就是明显的例子。高句丽王拥有了对五部部长的任免权,同时,也就能对五部的部长进行任意的惩罚。最明显的例子是,故国川王时,椽那部的于畀留、左可虑掌权,“其子弟并恃势骄侈,掠人子女,夺人田宅,国人怨愤。王闻之怒,欲诛之”,④[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2页。导致左可虑等利用椽那部的力量发动叛乱。而在大武神王时,犯有同样罪行的沸流部三部长仇都、逸苟、焚求的处分却仅仅是免为庶人。从中也可以看出,高句丽王对五部部长的控制力在增强。如果从陕父罢职事件算起,到乙巴素的任命为止,这一演变过程差不多用了300年的时间。⑤《三国史记》系陕父罢职事于琉璃明王二十二年(3),系起用乙巴素于故国川王十三年(191)。但《三国史记》的王系与积年有误,如按朱蒙立国于公元前126年的估算向下推算,陕父罢职事应在公元前86年左右,而191年应为故国川王元年,故国川王十三年为203年,上距公元前86年达289年。
第三,在拥有对部长的任免权以后,高句丽王自然也就拥有了对原五部部长的家臣的任免权。《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记载:“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⑥(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页。管理诸大加领地的家臣,原本是诸大加自行任免的,而现在,却“名皆达于王”,其任免已经在高句丽王的控制之下了。高句丽王任命的使者、皂衣先人也好,诸大加任命的使者、皂衣先人也好,其身份都是特定领地的管理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的身份与地位应该是一样的,但上述史料明确指出王的使者、皂衣先人地位高于诸大加的使者、皂衣先人,这显然是诸大加即部长们地位下降的结果。《三国志》所载上述史料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但不可能晚于《三国志》的成书,因此,认为高句丽王在公元3世纪已拥有对五部部长的家臣们的任免权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变化改变了高句丽地方管理模式上的双轨制局面,使各地完全纳入城、谷的统治体系之内。在地方管理体系中,完全是以地缘的方式组织人民,完全剔除了血缘组织的残迹。
第四,在将各部长及其家臣降为自己的属官之后,高句丽王集行政、司法、经济、军事、祭祀等大权于一身,真正成为集权的君主,这已是公元4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在高句丽王由高句丽王向集权君主演进的过程中,其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是,并不是所有处于前国家形态中的部族对邻近部族的征服都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这是因为:其一,高句丽人所征服的地区大多以前曾隶属于汉王朝,在此之前已经存在过郡县制,当地部族的血缘组织已经被改造为地方行政单位。无论是当地部族的上层还是普通的部族成员,都已经习惯于郡县制的管理模式。这使高句丽王不必花费过大的代价就能够对新征服地区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定数量的贡赋。其二,高句丽王既是五部联盟的最高军事首领,也是沸流部的首领,由于有沸流部的支持,使其很容易突破其他四部对其权力的制约。这种格局的形成是因为在五部联盟形成的过程中沸流部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联盟中处于核心部族的地位,因此,五部联盟的最高军事首领只能自沸流部中产生。其三,效忠于高句丽王个人的亲信集团的存在,才得以将新征服地区对王权的支持由可能变成现实。在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的前提下,血亲组织的复合体之间的征服战争,才能促使其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演进。
在高句丽王权扩展的四个阶段中,第二阶段代表着一种转折。高句丽王可以根据个人意志任命五部的部长,也就是血亲组织复合体的首领,不仅改变了血亲组织的首领由组成该血亲组织的各家族选举产生的传统,而且使得血亲组织的首领与血亲组织的成员之间不必一定具有血缘关系,这是对血亲组织的最大改造。虽然血亲组织的外壳仍然存在,但由于其首领已不再是依赖血缘关系获得权利并通过血缘关系对血亲组织进行管理,而是依靠来自血亲组织之外的任命获得权力,并依赖这种血亲组织之外的力量进行统治,因此,血亲组织的首领已经演变为国家形态下的地方行政官员,而血亲组织也就演变为国家的地方基层行政单位了。
因此,我们认为,公元2世纪末,高句丽已经进入成熟国家的发展阶段。①马彦也认为,高句丽至2世纪末始进入真正的国家形态,而高句丽的王权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本质性变化。参见马彦《二至三世纪时期的高句丽王权》,《东北史地》2009年第3期。但是,其政府组织形式的健全和成熟,则要迟至4世纪才最终完成。
六、社会的分化
在高句丽地方行政组织渐趋成熟、王权逐渐上升的过程中,高句丽政权内部也出现了深刻的社会分化。最初以朱蒙所部为核心的征服者集团,以及相对于征服者集团以“他者”身份作为映像存在的被征服者集团,在征服结束之后,都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开始分化,重新整合为新的社会阶层。移民集团中的父家长制大家庭瓦解,小家庭成为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细胞。伴随着官制的完善、公共权力的生成、税收体制的健全,高句丽政权最终真正地进入成熟的国家形态。
(一)
在朱蒙所部进行对外征服之初,高句丽社会可以分为三个阶层:1.作为征服者集团的五部的成员,其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国人”。2.各个被征服的邑落,或被征服部族的血亲组织的成员,其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下户”。①朴灿奎认为,高句丽“下户”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被征服地区的“下户”,即被征服地区的隶属民;二是高句丽五部内的“下户”,即高句丽社会的基本生产者。见朴灿奎:《高句丽之“下户”性质考》,《东疆学刊》2003年第3期。笔者认为,高句丽社会的基本生产者即是史书中所说的高句丽“国人”,所谓“下户”,不存在不同的分类,都是指被征服地区的隶属民。赵展的观点与此相同。见赵展:《试论高句丽的社会制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对于“下户”的性质,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是种族奴隶;也有的认为是农民,见姜孟山:《论高句丽国家的社会性质》,《朝鲜中世纪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20页。赵展认为是农奴;朴灿奎认为具有双重身份,即是本部族氏族共同体的成员,也是高句丽的隶属民。笔者认为,此时无论是高句丽还是被其征服的“下户”,都未步入成熟的国家形态,“下户”是指被高句丽部落联盟征服的其他部族。3.奴隶。不论是“国人”还是“下户”,在其父家长制大家庭中已包括非自由人。但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见于中国史书的高句丽“下户”就是高句丽人中的奴隶,这是不正确的,高句丽人的奴隶称奴婢,不称下户,如《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②(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4页。在朱蒙所部迁入的地区,奴隶也称“生口”,如《三国志》卷30《东夷·秽传》:“其邑落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③(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秽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9页。
最初,作为征服者集团的五部成员可能是很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其生活资料主要靠被征服者集团提供,也就是“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④(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页。高句丽人向沃沮人征收的租税就包括“貊布、鱼、盐、海中食物,千里担负致之”。⑤(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东沃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6页。五部成员的最主要任务是当兵作战,从事征服战争,所以才养成“国人有气力,习战斗”⑥(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4页。的民风。这种社会结构是高句丽早期对外征服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高句丽早期之所以确立如此的社会构成,主要是为其频繁的对外战争和征服服务的。最初的“国人”与“下户”的关系并不是阶级关系,而是征服者集团与被征服者集团的关系,其社会地位的差异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间的差异,而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差异。无论是“国人”的内部还是“下户”的内部,其成员都存在着基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社会身份。
限于资料,我们现在还弄不清楚高句丽人在朝鲜咸兴附近时的情况,但可以肯定,在高句丽人被迁往今中国辽宁桓仁附近之后,其内部就开始出现了分化。随着高句丽政权征服速度的放慢,也随着其政权统治的稳固,其内部的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
浑江流域的居民,很早就已经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汉四郡的设立,无疑对该地区的农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通过近年来对通化、柳河、辉南、海龙诸县的文物普查,一般来说在好多所谓的原始文化遗址里,均散见汉代的铁制生产工具。说明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在两汉时代已传入到这个地区。”⑦李殿福:《东北亚研究——东北考古研究(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当早期的对外征服结束后,五部中的普通成员就在新征服的地域定居下来,并迅速转化为自食其力的农业生产者。最典型的例子是乙巴素。他是琉璃明王的大臣乙素的后代,①《三国史记》卷16《故国川王本纪》与卷45《乙巴素传》都称其为“琉璃王大臣乙素之孙”,但故国川王在位时间为180年-197年,琉璃明王在位时间为前19年-18年,二者相距过远,因此,乙素与乙巴素不可能是祖孙关系,此处的“孙”只能理解为是其后代。出身于高句丽五部贵族家庭,但至故国川王在位时期,其已住在“西鸭渌谷左勿村”,“力田自给”,②[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45《乙巴素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38页。成为一名普通的农民了。由此分析,五部的普通成员的这一转化过程当出现得更早,也进行得更为彻底。征服者集团发生分化的结果是,其普通成员开始大量转变为自耕农,其中也包括少部分像乙巴素那样的五部贵族的后裔,“国人”逐渐成为高句丽政权统治下的平民的称呼;征服者集团的上层发展为高句丽政权的统治阶层和贵族阶层,这就是《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所载“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③(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页。《冉牟墓志》反映出,无论是冉牟家族还是依附于其家族的牟头娄家族,都是随朱蒙南迁以来就一直保持着特权地位,他们就是《三国志》中所说的“国中大家”。
被征服者集团同样也经历着分化,其上层开始进入高句丽统治阶层。如沃沮人在被高句丽征服之后,“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④(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东沃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4页。担任高句丽“使者”的沃沮人首领,虽然其身份最初属于“下户”,但在《三国志》所载高句丽官名中,“使者”列在“小加”之首,有资格参加高句丽人的重大活动,即参加“公会”,显然不能将之列入高句丽人“遇之如奴仆”的那些“下户”之列。
总之,征服者集团和被征服者集团内部分化的结果是,“国人”中的普通成员社会地位下降,其身份与“下户”中的普通成员越来越接近,他们共同构成高句丽的平民阶层,“国人”一词也就具有了新的内涵,指高句丽政权统治中心区内的平民。但“下户”中的上层,其地位是逐渐上升的,最终与“国人”中的上层一起,构成高句丽政权的统治者阶层,即“国中大家”。由于“下户”和“国人”一样,多数转化为平民,因此,“下户”一词也逐渐用来代指平民,成为“国人”的同义词。在伊夷模继位后,“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这里的“下户”一词就是指高句丽政权统治中心区的平民。
但对于新征服的地区来说,“国人”还是用来指作为征服者的高句丽人,当然包括高句丽平民在内,而“下户”则指新被征服的民族。《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国人有气力,习战斗,沃沮、东秽皆属焉。”⑤(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4页。此时被高句丽征服不久的沃沮人、秽貊人显然还都不包含在高句丽“国人”的范围内,无疑是仍旧将之称为“下户”的。而相对于沃沮人、秽貊人而言的“国人”,显然是包括所有沃沮、秽貊之外的高句丽政权统治下的民众。早期被高句丽征服的地区,现在已经成为高句丽政权统治的中心区,早期征服的“下户”,现在已经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反映出高句丽政权内部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反映出作为征服者的移民集团与被征服者土著居民之间的民族融合过程。
此后,高句丽政权内部主要存在三个社会阶层。其一,贵族阶层,也就是《三国志》所说的“国中大家”。其二,平民阶层,也称“国人”“下户”。对于新征服的部族仍然统称为“下户”,但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处于分化中的集团,其上层将进入贵族阶层,其普通成员会加入平民阶层。在三国时期仍被统称为“下户”的沃沮人、秽貊人最终在历史上消失,融入高句丽人之中,就可以证明作为被征服者集团的“下户”的这种分化过程的存在。其三,奴隶阶层,也称“奴婢”“生口”。没有证据表明,这个阶层是高句丽社会生产的主力,说高句丽是奴隶制政权是没有道理的。①关于高句丽的社会性质,中国学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五种说法:其一,奴隶制社会;其二,半奴隶半封建制社会;其三,前期是奴隶制社会,后期是封建制社会;其四,封建制社会;其五,先是奴隶制,接着是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最后进入封建制。而分歧的核心正在于高句丽是否曾存在奴隶制的问题。参见何海波《国内高句丽社会性质研究综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在高句丽政权内部征服者集团和被征服者集团间的界线逐渐消失,形成新的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之后,以征服者集团控制被征服者集团的原有统治模式就无法维持下去了,这既是高句丽政权向成熟国家演进的动力之一,也是最初的征服者集团五部的性质发生变化,五部贵族走向衰落、王权逐渐上升的原因之一。
(二)
《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聚,相就歌戏。”②(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3页。证明其社会的最基本单位还是邑落,也就是村落、村镇。
《三国志》提到高句丽人的特殊婚俗:
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傍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妇归家。③(晋)陈寿:《三国志》卷30《东夷传·高句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4页。
“婿屋”是女家生活起居的“大屋”后面的一处“小屋”,由女家成员的生活起居都在“大屋”来看,高句丽人此时已不再流行父家长制大家庭,而是以核心家庭为其主要的家庭类型。“其俗节食,好治宫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也反映出同样的居住模式。此外,高句丽人“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受牵连的仅仅是“妻子”,也反映出高句丽人的家庭结构已经是以核心家族为主要类型了。说高句丽人“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证明粮食存储也是以小家庭为单位,反映出宗族组织的衰落,已不存在宗族或大家庭的公有财产。
《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
王畋于质阳。路见坐而哭者,问何以哭为?对曰:“臣贫穷,常以佣力养母。今岁不登,无所佣作,不能得升斗之食,是以哭耳。”……给衣食以存抚之,仍命内外所司,愽问鳏寡孤独、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救恤之。④[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3页。
故国川王所遇到的这个人,“常以佣力养母”,因为“无所佣作,不能得升斗之食”而哭,证明其母没有其他人奉养,其家庭结构显然属于小家庭。其“无所佣作”的原因是“今岁不登”,说明其工作性质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应是为地主耕种土地的长工,或者是在农忙季节受雇于劳动力不足之家的短工。若是后一种情况,恰也可以证明,当时农村的主要家庭类型已是小家庭。
美川王在继位前流落民间,《三国史记》记载其经历:
与东村人再牟贩盐。乘舟抵鸭渌,将盐下寄江东思收村人家。其家老妪请盐,许之斗许,再
请,不与。其妪恨恚,潜以屦置之盐中。乙弗不知,负而上道,妪追索之,诬以廋屦,告鸭渌宰。宰
以屦直取盐与妪,决笞放之。①[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美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6页。
从其老妪亲自与美川王打交道,诬陷美川王偷鞋时亲自去“追索”,又去见鸭渌宰告状来看,其家人口比较简单,显然也是小家庭。
其中,前引《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故国川王》的记载系于公元194年,证明至晚在公元2世纪末,高句丽平民阶层已经以小家庭为主要的家庭类型了。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原来由父家长制大家庭承担的灾年救助工作,现在不得不由政府来承担。前引史料中称故国川王“命内外所司,愽问鳏寡孤独、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救恤之”,就是此变化的具体反映。
从《三国史记》的记载来看,高句丽王对灾民的救济最早可以上溯至闵中王在位期间。闵中王二年(45)“夏五月,国东大水,民饥,发仓赈给”②[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闵中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9页。。因为“大水”而导致“民饥”,证明救济的主要对象是农民,也就是高句丽政权下的平民。慕本王二年(49)“夏四月,陨霜雨雹。秋八月,发使赈恤国内饥民”③[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4《高句丽本纪·慕本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0页。。反映的是同样的问题。如果这些记载年代可靠的话,证明自公元1世纪起,在灾年对受灾平民进行赈济,就已经成为高句丽政权的一项新职能,这无疑也会对高句丽政权向成熟国家演进起到促进作用。
由于高句丽政权的职能日趋复杂,仅由原有的贵族家庭中选择官员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至太祖大王六十六年(118)“八月,命所司举贤良、孝顺,问鳏寡孤独及老不能自存者,给衣食”④[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4页。。高句丽王开始借鉴汉王朝举孝廉的人才选拔方法,命相关机构推举“贤良、孝顺”,其目的显然是充实官员队伍。推举的对象应该并不局限于贵族,也包括平民在内,因此,这种推举的进一步发展,才出现了故国川王时乙巴素因受到推举,由平民最终升任国相的例子。耐人寻味的是,在上述史料中,命相关机构推举“贤良、孝顺”的命令,与命相关机构“问鳏寡孤独及老不能自存者,给衣食”的命令是在同一个月颁布的。
(三)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在太祖大王以下的记事中,还经常出现“有司”“所司”的称谓,我们可以将相关史料排比如下:
太祖大王六十六年(118):八月,命所司举贤良、孝顺,问鳏寡孤独及老不能自存者,给衣食。(卷15《太祖大王本纪》)
故国川王十六年(194):仍命内外所司,愽问鳏寡孤独、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救恤之。命有司,每年自春三月至秋七月,出官谷,以百姓家口多少,赈贷有差,至冬十月还纳,以为恒式。(卷16《故国川王本纪》)
山上王元年(198):命有司奉迎发歧之丧,以王礼葬于裴岭。(卷16《山上王本纪》)这些史料中出现的“有司”“所司”,显然已经是隶属于高句丽王的中央机构,只是史料中对这些“有司”的具体名称没有留下记载而已。上述史料可以证明,至公元2世纪末,高句丽政府各部门已经比较健全,并且存在相对明确的分工。这无疑可以视为其步入成熟国家的标志。随着政府部门的健全以及其职能和分工的明晰,原本由高句丽五部贵族掌控的一些权力,逐渐转由政府相关部门来执掌。
见于《三国史记》的最早的分工明确的官职是“掌牲”,但此官名仅见于《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琉璃明王二十一年(2)春三月,“郊豕逸。王命掌牲薛支逐之”①[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3《高句丽本纪·琉璃明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9页。。此记载是颇值得怀疑的。首先,琉璃明王时代朱蒙所部进入浑江流域不久,尚未形成自己的国家体制,又已经接受了汉高句丽县的统治,其是否存在郊天制度很值得怀疑。即使我们从《三国志》的记载出发,认为高句丽遵从汉王朝的县国之制,祭祀灵星与社稷,②姜维东:《高句丽的灵星祭祀》,《北方民族》2001年第2期。所谓“郊豕”就是用于这些祭礼的祭牲,但此时高句丽县才仅仅建立了20年左右,这种源自中原的制度是否得到贯彻,高句丽人是否已经形成专门饲养祭牲的制度并任命专门的官员管理,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其次,见于《三国史记》的“郊豕逸”事件共有3次,上述为第二次。第一次奉命追赶的是托利、斯卑,《三国史记》中没有出现他们的官衔;第三次见于卷16《山上王本纪》中,时间远晚于前两次,仅称“掌者追之”,也没有出现相应的官名。因此,见于琉璃明王时代的掌牲,也许我们理解为“掌管祭牲者”,即“掌者”,是更为准确的。概言之,这恐怕还不是一种官名。
《三国史记》所载有明确执掌的高句丽新的中央官官名主要有两个:中畏大夫、知内外兵马事。中畏大夫从字面上来看像是出自汉语的官名,但是中国历代王朝都不存在中畏大夫这一官职。中畏大夫见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记载共有3例:
沸流那阳神为中畏大夫,加爵为于台。(卷15《次大王本纪》)
中畏大夫沛者于畀留、评者左可虑皆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卷16《故国川王本纪》)
(乙巴素)拜中畏大夫,加爵为于台……巴素意虽许国,谓所受职不足以济事……王知其意,乃除为国相,令知政事。(卷16《故国川王本纪》)
最早担任中畏大夫的是沸流部的阳神,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其身份是沸流部的皂衣。另外两位曾任中畏大夫的官员,一位出自椽那部的沛者,一位虽然出身平民,但在被任命为中畏大夫的同时“加爵为于台”,联系阳神也在被任命为中畏大夫的同时“加爵为于台”来看,中畏大夫一职按惯例也是由五部的部长即大加出任的,所以,凡是任中畏大夫一职时身份不是大加的,至少要授予其大加中身份较低的于台的称号。
椽那部的沛者于畀留虽然身为中畏大夫,但是《三国史记》明确记载,他因为是“王后亲戚”才得以“执国权柄”。乙巴素在被任命为中畏大夫以后,还觉得“所受职不足以济事”,并由此升任国相。这两个事例都可以证明,中畏大夫是高句丽早期中央官制中地位低于国相的行政官员,在正常情况下,中畏大夫不是执政官,于畀留身为中畏大夫却能够“执国权柄”属于特例。
“知内外兵马事”一职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仅出现两次,一次出现在卷17《中川王本纪》:“王命相明临于漱兼知内外兵马事”,①[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中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1页。另一次见同卷《西川王本纪》:“拜达买为安国君,知内外兵马事,兼统梁貊、肃慎诸部落。”②[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7《高句丽本纪·西川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3页。卷16《新大王本纪》记载:“拜答夫为国相,加爵为沛者,令知内外兵马,兼领梁貊部落。”③[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新大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0页。这条史料虽然没有明确出现“知内外兵马事”这一官名,但从行文中可以明显看出,明临答夫是以国相兼知内外兵马事,与后来同样出身于椽那部明临家族的明临于漱是一样的。从官名上分析,知内外兵马事应是高句丽早期官制中的最高军事长官。
知内外兵马事一职最早见于新大王即位之初,第一位任此职的官员是椽那部的明临答夫。明临答夫弑次大王、立新大王,控制朝政之后,所加封的头衔主要是三个:国相、知内外兵马事、沛者。沛者显然是指其出身部的椽那部的沛者,这意味着他成为其所在的椽那部的最高首领。兼任国相和知内外兵马事,意味着他既是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军事长官。
高句丽对军政权力进行区分的做法最早始见于公元2世纪上半叶。《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记载:“王以遂成统军国事”“以沛者穆度娄为左辅,高福章为右辅,令与遂成参政事。”④[高丽]金富轼著,杨军校勘:《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4页。这是明确规定,身为左右辅的穆度娄和高福章没有军事方面的权力。尽管此时对军政权力的区分还是不彻底的,但此变化毕竟导致高句丽最高领导层军政权力结构的变化,在高句丽王之下的不再是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王储或者左右辅,而是两套人马: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是王储遂成;掌握最高行政权的是一个“三人委员会”,包括遂成和左辅穆度娄、右辅高福章。《三国史记》将“遂成统军国事”系于公元121年,按中国史书的记载,遂成更可能是在这一年继位成为高句丽王的。但此条史料至少可以证明,在公元2世纪的上半叶,高句丽中央机构中已经初步地实现了军政职能的分开。
后来出任知内外兵马事一职的两人,明临于漱是以国相兼任,成为与明临答夫一样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权臣;达买是以王弟的身份出任,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从前掌握最高军事权的王储,错误地以为达买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储君的身份,这是达买后来受到猜忌被杀的原因之一。由此看来,知内外兵马事作为中央最高军事长官,由何人出任始终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史书称高句丽“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可能高句丽政府官员间已经初步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⑤中国学者通常就是运用《三国志》的上述记载来论述高句丽的“官位等级制度”。参见高福顺《高句丽中央官位的等级制度》,《史学集刊》2006年第4期;《〈高丽记〉所记高句丽中央官位研究》,《北方文物》2008年第4期。日本学者武田幸田也是自此出发来论述高句丽的“官位制”。参见[日]武田幸男《高句麗官位制の史的展開》,武田幸男:《高句麗史と東アジア——“広開土王碑”研究序說》,东京:岩波書店,1989年,第356-405頁。官员队伍机构健全、分工明晰、职能清楚、等级分明,这无疑是成熟国家的特征,因此,上述各方面的变化,无疑都可以视为高句丽向成熟国家演进的标志。
结 语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的后半期,一个以夫余人为主导的,包括夫余人、秽人、貊人的血缘组织的武装移民集团,在朱蒙的领导下,由东夫余南迁,进入今朝鲜咸镜南道的咸兴一带,在当地土著东沃沮和秽貊两个族群的交接地带驻扎下来。这个武装移民集团的人数并不十分庞大,最乐观的估计也不会超过2000户、万余人,但是,利用汉王朝刚刚撤销苍海郡,当地处于混乱状态的有利形势,朱蒙所部迅速征服一些相邻的部族或村落、村镇,成为在当地颇具影响力的一支政治力量。
在朱蒙所部中,血缘组织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最基本的社会单元还是父家长制大家庭,这使朱蒙所部具有比较强的内聚力,但是,朱蒙所部却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一个血缘组织了。朱蒙所部迁入的朝鲜咸兴一带,其社会发展水平可能比朱蒙所部及其所来自的东夫余都要稍稍先进一些,当地最通行的社会组织是“邑落”,也就是村落或村镇。作为传统血缘组织的部落,在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完全退化,不存在超越村落或村镇之上的地方行政组织。但是,早在朱蒙所部迁入以前,咸兴一带的村落、村镇已经呈现出发展的不均衡性,处于分化之中,已经出现较大型的村落,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一些实力较弱的村落不得不依附于实力较强的大型村落。然而,由于这一地区先后隶属于卫氏朝鲜和汉王朝,外来政治势力对当地村落的分化及其内部隶属关系的形成起到阻碍作用,使该地区政治组织形式演进异常缓慢。
朱蒙所部将主动归附的、同样也是以夫余人为主导的部族,改编为两个与自身结构相同的部,这就出现了早期高句丽五部中的三个:涓奴部、桂娄部和绝奴部。高句丽人新征服的村落,分别隶属于高句丽人的三部。由于在新征服的地区里拥有自己的私人领地,高句丽三部中的显要家族拥有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像高句丽王一样,任命使者、皂衣、先人等名号的家臣,去管理自己的私人领地,其领地上的人民对其具有较为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其领地内,这些强宗大族拥有行政、司法等各方面的权力,甚至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可以在接到高句丽王的指令时,去开拓新的征服地。高句丽王的特权还不十分明显,应该说,他更像是这些高句丽显贵中的首席,而不像是统治他们的君主。
在进入浑江流域以后,高句丽人仍旧按照其从前的模式从事对周边部族和村落的征服。在这里,高句丽人新编组两部,顺奴部和桓奴部,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高句丽人统治新征服地区的方式最初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被征服的部族纳入高句丽的五部体制之内,另一种是保持其原有社会组织,甚至是保留其原来的首领,使其隶属高句丽五部中的某一位显贵。但很快,高句丽人就不再将新征服者纳入五部体制了。
高句丽王无疑是高句丽对外征服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新征服的地区虽然也有一些被划为高句丽权贵的私人领地,但更多地却是直接隶属于高句丽王的。在对外征服中,高句丽王的身边逐渐凝聚起一个亲信集团,他们都是各部落的平民,无权无势,要通过对高句丽王的效忠来为自己求得权势和利益。由于亲信集团的成员在各自的部落中没有权势,高句丽王对他们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的荣辱完全取决于高句丽王,因而这些人成为高句丽王权的支柱。
高句丽早期王权的发展并不充分,包括王权以及王位的继承,都受到五部贵族组成的“诸加会议”或“群臣会议”的制约。随着对外征服的展开,王室势力急剧膨胀,高句丽王权也在迅速上升。高句丽王不仅能够对不法的五部贵族进行罚处,更为重要的是,高句丽王还借用贵族任命家臣需要报国王备案的传统,过问甚至是干涉五部贵族对家臣的任免。当管理五部贵族领地的家臣与管理高句丽王直属领地的使者、皂衣、先人,全都统一由高句丽王任命时,其身份也就由贵族的私臣,转化为高句丽政权的地方行政官员了。
社会最基本的单元依然是村落,但村落的管理者的身份却出现变化。在此,村落发展的不均衡性起到一定的作用,大型村落逐渐成为使者、皂衣、先人等高句丽地方行政官员的办公地点,并发展为“城”,这些地方行政长官的新头衔就是“城宰”,由他们负责管理某城及其周边村落,“城宰”的辖区成为高句丽政权的初级地方行政建置。为了加强对这些“城宰”辖区的管理,在其上又设置了太守,太守的辖区被称为“谷”,这就是高句丽政权最早的高级地方行政建置了。无论是“城宰”还是太守,都由高句丽王直接任命,其身份都已经是高句丽政权的地方官员,而不再是某贵族的家臣。
在此过程中,高句丽社会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最初的征服者集团与被征服者集团之间的界线逐渐消失,两者内部都在进行着分化,由于经济社会地位的接近,征服者集团与被征服者集团的上层,逐渐结合构成高句丽政权的贵族阶层,而征服者集团与被征服者集团的下层,也逐渐结合成为高句丽政权的平民阶层。奴隶阶层虽然是一直存在的,但并不构成高句丽社会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高句丽政权内人数最多的阶层应该是平民阶层。征服者集团中的下层普通成员开始转变为自耕农,散居于各村落之中,使高句丽五部的血缘组织彻底瓦解,这也是五部贵族衰落、无法与上升中的王权相对抗的原因之一。随着血缘组织的瓦解,父家长制大家庭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小家庭,特别是核心家族。由此引发高句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如,原本由父家长制大家庭承担的灾年救助工作,现在不得不由王国承担。
五部贵族衰落的过程,就是王权壮大的过程。当所有的权力都向中央、向高句丽王集中时,隶属于高句丽王的官员队伍就变得越来越庞大。为更好地行使这些权力,以从前高句丽王的亲信集团为核心,逐渐形成高句丽政权的中央官僚系统,政府的各部门开始相对健全,分工也开始逐渐明晰,高句丽王也开始采用荐举“贤良、孝顺”的方式,自平民中选拔人才来充实官员队伍。
显然,牢固的王权,健全的中央官僚系统,隶属关系明确的地方统治体制,是成熟国家的标志。当朱蒙所部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迁入今朝鲜咸兴一带的时候,这一切都还不具备,就是在《三国史记》宣称高句丽建国的公元前37年,高句丽政权也并不具备上述特征,因此,认为高句丽国家形成于公元前37年或更早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结合中朝两国的史书记载来看,高句丽政权呈现出上述成熟国家的特征,不早于故国川王在位期间,也就是公元2世纪末。因此我们认为,高句丽国家的形成不早于公元2世纪末,其政治体制的成熟与完善,则可能迟至4世纪。
K232
A
2096-434X(2017)03-098-22
杨军,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东北地方史、中外关系史、易经;吉林,长春,130012。
(续完)
责任编辑:刘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