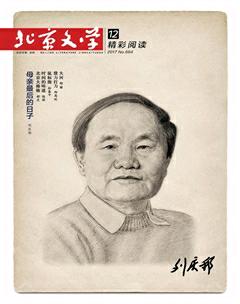逝者如斯(散文)
万华伟
爷爷走了,那是个肃杀的秋日。风乍起,满地零落的枯叶,在寂寂的黄昏里,蝴蝶一般飞舞。
爷爷离去的前夜,我就有心灵感应。夜里,我辗转难眠,恍惚之中,好像有人在低声地唤我乳名。我惊诧莫名,一时间,怅然若失。挨到天亮,就接到了爷爷离世的噩耗。
我泪落如雨,不敢相信,那个曾经如山一般的身影,突然间就坍塌了!急急赶回家中,我长跪在爷爷面前,紧紧攥着爷爷的手。这是一双写满了沧桑的手,枯槁苍白,青筋凸起,像无声蜷伏在手背的蚯蚓。曾经,这双抱我在怀的手,那么粗大有力;这双摩挲我头顶的手,那么慈爱温厚……这双无私地给予我爱与温暖的手,此刻却僵硬冰凉,这异样的感觉让我心痛如锥。二十多年来,我不曾这样紧紧相握爷爷的手,羞愧难当,是我疏忽了陪伴我的童年,给予了我无限关爱的我的血脉相连的亲人!
秋雨沥沥,老屋前的台阶湿漉漉的,雾气弥漫上来,漫过门前高大的槐树,漫过老旧的门槛,漫过挂在泥墙上低头颔首的蓑笠,一点一点渗透到我的心里。
爷爷是个古旧的人,喜欢穿长衫,制作的蓑衣也略长,和他那件长夹袄正相配。在我小小的心里,穿上蓑衣的样子,威风凛凛,确有侠士风范。蓑衣两只宽大的蝴蝶袖张开着,像鸟的翅膀,斗笠恰又平添一份神秘。遇上下雨的日子,爷爷总是急急忙忙穿蓑戴笠,房前屋后,来回地遮盖来不及抢进来的东西:刚收的麦子啦,散着芳香的草垛啦,爸爸的自行车啦……我在屋里翘首以待,侠士的身影快如闪电,只听见塑料布呼啦啦响,爷爷的脚步声从这头响到那头。终于,侠士卸下了他的铠甲,挂在墙上,雨水顺着衣摆往下滴,地上一会儿就一大片濡湿。我巴巴地守在旁边,心里升腾起小小的愿望:要是能拥有一件这样的铠甲,到雨中冲锋陷阵,该多神气呀!爷爷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等天放晴,就把屋后棕树上长着的褐色棕衣,一块块剥下来,又一块一块铺在门板上。我跟着爷爷亦步亦趋,生怕漏掉一个细节。爷爷粗大的手却十分灵巧,先把细麻线穿进针眼,再一行行地纳,前襟、后块、宽大的蝴蝶袖。这样的衣服不用扣子,爷爷搓了麻绳相系。我像得了宝物,一上身,人就胖了许多,像一只小刺猬,逗得爷爷开怀大笑。
深秋时,树叶落了一地,爷爷更加忙碌了。为了补贴家用,每天,他挑着两个箩筐走村串户地收废品,一个箩筐里装着牙膏皮、破凉鞋等杂物,一个筐子里装着一个大玻璃瓶,里面是菱形的姜糖。一杆自制的小秤,只有筷子般长短,却精致实用。秤的每颗星子都是用铜丝镶进去的,小巧而亮闪闪的秤盘是纯铜的,小小的秤砣用一根细细的麻绳穿着。你不用怀疑秤的准度,爷爷经过反复比较核对,和家里那杆供村里人称粮称豆的大秤一般精准。爷爷熬制的姜糖很香,村里大人小孩都喜欢。
一阵秋雨一阵寒,晚秋的风有些刮脸了。连续多日地走乡串村,爷爷的脸糙得扎手。每天,我守在门口,直到暮色四合,爷爷才挑着担,步履蹒跚地回来。两个筐子里的废品倒出来,满院子都是。爷爷把玻璃瓶里剩下的几颗姜糖赏给我,我用舌头细细地舔着,香香甜甜的滋味,让我觉得那个秋天格外醉人。爷爷坐在门槛上,心满意足地看着我,悠悠吐一口烟,烟雾就一圈圈漫过爷爷头顶,飘向远方。
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日子,潮气大了,屋里连桌椅都要长霉。院墙上的牵牛花开始疯长,迅速爬满墙壁,让这个季节有着最后的妖娆。这时爷爷就在家自制烟叶,一把铡刀架在旁边,爷爷把晒干的大烟叶片切得细细的,再用一个大布袋收好,吊在床侧。爷爷有一根铜烟锅,烟锅经常在门槛上敲打,锅口都变得坑坑洼洼了。爷爷把烟丝装进烟锅里,按得紧实,点燃一根火柴,猛抽几口,那火星就晕开了,呛人的烟味直往屋里窜。接着,奶奶的咳嗽就一声紧似一声。
水乡的夜晚,总是那样潮湿和闷热。爷爷拎上一桶水泼在地上压压暑气,再把竹床搬到院里,点燃蚊香。一缕异香,四处弥散,躁动的夜便安宁下来。爷爷轻拂竹扇,丝丝凉意随着树影摇曳。我躺在竹床上,望着那繁星点点的夜空,看月亮一点点地移动。
我问:“爷爷,月亮上面怎么有影子啊?”
“那是一棵桂花树。”
“树下好像有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叫吴刚,在砍桂花树。”
“桂花树会倒怎么办?”
“不会的。那是神树,今天砍一点,明天就還原了。”
星空慢慢变得邈远,桂花树模糊了,我在香甜的梦里分明见到了那个叫吴刚的神仙。
爷爷有一湾稻田,大约三亩地。站在高处远眺,就像弯弯的月亮。这田地,是爷爷最柔软的希望,也是爷爷最钟情的寄托。
插秧时节,奶奶牵着我走在窄窄的田埂上,给地里劳作的爷爷送饭。田埂边的野花开得不管不顾,蜂儿蝶儿上下蹁跹,我喜欢蹑手蹑脚地走近,轻轻抓住蝴蝶的两只翅膀,快速地放进玻璃瓶里。这样淘气的把戏,常常会受到爷爷警告,让我别糟蹋小生灵。说完,爷爷在秧田旁的水沟里洗净手,摸摸我的小脑瓜,再拿起筷,端起碗,有滋有味地吃起来。暖风微醺,他的大手摩挲我头顶的时候,我会感觉那温度像庄稼的汁液和泥土的温度,传到了我的血液,流进了我的灵魂。
因为爷爷,我总是觉得,无论我在哪里,我仍是农民的子孙,与泥土一脉相连。爷爷是一把庄稼好手,新插的秧苗,整整齐齐的,像一排排严谨的诗行。与其说爷爷是在种庄稼,不如说是在用粗糙的双手在大地绘一幅优美的田园风光,而劳动的光荣与收获的喜悦就荡漾在他深深的皱纹里。
趁着歇息半晌的工夫,爷爷便捉了田里的鳝鱼、泥鳅、甲鱼、乌龟让我带回家。待奶奶做完晚饭,爷爷就把甲鱼、乌龟糊上一层厚厚的稀泥,扔进尚有余烬的炉灶中。爷爷乐呵呵地说,晚上宵夜吃。我那时嘴馋,恨不能一口吞下,就不时问爷爷:“好了没有?”爷爷总是微微一笑,说,等会儿,等会儿。
月上柳梢时,煤油灯的火苗渐渐暗淡。想吃的东西一时半会儿也进不了口,我便和小伙伴们在打谷场上疯玩。印象中,那时的月亮好大、好圆。一望无际的原野,那么辽阔,那天地相连的远方,是怎样的呢?我总会想,总也想不明白。
月亮渐渐升高,爷爷苍老的声音响起,悠长的乳名声,从巷口,从街上,一直传到谷场上。我故意不吭声,躲在草垛里。情急之下,爷爷大喊一声“甲鱼烧好了”!馋嘴猫一样的我立马就蹦了出来。爷爷牵着我的小手来到灶房,用火钳夹出熟透的甲鱼、乌龟,除去焦枯的泥,一股肉香撲鼻而来。爷爷把甲壳撕开,去掉内脏,蘸上酱油、醋,一口一口地喂给我吃。那鲜美的滋味,至今还回味在我的舌尖。
味蕾是有记忆的,在这个飘雪的冬天,我格外想念故乡的冬,和只属于爷爷的味道。
当大雪覆盖了乡村,屋檐上挂起了冰凌,爷爷便在堂屋中间升起了火炉,摆上两把椅子,一老一少,你一句我一句,开始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背诗比赛。待我困倦,爷爷就找来一个旧搪瓷杯,置于火炉之上,撮上些许苞谷粒,用一双木筷不断地翻搅。只听“砰”的一声,苞谷粒爆了,开成了一朵黄白相间的花。我刚要去抓这新奇的花朵时,又是一记脆响,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在搪瓷杯里跳跃,香气四溢。在爆米花的诱惑下,爷爷教我背诵了近百首唐诗。我身上的那点文学底子,就是这样积攒下的。
爷爷不光教我背诗,还教我描红。他握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画很耐心的样子,历历在目。横、竖、弯钩之于我,太单调太枯燥,写着写着,就如鬼画桃符。这时,爷爷就会手持竹尺,轻轻敲打我的掌心。我故意“哇”的一声大哭,哭声引来了奶奶。奶奶连忙说:“乖,不哭,不写了,我们玩去。”爷爷拗不过奶奶,毛笔字就这样放弃了。很多年过去,我无从知晓当年爷爷的初衷,一个读过私塾的读书人,如何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在现实的土壤里,拼尽全力,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人。有没有在某个明媚的午后,再回首曾经的过往?笨拙如我,一直不曾读懂爷爷的内心。如今他的梦想,已然化作了坟头的一缕青烟。
穷家小户的日子,爷爷总是想方设法让它有滋有味。雪还没来的时候,爷爷早早就备下了取暖的树蔸。每冬的树蔸都是我和弟弟陪着他去挖。那时,他穿着对襟黑棉袄,扛着一把铁锹,我推着独轮车,弟弟抱着一捆绳子稳稳地坐在上面。
邻村伐了几排大树做屋,细树枝到处都是。我和弟弟捡细枝,爷爷一个人对付树蔸。俗话说老树虬枝,它的根扎得很深,分枝又太多。挖树蔸,是个拼力气的活。爷爷索性脱了棉袄,对着一个大树蔸开挖。他边挖边拿着一把砍刀砍侧根,半个树蔸就悬空了。我跳下坑,抢过爷爷手上的砍刀“哼哧哼哧”用力地砍了起来。弟弟问,这么多树蔸,干吗非得把根全挖起来?爷爷说,带根的晒干了好烧,暖和。
直到日头偏西,爷爷才挖出来几个树蔸,我和弟弟捡的树枝也有两大捆。那些空了的土坑,像一只只大眼睛,望着寂寥的天空。炊烟开始缭绕,我们筋疲力尽,肚子饿得“咕咕”叫。独轮车上的树蔸伸着虬龙般的手臂,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在晚霞中苍劲如画。
新挖的树蔸摊在院子里,爷爷隔几天就再添几个进来。不久,院子里就堆了十多个。他摸着手上硬邦邦的老茧说,够了,够烧一冬了。这才罢休。
整个冬天,那些树蔸不紧不慢地烧着,像一个好脾气的老人,昼夜不息。爷爷在火堆边扒拉,用火钳在烧过的树蔸上敲打,把炭敲下来,让树蔸烧得更透一些。而我们小孩是不怕冷的,风在门外吼,我们在雪里跑。雪人堆了好几个,像将军一样守在门口。爷爷抵在门上喊:快进来,烤烤手脚,别冻坏了!这声音仿佛还在我的耳边。
如果时光可以停留,我愿意永远拥有这样的冬天。
然而岁月无声,逝者长已矣,我是永远失去爷爷了,然而人生中许多温暖的陪伴,加剧了日后的念念不忘。我知道,担受无以回报的恩惠是痛苦的,我却只能承受这样的痛苦,如落叶不能重返枝头,我再也触摸不到爷爷温暖的双手了。这个如土地一样质朴厚重的人,终于归于泥土。
清明回家,去了一趟爷爷的坟。他的坟茔就在河畔,新坟四周是绿油油的豌豆,有的已经开了蝶似的花,花上有无数双眼睛,一眨一眨,仿佛璀璨的星空。坐在坟边,静默良久,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到与他重逢的方式了。空气中流动着甜丝丝的花香,故乡的河水在阳光下静静地流淌。倘若天地人生真有轮回,我愿再次久久地、久久地依偎在爷爷饱经沧桑的怀里……
(标题书法:马振水)
责任编辑 黑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