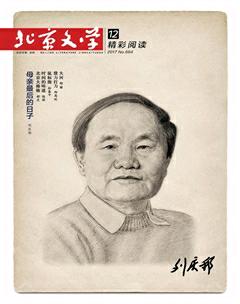我的婆婆(创作谈)
邵丽
婆媳之间的勾心斗角,是中国文化中挥之不去的阴霾,现在还被各种文学作品津津乐道。这种看似家长里短的争斗,被洇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几千年来弥散在宫廷、职场,到内外关系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悲哀。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写婆媳之间的故事。它看似千篇一律了无新意,但细细想来却触目惊心。这是一种很大很重要的关系,重要到甚至可以影响到大国崛起的程度——我觉得不管是婆婆还是媳妇,以及夹在她们中间那些左右为难的男人,只有让他们在家中、也在文学作品中真正站立起来,成为有血有肉独立的人,才能再去谈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
其实,我与婆婆的关系也没能逃出这种窠臼,有一段时间我曾经陷入深深的苦恼里。但我能从中走出来,并与婆婆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婆媳关系,我认为是我成长的一部分。所以从我开始写作,婆婆的影子就经常出现在我的作品里,但是说实话,我又很难把握住她,就像在生活中一样。
我婆婆九十岁了,她是个老人中的开明派,很新派的人物。我这么说,绝非妄言。她用新潮的手机,穿时尚的衣服,喜欢住在热闹的地方,最好隔壁就是个大市场。她每天都要逛街花钱买东西,不管用得着用不着。七十岁那年,她开始跳健身舞,并坚持识字写字,而且一发不可收。每天看完《今日说法》后,她都要写一篇观后感,她自己说那叫评论。现在这些评论堆起来,比她的个子还高。所以说起当今的热点问题,她比我们知道得还详细。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她都知道自己是谁,以及怎么安置自己。娶我婆婆的时候,我公公是个大户人家的子弟。英姿勃发,玉树临风,写得一手好字,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找个如花似玉的好媳妇本来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他生性固执,不讨父亲喜欢。父亲一言九鼎,强迫他娶了生意伙伴的女儿,也就是我后来的婆婆。我婆婆个子低,长得又不好看,一辈子也没让我公公喜欢上她。但她自从嫁到这个家,不卑不亢,活得有章有法。家里最穷困的时候,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自己的孩子过得体体面面。后来日子好了,她也从不懈怠,对子女的敲打从来没停止过。她既乐善好施,又洁身自持,只要力所能及,她从不麻烦别人。
我婆婆脾气刚烈,一言不合就暴跳如雷。据说在他们镇子上,没人敢惹她。想想这也是婆婆的生活策略,甚至可以说是战略。丈夫远在几十里外当医生,她孤身一人带着几个孩子,孤儿寡母讨生活,再加上他们的亲戚都是“地富反坏右”,稍微软弱一点,就不可能抬起头来生活。所以谁胆敢欺负她的几个孩子,我矮小的婆婆就会跳骂到这家人的门口,直到他们站出来认错服输。
在管教孩子方面,她也是这么独断专横。你犯个小错,她就拼命打你,朝死里打,而且很少在家里打,都是拉到大街上去打,生怕别人不知道。早自习起不来逃学了,她打;跟同学骂架了,她打;在你的腿上划一下,只要有个白道道,就说你偷着下河游泳了,她也打。但是你犯个大错,她别说打你,吵你一下都不可能。比如你失手打碎一个祖传的花瓶,或者不小心弄丢了学费,她都一笑了之。后来婆婆解释说,小错不管,最终你们会酿成大错;你们犯了大错,我不吵你,你自己都快吓死了,如果我再打你你还能活吗?
我老公说,母亲这句话影响了他一辈子。他觉得这句话既可以用来修身,也完全可以用来齐家治国平天下。
就是在这么个背景下,我嫁到了这个家庭,而且很快就要与她一起共同生活在只有七十多平米的屋檐下。我自小脾气就大,而且认死理儿,遇到这么个主儿,可见该有多大的冲突。开始的时候,确实有诸多的矛盾,有时候甚至还很激烈。好在我提前就有心理准备,再加上有老公在中间的调停,还算维持了一个基本和平的家庭局面。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我觉得这话既有贬义,也有褒义。从媳妇到婆婆,不管有多少委屈,谁说不是一种成长呢?后来我与婆婆之所以处得很好,就是我换了一个角度看她、欣賞她,觉得需要从她身上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她乐观、豁达、坦荡,大事从来不糊涂。她的一生历尽艰辛,但她从没抱怨过。她是个喜欢往前看的人。当然,与婆婆处好关系仅靠这些是不够的,“功夫在诗外”,说到底,是需要经营。
中国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尤其是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条条框框太多,太繁杂,要么是学会两头撒谎,要么是毫无原则的退让。家庭是组成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单元,社会和国家则是家庭关系的外延。市场经济给我们输送着财富和各种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输送着欲望、烦恼,以及更加纷繁复杂的家庭关系。
这部小说写了很久,也放了很久。当我从头翻看作品的时候我一直在疑惑,这真是我的婆婆吗?我想,尽管我竭尽全力去接近和还原她,也未必是真实的她。我在变,她也在变。即使我们都没变,生活也在变。也许这才是我犹疑不决的原因吧!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