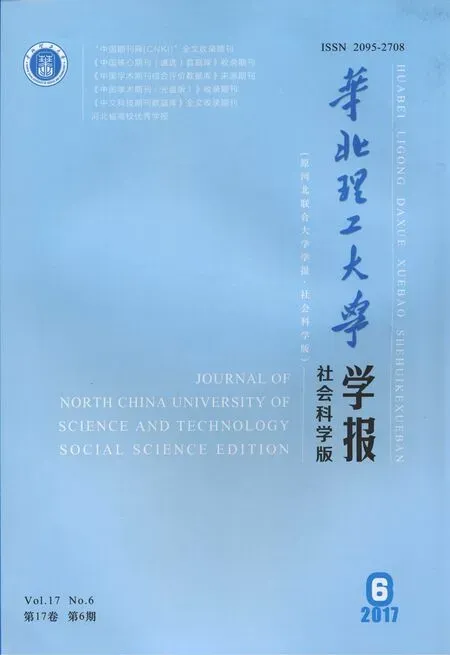《葵晔集》考求
崔巍
(华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唐山 063210)
《葵晔集》考求
崔巍
(华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唐山 063210)
《葵晔集》; 编译; 华人学者
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过不少英译选集,其中海外华人学者柳无忌、罗郁正合作编译的《葵晔集》便是不容忽视的一部作品,受到了英语读者的好评。然而,国内学界对该译作却关注甚少。文章从编译者治学生涯、书名解析、体例编排、译文述评等多角度切入,通过描述性地梳理分析,考求《葵晔集》的独特价值。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久负盛名的诗、词、曲更是不可或缺的瑰宝。得益于广泛的译介与传播,以诗、词、曲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作品能够为世人所了解和体悟。在广大的译者之中,既有国内受浓厚中国文化熏陶的本土翻译家,也有国外浸染于异域文化的外族汉学家,不过还有一类群体比较特殊,那就是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他们往往是儿时生于中国,受传统文化熏陶,而后求学海外,浸染于西方文化。这便造就了其在译介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方面独特的优势:既熟谙中国文化,能贴合中文原本意义,又体察海外文化,切近目的语读者,英文译笔相对适应阅读习惯。可以说这些华人学者为推介中国经典文学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其编译作品也理应得到国人应有的关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华人学者柳无忌、罗郁正合作编译的《葵晔集》便是成就突出的一部作品。
《葵晔集》(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于1975年由美国双日出版社(Doubleday, Inc.)首次出版,此外以旗下《安克尔丛书》(Anchor Books)平装本形式发行。一经刊印,销路极广,美国很多学校将其作为讲授中国文学的课本。翌年,又经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Indiana University Press)推出该英译选集的中文本《葵晔集:历代诗词曲选集》作为补充,以省去教师与学生在各种中文选集或专集中寻找原文之苦。《葵晔集》收录了具名的140位中国诗、词、曲作者的共965首作品,经52位译者以英文译成。可能由于时空的阻隔,这部名扬海外的译著在国内却鲜有探讨,对其独特价值的考求便甚为必要。
一、编译者治学生涯
《葵晔集》的主要编译者之一柳无忌(Wu-chi Liu,1907-2002)是著名的旅美诗人、散文家,为中国近代诗人柳亚子先生之子。他生于一个文学家庭,从小接受了典型的中国文化教育。10岁时加入其父组织的文学团体南社,17岁时开始对苏曼殊的研究。1920年至1925年在圣约翰中学及大学一年级读书。后入清华学校学习文学。1927年公费留美,获劳伦斯大学学士学位和耶鲁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相继在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任教。1945年后再度赴美,并从此定居,先后任耶鲁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中文教授。20世纪60年代初,在印第安纳大学创办东亚语文系,任系主任。其一生著作等身,包括《中国文学概论》、《西洋文学的研究》、《儒学简史》、《古稀话旧集》、《休而未朽集》、《苏曼殊》等多部作品,另外曾为多种百科全书、词典、期刊撰写过大量关于中国文学、哲学的文章。
而另一位主要编译者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1922-2005)则同样是著名的学者、翻译家。他家境殷实,从小接受私塾的启蒙教育。先后在上海圣约翰附中、圣约翰大学文理学院英文系求学。1947年大学毕业后远渡重洋,赴美求学。先在哈佛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1952年,他进入斯蒂尔曼学院英文系讲授英国文学。随后曾先后在西密歇根大学、爱荷华大学执教,讲授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课程。1967年,受聘为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数年后担任该系主任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其可谓著译皆丰,《辛弃疾》、《待麟集》等译著影响深远,还为《英译文学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20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等撰写词条,英译简介,担任顾问,作为《中国文学翻译》、《中国文学与社会研究》、《中国文学: 随笔、报道、评论》等丛书、杂志的主编或编委会成员,笔耕不辍。
综合两位编译者的治学生涯不难看出,他们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且有长期执教经历,对中英文的把握俱佳,既精通中国语言,又有西方文学的认识与涵养,故而所译中文作品能做到稳妥扎实,长居美国给他们提供了运用英文写作的能力与经验,英译文的畅达典雅也能得到保障。这为《葵晔集》的编译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二、书名解析
《葵晔集》(Sunflower Splendor)的书名,无论是中文抑或英文,都显得颇具风采。从选集开篇不难看出,它出自美国诗坛巨匠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的抒情长诗《李白来书》(A Letter from Li Po)中的诗行:
Each morning we devour the unknown. Each day
we find, and take, and spill, or spend, or lose,
a sunflower splendor of which none knows the source.
至于为何选用“葵”(sunflower)和“晔”(splendor)二字,或许在该选集中文本的后记中可找到些端倪。编译者有感于出版后的广泛好评和大力传播,谈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表示中国的诗、词、曲作品,倘用适当的英文译出,可能为西方的读者所接受与欣赏。我们这一份优越的文学遗产将如葵花的光晔一样,放射出一种鲜艳的异彩”(柳无忌,罗郁正,1976)。由此可见,二位编译者对中国文学及文化满怀着浓浓爱意,对所译作品感到欣慰并充满期待。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对“葵晔”这个词的选取都一致赞同,比如知名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在为国际汉学期刊《通报》(T’oung Pao)撰写的书评中指出,该选集书名的选择并不合适,因为尽管夏末时节向日葵在中国各地广泛生长,但它是新近时期才被引入中国的,所以除了最近的诗歌,向日葵在中国诗歌中是罕有出现的(Holzman,1978)。他的评论并非全无道理。据信,向日葵原产北美,约自明朝引入中国。如今所知最早记载向日葵的文献为明朝人王象晋所著《群芳谱》(1621年),该书中尚无“向日葵”一名,只在《花谱三·菊》中附《丈菊》一文提到“迎阳花”。“向日”之名,见于文震亨《长物志》(约1635年左右)。清初,陈扶摇所著《秘传花镜》中明确记载为“向日葵”。由此也印证了侯思孟教授的说法,确为晚近的明清时期才有,因而“向日葵”这一意象在明代以前便几无可能在中国的诗词曲中出现。当然,“葵”这一意象倒不是没有。例如汉乐府诗《长歌行》中有“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的句子,不过此“葵”非彼“葵”,这一句中的葵是指葵菜,为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蔬菜,与向日葵属不同物种。
若说书名中一定不能用“葵”(sunflower),不免有些吹毛求疵,《葵晔集》收录了自《诗经》到现今三千多年的诗歌,自然也包括了向日葵自明以来引入中国后的时期,另外编译者本身就是希望为中国文学塑造一个光鲜亮丽的形象,选用向日葵并无不可,况且英文中“sunflower”与“splendor”押头韵,无形中又增加了音韵和谐之美。
三、体例编排
《葵晔集》从前至后依次包括致谢、序言、导言、解释说明、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六部分英译文、参考文献、诗人及诗歌背景、附录一词曲牌名及翻译、附录二中国朝代及历史时期年表、作者索引。在致谢部分,柳、罗二人首先点出该英译选集由亚洲协会的亚洲文学计划资助,受到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拨款。随后感谢了为选集提供版权材料的译者和出版机构,包括提供卫德明译文的《亚洲研究》杂志,提供华兹生译文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提供傅汉思译文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杂志,提供刘若愚译文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提供傅汉思、刘若愚、王靖献译文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提供傅汉思译文的耶鲁研究生院杂志,提供迈克尔·沃克曼译文的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从中既可以看出二位编译者对他人版权作品的尊重与保护,又透露出他们审慎谨严的治学态度。
在序言部分,开宗明义,指出该选集的目的为展现中国经典格律诗歌的新翻译,在制作与设计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学者间协作,是解决旧问题的新尝试。接着从三个方面具体说明。首先,有五十多位译者参与了选集编译工作,绝大多数译文均是他们专门为该选集所准备,这些译者主要是美国、加拿大各院校东亚研究方面的专家或是接受过多年研究生培养的年轻学者,每一位都有其独特风格。此种编译方式属故意为之,这能活跃长期以来由一人译全书风格单调沉抑的传统。其次,选集期待在有限的空间中呈现出一种平衡各体裁、各时期、各流派的包容性。二位编译者注意到公众,尤其是学习中国文学的外国学生,过去只能接触到中国浩瀚诗歌中的一部分,故而经由某段时期或是某位诗人的作品来传达中国诗学传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还远远不够。最后,他们强调在翻译过程中察觉到了固有的困难,即汉语属富含典故的非屈折语,但并不完全赞同诗歌不可译的理论,所以便谨慎地审视汉语原文,坚决要求兼具准确性与可读性。力求达到的目标就是用地道的英语保持汉语语法和风格方面的主要特征(词性、语序、诗行长度及跨行、排比的使用,有时甚至是听觉技法),但不强求再现韵式。每篇译文都有三位不同读者参照汉语原文核查,并借助更大范围内的精选读者来测试。所有参与工作的编译者都达成了共识,想要忠实翻译诗歌并不只是熟练流畅掌握原语和目的语,还需要对原文的完全理解,包括意义、结构和细微差别,并且反对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中介合作者。选集的编纂始终遵从上述这三条原则。总地来说,该选集偏爱收录以前从未翻译过的作品,当然若是汉语原作意义重大或是英语译作存在优点也考虑收纳重译本,突出了首创性、新颖性;各时期、各流派作品的广泛采用,试图达到平衡的效果,体现了包容性、多样性;编译者对译文的层层把关、严格校对,保证了准确性、可读性。
在导言部分,又细分为三个小节阐述,由罗郁正独自撰写。第一节罗列了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六个不同点:1.中国诗享有三千年连绵不断的传统,发展出许多形式、格律和风格,“诗”可以泛指一切包括“词”、“曲”等的韵文,也可特指《诗经》;2.中国诗一开始就与音乐有密切关系,当配合诗歌的音乐已被遗忘的时候,诗歌本身仍然可以用来吟咏,而不只是朗诵;3.中国诗的节奏性不是基于音节的轻重组合,而是基于不同声调或抑扬顿挫字句的规律变化,声调格律的使用成为其最显著的特性;4.中国诗句中主语经常省略,显得更为简洁且增加了语意多样性;5.中国诗的社会渊源既有淳朴的一般人民也有广博学识的文人;6.中国诗的主题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对季节变化的重视、对仪式的遵守、对农民命运的关怀在任何时代的作品中都显而易见,反映友情的离别主题甚为普遍,相较之下,爱情主题成为其次。第二节论述了诗歌技巧上的发展,从最单纯、最少修饰的,到最复杂、最富于引喻的。分析了中国诗歌在技巧与知性上的繁复是由于知识源流的汇合——主要是儒释道三家。随后按时代梳理了诗、词、曲的演变过程,直至明清及近现代。第三节有总论性质,归纳出中国诗歌最突出的两个特征:注重实用性或说教性;具有作为自我表现或自我修养的功用。同时诗歌又有着崇高的目标,培植于日常生活之中,使人们不会忘怀。罗郁正在此为西方读者勾勒了中国诗歌的总体形象,导引他们尽快融入其中,以更好地领会和感受这些历经数千年的情感与智慧。
在解释说明部分,编译者就汉字罗马化拼读方式、地名、人名、参考的书目、引用的汉语诗歌文献、脚注、诗歌子类型名称、标题、作者个人作品的年代顺序以及关键词缩写等作了简要阐述,充分为目的读者考虑,减少阅读障碍,使其不至于错乱混淆。
在主体的英译文部分,依中国历史朝代的时间顺序划分成六大部分,分别为“In the Beginning: The Legacy of Shih and Sao”,“A World Fragmented: Multiple Voices in a Period of Intellectual Foment”,“Expanding Horizons and the Full Flowering of the Shih”,“Cross-pollination: The Predominance of the Tz’u, or Lyric Meters”,“The Rise of the San-ch’ü, or Song-poems”,“In the Long Tradition: Accommodation and Challenge”,共收录了140位具名的作者,凡965首作品,具体统计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1 选集具名作者与收录作品数目
依数据总体分析,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均以唐代收录最多,其次为宋代,二者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当然这也是唐诗宋词繁盛的必然结果,明清至今诗词的收录数目同样相当可观,作为有机补充,堪称是一大特色。从宏观来看,选集从《诗经》起至毛泽东诗词止,横跨三千多年;从微观来看,收录作者的作品数相差悬殊,多则五十余首,少则一二首。关于译文的述评稍后展开,在此不再赘述。
部分,编译者条分缕析,细化成四个小节,第一节为部分综述性研究书目,第二节为按出版时间排序的中国诗歌译本,第三节为背景与体裁研究文献,第四节为对个别诗人的研究与翻译。这给欲进一步钻研中国文学的外国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有利于激发他们广泛涉猎的兴趣。在诗人及诗歌背景部分,按前面译文所形成的六大部分,分别给了各部分所收录作者及其作品的详细介绍,做到了知人论事,知事论诗,将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拉近,起到了最大程度弥合时空阻隔的效果。
在两篇附录部分,附录一分别以威妥玛拼音和意译两种形式对比呈现了词曲牌名,附录二则提供了中国历史朝代年表,此二者均能以清晰的方式帮助读者加深理解。
在最后的作者索引部分,读者能轻松查阅以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列的各位作者其作品首次出现在选集中的页码,直接可以进行定位,提高了检索效率。
综观《葵晔集》的整个体例编排,编译者最大程度上贴近目的语读者,设身处地考虑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感受,体现着人文关怀又培养了其探索中国文学的兴趣,同时也透露出二人缜密的逻辑。
四、译文述评
《葵晔集》是由52位译者合作译成,译文之间的风格差异自然不可避免,当然如前所述,这也正是二位编译者的初衷。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译者集中翻译了个别作者的作品,按译者首次出现顺序排列如下:
这些译者或是当时就威名远扬的汉学大家,或是后来声名鹊起的年轻学者,正可谓“术业有专攻”,他们选择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作者作品进行翻译,而且从上表也能看出,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涉猎范围颇为广泛,不仅是为外国读者也为本土读者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
虽然有风格上的“异”,但也有方式上的“同”,即总体上以自由体译诗。这就涉及到了汉诗英译的方式问题,约有三派,即韵文体、自由体、散文体。韵文体派主张“以韵译韵”,追求格律,此固然为上乘之作,不过也可能出现“因韵害义”的现象;自由体派在确实不能用格律诗译格律诗的情况下做了变通,主张运用自由诗体来译,不一味求韵式,以便尽量保留原诗的思想、情节、意境和形象以及比较整齐匀称的诗行排列形式(刘重德,2000:6),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韵害义”;散文体派则是把分行的格律诗译成不分行的散文诗形式,比较少见。《葵晔集》即自由体派译诗的例证。这符合序言中所述二位编译者制定的目标——用地道的英语保持汉语语法和风格方面的主要特征但不强求再现韵式。各位合作译者在选集的翻译过程中也是很好地贯彻落实了这一指导思想。以下结合选录数目最多(56首)的杜甫诗来简要分析说明。
就原文择取来看,题材广泛,既有广为传颂的名篇,如《丽人行》、《垂老别》、《石壕吏》、《春夜喜雨》、《登高》、《旅夜书怀》;也有关注度相对不高的作品,如《羌村》、《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倦夜》、《宿江边阁》、《见萤火》。底本均为《全唐诗》(Ch’ üan T’ang shih)。
就译文出处来看,有Wu-chi Liu,Irving Yucheng Lo、Eugene Eoyang,Ronald C. Miao,Mark Perlberg,Michael E. Workman,Geoffrey Waters,William H. Nienhauswer,Jerome P. Seaton,Jan W. Walls,James J. Y. Liu等。这也是全书群策群力的一个缩影。
其中如倪豪士的《春夜喜雨》译文:
A Spring Night—Rejoicing in Rain
A good rain knows its season,
Comes forth in spring
Follows the wind, steals into the night;
Glossing nature, delicate without a sound.
Clouds on country road, all black,
Sparks of a lantern from a river boat, the only light.
Morning will see red-steeped spots:
Flowers heavy on the City of Brocade.
(CTS, P. 1322)(TR. WILLIAM H. NIENHAUSER)
题目顶行居中,译文居左对齐分行而列,尾行偏左有带详细页码的中文底本出处(此诗中CTS即是Ch’ üan T’ang shih),偏右为译者姓名。其他译作皆以此形式排版,对于个别文化负载词,以尾注解释。
总体为直译,甚至词序较原诗也几无改变,采用自由诗体,原诗的拟人手法依样复现。汉语律诗一般要求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英语译文则采用“Clause1,Clause2.Clause1’,Clause2’.”形式相应做了变通调整,譬如颈联,Clause1= Clouds on country road↔野径云,Clause2=all black↔俱黑,Clause1’=Sparks of a lantern from a river boat ↔江船火,Clause2’= the only light↔独明。尾联中的“锦官城”为成都的别称,译者并未过度阐释点明,直陈“the City of Brocade”,也保留了原诗的韵味。语言虽有转换,但意义却并未过多流失。该选集的其他译作也大体与之翻译策略相仿。至于对目的语读者是否因译者未采用“以韵译韵”而丧失阅读兴趣的担心,通过《葵晔集》也可管窥一斑。几乎全部以自由体译成的这本选集,不但销路极广,还被大学选作课本,在接受度上应不存在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译文质量取决于通顺传意,韵式并非必要决定因素。能做到格律与意义兼备诚然为佳,但若是实在难为而强求,效果不免适得其反,况且汉英诗歌的格律也不尽相同,完全再现似不太现实,难度极大,倒不如退而求其次,老实传情达意为好。

表2 部分译者主译作者作品
五、结语
《葵晔集》如“葵花的光晔”般绽放异彩,在于其独特的价值。柳、罗二人海外华人学者的身份利于沟通中西,其治学态度严谨,又有目的语本族语译者(其中更不乏汉学大家)的通力合作,将准确掌握的中文意涵以流畅的英语译文推介而出。文雅的书名增添了选集的艺术气息,使读者印象深刻。作者作品兼收并蓄,题材体裁丰富多样。体例编排合理,充分考虑目的读者,减少阅读障碍,增加阅读兴趣,同时透露出编译者的逻辑思考。自由体的译文保证了英语语法和风格的地道,在韵式上做了变通,有效避免了“因韵害义”现象的出现,并将这一思想贯穿始终。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大力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同时,海外动态、传播效果等也同样应引起关注。一些学者、译作在国外广泛流行,风生水起,在国内却闻所未闻的尴尬和遗憾应竭力避免。谁来译、译什么、怎么译,这些问题也还在持续探讨之中。《葵晔集》或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和启示,当然也就有必要进一步来考求。
参考文献:
[1] LIU W C, LO I Y C. 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M]. Bloomington, London, 1975.
[2] 江岚. 葵晔待麟:清诗的英译与传播[C]//广西大学、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文化与传播》编辑部.“全球化与区域社会发展:基于文化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南宁,2014.
[3] 柳无忌,罗郁正. 葵晔集:历代诗词曲选集[M].布卢明顿,伦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6.
[4] HOLZMAN, D. “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Book Review)[J]. T’oung Pao, 1978, 64(4/5): 321 - 331.
[5] 刘重德. 漫话中诗英译[J]. 山东外语教学,2000(01):1-7.
StudyonSunflowerSplendor
CUI W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Hebei 063210, China)
Sunflower Splend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Chinese scholar
I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have been many antholog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among which Sunflower Splendor co-edited by Wu-chi Liu and Irving Yucheng Lo, two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 is a hugely popular work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However, domestic academia ha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translation. The article researches on the unique value of Sunflower Splendor by means of descriptively combing and analyzing from several different angles like the study career of the translators, the analysis of the title, the style of the layout and the review of translated text.
2095-2708(2017)06-0099-06
H05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