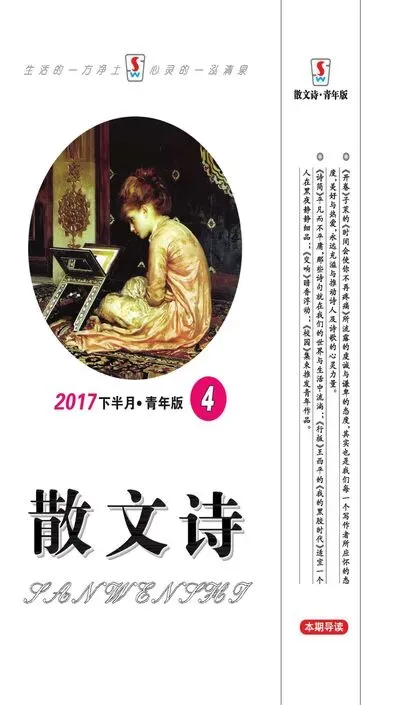冬储记忆
河南/冯敏生
冬储记忆
河南/冯敏生
时间迈着轻盈的步履,悄悄走进了冬日的视野。
偌大的旷野里,空荡荡的,格外静寂。炊烟袅袅的村庄旁,偎依着一两畦葱绿的冬白菜,在温润阳光的映照下,郁郁葱葱地招惹人的眼睛。坡畔上,孤零零地挺立着几棵沧桑的老柿子树,枝头上稀疏高挂着几只火红的柿子,那是农人特意留给鸟雀过冬的食物。在向阳的岭岭洼洼上,独自绽放一朵朵金黄的野菊花,点缀于寂寞的山野。就在这初冬的原野上,恐怕只能看见到这最后的一种水果和一种花朵了。
春花秋实,春播秋收。忙忙碌碌的乡亲们,已将丰收的果实,颗粒归仓。立冬过后,当门前的杨树上,只剩下几片零星的黄叶在风中飒飒作响的时候,山林中的小松鼠、猪獾等动物们,正忙着储藏过冬的食物。农闲下来的乡亲们,与动物们一样,也忙碌着立冬前的储备工作。
村里的女人们开始忙活了。腌酸菜,腌雪里蕻、卷心白等咸菜,那独有的味道,浸润北方农村淳朴的传统情结。母亲做的辣子酱,算得上村里的拿手菜。母亲将新鲜的青辣椒、红辣椒,清洗干净后,切成细丝,加上姜、葱、蒜、花椒等调味,将几只红苹果和酥梨切成薄片,放在石磨子磨成酱汁,装入木桶里,扑鼻的香气,弥漫到阳春三月。
站在村后的山冈上远眺,那屋檐下悬挂的一排排鲜红的柿饼和辣椒,成为山村冬日里最耀眼的风景。村里的女人们将红彤彤的柿子削成柿饼,用带刺儿的藤条穿成串,悬挂在屋檐下,历经阳光晒,寒风吹,雪花飘,直至变成酱红色,再捏成圆饼,密封在陶罐里,等到柿饼挂满了粉嘟嘟的一层白霜后,方才在腊月间拿出来,让人解解馋。女人们也将采摘回家的鲜辣椒,用麻线穿成一串串,挂在屋檐下,或者墙壁上。到了冬至前后,红辣椒风干了,倒进烧烫的大铁锅里干炒,直将辣椒炒得焦红,“哗哗”直响,香气弥漫,再倒进石臼里捣成碎粉,加些炒熟的芝麻、花生仁,泼上熟菜籽油,就做成一搪瓷盆红油花生芝麻辣子了。假如吃羊肉泡馍、吃模糊豆面,或烤干的玉米面馍片,拌上红油辣子,那其中的美味,妙不可言,既能冒汗驱寒,又让人浑身舒服,长精神。
与此同时,村里的男人们也不甘落后。“攒柴”是男人们一项重要的力气活。他们趁着大雪未封山前,都要进山去打柴火,用藤条扎成捆,然后背回家。每户人家都在门前的空地上,垛起一人高的柴垛,也有时,他们将碗口粗的树木截成一二尺长的小段,劈开,艺术地码放在屋檐下,远远望去,成为一堵富有立体感的柴火墙。如此攒柴,是要保证乡亲们在整个冬季能有柴做饭、烧炕,取暖用。
贮藏蔬菜水果,也是村里男人们入冬必做的工作。他们在门前朝阳的地方,精心选择一小片排水较好的小高地,开挖土窖,储存过冬的蔬菜。稍浅一些的土窖,一米多深,可以存贮土豆、萝卜;稍深一些,有七八米深,保暖性能好,可存贮红薯、大白菜、苹果等,取用时,必须在窖内斜一个小木梯子,这样方便人们取东西。邻居的发子哥,脑瓜灵,点子多。他利用村里闲弃的土窑洞、石窑洞,种植黄瓜、茄子、西红柿、青菜等蔬菜。他在窑洞门前,装上透光的塑料门,利用太阳能集成电路,在洞内安装自动照明、烘暖设施,还铺设了自来水管。当窑洞外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窑洞内,温暖如春,蔬菜葱葱绿绿,生机盎然。发哥家种植的新鲜的窑洞蔬菜,不仅满足了他家过冬用,也解决了村里人冬天的吃菜问题,尤其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村里人再也不用冒着严寒,步行去镇里的蔬菜市场买菜了。
在我的家乡,来自陕南的乡亲们居多,他们在冬日里有吃大肉、喝烧酒的传统习惯。村里土地广,所产的粮食足,每户人家都要喂养几头猪,酿上几坛老玉米酒。每赶在土地上冻前,总要杀上一两头猪,分解开来,挂在有烟囱的灶膛里,烟熏火燎,最后成为“熏肉”。当屋外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屋内的土炕便格外暖和,红泥火炉里炭火燃烧得很旺。火炉上,一小铁锅熏肉炖萝卜、土豆和红薯粉条,“咕嘟咕嘟”直响,上面飘着一层红油辣子、葱花和香菜,香气四溢。人们蜗居在温暖的屋子里边,边欣赏窗外壮观的雪景,边品尝着熏猪肉,喝着自酿的老玉米酒,享受着冬日惬意的生活,那其中的境界,用陕南的话说:“那真是美的太!”
在家乡,冬储飘溢的乡愁,令人回味无穷。此时此刻,冬天已经来临,四处漂泊的我,蓦地想起白居易的 《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多想抛弃纷扰的生活,在寂寥的冬日里,置一只红泥小炉,相邀几位老朋友,围着火炉,酌老酒,品熏肉,吃柿饼,谈古论今,交流文章,共同度过那浪漫的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