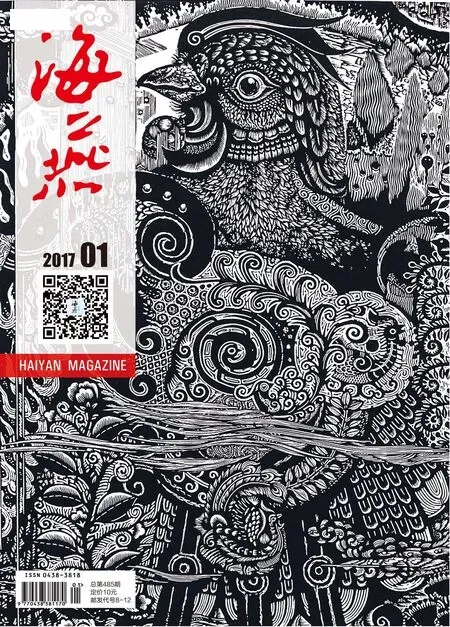我的一段学画经历
□单澍铭
我的一段学画经历
□单澍铭
我不知道不成功的学习经历是否也可以入文。大凡谈学习方面的回忆,多数是在成名之后的津津乐道,像我这失败了东西,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看呢?单从绘画技艺而言,我的学画是失败的,失败在忘记了“有志者事竟成”的古训。但毕竟学画使我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而且多多少少也陶冶了我的审美情趣,甚至直接影响了我的阅读,所以,我还是把少年时学画所碰到的人和事,写了出来,或许能折射出一点那年那月的痕迹。
学画的启蒙期
小时候曾有一个宏伟的理想,长大以后要当画家。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萌生的这个念头,不是很早的,大概在小学与初中之际。小学一到三年级是在文革前度过的,印象里总是用彩色蜡笔上的图画课。那时最爱看小人书之类的图画书,但没有产生对画画的特殊兴趣。文革爆发之后,到处都乱糟糟的,学校停课了。复学时已经是1967年的秋季了。原来的老师被“打倒”之后,换了不少由贫下中农推荐的代课老师,课堂上很少能静下来。倒是有一本省编美术教材,有天安门,有公共汽车。放学后,我就在吃饭用的饭桌子上开始临摹起来,用的是铅笔和蜡笔。
其实我的父亲是一位不错的小学音乐与美术老师。只不过早在1958年就因为“反右”中说了一些话,被开除公职,下放在生产队里劳动改造。记得父亲有一个苏式小课桌,斜面翻盖的,上面还有三层的小书架,上面有好多美术音乐方面的小册子。好像还有一本翻译苏联的人体艺术解剖方面的理论书,后面的附图是黑白裸体素描。文革中的我,看了感觉很不雅,就用墨汁涂抹了,现在想起来不只是可笑,也是愚昧。
因为父亲被劳动改造,加上文革中风声太紧,在我爱好画画的时候,父亲没有帮我太大的忙。那时正是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学校停课了,老师集中办班搞“斗批改”,在学校当老师的母亲很少回家;父亲碰上文革自然也好不了,被打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当时我家所下放的大队,“五类分子”都在挑大粪,还要扫大街。老人经常跟我说起这些事,说当时大队的于书记比较了解父亲,看到我父亲挑大粪,找到生产队队长,说这样的人怎么能挑大粪,他的字写的好,给安排一下。于是父亲开始一段很长时间的挣“脱产”工分。每天扛着小马梯,在公路两旁的水泥电线杆子上书写毛主席语录,用的是红油漆,父亲也不打方块格,用眼睛大致瞄一下,就用扁扁的油画笔,左一下,右一下,上一下,下一下,干净利索,我有时都看迷了。后来我在中学进了美术小组之后,我也曾模仿父亲那样挥洒过,但用的是可以擦掉的广告粉,办的是黑板报,比父亲的油漆好写多了。
小学毕业后,稀里糊涂地就进入了中学。我曾在别的文章里介绍过家乡小镇的这所中学,虽然也遭受了文革的“洗礼”,但毕竟是进京参加过全国“群英会”的重点中学,丰韵犹存,有名气的老师还在。像语文老师,王老师与刘老师是两口子,说的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年学校举办朗诵会,王老师用汉语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刘老师用俄语朗诵。美术老师也有好几位,尤其是城里下放来的马老师,就是我后面要提到的我们美术小组的指导老师。
上中学第二年,正好赶上小镇要在我们学校举办全镇运动会,画大幅招贴画就在操场上进行。课间及放学后,我与好几个爱画画的同学围在那里,看迷了。除了马老师,还有小镇其他画画有名气的。用的材料应该是水粉,当时大瓶颜料都叫做“广告色”。一幅画的是毛主席畅游后长江后站在江边挥手致意,一幅是亚非拉各国运动员手持鲜花聚集北京的宣传画,宣传画的主题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还有一幅是运动健儿投掷标枪,下面有醒目的两行大字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画毛主席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女老师,她用的方格放大法,我们在美术课里也学过的,就是在原图上画上小方格,再在画板上打上大方格,然后临摹,这样就容易把握了。学画的启蒙期有这样的实地观察,很多细节历历在目,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我就越发喜欢上了美术课,那时恨不得每天都有美术课,其实每周才一节。当时教我们美术的是王老师,他的爱人与我母亲是小学同事。王老师并不是美术老师,主专业是语文,客串美术完全是兴趣爱好。他的画也是不错的,教学语言幽默风趣。也可能我的画并不出众,所以很少得到表扬。倒是后来他又改回来教语文,我在他眼里“大放异彩”过一次。那是1972年,“教育回潮”风刮得知识分子又有点“翘尾巴”了,突然决定初中升高中实行考试淘汰制。语文试卷分为基础与作文两张卷,我属于异常发挥,结果得了100分。王老师大为兴奋,很是表扬了一番,我到现在还记得课堂上他提及这件事,在黑板上大大地板书了“100”的阿拉伯数字。也许就因为这个,进入高中后,我就开始当语文课代表,一直到毕业。美术兴趣却逐渐转移了。这是后话。
物理老师推荐我进了美术小组
初中物理老师姓吴,个子很高,有水平。我也非常喜欢物理课,考试经常得高分,初中毕业证上的物理成绩写的是“优秀”。有一天,那一节课是吴老师的课,天有点热。同桌的沈同学趴在桌上睡了,侧着脸,脸部特征很突出。这位仁兄人真不错,就是长得有点肥胖,头很大,于是同学们都喊他大头。我突然有了兴致,看着大头就画了起来,非常的投入。吴老师什么时候来到课桌前我都不知道。老师拿了我的画,看看画,又看看大头,嘴角掩饰不住有一丝笑意,没说什么就回到了讲台。我的脸顿时火辣辣的。下课后,我有些忐忑,心想准得挨批。谁知吴老师什么也没说,夹着教本以及我的画就走了。后来我听说吴老师回办公室后,拿着我的画问好几位其他学科的老师,像谁,结果我大获成功,竟然都猜对了。其实主要是大头的特征太明显了,一下子被我抓住了。后来我还知道,吴老师会油画,功底还不一般呢!中学毕业后,我下乡插队,当了报道员,去县广播站送稿,意外碰到过吴老师。原来他转行了,在广播站负责技术工作。我至今想念吴老师。在动乱年代里,我还听过他的物理讲座,内容是地球物理知识,结合我国刚刚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向我们展示了无穷的宇宙。那时正赶上所谓的“回潮”,善良的老师们以为这一下可以敞开讲知识了,因此各种讲座陆续开课。可惜好景不长,不曾想钻出了个“黄帅事件”,老师们的积极性很快就被打压下去了。
我“因祸得福”,被吴老师推荐到我期盼好久的学校美术小组。学校的美术小组在操场右侧的一排大瓦房里有活动室,每天下午放学后(那时上课很轻松的,一天最多6节课,少的只4节),我的师兄师弟们都很得意地夹着小画板来这里活动。我等只能站在窗外观看,可以说想加入美术小组,由来已久。感谢我的好物理老师,让我如愿以偿,我终于走进了在我眼里不亚于艺术殿堂的美术小组活动室。新来的马老师有职业画家的气质,重视写生与素描等基础训练,他的水彩写生好极了,领着我们去野外写生,还把他订阅的文革前的《美术》杂志借给我们看。我看到的是1959年的,装订到一起的厚厚的。我被贺天健的山水画迷上了,画风细腻而流畅,秀丽的山,秀丽的水,真乃人间仙境。还有吴冠中的谈井冈山写生的文章和画。井冈山本来就是我向往的地方,小学一年级学的一首歌第一句就是“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吴冠中画的是井冈山的杜鹃花。还有波提切利的两幅传世之作《春》与《维纳斯的诞生》,当时看着还脸红,但慨叹人体之美达到了极限。
我们沉浸在艺术之中,满脑子都是名画与名画家。除了练基本功之外,马老师还领我们参观过两次美展,一是大连15中的师生展,这是很有名的美术中学,到现在也很闻名;一是金州文化馆举办的画展。跟我很要好的吴同学,个子不高,除了画画,也爱好写作。金州回来之后很是兴奋,写了一篇文章,一起走路的时候还背给我听:“我从车站广场一路走来,过了一街,又是一街……”。其得意洋洋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后来学校也举办了美展,我得了三等奖,奖品是两本小书:彩色版《张思德》,另一本是文艺评论集。
那时是1972年,在文艺上值得纪念的一年。恰逢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好像老人家还批了一个文件,说是“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对文艺出版不满意。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打破了沉闷的空气,陆续重版了《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鲁迅著作单行本,修订重版了《沸腾的群山》《高玉宝》《闪闪的红星》等。各地方出版社也纷纷行动,出版了一批那个时代的文艺新书,虽然“左”的色彩极浓,但毕竟情况有所改变。也就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订阅报刊。首先是马老师帮我们订的浙江出版的《工农兵画报》,横16开,薄薄的20页,连环画为主,中间插页为彩色,刊登各类美术作品。我至今对这份刊物留有印象,刚订阅的时候是旬刊,每期定价为7分钱。翌年改为半月刊,定价为1毛钱。当时是集中邮到马老师那里,一小捆,然后分发。我一直订到毕业,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感谢国内几家大型数字图书馆,让我有机会重温了少年时的阅读。
美术小组的人和事
美术小组的日子是快乐的,我结识了不少师兄师弟。亚辉比我高一年级,人长得就很艺术。卷曲的头发经常使我想到普希金。这位仁兄成为我一生的至交。画画方面我得到他不少帮助。后来我爱上了文学,曾跟他约定,将来我的文章写好了,让他来做插图。他先于我下乡,等我毕业,他去了部队,也算是文艺兵,在部队做文化宣传以及电影放映工作。1975年,我写了一首五言叙事诗《大锤的故事》,先寄给他看。他来信告诉我,他把我的诗歌刊登在部队的宣传橱窗里,战士们反映不错。这给了我很大鼓舞,于是就又寄给了市群众文化艺术馆。那年代作协之类的机构基本停摆,群众性文艺创作一般归群众文化艺术馆负责。我还真等到了群众文化艺术馆的回音。那是在公社广播站,我发现他们的一封关于举办业余作者创作学习班的通知,上面就有我的名字,但因种种原因我未参加学习,成为大大的遗憾。部队的亚辉知道我喜欢书,经常寄书来。印象最深的是《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上册,当时是内部版的,是法国人写的一部空想社会主义作品。我读得很认真,其中关于服饰的论述,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说服饰的美是对别人的尊重,在那个穿着清一色的年代,我不敢炫耀他的观点。恢复高考那一年,我考入了师范中文班,学校竟然距亚辉部队驻地仅一站之隔,都在海边上。于是星期天就成了我们切磋的日子,或者他来,或者我去。后来亚辉爱上了摄影,并一发而不可收,转业后到了一家报社,担任了摄影部主任。经常在媒体上见到他的作品获奖,还参加过一次他的个人作品研讨会。如今亚辉在摄影界已是名人,镜头下的普通工人形象和深厚的城市文化成为他艺术创作的主旋律。早期的美术爱好与实践,肯定对他的摄影的优异成绩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我与亚辉是属于不常见面的朋友,无事几年不联系,有事的时候随时都行。那一年,长春的《书友周报》牧人来电话说,他的家人孩子等要到大连玩,他有事来不了,让我帮忙接一下。正好我当时有事需要外出,于是我就委托给了亚辉。其实我跟亚辉不在一个城市,我是在县城里工作。从接站到送站,亚辉全替我做了。我几次到亚辉所在的报社参加征文颁奖,只要我不回家,晚上亚辉也不回家了,与我彻夜聊天。
青云与亚辉同年级,是亚辉介绍我俩认识的。亚辉说青云父亲是“五七战士”,他是随父母下放到农村的。除了爱好美术,家里书很多,轻易不示人。青云家在小镇边上的一个四合院里。就是冲着书,我去了他家。巧得很,正好他从天棚的梯子上下来。原来听说过他的书就藏在天棚里,这下子被我逮个正着。谁知这位老兄比我还精,首先“发难”,问我都有什么书。正好我手头有一本50年代山东大学版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就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借了他的《青春之歌》。当时还叮咛再三,严格守密。那年代,若是谁读了《青春之歌》,可不得了。后来,青云全家回城了,就很少见到。据说青云安排在城里的博物馆工作,在文博事业上颇有建树。
也有酷爱画画却不屑与学校美术小组为伍的。我们班的高献就是其中的一个。高献个子高高的,坐在最后一排,平日爱有些滑稽的举动。那时的电影品种很少,除了“样板戏”,就是“三战”片。国外的主要是苏联早期的,朝鲜与阿尔巴尼亚等。《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也是那时的经典。高献最喜欢模仿影片中的对白,如列宁演讲的手势,卫队长马特维耶夫的话语。他平日也喜欢画列宁,主要是临摹当时上海出版的两本小人书《列宁在十月》与《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均是线描。虽然署名是某某美术创作组编绘,实际上都是名画家被“结合”了进去,由他们完成的。北京人美也出版了连环画《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与上海的风格截然不同。当时我们无论是美术小组成员,还是其他爱好美术的,主要的学习手段就是临摹连环画。譬如我喜欢临摹高尔基,版本是人美版的根据高尔基的三本同名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改编的。高献喜欢临摹列宁,也有欣赏杨子荣的。总之,在美术普及读物甚少的年代,唯一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大概就数小人书了,尤其对喜欢画画的孩子而言。
高献与我关系甚好,我放学的路正好路过他家,于是他的小屋就成了我们谈天说地的好地方。在学校他一般不谈画画的事,可到了家里就不一样了,把他保存的许多好东西拿给我看。那时已经是1973年了,新来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是吉林大学毕业的海鹰老师,年轻漂亮,还爱好篮球与排球。她课余领着我们去割草卖给奶牛场,类似于后来的勤工俭学,用割草换来的钱来买篮球排球足球。一下课海鹰老师就跟我们围成打排球,余下的钱用来购买图书,建立了班级图书角。当时我的兴趣已开始转向语文了,是班级的语文科课代表,管理图书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我本来就喜欢书,得到这个差事心里美得不得了,找到亚辉,花5分钱买了一块橡皮,刻了一枚“二中九五”(“九五”指的是我们九年五班)的藏书印,每本书都在封面、扉页与第10页上盖上这个藏书印,下面还有分类与编号,俨然正规图书馆藏书。图书大约100多本,其中最有价值的我认为是高尔基的《母亲》与《列宁回忆录》。快毕业时,《母亲》被平日并不善言谈的一个男同学借去,《列宁回忆录》则不知怎么辗转到了高献手里。我预感到这两本书将有不测,尤其是后一本,因为高献那么欣赏列宁的形象。果然,毕业时清点图书,高献对我说,你不用找了,包括《母亲》这一本,肯定不会回来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毕业了,高献竟然把那本《列宁回忆录》郑重地送给了我,说:“就知道你不会带走一本书的,给你留个纪念。”我到现在还保存这本书,并放在书架的明显处。我不知道这算是同学的友谊还是多少有点“徇私”。不过我心里还是很感激高献的。
广阔天地里结识的农民画家
1974年7月12日,我中学毕业,直接回到我家所下放的大队——红果大队。这是坐落在小镇边上的一个大队,城乡混居,人多地少,以果树为主,当时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省报市报经常报道。按照当时大队规定,该大队每年从中学回来的毕业生,一律安排到“治山连”(后来改名叫创业队)锻炼,专门治山治水,搞农田基本建设。当时还有一句顺口溜,称:“进了治山连的门,改观换了魂;出了治山连的门,要做革命的接班人”。治山连是民兵建制,下有排和班,连长、指导员、副连长、排长、班长等,常年奔波在全大队9个生产队的沟沟岔岔里。夏天地里长庄稼,我们就修水库;冬季农田空闲,我们就造梯田。每天早晨上山劳动前,先做广播体操,间休时唱歌,会战时漫山遍野红旗飘扬,战歌嘹亮,工地广播站是重要的工具。我在这里一干就是三年半,一直到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3月重新读书。这是我走上社会的第一站,不仅仅是学会了抡大锤,推单车,能挣“大寨工分”一等工,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跟我岁数差不多的青年,也初步了解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功能。三年里所见所闻的事情各式各样,跌宕起伏,甚至也可以说崇高与卑劣同在,生存与抗争并存。这些留给别的系列再写,现在仍说说文化的事。
最先认识的是大队会计主任老曲,能写一手隶书字。那时经常写标语,还要办板报,我已经当上了大队报道员,同时还办大队部门口的两块黑板报。老曲就是我的师傅,说话有些结巴,但人特别好,对我很照顾。他保存了许多老小人书,连个书角都没有折过,平日都放在柜子里。他是大队党总支委员,所以了解大队的人事安排等许多敏感的事情,从他的表情和话语,我能及时了解大队干部对我的态度,总而言之,大队干部是不怎么喜欢我的。我之所以能当报道员,还是母校的老师说了好话。那是我刚毕业一个星期,正赶上修水库,因为技术活如推单轱辘车,打炮锤都不会,就挑土,一个星期才换活。我的两个肩膀全都压肿了,真盼望还像上学那样有个星期天。就在第七天的早晨,工地上的广播喊我到广播室去,连长通知我到公社参加报道员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看到了好多我们这一届的同学,大都是语文学得比较好的。公社广播站站长原来是文教办的,他告诉我们,为提高全公社的报道水平,办班前,他特意去了学校了解毕业生的情况。原来如此。
老曲话语并不多,但眼神就能透露出许多意思,有时看到对我不公时,明面能说就说,不方便时就用眼神安慰我。因为那时招工,推荐上大学等对我们青年人比终身大事都紧要的事在我们这先进大队经常光顾,但总也轮不上我,我的前几任报道员都当了工人,我的同期一起学习的报道员当工人了,我之后的理论辅导员被送进大学。这些好事都远离着我。其实我心里清楚,问题不在于我干的好坏,在那讲阶级斗争的年月,我都几乎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列,怎么可能被贫下中农推荐?谁敢推荐?但我感谢老曲对我的关照,那些年里,我爱看报,老曲就帮我订阅了《光明日报》和《参考消息》;本来应该是我去县里参加优秀报道员学习班,大队却派了别人去,得到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老曲得知后,把大队部存放的一套送给了我,说我写报道能用上。这些虽说都不很正规,但扭曲的年代里,我感到的是温暖。后来我上师范读书,回来看望他的时候,到书店买了本《罗丹论艺术》赠送给他。
林钧相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刚毅。他跟我不是很熟,但我却一直关注着他。中等身材很消瘦的林,当时是公社电影放映员,工作地点是公社文化馆。林的最大喜好就是画画,那时他才是真正的美术爱好者。据说他很能吃苦,家离镇里很远,经常连续几个星期不回家,下乡放电影时吃派饭,在文化馆里待着时,经常是凉饼子就咸萝卜,而刻意不变的是对美术的那种痴心。1975陕西年户县农民画出了名,我们这里木刻渐成气候,当时全公社爱好木刻的人有好几十人。我认识林钧相时,他就是以木刻出名,我看到他作画时的情形,全神贯注,手法娴熟,就感觉他的很瘦的手指本身就是艺术品。
当时的旅大电视台来采访我们公社的农民画,公社革委会主任(相当于后来的党委书记)把机关唯一的一台老式吉普车给记者用,我当了向导。采访了周边好多地方,最终把镜头集中到了林钧相身上。
除了版画外,林钧相还开始了连环画创作,最先出版的是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故事的《战斗在三一三高地》,现在被连藏者称为经典收藏品;以后的几年里陆续出版了《暴风骤雨》《官岱里的战斗》《海上擒敌》等。后来发现林钧相艺术兴趣广泛,制作陶艺,又转向写意的水墨画,出版了《林钧相的水墨艺术》。在我所接触的当年画画爱好者的队伍中,林钧相是真正的画家,现在已达到了有着自己风格的一种艺术境界。
家乡小镇人杰地灵。插队农村期间,还有一批美术爱好者,忠深,青山,小泉等等。前几年家乡街道创办了《三十里堡周报》,彩色印刷,图文并茂,每期二三十版,一反工作简报式的官样八股,大篇幅记录百姓生活,社会新风,百年小镇文化名人,深受家乡人民的喜爱。每每新报一出版,大家都争着到各社区(村)领取阅读,成为小镇一道亮丽风景线。我每次回家都去取几份,平日里就从家乡的微信公众号里阅读,几乎一期不漏,并把她称之为家乡的“人民画报”。从这份周报上,我还经常看到那个年代我所熟识的美术爱好者的身影,书法绘画摄影以及民间剪纸雕刻等等,他们均被刊登在“小镇名人”栏目里,我为此感到欣喜万分。
我由懵懂的兴趣出发,度过了一段不长的学画时光,画没学成,却培养了我始终都是一名忠实的美术欣赏者。多年订阅美术报刊,闲暇时翻阅当成一种艺术享受,那一年参加读书征文获奖,把近千元的购书券全用来选了《中国书画欣赏词典》与《艺术家》杂志等。由于对美术的偏爱,挑选文学书籍,最爱插图本。少年时代早已过去,但美好的东西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忘,反而更加清晰了,所以写下了本文。祝福我的学友,祝福我早年的朋友。
责任编辑 刘佩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