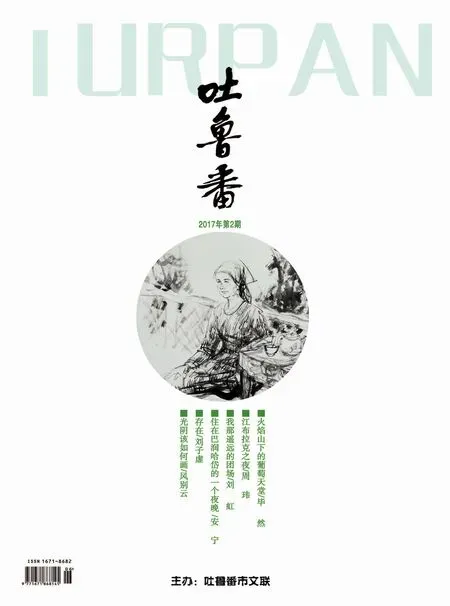我那遥远的团场
●刘 虹
我那遥远的团场
●刘 虹
初夏的早晨,这关中平原上的小城,早已炎热。往回总有风,徐徐,或粗鲁地吹,可今天,风热得躲起来,不知跑哪纳凉去了。若在故乡,这时节不过是春天伊始,万物复苏,山坡透出浅浅绿意,冰雪融化在山谷里。一轮红日,粘着草原上的露珠,从地平线冉冉升起,憋闷了一个冬天的牛羊撒着欢儿,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连队的人家,烟囱里冒起一缕缕炊烟,携着夜里的梦境,裹着奶茶的清香,粘着女主人的歌声,在蓝空,和一朵朵白云相遇,缠绕着飘向远方。
可现在,我在家,远离故乡的家,哪也不想去,谁也不想见,拒绝所有社交活动。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新常态,至少有五六个年头,一直都这样。除上班,除必要的采访,工作以外的任何社交活动,都抵制拒绝。
不是特立独行的人,却不愿让身外许多事干扰我的孤单。风卷浮尘的热闹,觥桄交错的应酬,圆滑的处世之道,令我厌倦,更多时候,宁愿眷恋一张床的平静。这世上,再没有比一张床,能给予我更多快乐与安详。床不大,能承受整个世界的悲伤。床无语,能温暖整个人世的冰凉。
这便是我胸无大志的人生,最精彩的华章。头安放枕上,四肢舒展,心便流淌成山野冰雪融化的泉水,叮咚之声轻快灵动。这时,寂寞隐退成山林中的薄雾,愚钝的头脑,如春天的林子,一夜雨后,长出那么多嫩芽,伸着纤细的手臂,向高远的天蓄势而发,一点点繁华。
于是起身,坐在电脑前,敲下一个个文字。我的心,我的思想,我的世界,在指尖下闪烁,跳跃。它们是一只只蝶,从一朵朵花苞里,探出精致的脑袋,身子,长长的触角,在空气里试试风的方向,然后抖动翅膀,向那个时空,向生命里那个春天飞去。
在塞外,在中国的边境,广袤厚重的草原上,冬雪覆盖了一层又一层,它们给低矮的房屋,盖上厚厚的棉被。雪,围在窗口,围在门口,偶尔露出那么一点光亮,光亮里腾起热气,热气里晃动的人影,那是生活殷实的人家。夜晚,寒星满天,装点圣洁的世界,天地纤尘不染,空气如加冰的饮料,冰凉甜美,吸进去,满胸满肺清爽。这样的夜晚,若有皎月,明晃晃挂在天山的雪峰上,那么整个童话世界,便温馨起来。
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温馨的童话。童话里白雪皑皑,雪山和苍松披上银装,连队通往外界的路,一排排挺拔的白杨肃然静谧,那是大自然这个伟大的艺术家,精心而作的冰雕作品。树林边逗留的马儿,也披着银色盔甲,现在,它们不需打仗,它们是掉队的士兵,三三两两,在雪地里觅食。一群群乌鸦站在电线杆上吵架,它们的外套,和世界黑白分明,形成鲜明对比,它们拍打翅膀,大声喧哗,争吵自己为什么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不能和世界融洽。
童话里我的乡亲,向我微笑。男男女女围着火炉,壶里的水在炉上咝咝作响,红砖茶在茶缸里泡了一遍又一遍,炉灰里埋着洋芋,香味在室内悄悄弥漫。他们说着祖辈们说过的话,讲着祖辈们口里流传的故事,交流着祖辈们传授的生活经验。他们表情生动,笑容灿烂。
这是一幅画,画里的童话,永远鲜活在三十年前那段时光。以后,随我的衰老,我的年岁,这个数字将逐年递增,但童话永远年轻,像一颗封存的珠宝,在记忆的深海,熠熠生辉。
常思考小康这个字眼。如果,小康需要牺牲纯净的精神世界,把人类的智慧,无休无止地用于开发财富,开发资源,填补日益膨胀的物质追求,甚至抛弃灵魂美德去服从肉体享受,不顾子孙后代,破坏环境,为眼前利益,身心疲惫地屈服于金钱奴役。如果,这就是人类对小康生活注解的全部意义,那么,我宁愿让我的心,昏睡不醒,让它永远在三十年前的童话里,那段殷实的日子里游荡,永不醒来。
殷实,多少有点知足的意味。殷实,是顺应自然,和它们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关系。兵团的连队,土地肥沃,让人不愁吃喝。人们住着低矮的土坯房,房顶铺着木板,木板上糊着厚泥。这样的房子就地取材,不浪费物资,也因气候设计,冬天保暖,夏天凉爽。冬天,大雪覆盖着房顶,犹如给房子盖上雪狐大氅,这就是整个童话里最奢华的画面。夏天里,房顶芳草横生,野花漫漫,给房屋添了不少妖娆。也不用担心夏季房顶会积水,因为从来都不会有连阴雨。雨像年轻人敏捷的身手,快速而不邋遢,不做无聊滞留。雨后,路上的石子被洗的发亮,浅蓝,深蓝,浅绿,墨绿,白的,黑的,花的,铺了一地,新鲜可爱,小巧精致。
雨后的天,柔软的像一匹刚刚从染房出来的蓝缎,天空同时出现几道彩虹,那是天女举行盛大的彩锦展览会。它们看上去那样近,仿佛触手可及,便忍不住要去赏玩锦缎的华彩。于是,不顾了脚下的泥泞,不顾了裤腿的湿凉,把臂张成翅膀的模样,远远地举着,举着,让风从指间一缕缕穿过,让风从腋下一片片滑过,托着臂朝着彩虹的方向飞去,去触摸那一弯虹影。眼看着近了,近了,那虹却不见了影踪。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风助麦涌,滚滚而去天边,直到和一脉远山融为一体。
麦田包围着连队的房子,它们一排排,一队队整齐排列。每排房前都有一排小房子,用于装煤炭,杂物,储备粮食之用。门前院子边种着杨树或柳树,杨是大叶杨,柳是红柳。有的人家,会垒起一个花池,撒上虞美人,八瓣梅的种子。八瓣梅,就是现在到处宣传的格桑花,可在连队,没人叫它格桑花。每朵花儿都有八个花瓣,人们叫它八瓣梅。六七月份,那些五颜六色的花儿开放,吸引左邻右舍的女人娃娃前来观赏。
夏季,多么短暂啊。那些花儿,没有开几天,冬天就来了。爱美的女人,柜子里的花裙,没来得及穿几次,就要收藏。娃娃们,还没在草丛里玩够,天就冷了。短暂的东西,总令人珍惜,夏季留给人的美,要用长长的冬季回味。
那时,人们对世界的破坏很小,索取很少,足迹只在方圆十几里活动,活动主要目的围绕产粮,为解决生活必需。还有,就是为美化环境,在连队周围种植树木。所植树木比较单一,除榆树,红柳外,就是成片茂密的钻天杨。除此,没有太多物质需求,无需思考太多挣钱方式,人们不懂得钻营,钱对人来说,满足基本需求就好。就连夏季,那种卖冰棍的营生,也不会有哪个大人愿意干,那是孩子为挣几个作业本钱去干的事情。如果大人干,自己觉得丢人,别人也瞧不起。团场,没有丰厚的物质生活,除了公家开的商店,没有谁做什么小生意。人们的价值观,还没有对做生意充满热情。
连队的商店,只有针头线脑,花布尼龙袜。当然还有油盐酱醋,烟酒糖果。烟是莫合烟,好点的是红山,雪莲,天池等纸烟。男人们更喜欢莫合烟,他们把孩子废弃的作业本,或者看过的报纸,裁成两指宽的条,撒上烟丝,卷成卷儿。旧报纸是卷烟最好的选择,韧而不硬,软而不糟,易于成型。卷烟,是个技术活儿。别看男人粗壮的手指捏不住针,可卷起烟来,却十分灵动。几个男人,常蹲在墙根下,晒着太阳,抽出纸条,分享一袋烟丝,比卷烟儿,看谁卷得好而快。那得第一的,定是有许多年烟龄了。烟卷好,点燃,深吸一口,吐出浓浓的烟雾,便觉得十分带劲儿。生活就有了极大满足,所有的辛苦劳作,仿佛都为这吞云吐雾间的惬意。
酒是伊犁大曲,简易的玻璃瓶,一排排摆在木制货架上。糖果是石河子食品厂生产的孔雀、米老鼠、熊猫,或者奎屯食品厂生产的金鱼,金猴等奶糖。新疆不缺鲜奶,有的是生产货真价实的奶糖原料。这些以动物命名的糖果,让娃娃们欢喜。那些南方才有的动物,印在糖纸上,在北国茫茫冬天,充满生机,甜美着娃娃的味觉,也填补了娃娃的想象。可见,那时糖果是用来哄娃娃的,大人很少贪恋口腹之欲。大人们的生活欲望很简单,只为了一家老小的糊口而已。
秤是公斤秤,糖果,酱醋都是散装的,要自带家什,才能买回去。男人们,站在水泥砌起的柜台边,抬起一根手指,指点江山那样,指点他们想要的商品。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一件小小商品,都能换取全家人的欢欣。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幸福点很低,些许满足,就快乐得无法自已。
从九月底到来年五月初,漫长的冬天开始了。人们躲在白雪覆盖的屋里,两三家凑在一起,通宵打扑克。对输家的惩罚就是钻桌子,人不需要太多钱,也就没有学会玩钱。
有时,并不打扑克,聚在一起编织一个又一个故事。故事里的神话,故事里的灵异,在口舌和耳朵之间,不断生产着,需要着,咀嚼着,回味着。故事里,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原型总能在生活里找到蛛丝马迹,却一次次调动听者的胃口。质朴的观念,善良,孝顺,仁慈,在潜移默化中传递。
女人们,更多的是在一起纳鞋底,织毛衣。讨论服装的裁剪与缝制,毛线的花色与搭配,有时交流食物的制作。兴致来了,几个女人会在一起,做一些食品。南方的点心,春卷,北方的麻花,糖糕都摆到桌上。相互学习中,也会说起远在口内的故乡,亲人,小时候的事。那些事里,有苦难和艰辛,寒冷和饥饿。她们对眼前的生活很知足。
她们并不批评男人的懒散,也不抱怨自己的辛劳。这些手工,一家人里里外外,春夏秋冬的穿衣,都需要她们缝制。可她们并不着急,有的是时间去料理,如果早早干完那些活儿,那么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天,将拿什么打发时光。她们像吐丝的蚕,一点点,慢悠悠,用柔软的情丝,缠绕温暖的生活。
男人们,冰雪融化后,要投入辛苦的劳作。他们要播种,施肥,锄草,灌水,收割。一望无际土地啊,男人们,干得可都是体力活。所以女人们心疼男人,乐得让他们在冬日里养精蓄锐。
冬天唯一的体力活,大约就是去拉冰。心疼男人的女人,常常包揽这项工作。她们挑着水桶,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拉着爬犁,连队后面,有一个人工蓄水池。夏天天山上的雪水融化,涓涓而来,便在这里储存起来。水池很大,像一个小小的湖,水清亮甘甜,够一个连队人吃用。池水深蓝如玉,倒映蓝天白云,微风习习,波光粼粼。周围长满青草,盛开白的,黄的野花。池边有小蝌蚪游来游去,水面有白蝴蝶和蓝蜻蜓飞来飞去。冬天,水结了厚厚的冰,像白雪下储藏着玉。女人们带着手套,拿着榔头,凿子,敲开厚厚的冰,把它们放到爬犁上,拉回家,放到大盆里融化,便可以吃用。
冬天,没有新鲜蔬菜和水果,每家只有窖藏的白菜,萝卜,洋芋。叫娃娃来,用一根绳拴了腰吊下去,再吊一只铁桶下去,不一会儿,就提起一桶菜,再把娃娃吊上来,这些菜,够吃好几天。就这样,一冬天的菜,都是娃娃们下窖捡的。还有夏季腌制的一坛坛咸菜,菜花,豆角,萝卜干,蒜头,鸭蛋,酸白菜。主食以面为主,卤面,蒸面,捞面,汤面,扯面,拉条,换着花样。最不缺的是牛羊肉,几家人分宰一头牛,或驴,把肉大块大块在锅里红烧了,埋在雪地里,够吃一个冬天。
大块的肉端上来,大碗的酒摆上来,如果再有一碟油炸花生米,便是招待客人的最好佳肴。几个男人围在桌旁,就着火炉的红光,脱掉外套,或划拳猜酒,或天南海北瞎扯,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直喝到面红耳赤,天昏地暗,直喝到雪落无声,覆盖了回家的路,才打着哈欠,穿上外套,告别主人,慢腾腾散去。他们走进雪夜,在雪地上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很快,那脚印又被白雪深深掩埋。
家家户户的生活都是一样。就连室内摆设都是一样的。大立柜,高低柜,八仙桌,床头的箱子,后来有了那种双人带一个茶几的沙发。这些家具,大多都是自家男人的作品。那时的男人,不但聪明,动手能力也很强,他们不仅会木工,就是泥瓦活,也能摆弄两下。
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上海的,江苏的,也有四川的,湖北的,还有陕西的,甘肃的。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远离内地繁华,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走到一起。在团场,每年大雪封山长达几个月,几个月里,人们和外界断绝所有联系。冰雕玉砌里,自成一个世界,虽无桃花源的逍遥,但也怡然自乐。即使冰消雪化,也哪都去不了,没有便捷的交通,最远只是去县上,很多人,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走出去,回一次家。
他们把对家乡,对亲人的怀念埋在心底。不同风俗,不同生长环境,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口音,交汇在一起,又把各种民风习俗,手工技艺,互相融合到一起,就像不同的食材,放在一起,制作出一种新的食品。就这样,形成新的文化,新的风俗,新的语言,组成新的生活群体,渐渐成为一样的人,或者说同一类人。他们生活闲适,心态平和,不急不躁。他们,有着与世隔绝的恬静,自给自足的满足,还有雪峰苍鹰,草原落日所带来的雄浑苍劲,天地高远之大美。
冬天,那样漫长。
生活节奏,那样缓慢。
某个清晨,沉寂了很久的喇叭突然响起,一首欢快的乐曲,在连队上空飘荡,传进每个人耳朵。人们跟随音乐走出家门,有来自大城市,或者懂音乐的人听出,那是一首小约翰·施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即使不懂音乐的人,也对这首曲子非常熟悉。每个春天,它都会跟随春的步伐,纷沓而来,像季节的时钟,在连队上空敲响。叫醒沉睡的人们,叫醒沉睡的万物。
音乐响起,人们就知道春来了。
春来了,激昂跳跃的音乐里,天气温暖了,屋檐下的冰柱,啪啪断裂,一头栽倒地上。女人们大方地走出家门,卸掉厚重的棉门帘,打开门,让绿色的春风吹进来。卸掉窗外的棉窗帘,打开窗,让金色的阳光照进来。把关闭一冬的慵懒,蜷缩一冬的腻烦,统统赶出去,
春来了,简短热情的旋律中,门前的雪人开始融化,雪野开始融化,大地腾起白烟,土地变得松软,树木爆出绿芽。人们换上单衣,舒展筋骨,活动关节,让身子轻盈起来,让心情愉快起来。只有夜晚,环抱连队的水渠,还会结一小层水晶般的薄冰,重温冬日的故事。
春来了,充满生机的节奏里,人们踩着节拍下地干活,一辆辆拖拉机开进田野里,一台台播种机开进田野里。就连一群群鸡鸭鹅,也在生动的乐曲中,扭动笨拙的身子,跑进树林里。在茂密的树林里,八只脚的蜘蛛,早就在草叶间结好一张精致的网。
春来了,春天终于来了。
现在,我在家,远离故乡的家,想到了故乡的春天。
这里距故乡那般遥远,这里的天灰蒙蒙一片,这里的空气充斥着刺鼻的味道,这里的人们住着高楼大厦,开着四轮汽车,吃着山珍海味,白天挣钱,晚上消费,通宵达旦,恨不能把一天变成25个小时,26个小时。
我在这繁华的城市,躲在我的家里,想到了塞外的春天。窗外是火辣辣的太阳,但这不要紧,我可以泡一杯香茶,用整整一天的时光去回忆,去思念,去穿梭那段时空。打开电脑,让那首《春之声圆舞曲》,在我的室内欢快响起,我在散发着青春气息的音乐里,在键盘上敲下一个个文字。
让我的心花怒放,让我的心蝶狂舞。我看到欢腾的春天,人们跳着春之声圆舞曲,走向原野,把汗水,把青春,把希望撒向原野。
——记二团十七连党支部书记李长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