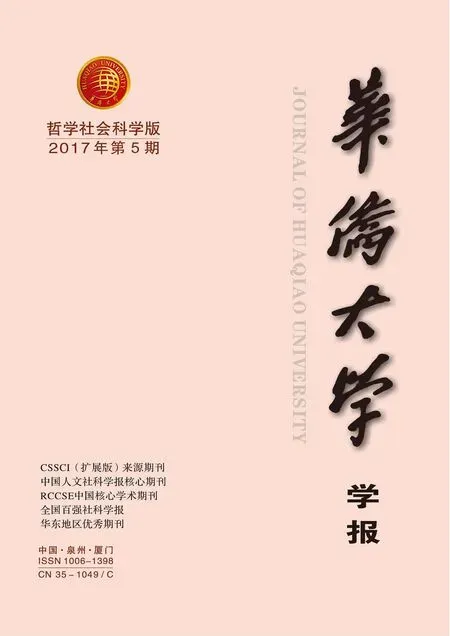论宋代奏议文论观的重道德人格倾向
○武建雄
论宋代奏议文论观的重道德人格倾向
○武建雄
宋代文论中缺少针对奏议的专门论述,无法考知宋人对于这一应用性文体的认识。但是宋代诗与奏议集序跋文对奏议的关注,表现出明显的重道德人格的倾向,宋人的奏议文体观念得以补全。宋人重道德人格的奏议文体观,有着文论家对文与道二层面长期论述为背景依托,并与重道轻文的观念相吻合。宋代奏议文论对道德人格的重视与强调,是帝王治政与士风重塑在文学观念上的映射,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体现出宋人文论观念的进步与超越。
奏议;文论;道德人格;士风
奏议是古代臣僚进呈君主的一种公牍文,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因行文对象的特殊性,奏议在写作时多讲究辞采、章法,因而又具备明显的文学性。
奏议肇始于君主制政体产生之初,至汉代时,形成章、表、奏、议四种基本文体类型。至赵宋时代,君主重视言路,士人参政议政热情高涨,奏议写作盛极一时,仅司马光一生写作奏议即多达351篇。与此同时,宋人热衷于编撰前代和当代奏议总集与别集,如《陆宣公奏议》《政府奏议》《国朝诸臣奏议》等。但与奏议写作繁荣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宋代并未出现专论奏议的理论著作或论及奏议的作品,因而对今人把握宋人的奏议文论观,无疑带来极大困难。不过,借鉴目前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对宋诗奏议吟咏与宋人奏议集序跋书写的解读,借以一窥宋人的奏议文论观念。
一
宋诗中有少量咏人而及奏议与因奏议而咏人的作品,诗人在吟及奏议时,表达了对此一文体的认识与理解。宋人咏人而及奏议和以奏议而咏人的作品,共有12首。分别为:
宋庠《赠浔州朱祠部》(《元宪集》卷十)
陈棣《沈德和使君生辰四首》其二(《蒙隐集》卷一)
晁说之《夜雨不少住枕上作》(《嵩山文集》卷九)
王灼《次韵答張迺直》(王灼《頤堂先生文集》卷五)
洪咨夔诗一首(韦居安《梅磵詩話》卷上)
姜特立《汪尚书挽章二首》其二(《梅山续稿》卷十三)
苏籀《读范龙阁五丈奏议三绝》三首(《双溪集》卷三)
《唐室》一首(《江湖后集》卷二十一)
王民瞻诗一首(分别见于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十四)
许棐《题陆宣公堂》(《梅屋集》卷二)
这12首诗,用抒情或议论的方法,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诗人对奏议作者或其作品的认识,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宋人的奏议文体观念。
宋诗咏及奏议时,借奏议以代表文人才华、学识。这样的认识体现于北、南宋之交苏籀《读范龙阁五文奏议》三绝其一。其诗为:“抚编屡叹才谟远,早岁升堂拜若人。亹亹聴言皆破的,龙虵蟠屈负经纶。”范仲淹为北宋仁宗朝名臣,以主导庆历新政名垂青史,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与参知政事时,屡奏谏疏言事论政,为后世赢得文名。苏籀此诗为读范仲淹奏议有感而作,诗中主要对其在仁宗朝时表现出来的富有远见的政见与卓异才识进行了盛赞。苏籀认为范仲淹的奏议切中时弊,亹亹破的,为时弊的解决开出了治病良方,其经纶才识幽奥深微如龙蛇蟠曲一样令人叹为观止。另外,陈棣的《沈德和使君生辰四首》其二,为祝贺秘书省任职的沈德和生辰而作,沈德和本人生平事迹无法考知,本诗写作语境决定了其措辞必为溢美,诗人在历赞沈地位尊贵、名德显赫以后,用“青藜照雠书,赤管供奏议”两句写其读书勤奋、并积极参政进言的状况。宋代统治者重视儒家意识形态,据汤建华研究,“宋真宗、仁宗时,州县学赐《九经》制度逐渐形成”*汤建华,唐金凤:《宋代州县学的赐lt;九经gt;藏书制度》,《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58页。,以期统一思想。宋代儒生经由科举入仕,进奏君主敷陈政见,奏议成为其展现才华、实现“平天下”政治理想的最为重要的媒介,因而宋人对奏议代表士人才华见识的认识,是奏议文体的自有属性。事实上,奏议的这个属性不仅为宋代所有,而且为历代共有。
宋诗吟咏奏议,更多从道德人格角度立意。宋代臣僚言事范围有着严格的限定,奏议多由台谏官员书写。帝王视台谏为耳目,并亲自擢授官员。《宋史全文》载:“台谏耳目之寄,祖宗以来悉出亲擢,自今毋托大臣荐进。”*李之亮校点:《宋史全文》中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61页。因而台谏官的品德与才学便成为重要的考量标准,虞云国总结为“严威刚直”“敏明不挠”“文行著闻,议论识体”*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2页。。帝王对台谏官的道德要求,根本上是为了巩固皇权的统治,而台谏官忠直进谏的品德,必然经由奏议得以体现。宋诗咏及奏议的作品,即多从写作者的道德人格角度进行立意,王灼赞美张迺直、洪咨夔颂扬唐坰即为此例。王灼《次韵答张迺直》一诗云“才如北海岂云疏,局促从来笑腐儒。只作文章希屈马,不将门户敌崔卢。公车奏议三千牍,京洛风尘十二衢。回首知君几多恨,肯甘华发老江湖。”张迺直其人生平无考,从王诗描写中可知其为洛阳士人。此诗中赞张迺直才华比肩汉代孔融,作文以屈原、司马相如为目标,甘于清贫不期富贵,在洛做官时尽忠职守,勤于进谏,数千谏书奉阙却难得一用,内心遗恨无穷,但仍汲汲以求,不肯终老江湖。王灼此诗中的奏议,已不只用来指涉张迺直才华,更多表达的是他以天下为计,关心国事的道德品行。全诗明显在塑造一个忠君爱国、心怀天下、淡泊清廉、勤奋治学的儒家士人形象,其中奏议代表的道德立意不言自明。靖康之难后,南宋诗人洪咨夔以诗论熙宁间史事,云:“君臣一德盛熙宁,厌故趋新用六经。但怪画图来郑侠,何期奏议出唐坰。掌中大地山河舞,舌底中原草木腥。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此诗意在激烈批评熙宁间主持新法的王安石,作为与王对立面的两个正面形象,分别为熙宁间向神宗献《流民图》的郑侠,与在金殿当面奏劾王安石的唐坰。其中唐坰不徇王安石荐引私情,而以公议为计,大胆纠劾王安石,让王安石出乎意料。诗人借“奏议”以表达唐坰的正直无私、勇敢无畏,显然认识到了奏议所承载的道德力量。宋庠《赠浔州朱祠部》一诗同样以奏议命意道德,其诗云:“粉署郎潜已十年,囊毫奏议委千篇。耻论頗牧云中级,去咏齐夷海国泉。路控驿疆逢瑞翟,气收炎浦見飞鸢。铃斋宴坐真腴盛,几种天花落帐前。”朱祠部其人不可考,从“粉署”一词推断其大概为秘书省郎官。此诗表达虽有仕途不得志而厌世归隐之意,但与此一立意相对立的“奏议”一词,突出的却正是其为官忠直尽言的道德节操。
非但如此,宋诗咏及前代文人奏议,也以道德人格立意。唐德宗朝时,谏官陆贽屡陈奏议,以犯颜直谏闻名,因此赢得了宋人极大尊崇,宋人赞忠直谏臣,时以陆贽为比。如姜特立《汪尚书挽章二首》,誉高宗、孝宗朝时忠贤正直的吏部尚书汪应辰为“千首歌诗如白傅,百篇奏议似宣公”宋人以忠直谏臣自比时,也引陆贽为同调,如晁说之《夜雨不少住枕上作》云:“陆公奏议同谁恨,屈子离骚亦独愁。”陆贽与屈原,后世多目以道德人格化身,晁引二人为同调,彰显个人品格的立意无疑。可见,奏议成为凝聚陆贽忠直品德的代名词。宋人直接歌咏陆贽的诗作,更为明显地侧重对其道德人格的褒扬。如南宋陈起《江湖后集》卷二十一《唐室》一诗,“唐室艰难势莫任,匡君奏议抵金鍼。塑人塑得先生貌,难塑当時一片心。”诗中论及陆贽以奏议匡时救世的史实,并指出宋人为其塑像,难以塑出其忠君爱国的赤诚之心,其中明显寓含着作者对陆贽道德人格的景仰。又如许棐《题陆宣公堂》一诗:“一编奏议从头读,句句冰联玉缀成。不是徳宗嫌切直,自缘唐室未升平。谄魂尽逐残星灭,义魄长随霁月明。我亦爱君忧国者,岁时来一拜先生。”诗人因奏议而讴歌陆贽,不吝溢美之辞,认为其如“冰联玉缀”的奏议,扫尽谄佞奸邪,体现出有如“霁月”一样光明的正义品格,表现出“爱国忧君”的道德情怀。
从宋诗咏人而及奏议,或因奏议而咏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宋人认为奏议一种文体代表着文人的才华学识与道德人格,而于后者尤为重视。作为承载政治见解与儒家道德的奏议,这二者为奏议文体所固有的属性,只是在宋代的突出强调,似乎显示着时代的集体认知。
二
宋诗咏及奏议具有重道的倾向,直指文人人格。如果说诗重抒情的特性使其对奏议文体的观照,多超越文体显性层面的特征的话,那么宋代序跋文章对奏议文体的叙述,或许更能说明宋人的奏议文论观念。
宋代序跋文章针对奏议进行叙写的,今存29篇,其中序文15篇,跋文14篇。序文有:韩琦《文正范公奏议集序》、曾巩《范贯之奏议集序》、苏轼《田表聖奏议序》、晁补之《何龙图奏议序》、杨时《邹公侍郎奏议序》、晁说之《韩文忠富公奏议集序》、李光《乐闲先生奏议序》、周必大《吴康肃公芾湖山集并奏议序》、周必大《黄简肃公中奏议序》、周必大《刘谏议谏稿序》、楼钥《范忠宣公文集序》、王炎《林待制奏议序》、叶适《胡尚书奏议序》、魏了翁《罗文恭公奏议序》、高斯得《沧洲先生奏议序》;跋文有:陈东《跋奏议》、李纲《玉局论陆公奏议帖跋尾》、陆游《跋钓台江公奏议》、陆游《跋欧阳文忠公疏草》、陆游《跋曾文清公奏议稿》、张栻《跋许右丞许吏部奏议》、楼钥《跋陆宣公奏议总要》、蔡勘《跋张大资政奏议》、陈宓《跋陆宣公奏议》、真德秀《跋傅侍郎奏议后》、真德秀《跋袁侍郎机仲奏议》、林希逸《给事丁先生奏议跋》、印应雷《跋第三书》、陈著《跋史独善奏议》。
宋代序跋文论奏议,少数以“文”立意,注重阐发其文学特征。狭义的奏议以议论为主,其文体原初功能为发表不同于时论的政见,刘勰《文心雕龙》称之为“议以执异”。*刘勰:《文心雕龙》,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06页。议论为奏议最基本的属性,议论的语言、方式、气势、风格及义理构成奏议显著的文学特征,宋人以此而论者,如陈东《跋奏议》以议论气势出发认为杨迈奏议“凛凛有生气”。*陈东:《宋陈少阳先生尽忠录》卷10,北京:北京市线装书局,2004年,第186页。王炎《林待制奏议序》以风格、辞采、气势评林待制奏议:“文章雅健,议论鲠切,笔力高远,言切而不浮,通达之识,劲正之气,悃欵之诚。”*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卷610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林希逸《给事丁先生奏议跋》以辞采、章法、美学风格评丁给事奏议:“简到而深切”,“春明玉洁,波折澜回,斡之毫端,曲尽其妙。”*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13,北京:北京市线装书局,2004年,第488页。陈著《跋史独善奏议》以辞采、风格论史独善奏议:“言外之意,隐而实彰,宽而实切”“明白洞达,劲正恳到。”*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卷8112,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50页。诸如此类评价,以文学特征视角审视宋人奏议,从语言形式、风格技巧、义理气势等方面的特征进行了揭示。然而对奏议文体以文学特征而论的,在序跋文中并不占主流。
宋代序跋文论奏议,多从“道”着眼,重视阐发作者的道德与人格。奏议为进呈帝王之文,作者的道德修养是立论的基础,奏议所阐述的主张又彰显着其人格,奏议文体对作者“道”的承载,有着显著的外在表现。宋代奏议序跋文评论文人奏议,正是经由儒家之道的阐发,进而论及其人格。此类论述不胜枚举,兹列数例如下:
束
*
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卷853.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李纲《玉局论陆公奏议帖跋尾》评陆贽奏议:“予观陆宣公,居仓卒扰攘之间,其奏议所陈,切中时病,屈折覼缕。皆根柢仁义,道理明白,真得作文之体,宜玉局之敬慕而不忘也。”*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卷374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苏轼《田表圣奏议序》评田锡奏议:“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安知来世不有若偃者举而行之欤?愿广其书於世,必有与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吕祖谦:《宋文鉴》,齐治平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65页。
真德秀《跋袁侍郎机仲奏议》评袁机仲奏议:“今观其奏疏遗稿,凛然精忠,无所回隐。”*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36,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第648页。
周必大《刘谏议谏稿序》论刘度奏议:“今公奏议心平气和,理正辞直,……上有问,据经对,不强谏争,惧章主过,削其稿,自后世观之光,果忠耶。”*周必大:《周益公文集》卷55,北京:北京市线装书局出版社,2004年,第242页。
魏了翁《罗文恭公奏议序》论罗文恭奏议:“论奏百数十,大义炳炳,甚至引裾排闼,号泣而随。”*魏了翁:《鹤山先生全集》卷54,北京:北京市线装书局出版社,2004,第266页。
从以上列举不难看出,宋人评论当朝或前代文人奏议,侧重对儒家道德“忠”“义”“孝”“仁”等的评价,而对文人道德品格的评价,又是与其正直无私、犯颜进谏、不徇私利而匡时济世的崇高人格相联系的。
宋代序跋文论奏议,部分兼论文学特征与道德人格。文论史上,论文有以“文”和以“道”而论两种标准,笔者此处所论的文学特征与道德人格,与文论史上的“文”与“道”大致相同,其细微差别后文将进行辨析,此处不妨借以用之。宋人奏议序跋,既以“文”论,又以“道”论的,如蔡勘《跋张大资政奏议》评张全真奏议:“其言仁而不肆,切而不迫,当于事情,达于国闦,而不离于道徳,贾谊、陆贽之学未能远过。”*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卷6255,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论文与论道相衔接。叶适《胡尚书奏议序》分论胡沂奏议,论其“文”为“词约而指要”“忧愤危苦,明白切至”,论其“道”为“恳怛忠尽”“富贵有节”。*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12,北京:北京市线装书局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高斯得《沧洲先生奏议序》论程公许奏议:“其词反覆曲折,足以周尽事理,其气忠厚恻怛,足以感悟上心,不沽激以近名,不矫亢以惊俗,而其爱君忧国之心,蔼然自有不可及者。”*曾枣庄,刘琳编:《全宋文》卷794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第158页。同样地,真德秀《跋傅侍郎奏议后》评傅侍郎奏议,其文为“辞气和平,直而不激”,其道为“精忠远识”。*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四,北京:北京市线装书局出版社,2004年,第607页。宋人序跋中这种论文与论道结合的做法,体现出儒家“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思路,是将奏议视为“文”“道”两个层面共同作用产物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此类序跋中,宋人以“文”论奏议,同样重视了其“道”的成分。
宋代序跋文论奏议,或论其“文”,或论其“道”,但重在论“道”,表现出明显的重道倾向。奏议文体对文人道德人格的烛照,被宋人充分发掘,这在奏议文体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
宋诗吟咏奏议,或宋文论奏议,较少关注其文学特征,而均表现出明显的重“道”倾向,并与文人人格直接相关。宋人的这一认识倾向,形成了奏议文论观鲜明的特色。由于唐代没有出现论及奏议的文论著作,唐诗与唐文也没有写及奏议,唐人对奏议文体的认识无由得知,因此,奏议文论重道德人格的倾向发生在何时,尚不能定论。不过,唐前文论作品多有涉及奏议者,正好将其与宋作一对照。
三国魏时,曹丕《典论·论文》在东汉蔡邕《独断》与刘熙《释名》辨析文体的基础上论奏议,他说: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魏宏灿:《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曹丕的这段评论着眼点有二,一是将奏议与其他各类文体相区分,分为四科八体;二是说明对各种文体美学特征的认识。他提到的奏议,其实是属于同一类别的两种文体,它们的共同特点为“雅”。关于“雅”,《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5页。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语曰:“雅言,正言也。”*何晏:《论语集解义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93页。郑玄注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从此可以得知,曹丕认为奏议这种文体,应该言谈正事而非小道,措辞优雅,音正义全,这属于文体特征层面的认识。
西晋时,陆机《文赋》论及各体文学,其中亦包括奏议,他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陆机:《文赋》,张少康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陆机所说的“奏”,当为后世所称的“奏议”无疑。陆机谈到的“奏平彻以闲雅”,似乎与曹丕的“奏议宜雅”有所相同,然而其内涵明显更广。《六臣注文选》中李周翰解释为:“奏事帝庭,所以陈叙情理,故和平其词,通彻其意,雍容闲雅,此言可观。”*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2页。李周翰认为,因为奏议是向帝王陈情言事的,所以要措辞平和,表意要明白易懂,风格节奏要雍容典雅。其中,对于“平彻”的解释,与宋人周必大评论刘度奏议“心平气和,理正辞直”,是相差无几的。这个观点结合奏议的施用场合与对象,谈奏议在行文、措辞、表达、风格方面表现出的特征,较有说服力。
南北朝梁时,刘勰《文心雕龙》在详细辨体的基础上,对各体文学的特征进行了系统论述,其中论赞奏启曰:
阜饬司直,肃清风禁。笔锐干将,墨含醇酖,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刘勰:《文心雕龙》,第424页。
论赞章表曰:
敷表降阙,献替黻扆,言必贞明,义则宏伟。肃恭节文,条理首尾。君子秉文,辞令有斐*刘勰:《文心雕龙》,第408页。。
刘勰对奏、启、章、表四类文体的这两段评论极富文采,个别词汇很难准确解释,但大体上可以看出,刘勰对四种奏议类文体的关注,着眼于“言”“义”“文”“辞”“理”几个方面,转换为现代词汇,即为语言、意义、文采、措辞、道理,这些方面涉及到的,均为文体层面的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见出,无论是曹丕主张的“雅”,陆机主张的“平彻以闲雅”,抑或是刘勰的论赞,他们所关注的,均为奏议作为一种文体的文学层面的特征,即“文”的层面,而没有关注到奏议对于文人道德的表达与人格的彰显,即“道”的层面,这与宋人重“道”的奏议文体观念形成了明显差别。
如果说宋人的奏议文论观总结于宋人对作品的评论,而曹丕、陆机、刘勰的观点源于直接的理论表述,尚不足以将二者对等比照,并得出宋前重文宋代重道的结论的话,那么,《文心雕龙》中刘勰对于两汉至晋时文人奏议的点评,当可以为之确证。兹引数例如下:
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刘勰:《文心雕龙》,第407页。
若夫傅咸劲直,而按辞艰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刘勰:《文心雕龙》,第423页。
刘勰评诸葛亮《出师表》为“志尽文畅”,评曹植《求通情表》《求自试表》为“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评傅咸与刘隗奏分别为“按辞艰深”“切正”“劾文阔略”,所关注处,不外文辞、风格、结构等方面,明显不出“文”的范畴。至此,可以明确结论,对于奏议文体立论:宋前重文,宋代重道。
四
从宋代治政与士风重塑层面考察,宋人论奏议重道德人格,实为宋代社会对儒家道德人格的内在需求在文学上的投影。
宋代承五代之绪,重建儒家道德人格为帝王治政的当务之急。宋之前的五代,十国分唐,军阀争权混战不休,士人朝秦暮楚演为常事,人心涣散,忠义节气尽失。《新五代史》描述当时情形:“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43页。有鉴于此,宋代帝王立国之初,即对倚重士人来重建儒家道德人格有着迫切需求与清醒认知。赵匡胤于国祚初开时,认识到士人群体对于道德人格重建的重要作用,特于太庙寝殿之夹室勒石三戒,其中之一为“不杀士大夫”*王夫子:《宋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页。,以养成士人直言敢谏风气。宋太宗时,着意提携“天子门生”,科举取士人数激增,欲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广建书院,颁赐《九经》,以兴文教。宋代帝王不仅重视言路,而且赋予台谏官员特权。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三》记载,宋真宗天禧元年,诏令御史台与谏院合并办公,职能混同,台谏官员由帝王亲自擢受。*《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台谏特许以风闻言事,而不必亲睹目见,为“仁宗庆历年间的政治实践中确立的。”*杨雄威:《政治常识的建构——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北宋台谏“风闻言事”特权化》,《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57页。宋代开国初帝王制定的对士人重塑儒家道德人格前后相续的政策,以“祖宗家法”的隐性威权为后代帝王所承继,开创了两宋言事士大夫重气节,以忠义相砥砺,修身立德,直言敢谏的开明政治局面。元人修宋史时,亦不无感慨地说,“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脱脱:《宋史》卷390,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9427页。。
重视道德人格的修养,亦为宋代士人群体的自觉要求。宋代帝王对言路的重视、对士大夫的空前礼遇与重塑儒家道德人格的寄望,增强了士人主体的社会责任感。在宋代特殊的政治语境下,士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与修身自我、担当天下的气魄胸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自省,与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抱负,无疑是士人群体人格自省的最好写照。在名臣巨儒的号召下,士大夫引相砥砺,涌现出一大批以忠义气节为尚、以犯颜直谏为忠的士人。《宋史·忠义传》描述当时名臣涌现的盛况道:“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脱脱:《宋史》卷446,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231页。《宋史·范仲淹传》评其“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脱脱:《宋史》卷314“范仲淹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277页。同样,苏轼盛赞欧阳修于仁宗朝对于宋代士大夫人格精神倡引的作用道:“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载《全宋文》卷1931,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崇尚忠义节气,重视道德人格,俨然成为两宋主流士风,历经神宗、哲宗朝新、旧党争,与靖康之难后的和、战之争,始终铮然煜耀,直至宋末而演为临难不屈,抗元死节的民族大义。
宋代士人对儒家道德人格追求的高度自觉,在文论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宋人论文以道德人格着眼,与宋代士风重塑的进程是一致的。仁宗朝时,文章家曾巩在给欧阳修的书信《寄欧阳舍人书》中论其文道:“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曾巩:《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3页。曾巩认为道为文的基础与前提,欧阳修正是因为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成就了文章写作的显赫声名。周敦颐《通书》中对道与文有着更为明确的阐述,他说“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周敦颐:《周子全书》,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第180页。周敦颐把文章分为道德与技艺两个层面,认为文章的核心在于作者道德的表达,而文本层面的言语文辞,只是文辞的艺术,没有道德表达的文,徒为华丽的辞藻而已。周的观点表达了明显的重道轻文的倾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宋人的观点。与曾、周稍异的是,部分宋代文章家在强调道的同时,从文以济世的观点出发,强调作者的道德实践与文章的社会功用,使文与道社会政治与主体人格相联系。如北宋中期欧阳修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提及:“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78页。欧阳修所强调的“君子为道”“知古”“明道”“履之以身,施之于事”透露出的,正是作者主体人格、社会实践与文学的统一。比欧阳修稍晚的王安石则进一步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他在《上人书》中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王安石:《王荆公文集笺注》,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1363页。王安石所说的“有补于世”的,指的是文章所承载的“道”,如“刻镂绘画”的辞,则是文学层面的“文”。宋人论文重道,并强调作文者的道德实践与主体人格,至此得到明确表达。以儒家之道论文,始于唐代文体文风改革的倡导者韩愈与柳宗元。但对道德人格的重视,在宋代文论中得到突出表达。
结 论
古代文论所指的“文”与今人不同,是一个既包括有韵之文,又包括无韵之文,既包括文学性美文,又包括应用性文体在内的宽泛而博杂的概念,今人多称之为“杂文学”概念。因而古人论文,当不独指涉纯文学文体,那么古人文论对文的阐述,也就不只针对个人书写的赋、书、记等文学色彩强的文体,也应该包括奏议、祝辞、铭诔等应用性文体。古人文论中对文道关系的长期关注与阐述,其中也必然包括对奏议文体的认知*潘链钰、李建中:《“经”“文”视阈下的中国文论话语范式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11-121页。。
即便古人对纯文学文体与应用性文体有着明确区分,论家论文时所指并不针对应用性文体,那么,从奏议文论家对文道关系的阐发,与纯文学文论家对文道关系的论述二者对比来看,也会发现两者表现出完全一致的趋势。文学自觉期的汉魏南北朝,论家对奏议文体的关注,停留在其文体的文学特征层面,奏议对文人道德命意的表达,尚未得到发掘。而此一时期,论家对文的论述,也多侧重辞采、章句、风格等文学特征。从唐代始,文体的载道功能被开掘,至宋代得到突出强调,并与作者的道德人生实践相联系。至于奏议,虽然唐代文论缺失,但在宋人的文学作品诗与序跋文中,以儒家之道论奏议并彰显作者的道德人格的观念得到了鲜明而生动的表达。因此,宋代文学作品体现出的奏议文体观念,与文论史上论家对文体以文道而论,至宋代时所阐发出来的重道观念,是不谋而合的,而这至少又反过来印证了,至少宋代文体观念中,像奏议一样的应用文与通常所谓的纯文学文体,并没有明确区分。故而宋人论奏议重视道德人格的倾向,有了宋代论文重道的大背景,以宋代帝王治政与士风重塑的内在需求为依托,结论的得出便显得更加充分。
任何文体均以文字为凭借,呈现为一定的语言文本形式,是为论家眼中的客体。而文字本身为人传情言志的承载,因而文体又具有了主体表意的意义。在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古代社会,主体表意主要表现为对儒家之道的传达与人格的彰显,是无须证明且必然发生的事实。从认知的程序来说,从文本客体至文本所映的主体情志的体认,是一个先后发生并渐次深入的过程。古代论家论文以及论奏议,所共同表现出的先及文学特征,后及道德人格的次序,由文本客体而及作者主体,正好吻合于人类认知的一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奏议文体观中表现出的重视道德人格的倾向,丰富了文论史的内容,具有深化及超越前代的意义。
文论观念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时代性。宋人论奏议重道德人格,是宋代社会帝王治政与士人重塑人格的主观需要,在文学评论领域的映射。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的角度而言,这一认识的出现,具有历史必然性。
【责任编辑陈 雷】
OntheTendencyofMoralPersonalityinLiteraryCriticismofZouYiinSongDynasty
WU Jian-xiong
Lack of exposition on Zou Yi in Song Dynasty’s literary criticism,we can’t know about people’s opinions on this practical writing in Song Dynasty.But it could be gotten from poems or preface and postscript in collections of Zou Yi in Song Dynasty,in which the tendency of moral personality is showed obviously.The Zou Yi’s view of writing stressing on the moral personality had a background of the literary features and moral expression in literary criticism’s history,which fits with the thought of the moral personality in Song Dynasty.The emphasis on moral personality in Song Dynasty is reflection of literature thought of the empires and administers and scholars personality,which is necessity of social hist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embodies the times’progress.
Zou Yi;literary criticism;moral personality;scholars’personality
武建雄,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滨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I207.6
A
1006-1398(2017)05-0107-09
2017-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