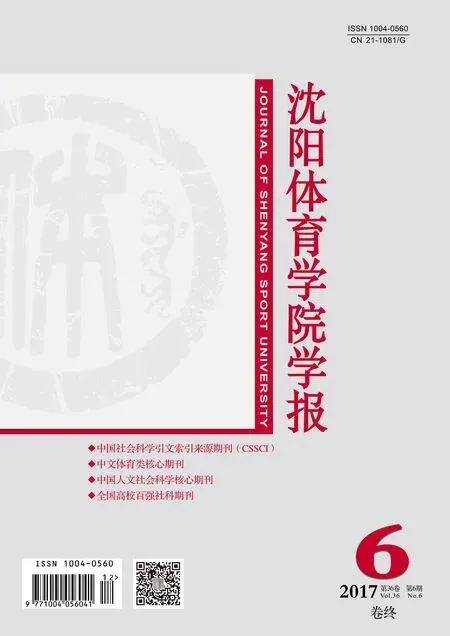运动伦理:理性现实下的感性反思
解 忍,王新雷,张晓丽
运动伦理:理性现实下的感性反思
解 忍,王新雷,张晓丽
(中北大学 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030051)
通过对《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一书进行通读,得知人们生活于被各种理性制度所压制的当今,只有通过体育这种超越于“社会进化”的感性文化对其进行抗衡,人们的感性思想才不至于被理性社会完全蚕食。然而,在努力由理性向感性过渡的过程中,运动伦理的存在成为人们的阻碍,它以一种“悲剧美”的存在混淆人们对这种超理性行为的认知。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阐述运动伦理的存在是社会系统的产物,同时也是历史哲学所遗留的问题。化解由理性走向感性中的这种阻碍,体育作为游戏的感性回归与作为感性工具的理性回归显得至关重要。人们在期望运动员具备强大意志的同时也需要其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运动伦理;体育;体育哲学;反思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问到:“人类有了技术和文化的巨大成就,文明为什么还不能使每个人都感到幸福?”在他看来人类的历史并不是一个逐渐完善的历史,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人类的本性也在不断地被现代文明所压抑,“文明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消除本能才得以确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抑制、压抑或其他手段)必须以强烈的本能不满足为前提的”[1],故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一直向社会规制所倾斜的历史。以历史悲观主义、冲突主义与虚无主义视角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对弗洛伊德哲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总结出“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压抑史”[2]。
人们不禁反思,在人类文明日益昌盛的今天,是什么压抑了人类的本性?笔者对我国学者李力研所撰写的《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3]一书进行通读。李将其概括为:在“自然的人化”过程即人类对外界能量的控制和利用的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在反向地控制和利用着人类自身,而这正是人类感到压抑、苦闷与不满的来源。李力研在陈述问题的同时也建构出了解决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在“自然的人化”过程中,只有“人的自然化”才能阻止理性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强大压制力量。笔者认为,“人的自然化”本质不一定是让人完全回归至大自然的浩瀚虚空之中,而应是在庄严的理性下夹带着微妙的感性,这种感性是阻止人完全沦为理性俘虏的有效工具,是让人感觉自身一直为“人”的生命来源。能将人类感性意识最好且最有力度显现出来的则是体育运动。体育是人生命的拐杖,是人在理性压抑下有力的感性支撑。
1 问题设想
李力研在全面地歌颂体育能带给人们感性力量的同时,也对体育运动进行了美的划分,认为体育之美包含崇高美与悲剧美。狭义的理解:运动员以优胜的姿态登上领奖台时,冠军形象、国歌奏起、国旗高扬三种情景形态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灵震撼,这是体育崇高美的显现;运动员在承受各种艰苦的训练、苦难、磨砺和巨大的期待之后没能成功,却依然能够以其坚持不懈、奋力拼搏、无畏拼杀的牺牲精神引起人们心头的共鸣,就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我认为那种明知自己跑在最后但还是咬牙跑到终点的运动员才是中国真正的脊梁。”这是体育悲剧美的显现。然而我们真的要完全赞成李力研和鲁迅的看法吗?
作为中国现代享有盛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弃医从文,由“医人”转为“医心”,由体力之启蒙转向心力之启蒙的做法着实让人钦佩。但是,鲁迅对体育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身体瘦小、体质孱弱,并且很少有体育锻炼的习惯。所以,这句名言的提出,完全是从精神意志的角度来阐释一种崇尚坚毅且顽强的人格品质。这种坚毅的品质是那个时代人们所需要的,是改变国家生存现状的有力武器。然而,这种品质可能忽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咬牙跑到终点之后的最终结果可能会造成运动员膝盖肿胀、身体虚脱甚或为他们以后各类隐性损伤的突发埋下伏笔。或者这样问,运动员明知自己体力将要透支,再跑下去无疑会给自身造成极大的身体危害,却因背负国家使命、社会舆论和企业赞助商的合约压力而选择继续带着伤病跑下去,就像北京与伦敦奥运会跨栏赛场上带伤参赛的刘翔一样,即使他最终拖着伤病跑到了终点,人们还会认为这是一种体育的“悲剧美”吗?
以上所述均为引出一个问题:李力研在赞同体育能带给人们感性生命理念的同时,却又在支持着体育悲剧美的存在。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主动还是被动角度论证,体育悲剧美是一种理性压抑的存在,将体育作为反抗理性存在的同时却又在赞同其悲剧美的伟大,这是自相矛盾的。体育悲剧美所倡导的理性精神是运动伦理的产物。
2 理论诠释
运动伦理最先出现于对运动员偏离行为的研究中。根据“临界正态分布方法”,运动员偏离行为可分为正向偏离行为与负向偏离行为,美国体育社会学者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与杰·科克利(Jay Coakleyi)将运动伦理视为运动员正向偏离行为的表现,主要包含以下4个层面[4]:1)运动员要为比赛做出牺牲,即要求运动员一切以比赛胜利为出发点,为运动献身并以大多数运动员伙伴的期待行事,不容置疑地接受竞争的要求;2)运动员要为表现杰出而努力,即运动员要不断地追求发展、力求更加完美、超越自身极限并最终达到顶峰;3)运动员要接受冒险和忍受痛苦,即运动员要自愿接受有害于自身健康和幸福的冒险,并以此为准则,向自身精神与肉体发起更高的挑战;4)运动员的追求永无止境,即运动员为了实现自己或他人所寄予的“期望”,不管遇到何种情况,都要努力去改变它、征服它、实现它,即使自己筋疲力尽、头破血流。杰·科克利笔下的运动伦理正是体育悲剧美的完美写照。
我国伦理学家刘湘溶在探究体育伦理时也指出[5],运动员通过竞技比赛不懈追求的目标应是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全面地发展自我,不断拓展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使人的内在“自然属性”与外在“社会属性”达成有机结合,实现协调发展。这表现出人类感性意识、感性行为或感性存在的整体性一面,是以全人类共同生存和发展为目标的整体意识。然而,现实的理性不仅对其进行压抑与束缚,而且还要瓦解感性的这种整体性。理性可以分化为不同的目标要求、不同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具体的行为手段。竞技体育中受到这种理性分化的影响,现今不合理的伦理表现:运动员为实现竞技目标,因采用过度训练、过度控制体重、带伤训练与参赛等手段而造成其机体机能与竞技能力之间的大大失调,进而导致运动员整个身体机制和心理机制都发生严重错乱的一系列伦理健康问题。这种竞技伦理严重地违背了发展体育的初衷,偏离了体育的真义。简言之,运动伦理即为运动员受外在理性意识(工业理性、组织理性、经济理性等)支配下,由自身“绝对的意志”向“相对的身体”发出挑战,其存在是体育本义正向发展的逆流,是人类社会理性异化的产物。
3 社会系统的产物:理性走向感性,运动伦理既是工具也是阻碍
运动员对运动伦理过度遵从的原因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阐释,而在每一方面中均包含着运动主体主动和被动的意识推动,主动中包含被动,被动中又关联主动,因承认被动而发起主动,因极力主动而又被动接受。主动的意识是向理性发起的挑战,被动的意识是对理性的顺从,可以说运动伦理的出现是社会系统的产物,纷繁错杂却又环环相接。“系统”是德国社会学家鲁曼(Niklas Luhmann)的基本概念。在他看来,任何一种人类行动以及与这种行动相联系的各种事件和过程,都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一般系统。尤其是社会系统,鲁曼把社会系统定义为各种社会行为的制度化模式,从整体社会到具体特定的行为模式,它产生于人们之间的行动关系,是借助于符号规则所进行的沟通[6]。
社会系统中的制度化模式是一种理性压制模式,而符号规则也是理性推导出的产物。利益本身为一种符号、一种欲望的代表,而欲望可以通过各种符号表现出来,比如货币符号、权力符号、审美符号、能量符号等,人类通过对这一类利益符号的获取而使自己更为感性地生活。然而,在最终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还要通过理性或超理性的付出。就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审慎’(即理性的智慧)对‘热情’(即感性的欲望)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人类全部历史的冲突。”[7]而这里的人类既包含运动员也包含各类从业人员。运动员依靠自身强大的意志向自己微弱的身体发出挑战,在利用绝对理性的同时也在被绝对理性所利用。从这方面来看,运动伦理的产生是人们在微观感性引导下因理性反噬而被动接受的产物。
另一方面,人类不一定要完全实现这一利益需求,才可以感性地活着或依照自己的本性而活着。在踏出理性之门之前,人们也可以依照自身固有的感性而生存,即依靠弗洛伊德笔下的“本我”而存在,然而这就需要“自我”兴趣的参与。“自我”兴趣在生活中会时刻调节着“本我”欲望,提醒人们要感受快乐,而不是感受痛苦。运动员出于对运动的热爱,因为兴趣使然,他们想要把自己变得更强,单纯的目的是为了在竞争中显示更多的优势,从而获取压制竞争对手的情感满足。在笔者看来,这仍是社会理性压制下的产物,运动员受到国家政治期待、社会舆论导向、企业商业催化、群体组织压力、队员集体行为等各类因素影响,他们只能在运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兴趣绝大部分为后天培养的产物,受训练时间影响,他们无从接触其他新鲜事物,所以只有在运动中不断突破才是他们的至高追求,兴趣也就在这种常年累月的训练中得来。从这方面来看运动伦理的产生是人们在宏观理性压制下因感性存在而主动追求的产物。除此之外,鲁曼认为过程就是系统,并且它具有一种结构,如果不是系统,它就不是过程,如果没有结构也就没有系统。系统的存在就是为了创建意义[8],意义对于人类经验和行动都是最根本的,而意义是由时间和历史所构成的,由意义起着最重要作用的各种事件,都是在其他各种可能性的维度内发生的[9]。由此可以推出(过程)系统即是历史系统,运动伦理的存在也是经过时间维度、物质维度和符号维度三种维度不断创建后而积淀下的产物。柏拉图《斐多篇》中的“灵肉分离”、笛卡尔《谈谈方法》中的“我思故我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绝对意志”等一系列理性主义者的思想都是对自身理性意志的赞赏,同理更是对自我感性肉体的贬低。所以从历史哲学角度而言,受传统“身心二元结构制”学说影响,为了创建出自身所谓的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运动员依靠自身强大的理性意识对自我肉体的不断冲击,甚至不顾肉体损伤的种种遵从运动伦理的行为不正是映衬着这点吗?由此,运动伦理的存在既是人类由理性世界通向感性世界的一种工具,更是一种阻碍。
4 体育的本源性反思
4.1 体育作为游戏的感性回归
尼采在《论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中提到:“只有在未被分割的当下才可能有幸福和行动,这是一条普遍规则。”而鲁曼对于社会系统的分析,主要是为了揭示当代社会不断区分化的机制及其各种可能的趋势,指出当代社会分化的特征及其所引起的一切复杂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分析不正是对当今理性现实下对残存感性进行不断瓦解的趋势分析吗?这正是现代社会不折不扣的理性特征。因此在社会系统的内部,人们急需一种超越于“社会进化”的感性文化对现代理性加以抗衡,使那些残存的感性继续为“人”所有。体育作为一种“人造的”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于社会进化的感性文化,在现实理性规则制度的压抑下早已丧失了其游戏本质,以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为代表的政治性、组织性、商业性早已贯穿于体育赛事之中。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席勒在其名著《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到:“只有当人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只有游戏,才能使人达到完美并同时发展人的双重天性(动物性与人性、感性与理性)[10]。”游戏不仅是表达、表现的手段,游戏本身就是生活。让游戏回归生活形式就是把游戏与人的存在紧密相连,只有与生活形式浑然一体的游戏才是人类真正的栖息之所。所以,将体育回归到一种纯粹的游戏是十分必要的。运动员只有在竞赛中尽量抛开人类后天习得的社会属性,将比赛看做一场游戏,在游戏中尽情展示自我,将自我所学、所获以一种“天然美”的存在展示给观众、也展示给自己,使自己在竞赛中与观众形成情感共鸣,这样就会使整个竞技场充满双向的情感输送,达成感性情感能量的仪式性串联。此时的体育才是一场游戏,不具有任何功利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快乐,而不是获胜。胜利之后的快乐是快乐,但它只会使胜利者与支持胜利者的观众快乐;过程之中的快乐也是快乐,但达成双向情感能量的仪式性互动不仅使胜利者及其支持者快乐,也会使处于劣势中的运动员及其支持者快乐,这才是体育真义所要达成的快乐。
当罗素还在其所理解的“审慎与热情不断冲突的历史”中徘徊不定时,其爱徒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则发出了颇有感性意蕴的时代呼唤,他认为只有当人将生活作为游戏来过时,并将竞技体育作为游戏去嬉戏、玩耍时,才能在生活中充分地实践人文精神[11]。体育作为游戏的感性回归,不仅可以增加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乐趣,还会减少其过度遵循运动伦理的行为。运动伦理的存在是运动员迫于现实而改变自身地位的工具手段,或者是被现实理性规则压抑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如果将每一场比赛单纯地视为一种游戏,运动员会真切地感受到体育的本质魅力,就像兴趣的习得一样,感性力量的习得也需要时间。运动员只有在每场比赛的感性回归中真正地获得乐趣,那么在日常训练中,他们才会以这种感性力量作为支撑。为比赛做出牺牲或接受冒险和忍受痛苦的非游戏性比赛不会让其感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他们不会继续选择尝试,这正是体育作为游戏感性回归的重要性所在。
4.2 体育作为感性工具的理性回归
体育作为游戏的感性回归是针对于竞技场中所有参赛的运动员而言,然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均具有特殊性,要让每一个运动个体都那样理解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对于个体主义者、绝对理性主义者而言,他们会认为当下的快乐不是快乐,即使是快乐,过程中的快乐也是短暂的,最终胜利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比赛过后用符号资本实现其他欲望的快乐才是永恒的快乐。怀有此类想法的运动员,一方面将体育视作一种工具,一种实现除比赛胜利外其他感性欲望的工具,但结果可能恰恰相反,这种实现其他感性欲望的工具反而会受到欲望的无限诱导而产生超理性行为。这种超理性是理性也非理性,理性意味着运动员意识到要想实现感性欲望目标必须采用一些超理性手段。例如以运动伦理为手段,认为只要以超出常人、超出自我极限的方式进行训练就会有所突破,最终达到运动顶峰。这种超理性手段可能来源于外部世界功利性的渲染,也可能来自内部群体顺从式的模仿;非理性则意味着运动员没有预估到这种超理性手段,即过度遵从运动伦理行为反而给其自身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仅最终目标没有达成,自己的运动生涯反而受到极大的危害,这无异于竭泽而渔、焚林而猎。这样的运动员在以解放感性为最终目的的同时却没有意识到马尔库塞否定性思维的存在,即在认识事物由感性上升至理性时,可能会使用某些超理性的行为作为手段,这时人们要对其加以否定。否定不是否定超理性,而是否定以超理性为最终目的的理性,这样才能使以获取感性为最终目的的运动伦理(超理性)的理性回归,只有运动伦理的理性回归之后,最后感性的永恒获取才能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运动员并未将体育作为实现日后自我感性欲望的工具,而是发源于内心深处的热爱,兴趣促使他们向自己相对的身体发起绝对的冲击,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胜利,获得压制对手的满足感。他们单纯地想赢,想赢的欲望促使他们不断地训练,不断地为比赛做出牺牲,甚至带伤参赛,为参与自身具有优势的公斤级项目而不惜以牺牲健康的方式来控制体重。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曾指出:“过度和不足的锻炼会毁坏体力,同样,超过或没有达到一定数量的饮食则会破坏健康;反之,适量的饮食、适度的训练既维持健康又可以增进体力。”而他们的这些做法是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工具来获取胜利的行为,与前者将体育本身视为工具获得赛后感性满足的欲望并无差异。所以无论是以自身身体为工具还是以比赛的胜利为工具,二者都以过度遵从运动伦理为表现形式。虽然最终结果存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但目的均是为了获得感性上的满足,前者是赛场之外依靠胜利获得更多利益符号式的感性满足,后者是赛场之内依靠胜利而获得当下情感符号的感性满足。由此可以推出,在实现感性满足的目标上,前者与后者相比,前者更为理性,因为他们将目光放得更为长远。与其这样评价,不如说二者均不理性,因为他们在实现感性目标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均发生了偏离,以挑战身体极限为工具和以体育产生的功利效应为工具,不是背离了身体的本义,就是背离了体育的本义。体育是通过有规则的身体运动改造人的“自身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12]。由此可知,体育的最基本任务是对人自身身体的改造,所以运动伦理的存在归根到底是在获取生命感性力量的指引下,以体育这种作为改造人的功能为依托,运动员在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理性手段发生偏离而产生超出规则的一系列行为方式的总和。
从运动伦理产生的外部原因分析,体育作为感性工具的理性回归要求运动员敢于正视自身身体的极限,抛开政治、组织、商业、历史传统以及社会群体舆论的压力,在教练的指导下,引进科学的力量与队友一同进行人本训练,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依据自己的承受能力执行训练计划,科学饮食,科学控制体重,勿要攀比队友、过度训练、带伤训练或比赛,总之一切“以己为本,健康为重”。从运动伦理产生的内部原因分析,体育作为感性工具的理性回归要求运动员认清理想与现实,理想是人们感性的追求,而现实却是理性的,人们要想以超越理性的方式来实现感性的理想,超理性行为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存在均要受到否定,即运动伦理必然要接受批判。如果在运动伦理这种超理性行为表现中加入“度”的标准来对其进行衡量,即运动伦理遵从实事求是、适度、适量的原则会使这种超理性行为真正回归至理性,进而超越理性,达成感性。就如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墓志铭所示:“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会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的光辉与有加无减的敬仰和敬畏:头上的浩瀚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头上的浩瀚星空启示人们要敢于追逐理想,心中的道德律令则要求人们须实事求是。不仅仅是运动员,对于每个正在遵从“生存伦理”的人来说,都要做到位其上者,感性天空;理性大地,在其心中。仰望星空之时,勿忘脚踏实地。
5 结语
回归引言,通过长篇叙述引出笔者在通读《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一书后的一种疑问——人们在极力用体育作为生存于理性现实中的感性支撑时,对体育悲剧美的存在是否持肯定态度?毋庸置疑,强大的生命意志不仅仅在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里(甚至更早),而是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每个个体均需要的。但如果这种精神被放大到某种功利性欲望符号之上,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冒身体之不韪而显意志之强悍,其存在则是值得褒贬的。运动伦理的存在,正是在理想引导下运动员与理性现实签订的感性契约。至于对契约的如何遵守、如何抉择,其决定权最终还是把握在自己手中。体育作为游戏的感性回归与作为感性工具的理性回归则显得至关重要。笔者愚钝,深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阐释问题,可能一不小心便会脱离实际,甚至好高骛远,但历史的发展总要以马尔库塞笔下的不断反思为理论源泉,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更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是对前人研究的一种敬仰。最后简为一言:“我认为那种明知通过一系列科学训练仍不及他人,会跑于最后,虽然内心失落,但仍咬着牙并健康地跑到终点的运动员,不仅是中国的脊梁,更是中国的血肉。”
[1]西格蒙·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M].严志军,张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3]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4]杰·科克利.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M].管兵,刘穗琴,刘仲翔,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刘湘溶,刘雪丰.体育伦理:理论视域与价值范导[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刘少杰.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7]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高宣扬.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9]N.Luhmann.The different of society[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10]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杨桦.体育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22.
Sports Ethics:Perceptual Introspection on Rational Reality
XIE Ren,WANG Xinlei,ZHANG Xiaol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 030051,Shanxi,China)
By reading the“Savage Civilization:The Philosophical Declaration of Sports”written by Li Liyan,I know that our lives are suppressed by various rational systems of today.Only through sports which is the perceptual culture that transcends the“social evolution”,our perceptual thoughts will not be completely disabled by the rational society.However,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from reason to sensibility,the existence of sports ethics becomes our obstacle,which exists in a kind of“tragic beauty”,and confuses our cognition of the super-rational behavior.The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conclude that the existence of sports ethics is the product of social system,and also keeps the legacy of historical philosophy.To remove this obstacle from rationality to sensibility,the emotional return of sport as a game and the rational return as a sensibility tool are crucial.We expect an athlete to have a strong will and a healthy body.
sports ethics;sport;sports philosophy;introspection
G80-051
A
1004-0560(2017)06-0088-05
2017-09-27;
2017-10-28
解忍(1993—),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
乔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