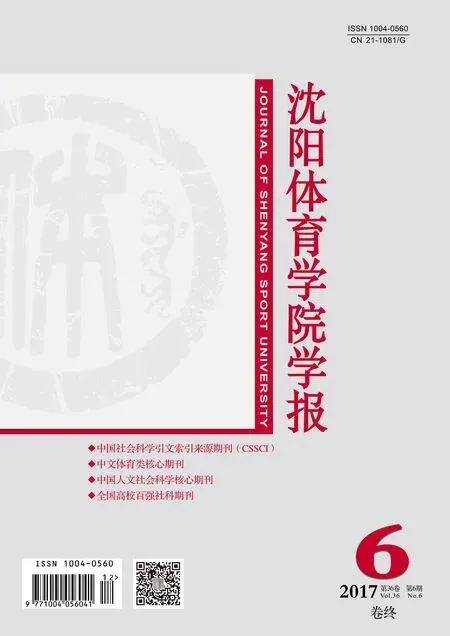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古典运动伤害治理
戴 羽,金鑫伟,曹景川
传统伦理视域下的古典运动伤害治理
戴 羽1,金鑫伟2,曹景川3
(1.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临汾041004;2.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研部,黑龙江牡丹江157011;3.山西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山西 临汾041004)
我国古代运动伤害治理受传统伦理影响颇深,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孝亲伦理影响下,相扑、枪棒等易发生身体伤害的活动多被禁止,法律甚至创设“戏杀伤罪”规制此类运动伤害;易发生溺亡的弄潮、竞渡等水上体育因儒家“死而不吊”的生死观而受到较大限制;在“人为贵”思想的支配下,体育意外事件的责任认定较古代西方更为严苛。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古典竞技体育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对抗性体育项目逐步被娱乐休闲型体育项目所替代,这也是造成中西方体育不同发展走向的重要原因。此外,受草原民族“赔命价”伦理习惯的影响,元代引入烧埋银制度使运动伤害赔偿成为独立的运行机制,但在“尊卑有序”“贵贱有等”的伦理观支配下,“同命不同价”被赋予身份正义的外衣。
传统伦理;运动;运动伤害;治理
运动伤害自古有之,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竞技体育、学校体育领域,古代的运动伤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古代运动伤害在传统体育(如角抵、骑射、竞渡)以及部分游戏、娱乐活动(如击壤、弄潮、弹弓)均有发生,其伤害类型大致包括相扑、枪棒等对抗性伤害,竞渡、弄潮等水上运动伤害,以及射箭、弹弓、击壤等远程伤害,我国古代法律对此均有相应的治理措施。与西方古代运动伤害治理相较,我国古代运动伤害受传统伦理影响颇深,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华法系不承认运动中的“自甘风险”,运动伤害责任认定严格,且多以禁治为主,对抗性强或有一定危险性的体育活动因伤害较为频发而受到较大限制。
运用文献整理法与历史分析法,探讨在传统伦理影响下我国古典运动伤害治理的路径与措施,并通过与古罗马运动伤害治理比较,分析我国古代竞技体育式微的原因。
1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与对抗性运动伤害治理
对抗性强的体育活动往往容易出现运动伤害,我国传统的角抵、拳棒是运动伤害频发的活动。角抵又称相扑,为“两两相当”的角力运动。五代以后,角抵在宫廷、民间盛行,据《角力记》载,宋人的角抵比赛“观者如堵,巷无居人”。民间甚至出现自发性的相扑组织——相扑社。相扑的流行使运动伤害频发。南宋高宗时,宫廷相扑手因“阅教闪仆”出现运动伤病,以致无法继续在御前当差,“(绍兴元年)十月二十一日诏军头司:正额等子彭遇等久在殿庭祗应,近因阅教闪仆伤病,不堪充扈卫祗应,特与免引呈,依合出职人例,陈乞外处院坊监及厢军见阙员寮”[1]。这是我国目前所见史料中最早的因运动伤病而无法履职的记载。《元典章》中也记录了相扑致死的案例:“至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书刑部符文:高万奴状招:与张歪头相扑作戏,万奴用拳于歪头左耳近下侵咽嗓打讫一拳,倒地身死。”[2]1445可见相扑因对抗激烈容易发生运动伤害,甚至致人死亡。
我国古代法律以“戏杀伤罪”对角抵、拳棒等活动造成的伤害定罪量刑:“诸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谓以力共戏,至死和同者。”[3]425《疏议》曰:“虽则以力共戏,终须至死和同,不相瞠恨而致死者。”[3]426此律所规制的行为是双方“共戏”,并非单独行为造成的他人意外伤亡。双方在“以力共戏”的过程中,并未有“瞠恨”的主观恶意,这是其区别于斗杀伤的主要标志。另外“戏”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大清律例》曰:“戏,以堪杀人之事为戏,如比较拳棒之类。”[4]800“共戏”双方对活动危险性有一定的认知,因此其刑罚要重于普通的过失杀伤。我国古代不承认体育活动中的“自甘风险”,只要运动过程中出现伤害,便需承担法律责任。这与儒家身体观、孝亲伦理紧密相关,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儒家孝亲伦理将身体毁伤上升到不孝的道德层面,其行为不仅辱身,同时也辱亲,“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礼记·曲礼上》)儒家身体观认为,只有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进行危害身体的活动,才是对父母的孝敬。
除“戏杀伤”的罪名外,历代政府也常通过诏令形式禁止“以力共戏”的体育活动,如宋真宗时的野场角抵禁令:“诏访闻忻、代州民秋后结朋角抵,谓之野场,有杀伤者,自今悉禁绝之。”[5]元代政府也下令禁止教习相扑、枪棒。“今后军民诸色人等,如有习学相扑,或弄枪棒,许诸人首告是实,教师及习学人并决七十七下,拜师钱物给告人充赏。两邻知而不首,减犯人罪一等。社长知情故纵,减犯人罪二等”[2]1940。该令甚至引入连坐制与告赏法,除练习者、教习者受罚外,邻里、社长知情不告者均需受罚,此外还许人告赏,以“拜师钱物”充赏金。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间相扑、枪棒的开展。明代以后,政府更加重了戏杀伤的处罚力度,“凡因戏而杀伤人、及因斗殴而误杀旁人者,各以斗杀伤论”[6],也就是说“至死和同”的戏杀伤与互相瞠恨的斗殴杀伤在量刑上一致,可见我国古代法律对于对抗性运动伤害的治理呈日渐加重的趋势,这与明代以后理学日益昌盛、孝亲伦理更深入人心有关。
2 儒家生死观与水上运动伤害治理
游泳、水戏等运动事故自古有之,《淮南子·诠言训》云:“度水而无游数(术),虽强必沉。有游数(术),虽羸必遂。”[7]可见先秦时人们已通过水上体育实践认识到游泳技术的重要性。除游泳外,竞渡与弄潮也是水上运动伤害高发的项目。
弄潮是宋元时风靡的水上体育活动,《武林旧事》载:“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而豪民贵宦,争赏银彩。江干上下十余里间,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饮食百物皆倍穹常时,而僦赁看幕,虽席地不容间也。”[8]可见弄潮儿在“争赏银彩”的刺激下“腾身百变”,各尽所能,而“席地不容间”“车马塞途”也充分说明该活动具有很高的观赏性。然而弄潮也是极具危险的活动,“竞作弄潮之戏,以父母所生之遗体,投鱼龙不测之深渊,自谓矜夸,时或沉溺,精魄永沦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滨,生也有涯,盍终于天命;死而不吊,重弃于人伦。推予不忍之心,伸尔无家之戒”[9]。竞渡也是运动伤害高发的项目,竞渡伤害正如《香山县志》所云:“其竞渡而夺标者,或劳伤,或溺死,或兴众大斗。”[10]除溺死外,竞渡伤害还包括劳伤、斗殴。宋人高斯得《西湖竞渡游人有蹂践之厄》形象描绘了竞渡事故:“唤船催入裹湖来,金钱百万标竿揭。倾湖坌至人相登,万从崩腾遭踏杀。府门一旦尸如山,生者呻吟肱髀折。”[11]竞渡者在“金钱百万”的激励下“倾湖坌至”,以致发生“万从崩腾”的“踏杀”事故,该诗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体育踩踏事故的史料。竞渡争斗殴击也常发生,宋代判牍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竞渡争斗死伤的案例:“舟道相遇,小人一朝之忿忘其身,刃石交下,赤龙舟偶以人多,舟覆,死者一十三人。”[12]
竞渡、弄潮者虽自甘风险,但沉溺事故屡出,这有悖于儒家的人伦大防,也与儒家基本的生死观相背离。儒家在生死抉择的命题上,是非常慎重的,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赤手与虎搏斗,不用船只渡河,这样死亡也不后悔的人,孔子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儒家看来,这并不符合成仁的要求。“舍生取义”是儒家倡导的所谓“善终”,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认为道义比生命更可贵,“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大诰》)显然因竞渡、弄潮等“奇技淫巧”而舍弃生命者绝非儒家所谓的“舍生取义”。短命夭亡、溺死等“不得其死”也为儒家所厌弃,《礼记》曰:“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礼记·檀弓上》)溺亡等非正常死亡在儒家看来即“不得善终”,甚至无法享用正常的丧葬礼仪。弄潮“死而不吊,重弃于人伦”,正属于孟子所谓的“非正命”。竞渡除溺亡外,且常伴有踩踏、斗殴事故,这不仅与儒家“死而不吊”的生死观相悖,也与“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孟子·离娄下》)的孝道伦理相悖,因此历代政府的竞渡禁令尤为常见。如宋太祖乾德元年四月“禁湖南竞渡”[5]88,开宝五年九月“禁西川民敛钱结社及竞渡”[5]2191。至清代,仍有禁止竞渡的法令,《(雍正)浙江通志》载:“俗好竞渡,每致溺,严禁之,归其舟为官渡。”总之,竞渡、弄潮等水上运动与儒家所倡导的“舍生取义”“生以载义”相背,反多冠以“奇技淫巧”“玩物丧志”,而溺亡的死亡形态又是儒家所谓的“不得其死”,不能享用祭祀礼仪,因此在传统伦理的影响与官府的禁治下,弄潮在元以后走向消亡,竞渡则逐步式微,仅端午时节作为民俗活动保留,无法再现宋元时从二月至五月均有竞渡比赛的场景。
3 “人为贵”思想与运动意外伤害治理
古今中外,运动意外伤害难以避免。我国历史上不乏因射戏而误杀伤他人的情形,南齐宗室萧权与弟射戏,矢激致其身亡,“次子权,与少子凯射戏,凯矢激,中之而死。”[13]除射戏外,射猎鸟兽而误杀伤人的情形更为常见,如《元典章》记录的射鹿误杀人案例,“为李猪儿首告:‘因射鹿,将刘伴叔误射伤身死。伊父刘福要讫人口、车牛、地土等物。’”[2]1448弹弓是传统弹射鸟兽工具,东汉李尤《弹铭》曰:“丸弹之利,以弋凫鹜。”[14]但若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弹弓,也容易造成意外伤害。《元典章》载:“江南城郭,人民繁盛,不务本业游荡之人,持挟弩子、弹弓,凡宫殿、庙宇、园林树木,但见飞禽坐落,辄便射打,不顾伤人,有司未尝禁约,深为未便。”[2]1944弓箭、弹弓等射程远、威力大,常引起不特定人的意外伤害,责任人又不易认定,因此弹射也成为古代体育意外伤害最为频发的活动。
我国古代法律对体育意外伤害的责任认定较为严格。《唐律疏议》以“过失杀伤律”规制射箭、弹弓、投石、举重、登高等意外伤害,“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3]427《疏议》又进一步解释了“过失之事”:“谓耳目所不及,假有投砖瓦及弹射,耳不闻人声,目不见人出,而致杀伤。其思虑所不到者,谓本是幽僻之所,其处不应有人,投瓦及石,误有杀伤。或共举重物而力所不制,或共升高险而足蹉跌,或因击禽兽,而误杀伤人者,如此之类,皆为‘过失’”[3]481。从立法目的来看,该律主要规制各种“耳不闻人声,目不见人出,而致杀伤”的意外事件,其所列举的弹弓、射箭、投砖瓦、举重、登高等是发生意外伤害的主要体育活动,可见律文是通过总结各种体育意外伤害的实践发展而来。唐律这一规定为后世所沿袭,从《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到《大清律例》,射箭、弹弓等致人杀伤的意外事件均以“过失杀伤罪”论。中华法系对此类意外事件的罪刑认定严苛,如《大清律例》关于围场意外伤人的规定:“围场内射兽兵丁,因射兽而伤平人致死者,照比较拳棒戏杀律拟绞监候,仍追银给付死者之家。”[4]803“绞监候”的处罚不可谓不重。此外射箭、弹弓等具有远程攻击的效果,致害人往往难以认定。为解决这一难题,辽代法令就规定书本人姓名于箭矢上,以备追究误伤责任:“癸亥,上(辽兴宗)猎马盂山,草木蒙密,恐猎者误射伤人,命耶律迪姑各书姓名于矢以志之。”[15]《大清律例》更是明确规定不书姓名于箭矢上或书他人姓名的,都要追究刑事责任:“箭上不书姓名及书他人姓名者,杖八十。”[4]596我国古代体育意外伤害严苛的责任认定与“人为贵”的儒家思想紧密相关,《荀子·王制篇》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儒家人为贵思想反映在司法上就表现为人命关天的仁道,因此凡伤及人命的体育活动,不论是体育意外亦或是风险自负的比赛均为法律所禁止。
4 “尊卑有序”“贵贱有等”与运动伤害赔偿
我国古代运动伤害赔偿起源很早,汉代《二年律令》就确立了过失杀与戏杀可赎的原则:“其过失及戏而杀人,赎死。”[16]唐律中明确了所赎之铜应入被杀伤之家,“听赎,其铜各入被伤杀家。”[3]425这是唐代运动伤害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不过汉唐律中的“赎死”“赎铜”虽一定程度上赔偿受害人,但从本质上讲,“赎死”“赎铜”只是身体刑的替代刑,并非独立的受害人赔偿措施。元代法律在唐律基础上实行追征烧埋银的措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唐律在赔偿方面的不足。如《元典章》“相扑作戏”案例:“至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中书刑部符文:‘高万奴状招:与张歪头相扑作戏,万奴用拳于歪头左耳近下侵咽嗓打讫一拳,倒地身死。’省部相度:量拟九十七下,仍征烧埋银五十两给主。”[2]1445该戏杀案例中,致害人不仅受九十七下杖刑,同时还需支付五十两烧埋银给受害人家属。这与唐律“赎而不罚”“以赎代罚”的处理不同,运动伤害赔偿已成为独立的救济措施。元代烧埋银制度源自草原民族“赔命价”的传统伦理习惯。“赔命价”是指以牲畜等财物作为杀伤人的赔偿,在东亚诸多草原民族中广泛存在,如拓跋鲜卑的习惯法:“民相杀者,听与死者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13]女真人在部落时期就有“杀人者,偿马牛三十”[17]的风俗。“赔命价”作为草原民族的习惯法,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与汉人“杀人偿命”的伦理相近,草原民族早期也崇尚血亲复仇,但在冤冤相报无休止的复仇中,草原民族意识到复仇并不能保护部族成员的生命。在仇恨与生存之间,草原民族最终选择了和解,采用偿付命价方式化解双方的矛盾冲突,一方放弃复仇,另一方则赔偿一定牲畜财物。元政府在处理运动伤害事故赔偿时,融合了草原民族“赔命价”与中原传统刑罚的制度设计,烧埋银制度不仅对受害人起到了抚慰与救济的目的,同时也为明清两代的运动伤害赔偿奠定基础。明清运动体育伤害赔偿基本沿袭元代,清代改烧埋银为埋葬银,“凡民人捕猎,遇有施放枪箭打射禽兽,不期杀人者,比照捕户于深山旷野安置窝弓不立望竿而伤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银一十两,给与死者之家。”[4]800因弹射、投掷、登高、驾船、乘马、驰车、举重等造成他人意外伤害的,同样要给付营葬与医药之费,“如弹射禽兽、因事投掷砖瓦不期而杀人者,或因升高险足有蹉跌累及同伴,或驾船使风、乘马惊走、驰车下坡,势不能止,或共举重物力不能制损及同举物者,凡初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人者,皆准斗殴伤人罪依律收赎,给付被杀被伤之家以为营葬及医药之资。”[4]800烧埋银制度引入后,我国古代运动伤害治理从单一的惩罚机制转变为惩罚加赔偿的多元解决机制。
在儒家构建的社会秩序中,尊卑有序、上下不失是其基本伦理精神。在古代运动伤害的治理措施中,“尊卑有序”的儒家伦理影响显著,如《唐律》规定,卑下不得与尊长戏,“其不和同及於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虽和,并不得为戏,各从斗杀伤法。”[3]425该规定体现了唐律维护尊卑长幼伦理秩序的立法宗旨。此外中国传统的“刑不上大夫”政治伦理最终以法律的形式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封建官僚社会。官员可凭借其身份适用官当、赎铜、除免等免除刑罚,如《唐律》规定九品以上官员犯流罪以下均可输铜以赎,七品以上官员犯流罪以下可减一等。在运动伤害赔偿方面,官品越高,人身损害赔偿也越高,如满清制定的“围猎误射罚例”:“凡诸王贝勒子公等误射王者,罚银三千两与被射之王,误射贝勒罚银二千两与被射贝勒,误射贝子公等罚银千两与被射贝子公,如王、贝勒、贝子公等误射一下之人视受伤轻重给银,若致死者,除偿身价外,仍罚银二百两,给被射之家。伤未死者,除照常给银外,罚银百两给被射之人,无伤痕者,罚银五十两给被射之人。”[18]该罚例以宗亲官僚的身份等级作为赔偿依据,清代王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赔偿金额最高相差六十倍,“同命不同价”也体现了我国古代运动伤害立法鲜明的“尊卑有序”等差性。根据犯罪者身份作出的同罪异罚判决在“别尊卑”“异贵贱”的法律伦理中被赋予身份正义的外衣。
5 中西古典运动伤害治理之比较
中西古典法律均有与运动伤害治理相关的立法,由于立法精神不同,二者差异显著。1)古罗马重契约,在体育伤害中承认“自甘风险”,并适用“无过错不承担责任原则”,角力、拳击、投掷等风险自负的体育比赛所导致的伤害可以免责。“(古罗马)限于自由人参加的、公开举行的摔跤、混斗和拳击比赛中,一个人无需为杀死或伤害另一个参赛者的行为承担责任。”[19]而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中华法系重孝道,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影响下,“风险自负”的对抗性体育活动并不被官方所提倡。2)古罗马法重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体育活动中意外伤害适用免责条款,其责任认定要轻得多。《学说汇纂》载:“数人玩球,其中一人在接球时将一努力学徒推开,该学徒摔倒折了腿,有人问,这个学徒的主人是否可以依《阿奎流斯法》对推倒其学徒的人提起诉讼。我回答说,他不可以,因为看上去更多地是由于偶然而不是过错才发生了这事儿。”[20]而中华法系重人命,往往以行为结果作为量刑依据。《唐律》中“耳目不及”“力所不制”等因偶然非过错而产生的运动意外伤害与《学说汇纂》所载案例接近,但其处罚结果却大相径庭。3)古罗马法重视私法范围内的权利平等,这使贵族在与平民开展体育活动时适用统一标准,而中华法系以法律形式明确“尊卑有序”“贵贱有等”,这不仅体现在赔命价的差异上,也体现在行业贵贱方面。不少体育、游艺活动也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贱业,这使官方在对待运动伤害时往往从重治理,甚至以禁令的形式加以限制。
6 余论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运动伤害治理主要通过律令形式予以规制,中国古代法律秩序正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伦理秩序,中国古典法律的基本价值与儒家社会伦理所追求的价值相一致。在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亲伦理的影响下,凡是伤及身体的运动项目并不被政府所提倡,儒家伦理浸染下中华法系以“戏杀伤”的罪名治理相扑、枪棒等体育活动造成的运动伤害,使得对抗性强的体育活动始终无法摆脱法律制裁的阴影,这是相扑、枪棒等传统体育活动式微的重要原因。此外,儒家生死观认为,溺亡属“不得其死”,甚至不能享受丧葬祭祀礼仪,这对弄潮等水上体育竞技产生了不利影响,不仅参与者多为“无赖不惜性命之徒”[9],且一旦发生沉溺事故,则“必行科罚”。与古罗马运动伤害立法相较,我国古代运动伤害立法“重民惜命”,不承认“自甘风险”,出现运动伤害的体育活动多被禁止,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生命,但也丧失了竞技体育追求极致、崇尚冒险的精神。在运动伤害赔偿方面,烧埋银制度的引入使运动伤害赔偿成为独立运行机制,改变之前“赎而不罚”的司法原则,体现了草原民族伦理与中原传统伦理的结合。但在“尊卑有序”“贵贱有等”的法律伦理下,同罪异罚被赋予身份正义,“同命不同价”体现了古代社会鲜明的等级性。
学界在探讨我国古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制约因素时,认为“农业文化、自然中庸的文化特色、专制的社会制度与形态、文化的早熟与继承性的文化传播途径”[21]是主要因素;也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以儒家、道家为两大支柱的封建哲学思想与竞争意识、竞技精神是相对立的。儒家仁礼伦理文化与道家的虚无无为的观念,均导致对个性的压抑及对平等竞争的体育精神的否定。”[22]然而,从运动伤害治理的视角来看,我国古代竞技体育在“重惜民命”“人命关天”“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下,易发生运动伤害的项目通常被禁止,运动伤害责任方也往往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在此背景下,我国古代竞技性与对抗性强的体育项目受到较大限制,古典竞技体育的生存空间逐步缩小,对抗性强的体育项目逐步被娱乐休闲型体育项目所替代,这也是造成中西方体育不同发展走向的重要原因。
[1]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3113.
[2]陈高华.元典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马建石,杨育裳.大清律例通考校注[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怀效锋.大明律点校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54.
[7]张双棣.淮南子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474.
[8]周密.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7:89.
[9]吴自牧.梦梁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52.
[10]田明曜.香山县志[M].清光绪刻本:100.
[11]高斯得.耻堂存稿[M].上海:商务印书局,1935:131.
[12]真德秀.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551.
[1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24,2873.
[14]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6:1613.
[15]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6.
[16]彭浩.二年律令与奏谳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98.
[17]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2.
[18]嵇璜.清朝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9]赵毅.<阿奎流斯法>:体育伤害责任的历史之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3(4):27.
[20]米健,李均.学说汇纂[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89.
[21]王岗.中国古代“竞技体育”的文化审视与民族传统体育的重塑[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3):306-308.
[22]旷文楠.中国古代竞技体育的发展与衰落[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9(4):15-21.
Governance of Ancient Sports Inju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Ethics
DAI Yu1,JIN Xinwei2,CAO Jingchuan3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041004,Shanxi,China;2.P.E.Department,Heilongjiang Forestry Vocation-Technical College,Mudanjiang 157011,Heilongjiang,China;3.College of Sports,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041004,Shanxi,China)
In ancient China,the governance of sports injuries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ethics.Under the influence by Confucian ethics of the whole body by the parents,such sports as Sumo,vulnerable to physical harm,were prohibited.The law even created“theater killing crime”to regulate such sports injury.Under the influence by Confucian“death without mourning”,sports of Surfing and Dragon boat prone to drowning were restricted.The cognizance of sports accident responsibility was more severe than that in the ancient west,because of the domination idea of“human being noble”.In that case,the living space of competitive sports was gradually reduced,and the antagonistic sports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recreational sports.This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sports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In addition,affected by the national grassland“compensation for the life price”ethical habits,the silver burial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Yuan Dynasty to make the sports injury compensation an in dependent operating mechanism,but under the ethical domination of“pecking order”and“gentle and simple being different”,“life with different price”was endowed with the coat of status justice.
traditional ethics;sports;sports injury;governance
G812.9
A
1004-0560(2017)06-0083-05
2017-09-15;
2017-10-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TY076)。
戴羽(1983—),男,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体育史。
曹景川(1978—),男,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人文社会学,E-mail:228525158@qq.com。
乔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