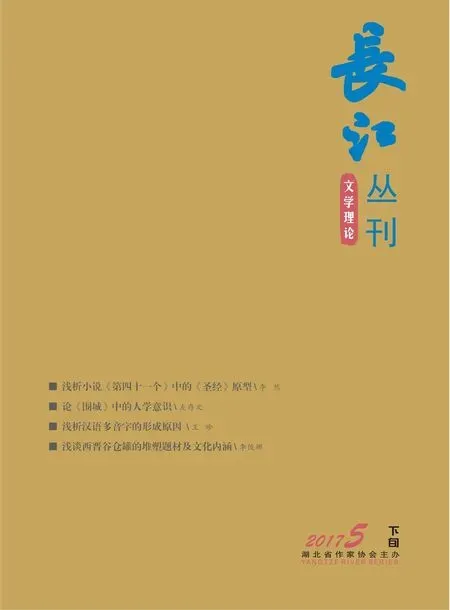韦伯和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及其异同
石红玉
韦伯和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及其异同
石红玉
马克思和韦伯作为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想家,对当时各自所处的社会均有非常精彩的论述。然而无论是对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的马克思还是秉持着悲观态度的韦伯,都不约而同的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政治经济视角的批判。本文从二者现代性理论的切入点出发,对两位思想家在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轨迹和未来走向上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得出二者在理论上的分歧和原因。
现代性 马克思 异化 韦伯 理性化
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出现在德国的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在他们所属的时代对社会的解读和预测放到当下还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对现代性的探讨上,二者的思想一直是后世的思想家绕不过去的,要么拓展、要么批判,也有综合二者思想以求在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做到完全和完善的学者。韦伯在现代性问题上有对马克思的继承,但更多的是分歧,韦伯以“理性化”吊诡为切入点,而马克思则用“异化”和“物化”来断言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的思想家在对待社会的变化时的谨慎和细致。
一、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解读
马克思和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解读都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范例的,二者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对待资本主义的情绪和取向。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状况的变化是引发整个社会形态变化的最终决定因素。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的私人占有状况愈加严重,一个阶级面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从未停止,商品拜物教充斥整个社会,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者一切痛苦和不幸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否定性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形态必将走向更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展望。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人的否定和对剩余价值的绝对追求在马克思看来是绝对不合理的,他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探讨的基础上找出了其中不可避免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最终会走向灭亡。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社会应该是无阶级的、资源共享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韦伯把现代性特征定义为“祛魅”,即理性化,这也是其现代性理论的总出发点。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行动的一系列考察,加之对文化价值(宗教)的社会意义的分析,得出现代资本主义是合理化的结果。韦伯心目中的理性是使一切事情成为可计算的、具有高效率的、以制度为依据来实现的,而资本主义正是这样一种存在,它使每个人都成为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原子,这些原子也被禁锢在某个位置上不能轻易改变,社会位置的设置要大于人的需求,这样的社会具有高效率和高执行力。但这也成为现代社会理性化最大的悖论——韦伯称之为工具合理性——正是这种禁锢着人们的工具理性使人们难以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也意识到这种合理性实质上是非理性的,因此他用“铁笼”来隐喻现代社会的生活图景。
二、对现代性的批判
从《哲学经济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批判。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中,马克思认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呈现出其所说的一种“对象化”的扭曲。这时,异化现象就产生了。马克思主要从四个维度来讨论异化的问题:(1)工人无权处置其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他生产的产品都为别人所占有,他自己也就无从受益。(2)工人在工作本身中异化:工作是作为达成某种目标的手段而强制发生的,并不会使工人产生内在的满足感。(3)既然所有的经济关系同时是社会关系,那么劳动的异化也就必然会带来直接的社会后果。但这也表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与市场机制具有了趋同性。(4)人类是生活在一个与自然界交互活动的社会中,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技术和文化,但是异化劳动将人类的生产活动降格为一种机械的适应性行为,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征服。这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关于“异化”的论述。
韦伯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形式合理性社会,实质上却是非理性的。这也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即现代人在经济行动上以利益(货币)为取向的做法是理性的,而价值理性被忽视了,这造就了现代生活中价值取向的非理性。韦伯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多方面(市场经济、社会分工、现代企业和国家以及宗教)的分析中发现了合理化所带来的悖论:在现代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中,统一的世界观不复存在,在任何理性的选择中都充斥着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冲突,且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价值合理性是工具非理性的,而形式合理性是实质非理性的,它们彼此之间处于一种永远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关系之中”在经济行为上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现代人对货币的狂热追求,这种狂热使本来属于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货币),当成工具本身来追求,货币本来是作为一种交换媒介而存在的,但是现代人却将其作为终极目标来追求,“为赚钱而赚钱”成为现代社会商业行为的准则。其他还表现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所存在的冲突,“具有形式合理性的市场经济在实质上是非理性的,而在实质上具有合理性的计划经济在形式上却是非理性的。不仅在经济行为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冲突,而且在政治领域也产生了相应的冲突:科层制的吊诡。科层制作为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组织具有高效、稳定、纪律严明的特点,它摧毁了传统社会中世袭的特权与不平等统治,顺应了民主制发展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科层制的发展却使官员们的权力得不到限制,反而阻碍了权力的合理扩散,而且科层制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形式规则使每个人被禁锢在其所处的位置上,无法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喜好来行动,所关心的只有利益,人的自由实际上被剥夺了。因此,韦伯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理性化一个悖论性的后果是,世界从新教徒暂时居住的异乡变成了难以逃离的“铁笼”,暗示了现代社会人虽然相对摆脱了宗教的枷锁,但又陷入了物质的、金钱的羁绊之中,对效率、金钱、商品的崇拜形成了新的拜物教,它对人的限制不仅在身体上,更在灵魂上禁锢人们,使现实变为实质上的非理性。
三、二者现代性理论的异同
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机器大工业在促进生产发展和人类生活方面的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利用和开发,导致了工人劳动的异化。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周期性地被破坏明确地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成为一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形式。韦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目的理性”或“形式理性”逐渐凌驾于“实质理性”或“价值理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无论是从经济行为还是政府组织方面来看,现代社会的形式合理性都超越于实质合理性而存在,这是韦伯所谓的“理性化悖论”,同时他也将现代社会隐喻为一座无法逃离的“铁笼”,思想和身体都是被禁锢的。这种分析可以说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是从经济和政治的视角来分析现代社会,同时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在运行和发展中的不合理趋势,对现代资本主义追求利益和只追求利益的价值取向持反对态度,都清楚认识到现代社会对人的桎梏来源于对金钱和商品的追求,这是二者在现代性理论中相同的认知。但相同的效果不代表相同的表述和意志,马克思和韦伯的现代性理论的不同点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界定。韦伯认为现代统治的合理性问题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出发点,而马克思却将现代性问题的解剖放在对劳动异化和资本对劳动的压榨上面;虽然两人都把现代性界定为资本主义,但其中的内涵却是大不相同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现于不合理的商品崇拜和金钱崇拜,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夺使社会成为一个非理性的集合体。在具体的形态批判上则是从人与劳动的异化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进行理性分析,看到了现代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压榨,从经济延伸到政治,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断言资本主义社会终将被自身内部所固有的矛盾而毁灭,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在韦伯那里现代性始于传统的消亡,“祛魅”的过程是将虚无的神现实化,人们不再信仰那个唯一的神,转而开始接受多元的价值和真理,这是一个“多神论”显现的过程。资本主义的体现就是在其形式合理性基础上对现代社会的金钱和效率的追求,但也将每个社会人限制在其位置上,无法按照自己的喜好的信仰来做事,这就是韦伯所谓的“铁笼”,以强大的控制使社会成为一个合理性系统,无法逃离、无法摆脱。可以看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一种暗含的批判,工具理性使价值理性受到轻视,进而被忽视。二者在现代性内涵解释上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对现代性反思的不同:韦伯从文化价值的合理性来阐述资本主义的秩序,从制度性的角度来开始现代性的揭示、诊断与批判;马克思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入手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非理性,揭示了在商品、货币和资本之间所出现的理性的悖论。而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预想这个问题上,两人的不同是最明显的。我们可以把这种预想看作是马克思和韦伯对现代性的出路的解答。韦伯作为唯名论的代表,将寻求个人尊严当作解决现代社会实质非理性的终极办法,而且现代性作为现代人不可摆脱的“天命”,人们只能是在现代性即合理性之中寻找自我的发生,换句话说就是要首先拯救人权。社会越是发展,合理性悖论带给人的苦果就越多且越严重,而韦伯认为要摆脱这些苦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不难从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展望中看出一种悲观的态度。而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则具有一种明朗的乐观态度: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进行了严谨而缜密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内部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在种矛盾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即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会使资产阶级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起是理所当然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基于对现代性出路的不同认识,最终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不是说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就是相互不兼容的,相反,这恰恰说明二者的思想是相互补充和彼此包容的。
四、结语
在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上,马克思和韦伯各有各的见地,二者的思想有相容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马克思一直秉持乐观态度,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人与劳动的异化,这种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悲剧性结局的根源。而韦伯读现代社会的发展持另一种看法,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充满了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被忽略了,但形式合理性却带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有秩序运行,这是现代理性的悖论。在这种悖论下,韦伯看到的是现代社会像一个“铁笼”一样禁锢着人们,人们也被其中暂时的利益推动着而无法摆脱。因此,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持一种悲观态度。在对二者现代性理论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理性与非理性的斗争,而对于道路的选择,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世界时政背景相关联的。
[1]付琼.马克思与韦伯社会冲突思想的比较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03):65~68.
[2]唐爱军.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域:韦伯与马克思[J].理论与现代化,2011(05):11~17.
[3]刘新华,刘欣.试比较马克思与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思想[J].前沿,2008(03):20~22.
[4]阳勇.马克斯…韦伯现代性的重构[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8:123~125.
[5]尹树广.现代性理论的批判维度及其问题[J].山东大学学报,2003:15~20.
[6]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
[7]文军.西方社会学经典命题[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5).
[8]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4).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石红玉(1989-),女,汉族,甘肃玛曲人,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