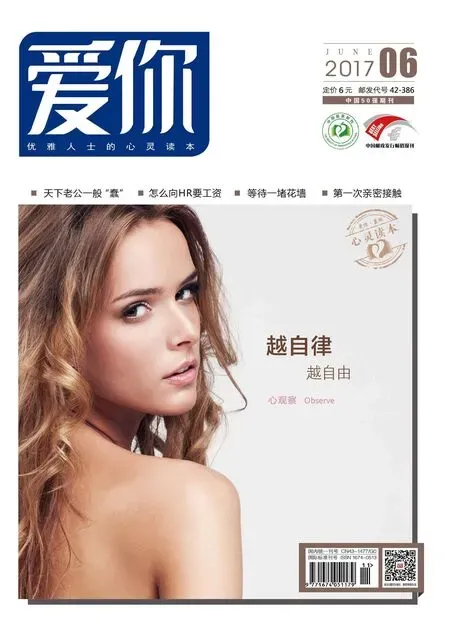支 票
◎ 吴正
支 票
◎ 吴正
接触支票,是在十六年前我到香港之后的事了。在香港的商业生活中,每日都有可能几十遍地接触支票,小到十几元,大到上百万元,而银行职员遵循的是同一套严格的核对程序——一字不合立即退票,反之,再大的金额也将从
你的账户中扣除,绝不容许事后的商榷与反悔。
在父亲的生意由我全盘接手后,慎重了一生的他仍别出心裁地保留了支票的签字及修改权。这明显构成了对我自尊心的伤害,但他似乎全然觉察不到,没有解释,更不用说有歉意了,有的倒是背地里向我母亲说的那么一句评论:“这是生意,不是写诗,形象思维可要不得!”
某日,在文件堆间埋头工作了一天的我抵家时,突然记起已有三日没有核对过已开出的支票的存根。令我全身血液冻结的正是这一次的核对:一张五万的支票由于会计多填了一个零,英文便也跟着写错,而最致命的是我竟在匆忙间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我奔进客厅,向银行拨去电话,居然忘了当天的办公时间早已过了。当我搁上彼端无人接听的话筒时,瞥见父亲正在客厅的另一角坐着看报,显然,他对此事还一无所知——他当然不会知道,至少在月底银行结单还没寄达前。
第二天一大早,银行还没开门的时候,我已经在那儿守候了。
“经理先生,”目标在我视野中一出现,我就迎了上去,“我开错了一张五万元的支票。”
“什么时候的事?”“三……三天前。”
对方的眼中露出一丝惊奇:“您是了解的,吴先生,我们可能已经无能为力了。”
“是的。”我颓然地低下头去。
“不过,我还是可以给您一份付款的影本。我让总行这就电传过来,您先请坐。”但当他边读着电传,边重回经理室时,我听见的是他迟疑的自言自语:“好像没错,好像……” 我腾地站起身来,一把抢过电传纸。这是一份与我签署的那份完全不同的支票影本,金额栏中明明白白地写着五万。当我瞥见票底处的那行刚毅的签字时,一切便都水落石出了。
我抓着电传纸,一路跑回家去,在逼近家门时,脚步反而放慢了。我装成若无其事地扭开大门锁把,父亲仍坐在客厅的一角,读着他的报、喝着他的茶。
“爸爸。”我说,“早上好!”
“早上好。”他连头也没抬一抬,但就在这连眼神都不曾交锋的瞬间,我们已和解了。
之后,真的没人再提起过这件事。十三年过去了,父亲永别我们也快有九个年头了,但我每次忆及此事,心中便会升起一股带韧性的感情,它构成了我对父亲回忆的一个鲜亮夺目的光点。
(摘自《浮生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铁路客运发展的记忆“存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