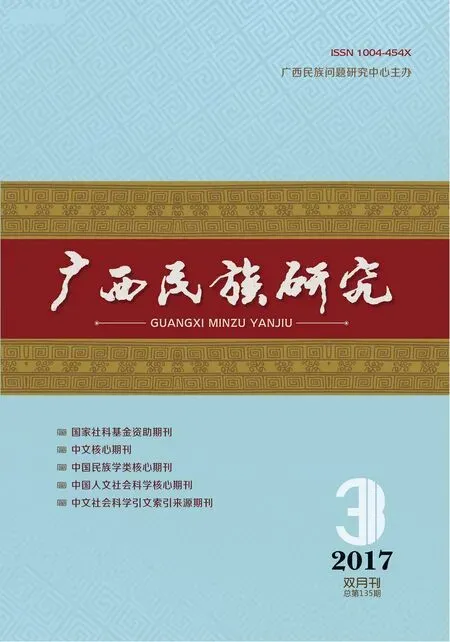从交往合理化看民族共识的生成机制
杨 佩
从交往合理化看民族共识的生成机制
杨 佩
民族共识和民族冲突一直以来都是民族研究的重要问题,民族的差异性并不是民族冲突的根源,而是民族共识的基础。在现代性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的激烈碰撞成为民族共识达成的主要障碍。本文试图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出发,以交往理性为手段,考察民族共识的生成机制。哈贝马斯将现代性危机归之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用交往合理化来重建生活世界,从而为民族共识的达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生活世界殖民化;交往理性;民族共识
中国地域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土地气候、风俗习惯大相径庭。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之间信仰、生活差异性很大。自古以来,民族之间的冲突往往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阻碍,这种破坏性有时甚至直接导致了国家的分裂,所以,民族之间和谐相处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不同的民族由于地域的分割常常会出现严重的分歧,传统社会交通的不便利又阻隔了日常交往,只是在少数边缘地带存在简单的贸易往来,文化上的交流更是少之又少。现代社会的管理机制迫切需要人们跨地区的交流合作,民族与社会不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而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局部隶属于整体,影响着整体的运作。社会发展需要民族的发展,不同的民族需要达成共识。全球化不仅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也推动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少数民族内部不断走出地域的局限外出打工、学习,民族之间的交流更近一步。于是在现代社会丰富多样的物质基础上,文化的差异性愈显突出,在信仰、教育、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歧愈加严重。现代社会民族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仅需要以物质利益作为基础的经济共识,更需要一种以文化交流为基础的民族共识,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平稳发展,为各民族人们的行为规范提供价值依据。
一、传统社会民族共识的生成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1]15共识是指主体之间的共同性,民族共识的主体便是各民族寻求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同民族即使生活上有差异,但是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民族之间的共识主要指民族之间就某个层面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是民族共识的基础,民族共识并不是强迫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在保持民族多样性的前提下在某个方面达成一致性意见,不是消除差异而是求同存异。民族共识具有时代性,根据时代主题的变迁不断变化,过去常常以利益或者权力为导向。由于民族发展程度的差距,民族共识很难站在一个平等的立场之上,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压迫。许多少数民族就是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被同化而销声匿迹的,因此民族内部对于民族之间的交往十分谨慎,总是以保证民族完整性为前提进行交往。民族文化是历史发展长期积累下来的,这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塑造出一种前见,并成为业已固定下来的思维范式。这种前见往往封闭又排外,将其他文化拒之门外,形成民族间相互理解的障碍。民族最早依血缘和地缘形成共同体,内部成员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形成了相同的生活习惯、价值倾向、理想信念。传统秩序统治下,民族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少数民族内部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使其既独立又封闭。少数民族文化以信仰为依托,以血缘为组织形式,以地缘为界限,主要表现为宗教性、地域性、传统性的特征。[2]26宗教信仰是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凝结出的精神核心,能够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和保持民族的稳定性,宗教信仰也为民族成员的价值观念的评价与选择提供依据,是少数民族价值观念的内核。少数民族由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性,在共同生活的经验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其文化习俗呈现出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生活习惯、生产方式、饮食文化造就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色。少数民族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文化上缺乏交流,带有强烈的传统性特征,由于文化的滞后、信仰的制约,价值观念的发展也十分缓慢。
中国历史经历了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漫长发展过程,民族间的交流互动也日渐紧密,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往形式。各民族主要以政治交往为主、以经济交往为辅,政治上和亲、授官相互支援,经济上关市、朝贡互通有无。[3]3但是这种民族间的交往并不是建立在和平平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征服和服从之上。这种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常常是自上而下的传播,由民族的领导阶层推动,底层民众执行,这就引起了民族内部极大的分歧和严重的冲突。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人民实行的压迫政策,在中国各民族之间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为民族团结制造藩篱,使民族的共同发展遭受损失。[4]144少数民族长期所处的不平等的地位也为日后民族共识的达成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影响传统民族共识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缘政治的变化。中国地域辽阔,各民族为了扩张领土、掠夺资源,经常发起战争,战争打破了原有的民族格局,战争结束后实现了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民族生活地域的变化,从而建立起新的民族共识。地缘政治变化有时为社会带来了民族大融合,有时也造成了民族冲突和民族隔阂。第二,经济贸易的往来。无论政治局势的紧张与否,民族之间一直保持着贸易的往来。民族生活地域的不同、土地的优劣直接决定了生产方式的差异性,同时生产方式的不同带来了不同的生产资料。日常生活资料的贸易使得民族边缘交界地带更容易达成共识,少数民族生活的基本需求促进了经济交往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第三,文化融合。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会向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地区迁移。新的环境迫使他们融入新的生产方式,逐渐适应了当地的文化,其本身文化只保留下一些形式的部分,成为一种精神归属。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前提,文化的融合是民族共识形成的重要环节。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形成了平等互助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央人民政府加强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流,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需求,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支援。但是这种帮助只是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在社会整体层面由于经验的缺乏、集中化的管理造成了资源调配的不合理、劳动者积极性的下降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意识到民族差异性在治理民族问题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政治经济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改革,开辟出民族交往的新格局。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逐步开放,加快形成新的民族共识的意愿更加迫切。
二、现代社会民族共识遭遇的困境
民族共识是不同民族成员所达成的一致性意见。作为民族之间所认同的文化理念,既是指导民族事务顺利进行的理论工具,也是解决民族冲突的主要依据。民族共识是在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既不是既定不变的真理,也不是适用万物的普世价值,它要求民族在交往中不断反思,不断打破旧的共识,建立新的共识。现代化进程推动着人们从旧的秩序中脱离出来,业已建立的共识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被人们抛之脑后。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渗透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最大程度地调动起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人口的资源性调配减弱了民族的封闭性,打破了民族交往的屏障,少数民族成员走出了地域的局限。市场竞争机制唤起了少数民族成员的主体意识,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同时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少数民族成员不再像以前一样享受经济上的特权,纳入到了市场自主运行的模式之中。由于资金技术缺乏、文化教育程度较低、信息交通不便,再加上长时间不平等的地位造成的文化歧视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民族冲突与误解,少数民族成员常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少数民族面对的是“旧规未撤,新规未立”的尴尬处境,其内部执行着严格的宗教信仰,外部面对的却是市场经济规则的泛化和实用主义横行。[2]114价值观的激烈碰撞呈现出两种样态,一方面是对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质疑和排斥,另一方面是自身价值的迷茫与失范。少数民族个体失去了对社会的信任,受到利益的引导,其表现极为突出。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转型期遭遇的问题是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须面对的,不能仅仅依靠民族共同体内部解决。人们需要的是将整个社会联合在一起发挥社会共同体的力量,这更需要人们达成新的民族共识。面对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任何少数民族个体的问题都有可能酝酿成为民族问题,民族冲突的根源不是文化的差异性,而是受到时代背景的激化。
(一)生活世界殖民化为民族共识带来的挑战
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不可能逆潮流而行,现代化遭遇的问题也是社会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说现代社会是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个体从原来的民族共同体中被抽取出来,重新组织成为更加高效的国家机器,从而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结构。马克斯·韦伯将这种社会结构概括为社会的合理化,即经济的簿记化、政治的科层化、文化的世俗化。为了迎合经济上可计算、可计划的价值倾向,政治上建立起科学有效、层层递进的官僚制度。政治经济上的合理化使得工具理性进一步膨胀,逐步占据价值理性的领域,于是就产生了文化的世俗化,即用目的理性的思维方式解释文化,瓦解传统文化中与理性相冲突的价值信仰,从而达到“祛魅”的最终目的。[5]76
现代性对民族共同体进行了全面的解构,科学技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经济改革结束了传统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政治管理制度代替了民族内部的等级制度,文化祛魅消解了人们的精神束缚,民族共同体转而成为一种信仰共同体。但是当目的理性侵入到人的精神领地,就会使民族个体被压制的情绪释放出来,反过来抵抗经济、政治合理化的过程,哈贝马斯将这一过程称为“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沿用了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周遭,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经济等从生活世界中衍生出来,在目的理性的推动下结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即“系统”。系统的完善使之与生活世界完全割裂开来,形成了与之不同的运行机制。以国家、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倾向于以结果为导向的系统性整合,目的是为了取得成功。而以文化、法律、道德、艺术、科学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活世界,倾向于以动机为导向的社会性整合,目标是为了取得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指系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反过来主导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以系统的准则和价值倾向作为生活世界的行动依据,最终呈现出韦伯所说的社会合理化过程,这也是资本主义合理性危机。
少数民族要从落后贫困的生存环境中解脱出来,首先要完成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改革,这种转变是推动民族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也成为生活世界的主导力量,将生活世界一同纳入到它的管理之中。系统是以货币与权力为媒介的管理方式,而生活世界是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模式,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现代社会无需语言的技术性交往缩减了交往的时间和成本,促进了系统的高效运转。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渗透,物化了生活世界的交往方式,导致了个体与社会、价值与事实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表现在系统超越了生活世界所容许的限度,还表现在超越了自我控制的限度,系统已经无法通过自我反馈机制进行自我完善。政治经济的分工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的分化,科学、道德、艺术、宗教由不同的人负责,实现文化专业化的同时,却带来了文化的贫困化。不同领域以合理化为标准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规则,分化越细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程度越深。“现代社会则分解为许多独立的系统,它们处于自我关涉的封闭状态,相互构成了对方的周围世界,仅仅通过互相观察而间接地发生接触,根本没有主体间共有的价值、规范和沟通过程。”[6]190科学技术、法律制度、艺术审美、伦理道德相互脱节同时由系统统辖,其结果是主体的分裂与异化。人们使用工具却无需了解工具的原理,人们努力劳动却不知晓劳动的意义,人们热衷于消费却始终被消费所掌控。
(二)主体意识面临的危机
系统从生活世界分离出来的同时,主体也相应地分裂成为旁观者和参与者。主体无法控制系统性整合,成为旁观者,本来由人的积极活动组成的政治经济系统却将主体性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只有在生活世界中,人们才成为生活的主人,以参与者的身份介入到社会性整合之中。随着旁观者和参与者角色的建立,主体分裂日益严重,然而这只是主体解体的第一步。系统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扰乱了与生活世界相互制衡的状态。生活世界遭到系统的钳制,主体则被货币与权力规训,主体与生活世界的连接越来越少,生活世界也越来越贫乏。主体被系统分割成碎片化的存在,其整体性意义被消解。马克斯·韦伯将之归结为价值理性的缺失和工具理性的胜利,主体在社会合理化过程中丧失了自由,在文化合理化过程中丧失了意义。[7]248生活世界对于主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系统的压制最终会造成主体的反抗。生活世界要改变被殖民化的现实,不是拆解系统,而是帮助人们重新树立起主体意识,将生活世界建构在系统之上,还原生活世界的本真。
对于生活世界殖民化,少数民族个体似乎感受得更为强烈,其造成的冲突也更为激烈。在改革开放之前,少数民族主体的传统生活秩序相对完整,政治经济文化结合得十分紧密,表现出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和稳定的民族心理,塑造出统一的民族共识。现代化的冲击,传统秩序的崩塌,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少数民族主体面临分裂与重建的双重压迫。现代化浪潮瞬间将个体抛入到无依靠、充满风险的环境之中,多数人产生了被剥夺、被抽离的感觉,相比之下少数民族个体更向往回到民族共同体的庇护之中。主体一旦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就不可能退回到传统生活之中,主体只能适应新的环境。人们维持着传统民族共识,但是却无法阻止民族历史基础的动摇,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也分割了少数民族主体的日常生活,价值信仰承袭传统,而社会管理方面却转移至系统之中,两套行为规范就像两列平行行使的列车,没有交集。生活世界的再生产无法为人们系统的再生产提供建设性的价值,系统的完善也无法丰富人们的生活世界,更为严重的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加剧,导致了系统进一步侵蚀主体的自主空间。少数民族的主体意识本身还处于待建构的阶段,很容易被诱导或者被摧毁,于是表现出相对主义、怀疑论等价值导向。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对立反映在少数民族主体上总是会演变为民族冲突,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成为民族主体之间无法弥补的鸿沟。
三、从交往的合理化重新审视民族共识
生活世界是主体参与的主要领域,其作为主体认知的前理解状况存在于主体的活动之中。主体实践的对象来自于生活世界,主体对象化的结果也被重新赋予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基础性地位的确立,才能帮助主体完成旁观者向参与者角色的转变。生活世界实践活动以理解为目的,主体之间的交往不是为了获取真理的客观性,而是为了达成共识。解决生活世界面临的危机不能仅用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而是要纳入到交互主体的运作之中。
(一)交互主体与交往理性的生成
生活世界主要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部分组成。“文化是一种知识储备,交往行为者通过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并用这些知识储备来做出富有共识的解释;社会就严格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力量而言,是一种合法秩序,依靠这种秩序,交往行为者通过建立人际关系而创立一种建立在集体属性基础上的团结;个性是一个用来表示习得力量的术语,有了这些,一个主体才会具有语言和行为能力,才能在各种现成的语境中参与沟通过程并在不同的互动语境中捍卫自己的同一性。”[6]387文化是主体对对象的理解,从中得到知识资源;社会是交互主体之间产生的共通感;个性是自我在交往中保持的统一性。文化的再生产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新旧知识之间的传承,也是文化得以延续的原因。社会整合从多样性社会中提炼出同一性,为差异性个体得以共存找出根据。个性社会化保障个体之间的和谐相处,个体也能在其中获得认同。在主体的交流互动中,生活世界完成了文化再生产、社会性整合以及个性社会化的过程。哈贝马斯想利用这种主体间的互动机制,跨越自意识哲学以来建立起的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的对立。先验和经验共存于交互主体之中,所以主体的行为才具有了反思批判的特点,正因为这样,生活世界才能不断更新。主体从他者的视野中既看到了差异性也看到同一性,他者不是作为客体被主体认知,而是在交往中相互了解。不同于主客体认知方式,交互主体的构成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主体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并以此为起点探索更多未知的可能。社会性整合所达成的文化共识贯穿于主体交往的行动之中,交互主体在相互理解中形成的观念也为共识提供资源。主体并不是像后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碎片化、孤立的存在,主体社会化不仅帮助个体完成社会认同,还获取了他者的认可。主体在一种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寻求生活的共同形式,主体既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既是个体也是集体。
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压制,用工具理性代替了传统宗教的上帝,启蒙走向了反启蒙的道路,造就了目的理性的权威。在许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理性嗤之以鼻的时候,哈贝马斯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倡重建理性。理性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人们将理性片面化之后才导致了生活世界的崩溃。理性不仅具有工具性、目的性的一面,还具有价值性的一面,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在他看来,交往理性是挽救生活世界的关键,交往行动应当遵循自身的规则,并不是在某种权威命令之下,也不应当是纯粹思辨的产物。哈贝马斯希望用交往理性弥合康德以来启蒙理性产生的裂痕。交往理性是主体在交往活动中达成的各种具有规范性的有效命题,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可以论证为日常语言范式。所以交往理性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先验形式,也不是社会系统强制手段,而是依据共同信念确立起的生活世界的同一性与主体性。交往理性具有语言性、开放性、暂时性、程序性的特征。[8]交往理性内在于主体交往的语言之中,语言是保持交往一致性的重要前提,主体间交往的共同性需要通过语言来确认。语言的畅通程度直接决定影响主体间理解的程度,语言的差异性也可能造成交往的障碍。现代社会系统的侵入为了提高交往的效率把语言简化为符号,却失去了语言的价值意味。与目的理性保持封闭性不同的是交往理性的开放性特征,目的理性正是由于其封闭性才走向灭亡。交往理性对每一个交往主体开放,任何主体、任何对象都可能成为交往活动的中心。交往理性产生于交往行为之中,随着交往主体与交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交往包括了主体的多重因素,但是其最终结果只能体现主体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意愿,所以交往理性是暂时的。人们不是在交往行为中发现一个既定的真理,而是在主体间的矛盾中达成共识。交往理性不是实质性、实体性的,而是程序性的有效交往行为,具有规范性的操作流程,是一个“输出表达、接受理解、反馈纠错”的可循环的路径,帮助人们达成一致性意见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二)从商谈伦理出发建构民族共识
通过交往达成的共识主要有两类,一种是文化传承延续下来的,另一种是通过理性论证的。前者依赖于生活世界文化的再生产,将历史资源以逻辑的形式展现出来;后者则在交往中依据具体情景界定,后者常常处于前者营造出的前理解场域之中。人们对于具体情景的意见的分歧,既可能来自于情景的复杂性,还有可能来自主体交往的不规范和表达的不清晰。由于情景的复杂性导致的歧义在人们深入交流的过程中自然会被克服,主体交往的不规范却经常被当作主体的差异性而被忽视。于是哈贝马斯想重申交往行为规范性的重要性,他将人的社会行为区分为四种类型:首先是目的行为,以结果成果为目标,以目的理性为导向,遵循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规则,不考虑主体性因素,不涉及价值只涉及事实;其次,规范行为,主要指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以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为导向,是人们集体行动的依据,也是社会稳定运转的保证;再次,戏剧行为,是个体差异的反映,表达了个体的主观意图,是个体在他者面前有意识的表现自己的行为;最后是交往行为,即主体间通过语言媒介达成一致性意见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达到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主体是具有一定语言基础和行为能力的人,既能够清晰表达自己意愿,也能够按照程序性操作交流互动。[6]83-84
哈贝马斯把普通语用学作为交往行为起点,语言在交往的过程中具有普遍适用性,人们的交流离不开语言媒介。语用学就是研究语言的起源、应用与效果,哈贝马斯把“普遍”放在“语用学”之前就是要强调重建语言普遍性应用条件。语言贯穿于社会各种类型行为之中,语言既可以描述事物的存在样态,呈现事物本真;还可以表达个体的主观意见,为主体“发声”;还是交往行为的中介,是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共识达成的手段。哈贝马斯认为语言的前两种功能也是为主体间交往服务,语言表达的意义并非取决于使用语言的具体情景,而在于语用学的规则,所以他主张对语言进行规范性分析。正是将普通语用学作为理论的基点,哈贝马斯把商谈从交往行为中提取出来,认为商谈可以对交往行为进行纠错。交往行为所依据的规则正是依靠商谈建立起来的,商谈的结果完成了交往行为自我更新。商谈达成的共识是一个能被广大参与者接受的可以论证的有效性规范。交往行为只是宽泛的主体间的互动行为,而商谈却具有实践意义。人们需要交往,交往需要规范,规范来自商谈。交往行为可能是暂时的、小范围的,但是其所遵循的规范可以为日后的交往行为提供借鉴。规范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商谈论证中得出的结果,每个参与论证的个体受到规范的约束。商谈就是为了达成共识,是一种可论证的共识,也是一种程序性共识。商谈共识的达成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认知的真实性。主体认知必须符合对象的发展规律,是对对象的真实反映。认知由于主体在思维方式、学习经历、价值倾向等方面的差别产生分歧,商谈正可以将人们的差异性认知聚集起来,形成对对象的完整认识。只要保证认知的真实性,将理解还原为对象本身,最终还是会形成关于对象的一致性意见。
第二,主体的真诚性。交往是以相互理解为目标的,所以主体在商谈过程中必须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图,是主体需求的直接反映。主体间的隔膜有时正是由于主体倾向的自我隐藏,主体只有打破虚伪的“假面”才能获得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主体对公共性价值的强烈需求是共识达成的动力。
第三,规范的正当性。共识的达成必须要以有效的规范作为前提,规范不是由某种传统权威或强制性命令决定的,而是在人们商谈的过程中产生的。规范的正当性取决于商谈是否符合程序,正当的规范才能被交往主体广泛接受并遵守。
第四,语言的可理解性。语言既是商谈的手段,也可能成为商谈的阻碍。语言必须建立在主体的前视域之中,并且被主体所理解才能成为商谈共识的通行证。人们首先要达成对于语言理解的公见,才能在语言交流中找到主体的共通性。
只有满足以上四种条件,才能达成行之有效的商谈共识。人们所达成的共同意见并不是每一个主体意见的简单叠加,而是经过商谈将各种意见融合形成共识。这种共识既是人们意图的呈现,也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在商谈中没有绝对中心的主体,每一个主体都有可能成为谈论的对象,每一种意见都应当被重视。
四、结 语
言语的产生就是用来交流的。哈贝马斯用一种对话式的语言代替了独白式的诉说,以语言作为手段建立起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规范,从而恢复生活世界的基础地位。但是,实际生活中语言本身却受到主体的历史、宗教、心理、习惯等多重因素影响,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所有由语言建立起的有效规范是否能符合每一种交往领域还有待考察。哈贝马斯所说的商谈共识是一个在理想的话语环境之中形成的,主体双方都是处于完全平等的状态,不受任何强制性因素干扰,每个主体都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商谈,于是主体要为自已负责。理想的话语环境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满足的,主体话语环境就是主体的实际生活,理想话语环境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人们只有满足了一定物质需求才能摆脱物的依赖关系,人们只有克服主体的异化才能走出人的依赖关系,走向人的全面发展。哈贝马斯为了批判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的交往行为,才诉诸于交往理性,但是交往只有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才具有现实意义。哈贝马斯想打造出一幢“普遍道德”的大厦,人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都可以用道德规范来化解。但是主体间冲突实际上是由主体的利益诉求引起的。
哈贝马斯的商谈共识虽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是还是可以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崛起带来建设性意义。当今时代,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紧密,而现代化进程全方位地渗透于民族文化之中,民族之间的摩擦也更为频繁,达成民族共识的意愿也更为紧迫。民族共识的形成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应当尊重每个民族坚持民族文化的权利。人们在一个包容开放的环境中交往,不同的信仰、价值观、文化传统都无法阻碍人们之间的交往。“每个人相互之间都平等尊重,这种尊重是对他者的包容,而且是对他者的他性的包容,而且在包容的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6]43哈贝马斯认为主体交往的前提是主体间的相互尊重、真诚相待,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理应受到尊重。其次,民族的多样性和开放性是民族共识不断进步的源泉。哈贝马斯认为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有其历史的渊源,不同地理环境和历史境遇积淀出不同的风土人情。文化本身并无优劣,只是在时代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略有不同。哈贝马斯提倡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文化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自我更新,要依靠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民族共识土壤的培育要从民族多样文化中吸取养分。最后,民族共识才是民族发展的主流,民族冲突所要达成的结果还是为了达成民族共识。哈贝马斯认为真正的共识不是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性胜利为条件,而是以破坏性最低的商谈的方式来形成。对于多民族的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成果要让每个民族成员受益,社会的发展需要动员各个民族成员的积极性,民族共识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事业。
[1]王希恩.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解析[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2]栗迎春,陈帆.转型与嬗变: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价值观[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
[3]杨盛龙,白正梅,孙毅.民族交往与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4]刘锷,何润.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刚要[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5]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王善英.理性化与人类生存境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8]艾四林.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辨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责任编辑:黄仲盈〕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NATIONAL CONSENS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RATIONALIZATION
Yang Pei
Ethnic consensus and ethnic conflict have always been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ethnic research,the difference of ethnicity is not the source of conflict but the basis of ethnic consensus.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the fierce collis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is the main obstacle for reaching a consensus.This article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ethnic consensus by means of using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which based on Habermas'theory of modernity.By ascribing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to the 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Habermas uses the communication rationalization to rebuild the life world which makes a firm foundation for ethnic consensus.
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ethnic consensus
C956【文献识别码】A
1004-454X(2017)03-0071-007
【作 者】杨佩,西安交通大学哲学专业博士生。西安,71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