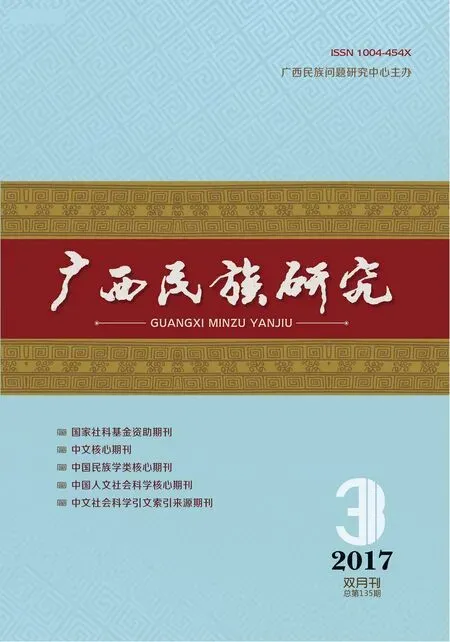试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
张淑娟
试论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
张淑娟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始于近代,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华民族的外在边界,一是其内部结构安排。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开端,单元民族构成要素成为民族精英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中援引的基本素材。同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也造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西方古典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实际的错位、单元民族意识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冲突、进化论哲学与共同体建构援引资源历史性的矛盾。民族精英结合实际努力消解这一紧张关系,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最终成为凝聚民心、共赴国难的时代旗帜。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资源;进化论哲学;理论建构;“中华民族是一个”
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对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促进作用已经达成共识。主要研究成果如下:黄克武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发展密切相关,指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信仰或意义确定的认同对象,而是经过不断辩论变化的符号,并列举了抗战时期几次主要的论争。[1]黄兴涛从民族精英自觉的过程入手,考察中华民族这一现代民族符号从萌生到确立的整个过程,并从学理上剖析了中华民族的结构。[2]沈松侨则通过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清末知识分子“英雄系谱”的建构,讨论历史书写与国族(nation)建构的内在关联。[3]高翠莲从民族实体和精英主观建构两个层面讨论中华民族的自觉进程,从纵向上阐释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进程,并在横向上展示其扩展的轨迹,说明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的曲折性、复杂性和独特性。[4]郑大华指出中华民族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接受,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的密切关系,梳理了中华民族从提出到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过程。[5]常书红通过分析革命派与维新派在对民族主义的解读上从根本对立到逐渐趋同的历史过程,认为“五族共和”是具有鲜明中华民族认同特征的新文本,并将这一方案作为满汉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表征。[6]宋志明认为民族主义是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社会思潮。[7]上述研究厘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和确立的基本过程,并从不同侧面论证了中华民族意识产生的历史根源、内在逻辑与现实需要。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关联与相关机制进行分析,同时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又是造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的关键性因素,进一步讨论民族精英消解中华民族理论建构内在紧张的种种努力。
中华民族在近代经历了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一历史过程,而中华民族自觉又包括中华民族实体自觉和民族精英主观建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诸多因素影响了这一历史进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相伴而生,呼应联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与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开端。
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基础和开端
民族主义是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灵丹妙药”被引入到中国来的。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首次提到: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之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8]20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浙江潮》 《新湖南》 《江苏》 《湖北学生界》等报纸杂志上出现了大量鼓吹民族主义的文章。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端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合流,并经历了复杂的生成过程,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不断涤荡中国传统民族观念。①佐藤慎一认为,“华夷观”是汉族将自身的生活方式体系视为文明,而将与之不同的异民族的生活方式视为非文明而产生的世界观。但是,“汉族/异民族”这一种族性的基轴与“文明/非文明”这一文明性的基轴未必经常一致。如果将重视种族性的方面称为“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将重视文明性的方面称为“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的话,根据对不同侧面的重视,华夷观对现实所起的作用不同。重视“作为实体概念的华夷观”时,如“非我族类必异”所表现的,概而言之作为排斥异民族的理论而起作用的倾向较强。相反,重视“作为机能概念的华夷观”时,“如夷狄变为中国,则以中国视之”(韩愈)所表现的,即使是异民族,只要满足一定的文化条件,就为中华世界所容纳。参见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6、157页。郑大华将上述两种“华夷观”看作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历史来源。参见郑大华:《略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随着丁韪良(William M.P.Matin)翻译《万国公法》、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及民族主义理念的传入,传统种属观念逐渐淡化和消解,以政治统一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增强。②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生成过程的具体论述参见张淑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生成与外来关键性因素》,《世界民族》,2010年第2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理论的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促使民族精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
与民族主义思想的传入相伴随,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相关的新概念涌入中国,民族、国民、民族国家、主权、领土、边界和外交等一系列的现代话语体系渐次展开,而这些新概念所包含的内在逻辑力量与统合能力逐渐影响近代民族精英思考现实问题的角度和方法,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经验被建立在新概念基础上的逻辑所取代,民族精英开始用新的视角和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境遇,提出与传统中国模式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
近代中国的历史遭遇促使民族精英将民族情感转变为强烈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理念相结合,形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而民族解放与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在政治舞台上交锋的过程中,主要政治力量也逐渐将自己视为清王朝的领土继承者与维护者,并以此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现实基础。
(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清晰的理论边界
民族主义思想刺激了民族精英的边界意识,与上述领土边界相对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清晰的理论边界。梁启超早在1903年就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9]75-76并且认识到民族主义巨大的凝聚力在于它使“种族之界始生,同族则相吸集,异族则相反拨”[10]10-11。中华民族这个更大、更具概括性的概念的提出变成了时代的需要与共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变化,在1920年11月的《修改章程之说明》中,他指出:“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洲专治。……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若单是做到推翻满族的专制,还是未曾完成。”[11]887他进一步指出:“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是完了。”[11]887经过激烈的斗争,中华民族的外在边界在20世纪20年代达成共识,理论共识为实践的努力提供了依据,民国政府对边疆问题逐渐重视起来。
(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提供基本素材
梁启超将民族主义思想引入后,“民族”迅速纳入到他的研究视野。1903年,梁启超将德国思想家伯伦知理的民族定义介绍进来:“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支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 同其生计。”[9]71-72梁启超将这八个特质作为判断一个人类群体是否成为一个民族的标准。他说:“有此八者,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隔离,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9]72
与维新派建国主张对立的革命派早期代表人物汪精卫1905年在《民报》发表了《民族的国民》,他在文章中指出民族的构成要素为:“一同血系(此最要件,然因移住婚姻,略减其例),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四同习惯,五同宗教(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减其例),六同精神体质。”[12]83而孙中山则认为民族是由自然力造成的:“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造成……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说,是自然力。分析起来,便很复杂。当中最大的力是血统。……次大的力是生活。……第三大的力是语言。……第四个力是宗教。第五个力是风俗习惯。我们研究许多不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13]187-188
梁启超和孙中山①孙中山思想与伯伦知理思想之关联,可参见夏良才:《孙中山的国家观与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版。、汪精卫②梁启超在“民族”上的观点与伯伦知理的关联可通过二人作品体现出来,汪精卫“民族观”与伯伦知理的关联可参见孙红云:《1905-1907年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关系》,《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虽然在政治主张上尖锐对立,但是所专注之重点却惊人一致,他们共同受到伯伦知理民族、国民和国家理论的影响,共同点是对“民族”所指与“nation”③作为与民族国家并生的现代符号,“nation”的政治意涵和政治建构痕迹都不言而喻,是民族精英在利用既有文化资源进行主观建构的基础上,在政权的塑造下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因此,“nation”形成过程也是权力斗争的过程,文化建设的内容依政治需要和时代诉求来确定,政治权力为“nation”的内涵建设张目,也成为民族建设(nation-building)的根本动力。“一个民族(nation)就是一个拥有国家的人民(people)” 是对经典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概括,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民族国家时代,“nation”被赋予明确边界,并被认为与国家的边界相一致。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符号与“nation”的内涵一致。都不在同一层面上,讨论的民族都是单元民族,民族构成要素都是单元民族的构成要素。诸多原因促使他们选择把伯氏的民族观点引入,但是其中必然有对中国多民族现实的清醒认知。尽管民族精英所引入的“民族”含义与“nation”并不一致,但是单元民族构成要素成为他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中援引的基本资源,并为其论证提供思想资源、想象空间与具体模式。
除上述几位近代典型人物外,近代中国民族精英(乌泽声、杨度、顾颉刚等)在论及“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的一个普遍现象,“并没有忽视和偏废通常被今人所提及的那些民族构成要素,如共同的地域(或称领土)、血统联系、语言沟通、风俗、生活方式、政治法律制度(包括平等的公民权),以及经济生活、共同的民族自我意识、历史记忆、文化心理素质(或国民性),等等。”[2]同时,“人们又较为普遍地更加重视其中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文化这一因素,尤其是在强调‘民族’作为一种人类共同体,不同于国家、国民和种族之独特性。”[2]可见,近代民族精英努力实现两个层次的民族内在关联上的“创造性转换”,民族主义所坚持的共同地域、共同文化传统、共同命运和共同的利益追求等因素成为近代民族精英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援引的基本资源。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导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质①关于民族主义的特质分析可参见张淑娟:《批判与反思: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再认识》,《学术界》,2016年第12期。更为突出,这就一方面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迅速发展,为其理论建构提供基础,而同时也造成了民族精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
(一)内外错位:西方古典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实际的错位
民族主义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精英在自由、平等与人权基础之上努力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国家边界的设定是构建民族认同的基础,也为以国家疆域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形成提供了可能,与此相适应,全体公民在文化上也成为一个紧密相连、团结一致的共同体。国家在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整合作用,“使民族得以被看成是统一体成为可能的关键结构性变迁,乃是现代国家的兴起。此前的政治形式既没有划定明晰的疆界,也没有促成内在的整合和同质化。”[14]350“合于理性的国家不是使用任何现成的质料,再经过人为的处置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它必须从培育和教化民族开始,才能达到建立此类国家的目的。民族,只有首先以切实手段解决了教育完人的问题,才能接下去解决完善国家的问题。”[15]7民族国家的整合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经济上不断加强内部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其次,国家观念的普及化,实现从忠于君主向忠于国家转变,并实现政治统一;再次,加强国家公共权力和法律建设,强化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控制,相应地在政治运作中普遍采取代议民主制;还有,通过公共教育、大众传媒以及国家的文化与社会政策规范通用语言,并加强文化同一性建设。上述政治实践正是西方民族主义古典理论所主张的“一个人民,一个国民,一个国家”实现的基础。
可见,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的典型模式是从国家到民族,按照国家的规模和范围形成民族(国族),并致力于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融合。而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路径与之相反,即从民族到国家,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以清王朝疆域为基础)成为民族主义这件“紧身衣”在近代中国遇到的最为紧迫的现实。近代中国民族精英在民族问题上诸多自相矛盾的提法,恰恰反映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错位。
首先,“民族”(nation)内涵的确立是民族主义社会动员的基础,也是民族建国情感认知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作为在近代被逐渐接受的现代民族符号,与“nation”的现代内涵无疑相一致,是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基础。作为民族主义动员基础和“中华民族”历史叙述理论前提的“民族”概念被民族精英引入中国时,却与“nation”在内涵上存在本质差异。在西方世界,“nation”从17世纪[16]4就获得并确定了现代内涵,在18世纪中叶以后被系统阐述,②卢梭和赫尔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系统阐述。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中国民族精英引入时却另有所指,就是其中的错位之一。
其次,梁启超讲到“小民族主义”时,接着提出“大民族主义”,而孙中山将“消极民族主义”发展成“积极民族主义”,从“小中华民族”到“大中华民族”,从“小民族国家”到“大民族国家”,既反映出民族精英尝试实现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统一,试图弥合单元民族与中华民族二者的内在差异,同时也表明了在理论建构中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根源恰恰是经典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实际,反映了近代民族精英的艰难选择与理论困境。
再次,经典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国家实际的错位还表现在试图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模式对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进行理论建构。孙中山甚至认为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民族成份更纯粹,更具备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的条件,可以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目标,“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余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17]621急于按照西方国家模式建国的民族精英们却出现了将民族与种族、种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相混淆的种种乱象。如孙中山在演讲中就曾指出:“第一之主义(即民族主义),为种族革命。谓排出他种民族,发扬自己民族,组织一完全独立之民族国家也。”[11]907这种混乱给中华民族理论建构造成诸多困扰。
(二)大小冲突:单元民族意识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冲突
如果说上述问题是外来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矛盾,那么单元民族意识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冲突则是面对中国实际理论进一步本土化的困境。随着民族主义的传入,晚清、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以及俄国、英国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挑唆,少数民族上层民族意识逐渐发展起来,一小撮上层分子企图通过各种途径达到民族分裂的目的,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都出现所谓“民族独立”的倾向。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这一提法成为地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方便法门”。早在1919年知识界就对“民族自决”这一提法所造成的可能的危险后果提出警告:“此次欧洲大战告终已还,‘民族自决’、‘民族自决’之声,遍闻于世界。其久困于他国专制压迫之下者,则欲乘此恢复其独立自由,其屡受他国之欺辱而濒于危亡者,则欲藉此以抗强御而图自存,其狡焉思逞日以侵略为务者,亦且外假民族自决抚慰扶弱之名,而内以济其剽窃并吞之欲。”[18]但是也有人发出相反的声音:“蒙古以历史,宗教,性质,习惯,语言文字无一与汉族两样,我们断不能说她不是另一个民族……如主中国民族(即汉族之通称) 自决,就无理由说蒙古民族不能自决。”[19]“蒙古民族与汉族绝不是一个民族。”[20]这些都成为助长单元民族走向分裂的依据。很快上述担忧就成为现实,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在“民族自决”的幌子下建立伪满洲国,并策动德王妄图实现内蒙古自治。日本的侵略意图是极力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同时肯定单元民族的存在,再利用“民族自决”煽动各族独立建国,成为受日本控制的被保护国。
单元民族意识发展在当时造成的严重后果与国家统一的愿望相背离,给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造成困难,有识之士实现民族一体化的愿望被强化,“中华民族”被强有力地倡导。时至20世纪20年代,中华民族的外在边界逐渐在知识界达成共识,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成为接下来理论讨论的焦点,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时期,典型的就是以傅斯年、顾颉刚等历史学者为一方和以吴文藻、费孝通、翦伯赞等学者为另一方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
(三)古今对立:进化论哲学与援引资源的历史性的矛盾
相对落后是民族主义产生的条件,近代中国的境遇成为民族主义产生的绝佳土壤,民族主义成为凝聚民心、抵御外辱的重要力量。但是产生条件的特殊性也导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二元特质更为突出,一方面渴望摆脱贫穷,向往先进。进化论哲学被近代主要的政治力量所信奉,用先进与落后的二元思维方式判断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另一方面为了鼓舞人心,激发民族意识,维系民族共同体认同,求助于传统文化。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二元特质也造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进化论传入中国后,不仅满足了人们尽快摆脱民族危机的诉求,并逐渐改变人们传统的历史观和思维方式。进化论所衍生的历史进步观逐渐代替“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静态历史观,进化论为近代中国不断进步、向西学习、革除旧制、批判传统提供了价值论证和思想武器,并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被主要政治力量奉为圭臬。
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符号是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而建立现代国家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与此相一致,需要全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文化为其建立提供理论支撑,引进西学与批判传统就成为当时理论界最主要的两项任务。“‘五四’以前的几十年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有两论。一是进化论,一是民约论。前者以生存竞争的理论适应了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后者以天赋人权的观念适应了要求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需要。两论的传播,在观念形态上是区分先前与近代中国人的重要标志。”[21]206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并经历漫长封建统治的国家,天赋人权、民主平等等与民族国家相关的学说都来自西方,西方代表先进,而向西方学习又以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为前提。
但同时,“世上并无蛰伏不觉(dormant)的国族等着我们找出其先天与俱的客观国族特性(nationality),以便将其自酣睡中唤醒;反之,人们乃是先被灌输一套虚构的国族认同,才会相信他们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国族群体。”[22]402与现代国家相对应的中华民族理论建构却需要借助传统,而完成“虚构的国族认同”资源只有在传统中才能找到。
进化论哲学与回归传统的紧张关系不断呈现出来,并往往表现在同一人身上。如梁启超在国家观上,提出国民、民族国家、国家至上等一系列观点,与此相对应,主张国家主权、平等自由等文化,而在民族认同上强调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意义,“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子,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为民族主义之根源也。”[23]6他认为传统文化的精髓代代相传,是凝聚民心、抵御外辱的力量源泉。为了挖掘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他甚至在1902年创办了《国学报》,宣传国粹,努力提升传统文化在民族凝聚中的作用,“孔子教义,其所以育成人格者,诸百周备,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之终身而不能尽。……使中国无孔子则能否搏挽此民族以为一体,盖未可知。”[24]68“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孙中山同样将“固有道德”看成恢复民族地位的基础,“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意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13]243
事实上,面对民族危亡,民族精英很难冷静思考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成分,不能使政治目标与传统文化达成妥协,放弃后者意味着共同体失去文化支撑,失去存在合法性,抛弃前者意味着裹足不前。在求新求变的时代里,传统文化必然遭到被矮化的命运,这种时代背景给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造成一定困难。
三、民族精英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内在紧张的努力
单元民族与中华民族虽然都包含“民族”一词,但是基本内涵与形成机理却存在诸多差异。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近代民族精英实际上承担着双重建构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在澄清国情的基础上辨析两种内涵迥异的“民族”,同时建立和阐明二者在理论上的内在关联,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提供理论依据和合法基础,使单元民族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认同中华民族。因此,结合实际以单元民族构成要素为基础,弥合单元民族与“nation”之间所指涉的差异,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内在紧张就成为近代中国民族精英努力的方向。
有学者在论及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时指出:“在‘中华民族’这个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体内部,族群分化的潜力和现实状况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社会事实。”[25]而近代中国处于列强包围之中,“中华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不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处在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民族分化的潜力更大。因此,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在实体上的完整,而民族精英的理论建构则是其中基础性的一环,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和拥护则是更为复杂的历史过程。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对西方国家挑战的应战,“包含对于‘中国’所具有的民族、人种、国家与文化之认同。”[1]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独特性的肯定与自我认同。民族主义典型的做法是对本民族的历史、语言与文化进行着重研究,而这反映了其深层次的心理需要:一方面,它表意了在外来文化的重大影响下,一种“自我认同”的急迫的追求。隐含在其动机之下的是一种恐惧,害怕文化的认同在心理上受到淹没甚至被根除;另一方面,又因当初其有向外大量求借之必要而感到自惭形秽——一种认为自己人“落后”的自卑感……“民族精神”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它包含了一种欲望,希望见证自己的人民和他们的过去对人类有一定的贡献,和其他民族比起来有同样的价值——特别是和那些在物质上显然优越的民族加以相提并论。[26]23-24中华民族作为涵盖国内各民族的现代民族符号能够超越政治立场的纷争和凝聚各民族的力量,为民族精英的文化努力提供方向,因此,各民族成员共享文化传统、认同共同的民族起源和英雄系谱、维护共同的民族利益成为必然选择。
第一,对单元民族构成要素的直接借助。中国是多民族世居的国家,有稳定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的广阔大陆上,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①参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上世纪30年代,禹贡学派则努力对地理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进行分析,顾颉刚指出:“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顾颉刚:《禹贡半月刊》 《发刊词》,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1日。)用松本真澄的话讲:“顾颉刚锁定的目标就是要考证中华民国的‘应有的’领土是怎样进化到现在这样情形的,居住在‘应该有’的领土内的居民是怎样进化到‘国族’的?”(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历史上各民族通过各种形式交往、交流和交融,形成比较稳定的分布格局。“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灭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7]1这些民族在几千年里曾有过统一的政治认同符号、统一的文化认同符号和保障民族统一、国家统一的政治制度,这正是中华民族没有走向自觉时的“自在民族实体”状态。
广阔的地域和各民族世代生息繁衍、交流融合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地理空间和历史想象。血缘、地域、风俗等因素是中国各单元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忽视这些因素,就等于忽视民族发展的历史,就如盖尔纳所言:“没有历史的民族,就是没有肚脐的民族。”[28]59对于已经接受民族国家理论及相关概念的民族精英,深知这些历史资源的重要意义。单元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提供内在支撑,这也能够进一步解释梁启超、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当初的立场。
同时,民族精英无论政治立场如何,他们对中国多民族的事实都有基本认识。民族精英之所以在谈及中华民族时,都要提及民族构成要素,也恰恰反映了面对中国多民族的现实,以及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时的内在紧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后,上述情况就基本不再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实际上,在抗日战争后期,学者们通过实际调查研究,已经认识到单元民族有自身的民族认同,这一点不能被忽视,在此基础上再形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才是合理选择,但是两种认同形成的机理明显不同,两者存在着矛盾,也存在统一性。
第二,重写中国历史。“在民族的核心处,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一堆叙事;这些叙事包括起源的故事、建国先祖的神话以及(国族)英雄的系谱。在民族起源处,我们发现民族起源的故事。”[29]121历史书写要满足现实需要,②参见米歇尔·德·塞尔托著、倪复生译:《历史书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作者谈到,作为一种行为意愿,历史书写从马基雅维利时代以来便一直受到政权的左右,换句话说,政治规训历史书写。而历史是将民族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的纽带,为民族发展逻辑提供理论依据。按照民族主义的内在逻辑,重塑民族历史,阐明民族起源,表述其过去辉煌,告诉世人“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将这些作为身份的表征和历史叙事的一部分。用共同生活的地域、共同经济生活、文化和血缘等民族构成要素论证中华民族存在合理性,以增加历史的纵深感,并确定特定的文化内涵,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重塑中华民族,而这一逻辑要在中国民族史中显现出来,因此,重构中国历史,进行新的历史书写成为必然选择。从单元民族的文化性到整体性民族符号到中华民族的政治性转变也需要在历史撰写中完成,即从根基性的表述到有意识的建构。
正是为了满足上述需要,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以民族过程为线索重新搭建中国史学体系,拉开了史学革命的序幕,他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30]7梁启超、马叙伦、邓实等人甚至认为中国“无史”,需要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围绕“国家”“国民”“群”和“社会”撰写新史。[31]2从现实政治需要角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现代性元素,从内部逐渐夯实中华民族一体性和凝聚力的基础。随着形势的发展,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性为核心的历史书写形成风潮,①根据黄兴涛的梳理,20世纪30年代与中华民族相关的史学著作有:易君左的《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 (1933)、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 (1933)、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 (1935)、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1936)、黄籀青的《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 (1936)、陈健夫的《西藏问题》 (1937)、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 (1937)、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1938)、罗家伦等的《民族至上论》 (1938)、熊十力的《中国历史讲话》 (1938)、张大东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 (1941),等等。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 (香港),2002年第1期。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确立和广泛传播。
第三点,强调民族意识之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从强调民族构成的客观要素转向强调民族的主观意识,反映了民族精英思想中有关民族问题的微妙变化,即从纯粹文化实体转向政治文化共同体,这一转变既可以避免在民族构成客观要素上无休止的争论,又能实现从单元民族到“nation”的顺利过渡,实现“创造性转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铺平道路。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指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迳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32]1同时,梁启超指出了民族意识产生的机理:“举要言之,则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人(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戟、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32]2而民族意识形成的标志是:“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了。”[32]1-2
孙中山也谈到了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民族主义之范围,有以血统、宗教为归者,有以历史习尚为归者,语言文字为归者,复乎远矣。然而最文明高尚之民族主义范围,则以意志为归者也。如瑞士之民族,则合日尔曼、以大利、法兰西三国之人民而成者。此三者各有血统、历史、语言也,而以互相接壤于亚刺山麓,同习于凌山越谷、履险如夷,爱自由、尚自治,各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组合而建立瑞士之山国,由是而成为一瑞士之民族。”[33]186-187他进一步指出:“迨中国同胞发生强烈之民族意识,并民族能力之自信,则中国之前途,可永久适存于世界。”[34]89
齐思和则以唤起民族意识为己任,认为“民族”的形成和民族情绪的高涨,外国侵略势力的压力是不可或缺要素。他引用了泰戈尔在《西方的民族主义》中的论述:“西方的雷声隆隆的大炮在日本的门前说道:我要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于是乎出现了。”因此,在他看来,“形成民族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命运共同体一员的情绪”。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这种情绪的形成,内部的原因是由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忧患经验和共同的光荣和耻辱的追忆,外部的原因是由于外侮的压迫激起了内部团结的情绪,民族意识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民族意识才能得以高涨。[35]134
另外,民族精英又处于时代的前沿。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代表的民族精英是最早萌生民族意识的群体,因此,随着形势发展,他们无一例外地强调民族意识的重要性。
第四点,为了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内在紧张,避免“给野心者一个侵略机会”,随着全面抗战的到来,部分民族精英甚至直接否定单元民族存在的事实,对中华民族进行“同源同种”论证,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是一个”。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知识界认识到对中华民族统一性论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傅斯年认为:“蒙、藏、缠回,只可算是中华民族的支派”“汉族一名……不如用汉人一名词”“若必问其族,则只有一个中华民族。”[36]204-205顾颉刚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傅斯年字孟真——引者注)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告国人。此为久蓄于我心之问题,故写起来并不难也。”[37]197因此,顾颉刚鲜明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认为在血统上和文化上经过长期融合,“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能再析出什么民族”,没有汉族,也没有“五大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中国人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应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称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38]
文章一出即引起很大反响,《中央日报》 《东南日报》 《西京平报》等报纸纷纷转载,而《益世报》边疆周刊收到大量讨论性的文章和书信,①如张维华的《读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后》、费孝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白寿彝的《来函》、马毅的《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鲁格夫尔的来函、顾颉刚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翦伯赞的《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黄举安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席世锽的《中华民族起源问题质疑》、何轩举的《中华民族发展的规律性》等。引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结构问题的大讨论,主要围绕国内少数民族地位问题展开。无论学者们在此立场如何对立,但是此文(《中华民族是一个》)“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惟一之立场”[39]126。他们直接否认构成中华民族之族类的“民族”身份,“在逻辑上说,整体和部分不能同时用一个名词。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名词,其中若干部分人民即不得统率亦称为民族。”“满洲、蒙古、西藏只是籍贯,所以住在那些地方的人民只应称‘人’,不应称为民族。民族这名词的应用既专限于中华民族,那么所谓民族自决是中华民族的自决。”[40]避免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民族”分裂中国,对加强民族团结、防止利用民族问题分裂国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黄举安也于1941年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提到,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虽然有过各种民族名词的记载,但是否都能当得起民族的称号,实在大有讨论的余地。“现在一般人称的汉、满、蒙、回、藏、苗、夷等名词,同样没有存在的价值。”他根据历史记载认为,“满人早就同中华民族凝成一体,无分彼此了”,“蒙古是匈奴人的后裔”,而“匈奴出于淳维,淳维出于夏后氏”。并且进一步证明,藏族、苗族和汉族都是同源的。同时,从血统上证明中华民族是同源的。[41]为了避免授人以柄,顾颉刚认为民族是:营共同的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结而言的人们。[42]虽然这一观点显然有悖于中国多民族的事实,但是其政治上的关怀,“俾尽书生报国之志”的爱国热情却可以理解。部分民族精英用这样的极端方式论证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消解中华民族建构的内在紧张,在理论上为后来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概括奠定了基础。“中华民族”也逐渐成为凝聚民心、共赴国难的时代旗帜。
四、余 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的过程是内与外、古与今、大与小矛盾不断调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内涵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有识之士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奔走呼号,终将其塑造成为民族团结的旗帜。
回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之路,可得出以下启示:首先,外部环境造成的危机会为理论建构提供契机,博得人们的同情与理解,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构本身,这一建构过程需要经过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长期探索,才能使理论建构逐渐趋于成熟;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建构的具体方法也要不断调整,在民族国家时代,这一过程没有终点,一直在路上;最后,要通过实践夯实和丰富中华民族理论建构的具体内容,而不能停留在口号式的宣传上,才能为其提供有力的内在支撑。
参考文献:
[1]黄克武.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J].近代史研究,2016(4).
[2]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J].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1).
[3]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33).
[4]高翠莲.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5]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J].民族研究,2013(3);“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J].近代史研究,2014(4).
[6]常书红.清末满汉关系的变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诞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7]宋志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的觉醒[J].史学月刊,2006(6).
[8]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G]//饮冰室合集:文集第6卷.第一本.北京:中华书局,1989.
[9]粱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G]//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3.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G]//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0.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孙中山.修改章程之说明:民国九年十一月四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席上的演讲[G]//国父全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0.
[12]精卫.民族的国民[G]//张枬,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13]孙中山.民族主义[G]//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5]梁存秀.论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G]//哲学门:第2卷.第1册.北京:北京大学哲学系,2001.
[16]C·J·H·Hayes.Essays on nationalism,New York[M].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
[17]孙中山.民族主义[G]//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8]隐青.民族精神[N].东方杂志,1919-12-15.
[19]彭十严.从国家主义觉悟过来告朋友并致青年[J].觉悟,1926-11-27.
[20]李春蕃.为民族自决主义而战:续[J].觉悟,1924-04-18.
[21]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2]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M].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23]梁启超.新民说[G]//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2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3[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5]关凯.族群政治的东方神话——儒家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认同[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26][美]艾恺(Guy S,Alitto).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27]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28]David Mc Crone.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ism:Tomorrow’s Ancestors[M].London:Routledge,1998.
[29]Geoffrey Bennington.“Postal Politic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the Nation”in Homi K.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M].London:Routledge,1990.
[30]梁启超.新史学[G]//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北京:中华书局,1989.
[31]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G]//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历史卷):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32]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G]//饮冰室合集:专集之42.北京:中华书局,1989.
[3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4]孙中山.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G]//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国父全集:第2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73.
[35][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M].鲁忠慧,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36]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G]//王为松.傅斯年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3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1938-1942:第四卷[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
[38]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J].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9).
[39]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G]//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0]邱椿.边疆教育与民族问题[J].教育通讯,1939(24).
[41]黄举安.中华民族是整个的[J].蒙藏月报,1941(6).
[42]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J].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20).
ON THE INTERNAL TENSION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TIMES
Zhang Shujua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began in modern times mainly deals with two aspects in its content:one is the outer boundary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other is its internal structure.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was the foundation and beginning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key factors in the composition of singular nation became basic materials cited by national elites i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Simultaneously,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also caused the inherent tension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the dislocation of western classical nationalism and the reality of China composed of multi-ethnic groups,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 ethnic group and the identity of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evolutionary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ci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National elites tried to dissolve this tension,and committed to the realization of“the one Chinese nation”,“The Chinese Nation” eventually became the banner of the time that united the will of people and helped them to face the national calamity together.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ideological resources;evolutionary philosophy;theoretical construction;one Chinese nation
C95【文献识别码】A
1004-454X(2017) 03-0048-011
〔责任编辑:黄仲盈〕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近代中国的互动研究”(16BMZ003)。
【作 者】张淑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辽宁阜新,12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