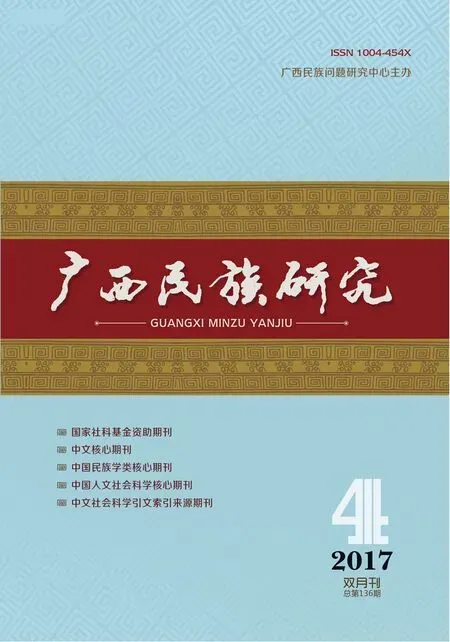民族、婚姻、伙有共耕与上帝:基督教嵌入藏区傈僳族社会之阐释*
——以滇西北德钦县霞若乡为例
叶远飘
民族、婚姻、伙有共耕与上帝:基督教嵌入藏区傈僳族社会之阐释*
——以滇西北德钦县霞若乡为例
叶远飘
基于对云南西北部一个傈僳族乡村全体傈僳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信基督教的过程进行考察,指出傈僳族信仰基督教是身处碎片化、原子化社会结构中的族群面对周边民族的歧视与物质资料和人口再生产的重重压力下作出的无奈选择,提出“婚姻—家庭—土地—民族”是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传播的网络,这一模式可以解释为什么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传播呈现出民族性特征,区别于基督教在汉族乡村社会传播呈现出的宗族性特征。
藏区;傈僳族;伙有共耕制;基督教
2016年10月,笔者赶赴云南西北部藏区进行调研。尽管去之前,笔者已经从文献中了解到云南西北藏区是基督教在我国藏区唯一传播成功的地区,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大多为傈僳族,但进入到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下的霞若乡以后,傈僳族信仰基督教的场景还是令笔者感到震撼——在该地,基督教已经被傈僳族视为本民族的民族宗教,成为区分傈僳族与其他民族的关键要素。期间,该地区的一位被公认为最熟悉《圣经》的女基督教徒骨干告诉笔者关于她本人皈依基督教的故事:她的母亲在结婚前谈过几场恋爱都无疾而终,印象最深的是和本乡的一个藏族小伙子爱得无法自拔,但是按照傈僳族的传统风俗,结婚时女方需要以银耳珊瑚及麻毯回赠男方送来的猪、牛、羊等,由于母亲家里穷,拿不出财礼,被男方家嫌弃,婚姻告吹了,母亲曾数次寻短见,这时早年过世的邻居托梦劝她的母亲信仰上帝,并向她保证,信了“主”以后命运就会好转。于是,她第二天就到了维西县的基督教堂去受洗。之后,其母亲的生活果然有了起色,后来与同样信教的本民族男子结婚,对方当时送了1000元礼金,而且不需要母亲回礼,此事让当时很多嫁女儿的家庭羡慕。在结婚当天,母亲当着牧师的面立下规矩,要求日后自己的儿女们要一辈子侍奉“上帝”。
这个故事吸引笔者注意的并非其真实性如何,而是作为当地基督教的骨干在选择性的历史记忆中突出了民族婚姻与基督教传播的纠结。显然,故事叙述了一位女性从不幸到幸福的婚姻,而由不幸走向幸福的转折点就是主人公听了那个能够代替上帝向主人公做出种种保证的“邻居”的话,那么这个“邻居”是什么来头?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我们不能把这种记忆简单地视为个体对信仰的一种文化创造,应将其置于乡村的网络社会脉络中重新理解,进而去追求这种记忆背后隐藏的历史。基于此,笔者持续在该地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田野调查,现以第一手资料对上述思考展开叙述。
一、傈僳族皈依基督教及相关成果的解释
霞若乡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东南部,东与茶马古道的中转站——奔子栏接壤,北面穿过白茫雪山则是历史上著名的汉藏贸易要地——升平镇,西南面视野开阔,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连成一片。该乡平均海拔为2362.6米,年平均温度在10.7℃,面积1359平方千米,辖霞若、石茸、夺松、月仁、施坝、各磨茸、粗卡通7个行政村,91个村民小组,214个自然村,总人口为8290人,其中傈僳族4394人,藏族3813人,分别占全乡总人口的53%和36%。①霞若乡2010年政府统计数据。两个民族的分布格局比较清晰,藏族多居于平均海拔在2100米的河谷台地,而傈僳族大多居于平均海拔2400米的高山区老林。地理的分野亦为宗教的分野——藏族信仰藏传佛教,在海拔2400米以下的房子屋顶上到处可见用砖头砌成的煨桑炉;傈僳族原本信仰本民族的原始宗教——尼扒,兼有一定的祖先崇拜,但是自1991年②德钦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证实,基督教向霞若乡传播始于1991年。但笔者调查发现,实际时间可能要早得多,1991年是传教士进来传教的年份,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人皈依基督教,在家里做礼拜。基督教由西南面的维西县传播进入到该乡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该乡傈僳族的“民族宗教”,海拔2400米以上的地方随处可见用木头制成的大小十字架挂在房屋顶上。
回顾历史,基督教在滇西北传播显然比向该乡传播的时间要早,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 的傅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神召会(The Assemblies of God)的马导民(Clifford Morrison)等传教士就将基督教传至云南滇西北傈僳族社会,并分别于20世纪3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两次达到高潮,信仰的人数剧增。[1]关于傈僳族接受基督教的原因,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认识:一是从文化、卫生的角度考察,认为早期传教士采用的“赠医施药”[2]213-214与“文字布道”[3]227两种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是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考察,将其视为傈僳族受异族与阶级双重压迫在政治层面做出的反抗;[4]三是从经济的角度考察,认为傈僳族皈依基督教受工具理性驱使。确切地说,基督教禁酒的教义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他们摆脱贫困的迫切心理,具有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的功能。[5]
上述三种观点皆成一家之言,对于解释具体的、历史的傈僳族皈依基督教有较强的合理性,但是能否解释霞若地区与藏族混居的傈僳族接受基督教则需谨慎对待。比如前两种观点主要是针对民国时期小聚居,而非大杂居的傈僳族社会(主要针对怒江流域傈僳族聚集区)所面临的环境而言的,但身在藏区霞若乡的傈僳族接受基督教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时间要比其他地区的傈僳族接受基督教晚了近1个世纪,这时候的傈僳族社会内部,无论是政治、卫生、文化方面都已经与民国时期大不相同。至于第三种观点,笔者的田野调查材料证实在一定程度上有说服力,因为对于许多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傈僳族而言,喝酒耽误生产也是他们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之一,其实对照藏族对酒的态度也可以相互印证。目前乡里的藏族喝酒闹事的案例比较突出,在笔者做完田野调查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乡里还发生了因为喝醉酒引发的严重刑事案件。事实上,乡政府大约在2010年针对藏族喝酒的情况组织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戒酒行动,当时请了活佛为藏民念戒酒经,劝藏民不要喝酒。据说仪式过后的两三天,确实没有人敢喝酒,可是时间稍微一长,藏民又忍不住喝了起来。后来民间就开始流传,说活佛并没有规定大家不能喝酒,而是说大家不能喝醉。傈僳族信仰基督戒酒成功与藏族信仰藏传佛教戒酒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酒并没有像傈僳族那样给藏族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如果从两个民族的生产环境去考察,当可发现藏族大多住在海拔较低的地方,占有相当大面积的肥沃水田和干田,水田盛产水稻,粮食充足,干田盛产的苞谷、青稞和大麦,都是酿酒的上好原料。反之,傈僳族山上的坡地只能种杂粮,杂粮大多只能用来煮粥,很少能酿出质量好的酒。因此,藏族总是在笔者的面前炫耀说,藏族家酿的酒喝不完,而傈僳族只能买酒喝。
权且认为“基督教的禁酒教义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傈僳族力图摆脱贫困的心理”,但是社会是有等级的,同属于傈僳族,内部也存在贫富差距,所以它实际上回答的是为什么那些贫困的傈僳族接受基督,而不能回答为什么全体傈僳族认可基督。换言之,它只是在部分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没有在整体层面说明“怎么样”,为学术界沿此思路进一步考察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内部的传播网络留下了空间。
二、民族婚姻:外部基督教向傈僳族社会传播的途径
诚如故事揭示的那样,该地区的基督教传播可能与婚姻存在某种密切的关联,有必要先考察该地区傈僳族的婚姻圈。傈僳族目前流行自由婚恋,但其通婚圈相对较小。以施坝村为例,该村有38户家庭,计194人,平均每户约为5人。据统计,村中约25%的人口处于前生育年龄阶段(0-15岁),其中男26人,女24人,基本持平。而处于生育年龄阶段(16-45岁)的人口占58%左右,女的60人,男的57人,女比男多3人。①数据来源: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统计整理。该村的人口统计学表明,无论是在将来还是现在,该地区傈僳族男女比例是平衡的,在适婚年龄阶段,不会出现单身家庭。然而,有必要指出,该自然村的38户家庭是由虎氏、蜂氏和鱼氏3个氏族裂变而成的,有些家庭还存在很近的血缘关系,这决定了适婚年龄的男女无法把配偶限制在单个自然村内,通婚圈自然要向村的上一级单位——“乡”扩展,这势必遇到与藏族能否结亲的问题。田野中的确发现有这样的事例,但却往往被当地群众视为“特殊”。尽管过去几十年,我国已经实行了民族平等的政策,该乡两个民族的关系也还算融洽,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身处整个大藏区的藏族在潜意识中多少还带有对傈僳族的歧视。在傈僳族的观念中,藏族往往是不讲道理的人,编号为6号、10号、12号的家庭在接受笔者访问时都一致认为藏族很野蛮,他们说:“我们信基督,是不喝酒的,但藏族无论男女,经常醉酒,最好要躲着他们,女的喝醉酒以后也会打人的,公安也管不了。” 从“公安也管不了”这一句可以看出,藏族的一些所作所为在傈僳族看来很过分,但又无可奈何。难道一个傈僳族人口比藏族人口多的乡,傈僳族还会被藏族歧视吗?一名藏族干部却这样回答笔者:“你不要以为它冠上傈僳族民族乡的称号就说傈僳族多,那只是为了得到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要知道,‘霞若’是藏语的发音,并不是傈僳族语的发音。‘霞’在藏语是‘岩石’的意思;‘若’为‘下方’的意思。”更多的藏族相信傈僳族有“很多下药害人的巫师”,以下是笔者的报道人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我13岁的那一年路过傈僳族人的家,在那里喝水。水是我从家里自带的,按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晚上回到家后我就开始发高烧、肚子痛,胀得像怀孕一样大,请喇嘛来看都说快要死了。后来我妈妈说我是中了傈僳族下的“蛊”,她去找了傈僳族的“刀巴”帮我做法,那个“刀巴”念了很多咒语,然后往我的肚子吐口水,当时感觉肚脐很辣,还听到劈里啪啦的声音,像把虫子烧死一样,肚子就好了。②访问时间:2016年11月3日,地点:霞若乡夺松村,被访问人:卓玛,女,藏族,33岁。
许多藏族对笔者表示,可以到傈僳族的家去做客,但是最好不要吃他们家的酒饭。笔者曾经在许多藏族群众家做客,入门以后,都能品尝到主人端过来的酥油茶或青稞酒;笔者也曾经到过一名被藏族视为下药害人,但现在已经信基督的傈僳族老妇女家做客,她很热情,但自始至终没有给笔者递上一杯酒,这说明她的潜意识已经习惯了这种歧视。
如此一来,要保持本民族人口的繁衍,霞若乡的傈僳族必须将通婚半径向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毗邻的乡村延伸。近10年的婚姻统计数据表明,16-45岁的傈僳族适婚男女与维西县毗邻乡村通婚的比例占60%。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是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传播的大本营,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莫尔斯就在维西县成立了“滇藏基督教会”,并将此作为长期传教的活动据点。仍然以施坝村为个案说明问题:从1991年到1999年10年间,娶进来或者入赘的婚姻共计31例,其中有18例的配偶来自维西县,占总人数的58%,而来自维西县的配偶几乎都是在结婚前就已经是基督教信徒,他(她)们的另一半则在结婚前后改信基督教。可以说,维西县的基督教向霞若传播最先依赖的是婚恋网络。诚然,婚恋固然只是基督教传播的充分条件,但年轻人如果在恋爱方面受挫折以后,离信教就不远了,这是因为基督教严禁婚前发生性行为,而傈僳族的传统婚恋文化却实行“公房制”①公房制:即在傈僳族社会,男女12岁以后被认为属于成人,可以自由谈恋爱。男方通常在自家的田地附近单独建一个简陋的房屋作为恋爱的场所,恋爱期间允许发生性关系。。众所周知,在父权制社会,性的主动权掌握在男子一方,恋爱中的男性多以能和女伴发生性行为为荣,否则他会被人认为没有本事,而女性多半是“逆来顺受”的,甜蜜的背后遗留下的是怀孕、流产、分手等无奈,而这些后果大多由女性承担,无疑增加了她们身心受伤的几率,当恋爱过的女性在接触基督教的男性时自然就有了对比,这就是为什么在婚恋阶段,该乡信仰基督教的青年女性比男性多的原因。当男性在婚恋方面面临本乡逐渐转变为基督徒的女性与维西县全部是基督徒的女性夹击时,男性自然也会开始信仰基督教,以下便是一个生动的个案:
25年前,现年48岁的阿木与一帮同龄年轻人到维西县去“钓姑娘”,期间与时年21岁的姑娘认识。但在后来的进一步交往中,早就皈依基督教的姑娘提出分手,因为她忍受不了对方身上的烟味、酒味和汗味。阿木为了挽回姑娘的心,原本信仰藏传佛教的他还是下决心戒烟戒酒,为此他还遭遇到在一起玩的藏族朋友的嘲笑。但他坚持每次在两人约会之前都使用香皂洗澡,使自己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皂味。日子久了,阿木发现,戒烟、戒酒、洗澡符合现代生活的潮流,在与姑娘结婚当天同时受洗。
三、伙有共耕制: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内部流动的网络
前面谈的是基督教是怎么来到霞若乡的,接下来我们分析基督教来到霞若乡以后又是如何进一步在傈僳族社会内部流动的。在此之前,有必要认识傈僳族传统的家庭、祖先祭祀和亲属称谓,因为这种碎片化、原子化的社会结构将决定基督教在该地特有的传播模式。
傈僳族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制小家庭,这种核心家庭一般只包括父母和未婚的子女两代。有多个儿女的,女儿长大以后要出嫁,不能继承家里的财产(入赘婚除外)。有多个儿子的,大儿子结婚以后按人口比例获得远离家里的一部分土地另起房子生活。由于该乡地广人稀,家与家之间的距离比较远,人员的流动性不强,导致近亲弟兄分家迁到别处后就很少再联系,兄弟之间共同的祭祀活动也不多见。但是,如果大哥结婚去世的时候弟弟还未成家的,弟弟有义务娶大哥的妻子入门。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是在通婚圈有限的环境下通过淡化血缘观念缓冲伦理以解决人口再生产压力的变通。在改信基督教之前,傈僳族有祖先祭祀,傈僳语称之为“尼词底”,但祭祀对象通常只限于二代以内的、自己见过的祖先,属于一种近祖崇拜,特殊情况下也包含没有成家就去世的兄弟姐妹,这是傈僳族突出核心小家庭成员的表现。故而,尽管该乡所有傈僳族的家庭是由十几个氏族裂变生成的,但氏族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笔者在田野调查期间问及氏族概念时,许多群众只表示:“好像听老人说过,甲家和乙家以前都崇拜某种动物。”在现实生活与劳动生产当中,被认为曾经崇拜共同动物的各个家庭并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走得更近。与这种家庭结构相对应的是傈僳族的亲属称谓,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在横向上对核心家庭成员实行分类式称谓,但对与核心家庭成员无血缘关系的外来加入者不区分。举例如下:家庭内的子女以Ego为中心,无论男性、女性都有排行名,如用阿普、阿得、阿娜、阿妮等,但是对哥哥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统称“玛拉”;同理,对于姐姐的丈夫和妹妹的丈夫统称为“咩武”。二是在纵向上对于与父母同一辈的亲属加予区分,而父母之上的亲属就不再区分。仍然以Ego为中心,父亲的哥哥称为“哦扒”,父亲的弟弟称为“阿坞”,母亲的姐姐称为“哦玛”,母亲的妹妹称为“玛有”,但对于父亲与母亲的父母一辈,即Ego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则统一称为“阿叭”。[6]这种对核心家庭内成员实行专有称谓,核心家庭以外的亲属实行概括性称谓的做法无疑是傈僳族父权制核心家庭、近祖崇拜的思维反映。
传统汉族乡村社会的宗族观念在这些地区并不存在,傈僳族重视核心家庭成员,但在核心家庭以外就不再依据血统的远近整合人群,那么整个村落的人群整合方式又是如何呢?——那就是通过土地耕作方面实行的“伙有共耕制”。“伙有共耕制”是傈僳族传统社会固有的一种劳作制度,也是傈僳族在淡化血缘观念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不足的环境中采取的一种土地耕种合作制度。具体形式是两个以上的家庭共耕一块土地,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甲家出力、乙家出物的形式,也有两家平均出钱出力的形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所得粮食皆平均分配。需要指出的是,“伙有共耕制”并非仅局限于两个家庭之间,如甲家和乙家实行“伙有共耕制”的同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精力再选择和丙家实行“伙有共耕”,而实行“伙有共耕”的两个家庭并非是兄弟各自组成的家庭,而是谈得来、处得好的邻居、朋友。这样,借着“伙有共耕制”,傈僳族原子化的核心小家庭组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而最初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很自然就通过这张网向伙伴传播基督教,因此这张网就是基督教在傈僳族社会内部流动的血脉。下面我们以一些个案说明:O与P是自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O娶了维西县的姑娘,同时受洗加入基督教会,P则与本村姑娘结婚,但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婚后选择在一起实行伙有共耕。O信仰基督教,星期天不劳动,但他提前告诉对方,对方认为这是信仰问题,要尊重,所以这不影响双方的合作。O一直利用机会向对方传教:“你天天劳动也不见生活就比那些不天天劳动的好,还是要做上帝的孩子,死后可以回上帝的家。”P听后看看周围和自己,比较以后也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后来又在他的鼓动下陆续参加了几次活动,信仰慢慢就发生了转变,直到受洗。M与基督徒X实行伙有共耕,对方多次给他讲加入基督教的好处,M一开始并不理会,但双方存在劳动合作,不好撕破脸皮,就一直听他讲。后来自己的父亲过世了,帮忙的人手少得可怜,但是看到对方家里无论什么事,都有许多信徒去帮忙,就感觉这个组织挺有爱心的。一次,M大病一场并得到X及其教友的帮助后果断受洗。基督教徒D与B实行伙有共耕,D虽然星期天不从事劳作,但能提前告知对方做好安排,从不失言,而B却经常酗酒,醉得不省人事,好几次都耽误了生产,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了,于是决定戒酒,跟着D出入教堂,后来受洗。A与C实行伙有共耕,后来前者信教以后多次向C传教,但C不为所动,A就认为两个人性格不合,向对方提出不再实行伙耕制,他希望能找信徒一起合作。由于信徒之间都很团结,A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伙伴,但是C再找伙伴却相对困难,过了一段时间,他也加入基督教。
总而言之,傈僳族固有的伙有共耕制是基督教在该地发展的显著特点,最初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三三两两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礼拜,然后利用“伙有共耕制”的网络渠道向劳动伙伴的核心小家庭传播,对方家庭接受了基督信仰以后又将基督教传向与自家实行伙有共耕制的新的核心家庭,使该社会的劳作制度逐渐呈现出基督徒伙有共耕制,其特点是不吸烟不喝酒,安息日不劳动,星期三、星期六晚上做礼拜,不与非信徒通婚。宗教信仰已经成为社会分化的重要指标,信徒的人际关系之拓展和维持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形成人际依恋,使信徒倾向于与其所处社会网络的宗教属性保持一致。[7]
四、结 论
中国的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历来非常发达,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杨庆堃曾用“分散性宗教”[8]271-272作为指称,并认为它与基督教依赖的社会基础有着本质的区别。近代西方社会中人与人的结合方式是“团体格局”,就像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9]25在这样的社会中,它非常有必要创造出一个全能的上帝统领社会。然而,“分散性宗教”所依赖的社会基础是由传统的人伦道德维护的“差序格局”[9]27。由于“伦理本位”的社会能让人在现世人伦关系当中获得人生的意义满足,道德代替了宗教。[10]88因此,我们在分析新时期基督教在乡村社会传播的时候一方面固然要注意它所运用的手段,但乡村社会自身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使其得以在内部流动不容忽视。
追根溯源,傈僳族是来自西北古羌族系沿三江并流南下与当地土著融合而形成的,公元8世纪中叶,傈僳族受唐朝、南诏和吐蕃三大势力的统治,至元、明时期,又分别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金沙江东岸彝族奴隶主的统治。在异族的长期统治和剥削下,不堪兵丁苦役重负的傈僳族进行过多次斗争,但皆以失败告终,为了生存,只能不断往深山老林迁徙。毫不夸张地说,傈僳族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受异族歧视不断迁徙的历史。事实上,长期的迁徙早已使傈僳族的社会结构碎片化,如其对核心家庭内成员实行专有称谓,对核心家庭以外的亲属实行概括性称谓正是其社会固守原子化的核心家庭为本,而其他亲属关系松弛易变的表现。但无论如何,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面临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困境时是非常渴望集体关怀的,如此一来,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实行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傈僳族要同时保留“妻兄弟婚”——这是为了防止缺乏集体主义关照下的单亲家庭陷入生活的绝境。但是,迫于物质与人口再生产的压力需要淡化血缘,需要杜绝联合家庭和扩大家庭的出现,需要杜绝因共同祖先祭祀而发展起来的宗族组织。在两难的境地之中和社会自身又无法发展出共同体的情况下,伙有共耕成了他们渴望共同体唯一能够采取的有效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手段。毋庸置疑,在传统社会乃至集体主义时代,伙有共耕制带有“道德”意义上的互助。但自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道德”意义上的义务式互助已经逐渐趋于理性——这时候的伙有共耕制不再由“伦理本位”的道德主导,而是基于核心小家庭,依照“经济人”的原则重新组合。伦理本位的崩塌使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分散性宗教”走向衰落,准宗教意义上的道德被冲垮了,唯有一个全能的上帝才能将这个碎片化的社会再次凝聚起来——这既是生产生活的需要,也是傈僳族重建传统互帮互助之道德的需要。因为“西方的教堂,超越所有的村庄和所有的社会群体。在一神的支配之下,教堂的等级制度画下来就是我们社会学所说的‘society’”。[11]
本文选择的虽然只是一个地区的个案,但是该个案所折射出的共性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即基督教在霞若乡以“婚姻—家庭—土地—民族”的链锁进行传播的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傈僳族社会?事实上,在这一链锁中,“婚姻—家庭”只是基督教向霞若乡传播的外部途径,而“土地—民族”才是基督教在霞若乡内部社会流动的网络。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外因只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因此,即使“婚姻—家庭”途径或许只是特例,它不适用于解释其他地区的傈僳族社会,但是依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伙有共耕制度而形成的“土地—民族”传播网络在整体上却能够有效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全体傈僳族为什么把基督教当成了本民族的宗教。
[1]黑颖,杨梨.傈僳族基督教信仰的本土化与民族身份认同[J].世界宗教文化,2016(1).
[2]杨学政.云南境内的世界三大宗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3]颜思久.云南宗教概况[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
[4]高志英.20世纪前半期中缅傈僳族的基督教发展[J].世界宗教文化,2010(6).
[5]卢成仁.体味变化与基督教传播——怒江傈僳族的田野调查[J].二十一世纪月刊,2011(10).
[6]卢成仁,刘永青.核心家庭与人群结合——云南怒江娃底村傈僳族亲属称谓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2(3).
[7]阮荣平,郑凤田,刘力.宗教信仰选择——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J].社会,2013(4).
[8]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11]王铭铭,刘铁梁.村落研究二人谈[J].民俗研究,2003(1).
ETHNIC GROUP,MARRIAGE,CO-OWNERSHIP AND CULTIVATION BY SHARERS AND THE GOD:AN INTERPRETATION TO THE EMBEDDEDMENT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ISU SOCIETY IN XIARUO TOWNSHIP,DEQIN COUNTY,NORTHWEST YUNNAN
Ye Yuanpiao
The LiSu people in the northwest of Yunnan province chose to believe Christianity from the 1990s,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ethnic living in the atomized and fragmented social structure,facing discrimin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people and the multiple pressures of reproduction of population and material goods.Based on investigation to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of the Lisu people in a township,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mode of“marriage–family-landminority” is the network of Christianity spreading to the Lisu society,it can be used to explain why Christianity spreads in the Lisu society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which differs from the Christianity’s growth in the Han societ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lineage.
the Lisu people;co-ownership and cultivation by sharers;Christianity
C912.4【文献识别码】A
1004-454X(2017)04-0066-006
﹝责任编辑:袁丽红﹞
【作 者】叶远飘,广东医科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人类学博士。广东湛江,524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青川藏滇结合部多元丧俗信仰的宗教人类学研究”(16BZJ006)。